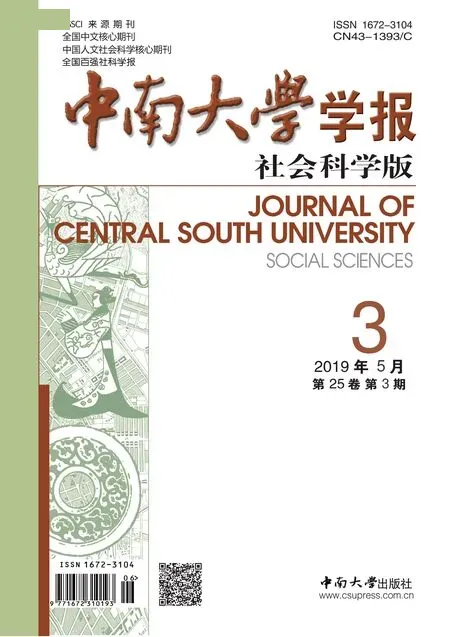宋代词科记体文论略
2019-01-04戴路
戴路
宋代词科记体文论略
戴路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宋代词科记体文是依托词科考试规范、围绕历代典章制度、承载学术文化传统的独特文体,具有文章学上的典范价值。宋代词科记体文以叙事性为根本特征,分为今题与拟题两种形式。今题记体文产生于君臣交际的语境中,其叙述策略是演绎君王意图,告诫在位臣僚,在祖宗家法中寻找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依据。拟题记体文考察士人对宋前历史典故的考证、记诵与描述能力,隐含了传承斯文的价值立场,具有深厚博雅的文体内涵与丰赡严整的形式特征。
宋代;词科;记体文;今题;拟题
宋代词科是在进士常科之外单独设立的,旨在选拔朝廷公文写作人才的考试科目。词科的开设时间跨越两宋,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到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经历了“宏词”“词学兼茂”“博学宏词”“词学”等名称的演变①。词科的考察内容包括“词”与“学”两个方面,即文辞遣造能力与典章制度的记诵功夫,所谓“试之以骈俪,律之以程度,参之以记问,合则取,否则黜”[1]。从北宋到南宋,词科的考试文体最终定型为“六题十二体”,其中“记”与“序”主要以散文写作。记体文在词科考试中出题最多,总共69题[2],现存篇目也较为丰富。宋代词科记体文的研究,立足词科考试制度与知识体系,关注“记”的形式特征与文化内涵。它有助于词科制度研究的深入,呈现“博学”与“宏词”在四六文之外的表现形式。同时,从词科文体规范的角度切入,又对“记”这一文体的综合研究有所推进。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词科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聂崇岐的《宋词科考》[3],近年来愈加引起学界的重视。在词科史研究上,祝尚书、何忠礼、张骁飞②等学者的考察为我们认识词科的名称变迁、程试格法、历年考题、中选情况等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同时,词科与文学的交互研究日渐深入,王水照、钱志熙、管琴、钱建状、曹家欣、倪春军③等学者围绕词科与文章学、骈文创作、士人风气、文学交游等进行了细致辨析。这些启示了我们推进词科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对词科文献与士人的考证,进一步还原词科制度的历史真相;二是立足词科文体规范,通过文本层次、撰者群体、典章制度的综合考察,建构出词科学术体系。在此之前,祝尚书《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 文》[4]已从词科程文体式与文章学技巧的角度有所关注。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现存宋代词科程文篇章,对照王应麟《辞学指南》的相关论述,对词科记体文的体式属性、叙述策略、文法技巧等进行深入探讨。
一、词科记体文的体式属性
“记”是唐宋以来逐渐兴盛的文体,在文体学研究中又称“杂记”,关于其源流、分类、功能、风格等,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④,但从词科角度切入的并不多见。一方面,现存词科文章不算丰富,在层次纷繁的记体文研究中未能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对专门研究宋代词科的学者而言,“制”“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四六文体往往是关注中心,而用散文书写的记体文时常被忽略。这就需要我们仔细梳理宋代词科文章,从中归纳出其独具特色的文体属性与文章风格,探讨词科记体文与一般记体文的关系,为词科制度与中国古代记体文的研究提供更多佐证。
王应麟《辞学指南》卷四《记》记载:
记者,纪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贡》《武 成》《金縢》《顾命》,记之属似之。《文选》止有奏记而无此体。《古文苑》载后汉樊毅《修西岳庙记》,其末有铭,亦碑文之类。至唐始盛,独孤及《风后 八阵图记》,今之拟题仿此。若今题,则以承诏撰述者为式。”[5](1005-1006)
王应麟强调记体文的纪事功能,叙事性是记体文的根本属性。此种观点来源于真德秀。《辞学指南》卷四引“西山先生”语曰:“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词科所试,唯南渡前《元丰尚书省飞白堂》等记及《绍兴新修太学记》犹是记体,皆可为法,后来所不逮。须多读前辈叙事之文,则下笔方有法度。”[5](1007)记体文的特色在于“善叙事”“叙事有法”,避免渗入过多的议论。后世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以叙事为记之“正体”,正是基于此种论调。如果说宋人好议论的风气使其日常创作的记体文沿着“变体”的路径充分发展,那么词科记体文则谨守叙事这一“正体”,使我们看到宋代记体文的另一种面貌。真德秀《文章正宗》有“辞命”“议论”“叙事”之分,记放在“叙事”一类,所选篇目多为韩柳等人述事绘景的记体文。这和《辞学指南》中“西山先生”对记体文叙事属性的体认正相映衬。
回到词科记体文,尽管真德秀推崇的《元丰尚书省飞白堂记》与《绍兴新修太学记》皆已亡佚,但现存宋代词科记体文考试的篇章均保持了叙事的主基调。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字词:“以文字载其本末”(晁咏之《宗子学记》[6](409));“宜有文字,纪其始末,敢摭前事而为之书”(洪适《汉五属国记》[7]);“何足形容万一,姑究其诞”(谢黼《诏赐宗室座右铭记》[8]);“不能究尽圣德,姑记梗概”(葛胜仲《重摹太宗皇帝御书飞白玉堂记》[9]);“独著其正名之旨,以告学古者”(吕祖谦《少皞氏官名记》⑤);“姑载其略,以补国史之阙”(唐士耻《仁济殿记》[10]);“兹图外之眇指,敢正列其义,以诏万世”(王应麟《周山川图记》[11](11))。其中,“载其本末”“纪其始末”“载其略”“记梗概”“形容”是叙述的形式,“正列其义”“著其正名之旨”“摭前事”“究圣德”“究其诞”是叙述的内容,“以告学古者”“以补国史之阙”“以诏万世”是叙述的功用。这些都体现出词科记体文鲜明的叙 事性。
具体而言,词科记体文又可分为拟题与今题两种形式,如前引王应麟语曰“独孤及《风后八阵图记》,今之拟题仿此。若今题,则以承诏撰述者为式”。拟题即拟古之题,所用皆是周、秦、汉、唐的旧事,文末以“谨记”结尾。今题均为本朝故事,应试者须模仿词臣应诏撰文的口吻,文末题“臣谨记”。
《辞学指南》记载了开科以来的历年试题,现存的篇目有:①拟题:李正民《汉麒麟阁名臣图记》(政和七年)、洪适《唐勤政务本楼记》(绍兴十二年)、周必大《绣衣卤簿记》(绍兴二十七年)、王应麟《周山川图记》(宝祐四年)。②今题:吴兹《籍田记》(绍圣四年)、谢黼《诏赐宗室座右铭记》(元符二年)、葛胜仲《重摹太宗皇帝御书飞白玉堂记》(元符三年)、晁咏之《宗子学记》(建中靖国元年)、王云《重修秘阁记》(崇宁元年)。
除此之外,在词科应试士人的习稿和进卷中,尚存一些记体文,其中拟题有洪适《汉五属国记》《汉武功赏官记》《汉云台功臣记》《唐筹边楼记》,唐士耻《唐贞观凌烟阁功臣记》《汉永平车服制度记》,王应麟《汉百官朝会殿记》《唐七学记》等。今题有洪适《都亭驿记》,吕祖谦《讲武殿记》《隆儒殿记》,唐士耻《绍兴新建太一宫记》等。今题主要描述皇室与朝政盛举,发挥润色鸿业的效果,而拟题重在考据源流、陈述沿革。宋室南渡以后,拟题的比重有所提升,尤其是汉唐故事,成为士人常习常考的内容。通常的记体文题材比较广泛,如收录宋人文章的《续文章正宗》共有五卷记体文,卷十二为“学记”,卷十三为“堂、斋、厅壁、园亭、轩”记,卷十四为“楼台、园、门、城池、湖、井、堤、山水、石”记,卷十五为“寺观”记,卷十六为“祠庙”记。曾枣庄《宋文通论》进一步将宋代记体文划分为建筑物记、学记、山水记、书画记四类。与普通记体文相比,词科记体文的题材范围较为集中,主要针对典章制度与历史名物,如王应麟所言,“记题最多,如宫室兴造、制度名物皆可为 题”[5](1007),围绕历代和本朝的官制、舆服、兵制、地理、城池、宫室、学校等展开。首先,这类题目侧重考察历史文献的记诵功夫,因此撰者主要是陈述史实,而非阐发义理。其次,题目涉及的建筑、图谱、学校等攸关王朝兴废与国运迁转,所记非一时一地之事,而是“补国史”“诏万世”,具有重要影响力。最后,撰者秉持词臣的立场,不能像一般记体文那样发表个体的独立见解,而是本着对皇帝负责、向天下号令的态度,保持谨严庄重的行文风格。这是词科记体文区别于一般记体文的显著特征。
二、君臣交际与历史叙事:今题记体文的书写策略
从词科记体文的命题历史看,北宋哲宗朝与徽宗朝前期的“宏词科”全为今题;徽宗朝后期“词学兼茂科”及南宋“博学宏词科”开设后,拟古的题目逐渐增多,呈现古今交错的趋势。而在晚宋理宗朝另外开设的“词学科”与“小词科”,为降低“记问”的难度,所出全为今题[12]。正如王应麟所言,今题“以承诏撰述者为式”,《辞学指南》列出了格式:
曾子开《重修御史台记》首云:“元祐三年新作御史台,有诏臣某为之记云云。”末云:“辄因承诏诵其所闻,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称列圣,褒大崇显之意焉。”东莱《隆儒殿记》首云:“仁宗皇帝皇祐纪元之三载云云。”末云:“臣既述其事,谨待制旨而勒之右。”周益公《选德殿记》首云:“皇帝践阼以来,宫室苑囿无所增修,独辟便殿于禁垣之东,名之曰选德云云。”“一日命臣:‘汝为之记。’臣愚学不足以推广圣意,词不足以铺陈盛美,谨采《诗》、《礼》云云”,次第其说。末云:“陛下神圣,必于此有得焉,而臣何足以 知之!”[5](1009)
王应麟提到的吕祖谦《隆儒殿记》,来自吕氏词科进卷,是规范的程文,所谓“本科之文”;而曾肇《重修御史台记》与周必大《选德殿记》则与词科考试无关,是奉旨撰文的词臣在实际场合的作品。词科文章以“承诏撰述者”为式,除了模仿开篇交待缘由、末尾表明用意的格式之外,更深层的是秉持一种以臣事君的叙述立场。词科考试本为选拔和储备公文写作人才,中选者的理想归宿是在翰苑充当“代言”角色,“宏词”与“博学”的用途在于“铺陈盛美”和“推广圣意”。值得注意的是,词臣的“代言”功能因为文体的差异而各有侧重。制、诰、诏等是代君王立言,不乏以上令下的叮嘱告诫。表是代大臣立言,以臣禀君时要讲明职责、坦承忠心。记体文同样处于这种君臣交际的语境,诸如“臣谨记”“谨待制旨”“臣何足以知之”等均是向君王宣誓效忠,只不过它还充当皇帝和朝臣之间的中介。一方面“推广圣意”,将圣上的微言大义推演而出、铺陈而尽,让皇帝满意;另一方面是将皇帝的美德与鸿业讲给大臣听,让朝臣受到感染、获得启发。与制、表那种君臣直接对话的语境不同,记体文的撰者更像一个客观的讲述者,将制度沿革、历史掌故、施政理念一一讲述。
关于此类记体文的生产和流通方式,周必大《选德殿记》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淳熙五年(1178)五月,周必大获旨撰记,闰六月记成进呈。据周必大记载,“此记淳煕戊戌闰六月十四日进呈于倚桂殿。至九月五日,上遣中使李裕文携至所居,宣旨令写进,欲 刻之石。盖留禁中八十日,往往粘置屏间,其迹尚 存”,“寻命修内司石工张隽刻石,十一月十日立于殿上”[13](130)。在刻石之前,文章被粘于屏间,便于君臣观览。而刊刻完成后,周必大又奉旨进殿,亲览己作,接受赏赐。据周必大《跋御书》记载:“淳熙五年十一月甲申,臣递直禁林中。漏上三刻,蒙宣召至选德殿,有中使谕旨云:‘内翰所作《殿记》,词义甚美。令刻石立殿上,特命观览。’读已,趋至后幄。上面南坐,起居毕,诣榻前再拜谢。天音奖谕如初。”[13](131)孝宗下旨让周必大观览己作,是给予词臣的莫大荣誉。而选德殿本是孝宗召集大臣商讨军国大事和古今治乱的要地,刻石的记体文能够得到广泛的观摩和阅读。孝宗所夸赞的“词义甚美”,一是切合圣意,一是文辞华赡。这可从周必大记体文与洪迈、陈傅良同题之作的对比中看出。
首先,早在乾道三年(1167),洪迈应召选德殿时就奉旨撰写殿记。在刻石隽文上,孝宗最终选择周文而非洪文,大概在于撰者对“选德”主旨的把握。如洪氏《选德殿记》所写,“成天下之事者莫大于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于至明”[14](93),洪迈从孝宗阅读《尚书》和《资治通鉴》引入,谈到天子勤与明的独特性,又从反面列举了唐玄宗“明而不勤”和唐文宗“勤而不明”的例子,以规谏宋孝宗。再看周必大之文,从《诗》《礼》中的射礼出发,自三代到秦汉以下渐次说开,紧扣“以射观德”的主题,以“合兵民于已判,同文武之异辙”[13](130)为旨归。相比之下,周必大比洪迈更能凸显“选射观德”的核心意涵,把握了宋孝宗崇尚武功而不废文治、力图中兴的心态。记体文撰成后,周必大再次向孝宗表明自己的用意,《缴选德殿记札子》曰:“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即已寓意弧矢……是以平居无事,人人阅习,月来日往,同乎自然。兵农所以不分,文武所以为一,……今主上特取选射观德之义以名便殿,储精复古,至深至远。”[13](749-750)这就将《选德殿记》的主题讲得更明确,为孝宗“文武为一”的观念找到充分的历史依据。孝宗的多次宣旨与奖谕正在于周必大深契君心。
其次,周必大撰记之前,陈傅良已代写草稿,周必大在陈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和提升。陈傅良所撰《选德殿记》今存明弘治本《止斋文集》中,题下注“代周子充内翰撰进”[15]。对比两文,我们发现周必大的文风更加整饬而富有气势,如论及秦汉以下兵民分离的史实,陈傅良曰:“盖自秦汉下迄五季,数千百载间大抵亡具。”[15]而周必大则进一步铺陈:“一夫关弓注矢,则途之人往往麕惊兔逸之不暇;烽燧才举,而卿大夫至无可使,未免拔将于行伍之中。何者?其具素亡也。”[13](129)周必大在描述干戈纷争年代时,运用了“麕惊”“兔逸”“烽燧举”等生动的物象,在“览示中外,感讽臣子”时更有鼓动性。
以上不惮繁冗介绍周必大《选德殿记》的写作和流传过程,旨在还原应诏文体的实际应用场景,突出其叙述策略,即如何揣摩和推演君王的意图,如何铺陈历史情境,打动潜在的阅读者。鉴于词科应试者的未来走向,“以承诏撰述者为式”的今题记体文同样也应坚持此种叙述策略。例如绍圣四年(1097)吴兹所撰词科程文《籍田记》即紧扣哲宗的“绍述”国策,“伏惟皇帝陛下继志述事,此骏惠我神考之烈,行闻训敇有司,刺经错事”[14](441)。宋神宗于元丰二年(1079)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籍田礼,在京城东南置田千亩,移先农坛、神仓、斋宫于其中。到绍圣四年时,哲宗有意再行籍田礼。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六记载:
权礼部侍郎范镗等言:“国朝故事,园苑观稼,系属游幸,今车驾亲临耤田,即系典礼。先农坛系元丰中移就耤田建置,臣等参详,每遇车驾临幸,合差官祭告。乞遣太常卿,于至日质明行礼,用御封香、祝文、礼料并如常仪。又耤田所稼,皆以为粢盛之实,车驾临幸,则取新荐献,当在所先。乞俟刈麦讫,以所进麦约合用数,先以黄绢袋封贮付所司,令变造礼食,于临幸次日荐之太庙。其遣官、礼料并如逐时荐新之仪,然后进供颁赐,并如故事。秋观刈禾,亦合准此。又刈麦稼穑,系同一时,今乞候观麦礼毕,车驾移幸稻池彩殿以观稼。”诏可。二十一日令定仪 注。[16]
此处详述了绍圣四年的籍田仪式,包括祭告先农坛、供奉祝文、荐献粢盛、荐享太庙、观览禾稼等,同时,朝廷也修订了礼书。吴兹《籍田记》正撰写于此种背景之下,所谓“望朱纮之光,听鸾辂之音,作为歌诗,以告成功”[14](441),起到了称颂圣德的作用。这种称颂,将绍圣和元丰连贯起来,对神宗籍田礼的场面进行了细致描述:“屹屹崇坛,先农是祠;耽耽斋宫,于焉祗祓。府史徒胥,莫不备设,统之以令,而隶于太常,农祥晨正,土长冒橛,各扬所职,无敢不敬。迨其西成,嘉谷茂实,钟而藏之,是为神廪,上帝粢盛,于是乎出。取为酒醴,百礼既洽,槁秸养牲,牲则肥硕。萧茅所供,下逮果蓏,凡岁时所以事天 地宗庙者,罔不取足。于是德馨所闻,神其有不怀者乎?”[14](441)神坛的祭祀,府司的分职,谷实的丰茂,礼仪的完备,在文中得到充分呈现,文风简洁典雅。“以告成功”既是对哲宗隆礼理念的演绎,也是通过对元丰朝盛大典礼场面的回顾,将当朝的盛治昭告 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吴兹《籍田记》“骏惠我神考之烈”后,又有“以举雍熙、明道之故”,通过神宗历史叙事的过渡,将当下的国策与祖宗家法贯通起来。此种叙事逻辑在现存北宋词科今题记体文中皆有体现。如晁咏之《宗子学记》将哲宗建学与神宗“新太学、辟三舍”的举动联系起来,突出哲宗“成神考之志”的盛德。诸如“自元丰以及于今如一日”等话语,鲜明地突出了两朝历史的连贯性。而葛胜仲《重摹太宗皇帝御书飞白玉堂记》与王云《重修秘阁记》则分别在称颂宋太宗崇儒尚文功绩的同时,将哲宗朝与徽宗朝的文治政策直接与祖宗家法联系起来。葛胜仲形容绍圣亲政的哲宗“光昭祖宗之遗宪而崇起之”[9],王云则强调太宗“自时厥后,累圣相承”,徽宗是“绍休圣绪,上监成宪”[6](479)。可见,无论是凸显“绍述”“崇宁”的基本国策,还是强调祖宗家法的传承,词科记体文都在努力建构出一套前后互不排斥的历史叙事。尽管在熙丰与绍圣之间存在元祐更化的逆转,徽宗朝的政治走向相对于祖宗之法有很大的偏离[17],但官方的话语体系却必须维持国策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看,词科设置的初衷就是要考验士人勾连本朝历史和现实政治的能力。作为词臣的储备人才,要善于研究礼仪、学校、馆阁等制度的源流演变,为当下施政找到合法性依据。而到南宋以后,随着帝王对祖宗家法的不断推崇,词科记体文的此种立场就更加明显,诸如周必大《绣衣卤簿记》“盖莫为于前,无以彰异时创业之功;莫继于后,无以见今日中兴之治”[13](939)等语与北宋诸文一脉相承。这是我们在分析词科记体文叙述策略时不可忽略的。
三、深厚简严:拟题记体文的文体内涵与形式特征
如果说今题记体文重在构建本朝故事与当下国策的纽带,那么拟题记体文则主要考察士人对宋前历史典故的考证、记诵与描述能力。从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设立“词学兼茂科”开始,记体文中的拟古题目逐渐增多,承担起词科考试“参之以记问”的功能。吴曾《试辞学兼茂科格制》谓“内二篇以历代史传故事,借拟为题”[18],王应麟谓“今之拟题仿此”,所谓“借拟为题”“拟题”,均指这种拟古之题。士人应试之前,须对历代典章制度通盘了解,经历编题、诵书、编文等环节。《辞学指南》引洪咨夔语曰:“如《汉郡国风俗本末》《唐山河两戒》等记,若非平居考订成次序,寸晷之下,虽以全史翻阅,殆未易着手。”[5](1008)记体文涉及的制度名物来源广泛,从经部的《尚书》、《周礼》到史部的正史、会要、实录等,对应试者的知识结构有较高要求。而在具体的文章写作中,历史典故的萃取、加工与组合是必备功夫。《辞学指南》卷四引真德秀语曰:
盖有出处事多,如《唐折冲府》者;出处事少,如《汉步寿宫》者。事多,贵乎善剪截,不然则繁冗矣。事少,贵乎铺张,不然则枯瘠矣。如《汉金城屯田》,出处几五七板,而欲敛为一篇;《汉步寿宫》,出处才数句,而欲演为一记。须将本科之文如此类者,细观其布置之法。事多者,笔端自为融化,不全用古人本语;事少者,自作一规模,不使局促,则得 之矣。[5](1007)
此段讲明了拟题记体文的写作要领。一是寻找出处,这离不开应试者前期的知识储备,所谓“平居考订成次序”。二是对历史材料的加工,“不全用古人本语”“自作一规模”等都要求撰者在既有典故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语词。三是根据材料来源的多少布置文章格局,多则注意剪裁,少则讲究铺张。以李正民《汉麒麟阁名臣图记》为例,此题出自《汉书·苏武传》,经过李氏改写后的段落如下:
甘露三年,帝思股肱之美,乃诏取名臣之尤者十有一人,图画于麒麟阁,法其形貌,书其官爵姓名焉。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躬秉节谊,定万世策以安宗庙,功德甚茂,其冠群后,尊而不名;曰安世,宿卫忠正、勤劳王家;曰增,宽和有守、世载令闻;曰充国,料敌制胜、奋威先零;曰相,严毅廉正、总领众职;曰吉,宽厚不伐,同心辅治;曰延年,典司朝正、练习宪章;曰德,宗室之良、持身谨厚;曰贺,儒术自进、列位九卿;曰望之,忠正不挠、经术该明;曰武,仗节忘身、不辱国命。并能毗予一人,勒功王室,内膺心膂之寄,外备爪牙之任,允文允武,曰勋曰庸,是宜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召、仲山甫焉。[19]
通过和《汉书》原文的对比,可以发现李正民在节录史料的同时,进行了几项改动和处理。一是简明交待事情缘由,时间、地点、主人公、名臣的人数等浓缩为一句,保证叙事的有效性。二是删去众多名臣的头衔。《汉书》出于纪史的庄重性,详述十一位名臣的官职爵位,但此文重在凸显“君臣相遇”的意义,出于叙述简洁的需要,省去了除霍光之外十位大臣的官爵。三是为十一位名臣分别增加赞语。诸如“料敌制胜”“总领众职”等褒扬性词汇分别来自《汉书》各位名臣的本传,此文在描述时将其整合到一起。总之,汉麒麟阁名臣图的典故较多,李正民“不全用古人本语”,而是在《汉书》的基础上进行了提炼与融合,这是拟题记体文的基本写法。
如果说李正民对《汉书》史料只是小范围的加工,那么王应麟《唐七学记》则充分体现出剪裁与融化的功力,达到真德秀所谓“敛为一篇”的效果。《唐七学记》云:“谨参合《百官》《选举志》《儒学传序》《六典》《会要》,而记其略。”[11](17-18)王应麟在考察唐代学制沿革的同时,将相关史料排列成整饬的句式:
若三品以上子孙,国子学教之;五品以上子孙,太学教之。曰广文以领国子生之业进士者,实维天宝九载七月乙亥之制。曰四门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异者,实维元魏太和二十年之制。律学昉于晋、梁,复于贞观六年之二月,又复于龙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隶祥刑,而律令格式法例于是习焉。书学昉于晋、隋,复于贞观二年之十二月,又复于龙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隶兰台,而石经、说文、字林于是习焉。算学沿隋之旧,置于贞观二年,复于显庆元年,越三年九月废之,以录太史,及龙朔二年复之,以隶秘书,而九章、五曹、缀术、缉古之属于是习焉。训导之职,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直讲,孙其业也。选举之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兴其能也。[11](18-19)
有关唐七学源流、生源、官署、教职的历史记载较为庞杂,王应麟选择排比句式铺陈史实,同时又利用伸缩之法增加长句的叙述容量。《辞学指南》卷一《作文法》曰:“西山先生问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公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子归取古人书熟读而精甄之,则蔚乎其春荣、薰乎其兰馥有日矣。’”[5](916-917)作文之法如同经商与起舞,要像商人积攒本钱那样累积知识典故,也要将读书所得像舞者那样展示给世人。在词科文章的写作中,王应麟极为享受这种知识的愉悦,力图将推广圣意的献纳润色之文改造成具有独立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的学者之文。正如《少皞氏官名记》所言的“独著其正名之旨以告学古者”[6](551),与词科今题“究尽圣德”“稽首拜手”“以告成功”的姿态有所区别。拟题记体文隐含了一种辨章学术、传承斯文的使命感。王应麟《周山川图记》宣示“正列其义,以诏万世”,不为一朝一君之政绩,而为万世不泯之文脉。这是我们在领略王应麟文章博雅学问与恢弘风格时需要挖掘的文化情怀。与此同时,在文章写作中,王应麟也十分注重对学问的“敷绎”功夫。在词科骈体中,王氏强调以简驭繁的“包尽”效果,如《辞学指南》卷二曰:“制头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如题目有检校少保,又有仪同三司,又换节,又带军职,又作帅,四句中能包括尽此数件是也。”[5](930)其方法是运用替代词和缩略语涵盖任命对象的官职头衔,利用骈体对仗“彼此相资”的互文性与平面铺排的手法增加叙述容量。和骈体类似的是,王应麟的词科记体文也需要“包尽”功夫,所谓“出处几五七板,而欲敛为一篇”,也是以简驭繁的行文方式。但记体文不能 像骈文那样使用替代语,而是更多地运用古文伸缩 之法。如上文“律学昉于……复于……又复于……越明年……于是习焉”“书学昉于……复于……又复于……越明年……于是习焉”“算学置于……复于……越三年……于是习焉”就是根据史料的变化,利用古文转折腾挪、可长可短的句式进行灵活叙述,最大限度地涵盖史实。在考究学问的同时,王应麟对文章的叙事技巧亦有深刻的体认。
王应麟论及记体文时指出:“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语赡。”[5](1006)如果说今题记体文的“语赡”侧重“铺陈盛美”,那么拟题记体文语词的丰赡则奠基于词科知识世界的博雅。只要检阅南宋词科中选者的论著,如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王珨《两汉兵制》、王应麟《汉制考》《六经天文编》等,我们不难发现词科考试实质上推动了天文、地理、经制、军事等领域研究的深入。王应麟《玉海》的编纂,更在词科学术史上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建构起精深完备的词科知识体系。四库馆臣评价唐仲友“名物制度考有据之典难”“可征其学有根柢”[20](1147),评价王应麟“贯串奥博”“尤为博 洽”[20](1151),都体现出词科学术博雅深厚的发展趋势。对于围绕历代名物制度的拟题记体文而言,所谓“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5](907),文章写作过程中的记问、钩沉、稽考正是对词科知识世界的有效呈现。已有研究者指出王应麟的词科记体文开启了清代考据派文章的先河,其特征是将考据与辞章融为一体[21]。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辞章与考据的相互融合,开出了宋代古文的单独一脉。王应麟谈论记体文的“语瞻”时,提到韩愈《南海神庙文》与苏辙《兄涣字序》的示范意义,在总结词科文章的总体写法时,又引用朱熹涵泳六经、培育根本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韩、苏视为文章家之文,将朱熹视为理学家之文,那么王应麟等人撰写的记体文恰好是自成一体的词科之文。除了对辞章技法和道德义理的吸纳,词科文章的显著特征在于其知识性。《辞学指南》在总论“作文法”之前,单列“编题”一项,尤其是记体文,如王应麟所言,“记题最多”“须详加编纂,庶无遗失”[5](1007)。编题是根据写作的需要,将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学问按照天文、地理、宫殿、田制、仪礼、官制等类别重新整理和编纂,其实质是知识的再生产。创作之前的编题和前述相关领域的研究一脉相承,共同构成词科学术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考察词科文章特性时不可忽视的知识因素。
当然,作为科考程文,应试者又非常善于把握文章写作的法度与技巧,这让拟题记体文在丰赡的知识体系之外,又具有严整的形式特征。《辞学指南》论及记体文写作时强调“作文贵乎严整”“记序以简重严整为主”“凡文体严整者皆是”[5](1007)。严整包括文章的布置、典故的融化、语词的剪裁等,这里重点谈文章的间架结构。《辞学指南》曾记载真德秀问学陈晦之事:“初见陈国正晦,呈《汉金城屯田记》,甚喜,其铺叙之有伦,数蒙称奖。”[5](917)此处《汉金城屯田记》即拟题记体文,而“铺叙之有伦”,则指文章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这种形式特征在拟题记体文写作中普遍存在。如李正民《汉麒麟阁名臣图记》,起首点明“元首股肱,相须一体”的大意,其次叙述十一位名臣的事实,接下来用“于戏”点出汉宣帝绘图的价值,最后用“窃尝观”评价汉宣帝崇德报功的意义,文章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又如王应麟《周山川图记》起首点明“周德隆泽洽,用造区夏”的大意,其次用一段小序申说大意,接下来以“谨敷绎旧闻而为记”引起正文,铺叙山川河岳的分布情况,起承转合较为分明。《辞学指南》多次谈到记体文的“法度”“布置之法”,提示学文者注意模仿和运用这些写作要领。
总之,一方面,拟题记体文在南宋的兴盛标志着词科制度的知识学转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谄谀夸饰的风气,将应试士人的关注领域引向历代典章制度。另一方面,承载这种知识体系的词科拟题,也逐步完善了自身的文体结构。记体文从北宋后期的改写史料,到南宋的“敷绎”“布置”“剪裁”“融化”,其深厚博雅的文体内涵与丰赡严整的形式特征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四、余论:作为考试规范与文章典范的记体文
一方面,作为词科考试“六题十二体”的记体文,是出题数量众多、考试地位显著的散文文体,是我们在制、表等四六文体之外,理解“博学宏词”内涵的有效窗口。鉴于朝廷对代言人才的总体定位,词科记体文不可避免地具有君臣对话的应用功能,其关注重心始终在维持国家运转的典章制度。不管制度名物的表现形式如何,其立场始终是崇儒右文;无论是祖宗之法还是汉唐故事,其视角始终是稽古追远、考镜源流。对词科士人而言,无论是当下的场屋应试还是未来的翰苑掌制,词科文章提倡的是公共表达,消泯的是个体见解,这就使“述古”成为记体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区别于宋代一般记体文的议论风气。但是,当稽古考史的风气愈发浓重之后,撰文者往往在史实中发掘真知,在制度沿革中寻找文化价值,这又会促成超越权力关系的独立见解。王应麟对词科学术与文章的探讨,即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它使词科文体的边界与内涵更加清晰。从这个角度看,词科记体文是依托考试制度、扎根历史传统、承载文化价值的独特文体。
另一方面,词科记体文相对于一般记体文又具有文章学上的典范价值。现存词科记体文,很多入选《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圣宋文海》《南宋文范》,这体现出编者对其写作示范性的体认。而《辞学指南》归纳的众多技巧要领,如就题立意、体制转换、叙事有法、剪截融化等,又对一般记体文的写作具有指导意义。《辞学指南》所载真德秀关于记体文起源和叙事性的论述,后来被明人《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转引,成为判断记体文源流演变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词科记体文广泛学习韩、柳、欧、苏等唐宋古文作家的形式特征,重视朱熹对文章的培植与涵养功夫,提倡典章制度的记问与考证,实际上开启了明清文章家融合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先声,具有文体变革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 参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宏词”、《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王应麟《辞学指南序》。
② 参见祝尚书《宋代词科制度考论》,《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第181−192页;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附录八《宋代词科一览表》,中华书局2013版,第326页;张骁飞《王应麟文集研究》第六章《<词学指南>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此外,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诸葛忆兵《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亦提供了词科制度的丰富史料。
③ 参见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第227−233页;钱志熙《试论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求是学刊》2014年第1期,第100−109页;管琴《词科与南宋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钱建状、张经洪《宋代词科与士人的文学交游》,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8−17页;曹家欣《王应麟词学指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倪春军《宋代学记文研究:文本生态与文体观照》第三章第四节《学记与词科:王应麟的词科学记与专科学记》,复旦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④ 参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十一章第二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377页;曾枣庄《宋文通论》第二十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653−778页;吴承学、刘湘兰《杂记类文体》,《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2期,第105−113页。
⑤ 此文载《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四五,题名为吕祖谦,但笔者怀疑为唐仲友之作。唐仲友绍兴三十年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时,所试记体文题目正是《少皞氏官名记》。而《悦斋文钞》卷四《官制总序》中有“为民设官,其来尚矣,立制定名,则与时沿革。伏羲始以龙瑞为龙师而龙名;炎、黄、少皥,火云、凤鸟亦皆以祥纪”等语,对上古官制渊源多有论述,俟考。
[1] 许应龙. 东涧集: 卷10[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76.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19.
[2] 张骁飞. 王应麟文集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34.
[3] 聂崇岐. 宋史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27−170.
[4] 祝尚书. 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3(5): 96−105.
[5] 王应麟. 辞学指南[M]. 历代文话第1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6]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M]. 续修四库全书1653.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洪适. 盘洲集: 卷26[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8] 江钿. 新雕圣宋文海: 卷7[M]. 宋集珍本丛刊 91.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473.
[9] 葛胜仲. 丹阳集: 卷8[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27.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85
[10] 唐士耻. 灵岩集: 卷4[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1.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46.
[11] 王应麟. 四明文献集: 卷1[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2] 戴路. 晚宋词科制度补考[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7(04): 122−133.
[13] 周必大. 文忠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47, 1148.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4] 祝穆. 古今事文类聚[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927, 929.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5] 陈傅良. 止斋文集: 卷39[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1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486[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1559.
[17] 邓小南.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440−450.
[18] 吴曾. 能改斋漫录: 卷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17.
[19] 李正民. 大隐集: 卷6[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33.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5.
[20]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 卷135[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1] 钱志熙. 试论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J]. 求是学刊, 2014, 41(1): 100−109.
A brief study on narrative prose of Ci subject in the Song Dynasty
DAI Lu
(Institute of Chinese Vernacular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The narrative prose of Ci subject in the Song Dynasty is a unique type of article with canonical value in writing art,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norm of Ci subject, center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previous dynasties and carrying the academic cultural tradition. The narrative prose of Ci subject is characterized by narration and is divided into two forms of the present topic and the simulated topic. The narrative prose with present topic arose in the context of exchanges between officials and the emperor, whose narrative strategy is to surmise the emperor's intention and to warn the officials in power, hence finding justifiable proof for the political practice from the ancestors' rules. The narrative prose with imitated topic examines to know if men of letters could investigate, memorize and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allusions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which thus contains the valu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with profound and elega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as well as rich and strict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The Song Dynasty; Ci subject; the narrative prose; the present topic; the imitated topic
2018−10−06;
2019−04−25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南宋荐举官制与四六启文研究”(17YJC751005);四川大学专职博士后研发基金项目“晚宋骈文文体研究”(skbsh201832)
戴路(1986—),男,重庆合川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章学,联系邮箱:dailu1986@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9.03.019
I207.6
A
1672-3104(2019)03−0168−08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