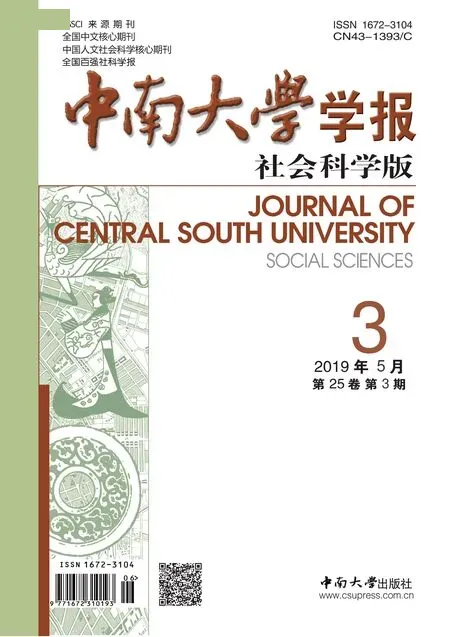语言与实践:实用主义解释学的两条进路
2019-01-04吴三喜张文琦
吴三喜,张文琦
语言与实践:实用主义解释学的两条进路
吴三喜,张文琦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里弗塞德,92507)
实用主义解释学是哲学解释学在北美传播的成果之一,它继承了实用主义和解释学传统中的反表象主义认识论要求,对肇始于笛卡尔的近现代认识论传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以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以表象认识论为线索重构了笛卡尔—洛克—康德式的认识论传统,并以语言行为主义为方法论途径,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最终要求将作为知识之可能性条件的先验法则再次置入具体的语言使用规则之中,因而呈现出典型的语言哲学色彩。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虽然同样以笛卡尔认识论为批判性起点,但通过对科学解释学效应、社会科学解释学效应以及哲学解释学效应的考察,将实践理性突显为关键要素,因而最终呈现出浓重的实践哲学色彩。实用主义解释学的这两条进路,一方面源自实用主义哲学本身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本身对语言和实践的双重强调。
语言行为主义;相对主义;客观主义;语言;实践
众所周知,解释学(hermeneutics)最早作为一种方法论起源于中世纪的解经学,近代的施莱尔马赫积极复兴了这一人文科学方法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经过狄尔泰、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哲学解释学成功地从作为单纯方法论的解释学传统中脱颖而出,成为解释学在现代最为有力的呈现样式。可以这样说,狄尔泰、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更新解释学的做法奠定了哲学解释学的基本格局和意义空间,其后围绕解释学而展开的各种争论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意义空间内发生的。在当代北美解释学的传承中,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狄尔泰主义解释学的拥护者,他们主张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限制解释学的渗透,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方法论差异。而以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为代表的激进解释学(radical hermeneutics)流派,则是海德格尔解释学的推进者,这种后现代解释学在精神资源上除了借鉴早期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思想之外,还积极吸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在这两种形态之外,作为哲学解释学在北美传播的成果之一,以罗蒂和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是第三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解释学。在精神取向上,实用主义解释学既不同于狄尔泰主义解释学,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而是更加靠近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立场。不过,罗蒂和伯恩斯坦借鉴伽达默尔思想的路径有所不同,罗蒂是从英美语言哲学的路径来接纳解释学的,而伯恩斯坦则更加注重解释学中的实践要素。由此,实用主义解释学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演进风格。
一、实用主义解释学的语言哲学进路
在实用主义哲学领域,罗蒂对解释学的推崇最为明确和激进,这与他极端的反传统认识论立场是一致的。在罗蒂看来,对于传统认识论而言,解释学是这样一种相反的希望,即“由认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被填充”[1](335)。也就是说,在罗蒂所设想的后哲学文化中,解释学不是传统认识论的替代物,不是另外一种通达客观的、绝对的真理的确定方法,而是一种力图保持自由对话空间的努力。罗蒂所持有的这种解释学观点,一方面来自他对认识论的“语言行为主义”改造,另一方面来自他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语言哲学改造。由此,以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就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语言主义特征。
与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强调不同,罗蒂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和批判传统哲学的。就整个西方哲学而言,罗蒂尤为强调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存在物的类型区分问题,也即身心问题;二是知识的合法性问题,罗蒂将之概括为知识的“基础”问题[1](18)。一般而言,认识论指的不是别的,而是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综合,即对知识之基础和合法性的探究其实就是对认知活动得以在其中顺利发生和进行的“心”的规律的探究。在罗蒂看来,这一探究的关键性成果始于近代的笛卡尔,后由洛克和康德等人加以推进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这种探究的经典范式。罗蒂认为,这种范式就是表象主义认识论。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有很多意义,美国学者威廉姆·布莱特纳曾区分出三种代表性的表象主义。第一种表象主义可称之为“间接表象主义”(indirect representationalism),以笛卡尔、洛克、贝克莱等人为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心灵唯有依靠自身的间接表象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指称或意向。布莱特纳表示,这种表象主义之所以是间接的,是因为在心灵和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起中介作用的表象,“心灵的眼睛直接对准表象,而表象又指向对象,由此就能够让心灵间接地对准对象”[2](190)。第二种表象主义可称之为“语义表象主义”(semantic representationalism),它尤其与布兰顿的塞拉斯式的推论主义(inferentialism)相对立。根据布莱特纳的表述,这种表象主义首先要确定词与物的关系,进而再围绕该关系建立意义理论。而塞拉斯和布兰顿的推论主义则正好相反,它主张我们首先拥有好的推论并将这种推论作为基础来构建指称理论和真理理论[2](191)。第三种表象主义可称之为“现象学的表象主义”(phenomenological representationalism),其代表人物是德雷福斯。现象学的表象主义认为:“信念和意愿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并有权解释人类行为。我们如果想要感知和行动,即一般地与对象产生关系,必须有某些内容在我们心里,这些内容是‘意向性的表象’(intentional representation),它们使我们能够指向对象。”[2](191)在这三种表象主义中,间接表象主义是表象主义认识论中产生时间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认识论范式,而语义表象主义和现象学表象主义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表象主义的当代模式。罗蒂激烈攻击的认识论主要指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间接表象主义。虽然布莱特纳声称间接表象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笛卡尔,但是要想从笛卡尔过渡到间接表象主义,必须要有洛克哲学的改造才行。间接表象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心灵与世界之间,表象充当了一个必要的沟通渠道,它既是世界的影像,与世界相关,又是内在于心灵之中的东西,因而心灵能够借助表象去指称世界和认识世界。如果这个链条中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间接表象主义就无法成立。在笛卡尔的第三沉思那里,与表象等同的概念是“影像”(image)和“观念”(idea)[3](25)。笛卡尔认为,我们之所以会经常将我们的观念判断为有关外物的观念,主要是因为一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原因。笛卡尔举的是关于火和热的观念,他说当我们身边有火时,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必然会感觉到火的热度,这时有关火或热的观念就是来自外物的。笛卡尔将这样的解释称为是一种“自发倾向”,并将其与出自自然之光的解释对立起来[3](26-27)。仅从自发倾向来解释观念、表象必然与世界相关的做法是可疑的,因为正如笛卡尔指出的,完全有可能在我们自身之中有一种我们不知道的功能,正是此功能产生了观念,并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观念来自外界。也就是说,在笛卡尔看来,自发倾向使我们认为的东西有可能是错误的,它不具有绝对明见性。因此,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来看,心灵之中的表象并不一定就是关于世界的表象。与此相反,洛克恰恰认为自然教导我们的东西是无法被怀疑的,“如果说有印在心灵上的真理,但心灵又不知觉之或理解之,这在我看来是矛盾的,因为‘印在’指的就是使真理被知觉;将某物印在心灵上而心灵对其又没有知觉,这是不可理解的”[4](15)。也就是说,洛克认为自然印在我们心灵之上的印象是没有办法去怀疑的东西,我们不能像笛卡尔假定的那样去设想这种印象来自内在的某些功能,我们只能接受它是外物印压的结果这一事实。由此可见,间接表象主义的关键环节,即表象是关于世界的表象,最终是在洛克的推进中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被确定下来的。
但是由洛克促成的这种间接表象主义,由于洛克哲学本身的含混性而一直处于一种认识论上的不稳定状态。一方面,表象或观念尤其是外部观念充当着心灵与世界之间的纱幕,是心灵认识世界的中介;另一方面,似乎观念本身又在取消着这种间接性,因为观念指的是外部事物对感官的印压,而正是仅凭这种印压心灵就能够直接认识世界。这种不稳定性罗蒂看得很明白,他指出在洛克那里存在着一种犹豫不决,“他需要一种认识这种表象的机能,这个机能判断这些表象而不是拥有它们……但是他却不可能找到它,因为假定有这样一种机能就会使幽灵闯入准机器之中……他充分保存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把知识当作由进入灵魂的物体一类的东西所组成”[1](159)。既然思维的对象是观念,这样就似乎在观念之外存在着一种观看观念、判断观念以便形成知识的“第二”心灵。但是,洛克又反复论述说观念直接就印在心灵之中,心灵对观念有直接的知觉,这种直接的印入和直接的知觉本身就是知识,不再需要“第二”心灵对其进行判断。从前一个维度看,洛克是间接表象主义的,从后一个维度看,他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基本上是一种直接认识论,即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对事物形式的直接拥有或把握,不需要在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起沟通作用的表象。洛克的这种间接表象主义认识论,是塞拉斯曾批判过的“所予神话”的典型。塞拉斯区分了两个空间:对于一个知觉片段而言,对其进行经验描述是发生在自然的逻辑空间之中的,而将其视为一种认识状态则是发生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的[5](679)。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混淆了这两个空间。对洛克而言,表象本来是一种完全自然主义意义上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同时又被洛克视为知识的最初形式和基本构件,心灵对表象的接纳这一过程本身被视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这一自然主义程序又被置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正如罗蒂指出的,如果把知识首要地看作是人与对象的关系而非人与命题的关系,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用生理学来解释知识论,把因果性的外界刺激当作一种直接的非推论的知识[1](157)。最早对洛克的这种间接表象主义加以修正的不是塞拉斯和罗蒂,而是康德。表象在洛克那里既是自然主义的刺激印象,又是理由空间内的知识基础,要想调和这里面的矛盾,有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将经验对象重构为认知性的,即麦克道威尔所谓的“概念事项”,由此经验对象作为认识对象就能够在理由的逻辑空间内正当地发挥作用了。在康德这里,这一重构是通过强调直观和概念的结合来完成的。在直观中呈现的感性所予如果没有概念的介入终将是一团没有秩序的感性杂多,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象或经验,这就是康德所谓的“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6](52)。然而,康德修正表象主义认识论的做法在罗蒂看来并没有彻底脱离近代认识论的樊篱。洛克的问题凸显为他无法在被动的、接受性的心灵和知识、命题的建立之间构建联系,针对此问题,康德将接受性的心灵改造成构造性的心灵。在罗蒂看来,这种构造性的心灵观念无异于是说“在心的构成性行为之前不存在有效的事物(客体)”[1](161-162)。所以,以罗蒂的立场来看,康德的策略终究没有避开表象主义的窠臼,“外部空间是由栖于内部空间的表象所构成的”[1](162)。
为了解构这种笛卡尔−洛克−康德式的表象主义认识论,罗蒂提出了他的语言行为主义思想。正是这种语言行为主义思想,构成了罗蒂引入解释学的“前理解结构”,从而也造成了罗蒂对解释学的语言主义理解和侧重。以罗蒂的立场来看,行为主义认识论立场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立场,也不是代替传统认识论的新认识论立场。正如罗蒂所说,它与华生等人的行为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行为主义认识论指的仅仅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参照社会使我们能说的东西来说明合理性与认识的权威性,而不是相反……我们最好把这种行为主义看作一种整体论,但它不需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基底”[1](190)。之所以说这种行为主义是一种语言行为主义,是因为“它声称,如果我们理解语言游戏的规则,也就理解有关在该语言游戏中为何要完成某些步骤所应理解的一切了”[1](190)。也就是说,关于“S知道P”这种标准的认识论问题,行为主义并不主张将其视为对主体与客体之间镜像关系的描述,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在S所归属的团契中被保障的可断言性[1](191)。真理不再被视为一种符合,而是被看作一种“有保障的可断言性”,这种可断言性之所以能够获得保障,主要的根据就是一种共同参与的语言游戏。在这一点上罗蒂完全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语言游戏理论。但是,这种语言行为主义是如何来转换或取消笛卡尔—洛克—康德式的认识论传统的呢?在《斯特劳森的客观性论证》中,罗蒂明确阐述了这种转换的具体方式,并将这种解释视为对斯特劳森重构康德哲学的推进和发展。康德对直观与概念之间必然关系的坚持,在斯特劳森那里被解释为对纯粹“感觉材料经验”(sense-datum experience)之不可能性的证明。不过,斯特劳森的证明仍然采用了一种先验论证的方式,有时斯特劳森也将这种方式称为是一种与“超验形而上学”相对的“科学形而上学”,它的任务在于探索“理念和原则的限制性框架,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应用对于经验知识而言是本质性的,并且隐藏在任何我们能够形成的完整的经验概念之中”[7](219)。由此可见,斯特劳森对先验论证的规定与康德的先验演绎如出一辙,它们都是对概念框架的先验探究。在罗蒂看来,对感觉材料经验之不可能性的证明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先验探究模式。他给出来的论证方案是语言行为主义,并且认为语言行为主义是康德先验演绎和斯特劳森先验论证的最终归宿。语言行为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能够使用一个概念就是能够做出一个判断,也即将一个思想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拥有的仅仅是感觉性质词汇,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句子。”[8](219)也就是说,感觉性质词汇在没有概念词汇的参与下是无法单独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的。如果我们仅仅有诸如“红的”“硬的”等感觉性质词汇而没有诸如“桌子”“事物”等概念词汇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完整的语言能力,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一种机械性的刺激反应,与经过训练的鹦鹉在看到红色面板时发出“red”声音的做法无异。而这样一来,我们甚至都不能说我们还拥有诸如“红的”“硬的”等感觉性质词汇,只能说我们拥有一种与某些视觉输入相关的反应状态。所以罗蒂说,如果我们要想知道感觉性质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先行知道什么样的事物能够是红色的[8](220)。真正的完整的语言能力是能够做出判断形成完整句子的能力,就其最基本的构成来看,也就是形成主谓判断的能力。康德对直观与概念之必然关系的强调说到底指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形成主谓句的能力。感觉性质词汇和概念词汇必须在结合中才能发挥正当的作用。所以,最终说来,康德的先验哲学以及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都可以也应该被还原为一种语言哲学。
至此,我们已经交代了罗蒂对传统认识论的语言行为主义的批判和改造。这种语言行为主义构成了罗蒂接纳解释学的主导性的“前理解结构”,正是基于此,罗蒂的新解释学思想凸现出一种典型的语言哲学色彩。在罗蒂看来,解释学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努力:它“把种种话语之间的关系看作某一可能的谈话中各线索的关系,这种谈话不以统一着诸说话者的约束性模式为前提,但在谈话中彼此达成一致的希望绝不消失,只要谈话持续下去……解释学……希望学会对话者的行话,而不是将其转译为自己的语言”[1](337−338)。用语言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认识论追求的是诸话语之间的一种“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这种可公度性乃是衡量一切相关话语的最终标准,凡与可公度性不一致的话语,要么被贬低为“非认知性的”、非理性的,要么被视为一种纯粹表现主义的、私人性的东西。然而解释学却并非如此,它不追求这种可公度性,而是将其悬置为一种希望,力图尊重和保持话语之间的对话乃至竞争状态,其目的不是追求起约束和统一作用的真理,而是努力增进人类话语模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在罗蒂看来,认识论将一切日常话语还原为粗糙的、初始的研究,而解释学则将一切研究还原为一种特殊的话语。话语模式的多样性最终服务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更新,后者采取的既不是自我意识反思的途径,也不是一种关于“经验”的形而上学思辨或现象学分析,而是一种“教化”(bildung)过程。比伽达默尔更进一步,罗蒂将教化改造为一种以语言现象为核心的自我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目的不是掌握知识,而是不断形成和更新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故事,掌握谈论事物的不同方式[1](337-338)。罗蒂更新解释学的方式说到底根源于他的新实用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采用分析哲学的语言主义策略。罗蒂曾明确表示,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分析哲学的早期形式“代表了某个极好的观念(对哲学反思来说语言比经验是一个更有成果的话题)……通过后来的语言学化,实用主义的新生如何成为可能”[9](98-99)。甚至在更为极端的表达中,罗蒂走向了一种泛语言主义,“我们能够做的所有事情仅仅是重新编织信念网络……我们不可能走出自己的头脑”[10](101)。究其根源,除了受到塞拉斯、戴维森等语言哲学家的影响外,正如大卫·希尔德布兰德指出过的那样,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语言主义维度可能是决定罗蒂更新解释学的另一重要因素,因为伽达默尔曾强调过“所有关于世界的人类经验的本质性的语言性”[11](8)。不过,与罗蒂的这种新解释学不同,新实用主义阵营中的稳健派人物伯恩斯坦采取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不以语言哲学为准则,而是力图复活由亚里士多德开辟的实践主义传统。
二、实用主义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进路
虽然与罗蒂更新解释学的策略有所不同,但是伯恩斯坦借鉴解释学资源的初衷与罗蒂是一样的,即两者都意在用解释学来克服近现代哲学中的意识哲学困境,即一般所谓的笛卡尔主义传统所面临的诸种困难。不过,两人对近现代哲学基本困境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述,在罗蒂看来这一困境明显地表现为表象主义认识论问题,而在伯恩斯坦看来,这一困境则主要是指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12](7)。
根据伯恩斯坦的看法,客观主义与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密切相关,客观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在确定合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与正确的本质时,必然存在我们可以最终求助于的某些永恒的、非历史的模式或框架。”[12](8)而与此相对,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虚无主义、反本质主义等有关,主张“当我们检验那些哲学家视之为最基本的概念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这些概念都是相对于某一具体的概念图式、理论框架、范式、生活形式、社会或文化的”[12](8)。我们可以看到,伯恩斯坦对客观主义的刻画与普特南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刻画如出一辙,它们都是对“大写的实在”“大写的真理”的追求,并将其视为人类所有生活形式的合法性根基。在伯恩斯坦看来,人类对这种终极基础的追求来源于一种“笛卡尔式的焦虑”。笛卡尔在其著作中区分了人类生存的“非此即彼”(either/or)境况:我们要么寻得最终的凭靠建立起稳固的生存,要么将自身逐入永久的动荡不安之中,在这两种境况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伯恩斯坦认为,几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所有努力都在尝试解除这一焦虑,不过这些尝试的方式基本上都是试图通过寻找某一牢固之物来缓解这一焦虑,诸如笛卡尔的我思或上帝、康德的先验统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等。它们都是在笛卡尔先行规定好的方向上来解决这一焦虑的,因而伯恩斯坦认为这些尝试最终说来没能触及问题的根基。要想真正卸除笛卡尔式的焦虑,必须先行分析和清理这一焦虑产生的前提,进而解构、置换这一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我们从它的富有诱惑性的引力中解脱出来”[12](19)。
在考察了现代哲学的最新发展之后,伯恩斯坦指出,笛卡尔式的焦虑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后期遭到了颠覆性的批判。之所以说是颠覆性的,是因为新的哲学范式从起点处就不承认这一焦虑得以成立的前提,人类境况并不必然摇摆于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两个极端。这一新范式的形成除了借鉴实用主义哲学之外,另一个尤为重要的资源就是解释学。解释学所带来的影响在伯恩斯坦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分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解释学冲动、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效应以及哲学解释学冲击。我们先来看科学哲学中的解释学冲动,它又被伯恩斯坦称为“科学解释学维度的复兴”。在伯恩斯坦看来,这一冲动主要体现在以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库恩曾明确将自己的工作与历史研究中的解释学关联起来,“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必须为自己发现的东西,大多数历史学家在专门训练课程中已通过实例而学到。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都在运用解释学(hermeneutics)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学更为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性影响”[13](4)。根据库恩的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科学研究者团体以及大众一直以来都误解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认为科学理论的变革是严格按照理性和经验原则来完成的,是一种客观知识不断累进的过程,新增的知识以已有知识体系为基础,不会取消旧有的知识储备。但是库恩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念,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不是一种渐进的、完全以理性和经验原则为标准的知识积累过程,而是一种断裂性的“范式”转换过程,库恩将此称为“非累积性事件”[14](85)。所谓“范式”(paradigm),按照库恩的说法有两个基本意思:“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承诺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13](288)也就是说,范式就是某个科学研究团体内部一致承认的某些前提、原则和规范等,它是辨认一个研究团体的最重要标志。在库恩看来,科学演进的实质就是诸多范式之间的交替过程,旧有范式最后被新范式代替不是通过逻辑或实验的方式,而是通过一场诸如政治剧变那样的革命。虽然范式转换的起因往往是旧有范式在解释某些新现象时表现出某种不适当性,但是范式转换的意义却不能完全归结为对新对象的不同诠释,因为对象在旧范式和新范式之间的呈现是不一样的,与其说范式转换的意义在于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诠释,毋宁说在于世界的改变,“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14](101)。库恩指出,范式一旦转换,科学家就是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工作了。
库恩的这种以范式转换为核心的科学哲学往往容易被解释成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主张。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把库恩的上述思想视为一种对非理性主义的拥抱,因为在他看来,库恩在阐述科学范式的转换时诉诸的不是逻辑或实验支持,而是含混的、神秘性的世界观交替,这在劳丹看来无异是一种非理性主义主张。然而,从库恩科学解释学的立场来看,劳丹之所以会持这种见解,恰恰是因为他局限于笛卡尔式的焦虑之中,认为如果我们抛开了传统的理性、客观性概念,我们就只能滑向非理性、主观性的深渊。库恩多次表示,其整个科学解释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重新探讨和界定理性、合理性等概念。他一方面指出传统合理性概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给出一种新型的合理性内涵。这种新型的合理性概念既不以传统理性、客观性概念为准绳,也拒绝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的道路,而是力图探索一条以被担保的可断言性、非客体的客观性、可错论中的进步论等为核心的中间道路。这样的道路完全不承认笛卡尔规定的“非此即彼”境况,因而也就不可能被该立场批评。
在科学哲学领域兴起的这一解释学运动,同样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就是伯恩斯坦指出的解释学效应的第二种表现。相较库恩而言,彼得·温奇(Peter Winch)著作中的解释学效应更为隐蔽,彼得·温奇更多继承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不过,在伯恩斯坦看来,彼得·温奇的社会哲学思想就其实质而言已经非常明确地站在了解释学的立场上。在关于社会学的诸多观念中,彼得·温奇主要反对的是那种以自然科学为模范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模式,这种社会学理念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知识成就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典范,社会学也应当力求效仿这一模式,否则社会学就无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在这种研究潮流的影响之下,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概念如“移情”“想象”“理解”“解释”等就成了一种非研究性概念,它们不被认可为正当的研究方法,而是被简单地视为主观性的、表现主义的修辞。反之,数据统计、实证研究、因果性说明等则成了人文科学应当遵奉的基本原则。针对这种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彼得·温奇在其著作《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重新为“理解”“解释”等正名。彼得·温奇指出,以孔德、斯宾塞及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对说明(explan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的排序是不准确的,理解并非必然以说明为前提,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任何说明都是在理解的视域内发生的,“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15](2)。在彼得·温奇看来,说明之所以是说明,原因在于理解存在某些需要被填补的不足之处,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才能意识到理解的不足,而这些标准只能是已有的理解,所以理解就构成了说明的前提。既然理解是更为基础性的现象,那么又该如何理解“理解”呢?温奇在借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基础上指出,理解总是积淀在我们已有的概念体系之中,把握这些概念体系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其视为是对某种“生活形式”的表达。理解某种生活形式的最好途径就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实践性地参与到这种生活形式之中,而不是做一种外在性的分析和研究。由此,彼得·温奇进一步指出,真正的理解是以“活动的参与者所具有的非反思性的理解为前提”[15](95)的。所谓非反思性的理解,指的就是对某种生活形式的熟悉感。彼得·温奇举例说,宗教学家要想真正理解宗教运动,其自身首先就得具有一些宗教感情,如果非得以移情、想象等能力来代替这里所说的具有某种宗教情感的话,那也不能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些概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温奇新社会学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其实是一种实践智慧,它既不承认实证主义式的客观主义知识论,也不会仅仅将对生活形式的尊重视为一种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
以伽达默尔为首的哲学解释学在伯恩斯坦看来代表着破除笛卡尔焦虑的最重要力量。笛卡尔焦虑源自一种非此即彼的境况,这种境况的认识论含义是指人类理性唯有摆脱各种成见和传统信念,遵循理想化的方法论程序,最终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成就客观的、与事物本身相符合的镜像知识。而那些成见、传统、非理想的方法等就成了理性进展道路上的阻碍,如果不能克服这些阻碍,理性必然会陷入非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泥潭之中。在伽达默尔看来,相对主义建基于客观主义,正因为笛卡尔主义先行规定了客观性的含义,所以才会将一切偏离此客观性的现象视为相对主义的。与笛卡尔主义不同,伽达默尔并不将认识的目标确定为对这种客观性的准确反映,同时也反对将理性去语境化的做法。由此,在知识论和真理观上伽达默尔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颖的观念,即理解的目标不是客观知识,而是在效果历史的作用下通过视域融合不断向更高的普遍性攀升,“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16](391)。
根据伯恩斯坦的看法,以上三种解释学效应(科学哲学中的解释学冲动、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效应以及哲学解释学冲击)见证了解释学的强大影响力和生命力。并且,它们还很好地解释了解释学的实践主义倾向,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彼得·温奇。在彼得·温奇的社会哲学诞生之前,以穆勒、涂尔干、帕累托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研究范式的极端表现就是将社会意义层面的多元实在论现象还原为一种一元实在论现象,并且认为自然科学及其解释原则为我们提供了把握这种一元实在论真理的方法论典范。穆勒的“道德科学”理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穆勒的基本观点,道德科学本身就不应该单独存在,它只是一个“科学表面的污渍”。之所以它被认为是一种污渍,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及其研究结论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未有定论的不稳定状态。所以在穆勒看来,我们需要应用一种一般化的科学方法,并仅仅关注那些能够被认为是可靠证据的东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出同样的普遍的结论。在穆勒看来,不仅道德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彼得·温奇将这点看得很明白,他指出,穆勒虽然在《逻辑体系》的第六章专门命名和研究道德科学,但是究其本质而言,道德科学的逻辑和其他任何科学的逻辑是一样的,而一般科学的逻辑作为穆勒整个工作中的主体性部分,完全建立在一种极端化的休谟主义观念之上,即凡存在可经验的或潜在的因果关系的地方,就存在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对于穆勒而言,这种因果关系不是别的,正是齐一性(uniformities)。如果不存在可经验的或潜在的齐一性,则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的必要。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及道德现象本身就是高度复杂多元的,如果仅仅用齐一性和因果性作为解释法则来对其进行研究,必然会将多元论还原为一种毫无张力的一元论。因此,彼得·温奇的社会科学解释学效应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他借助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理论,用实践哲学的路径来为人类生存中的意义多元性提供论证和支撑。彼得·温奇认为,虽然维特根斯坦也和穆勒一样强调逻辑科学的规范性特征,但是两人的结论完全不同,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规范性类似于一个语言游戏的参与者在使用词语时所遵守的那种规则性,但是这种规则并非是通过反思、一般化、普遍化等操作就可以被准确把握和认识的。也就是说,其本真的存在方式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游戏规则的这种实践性被维特根斯坦称为“他(游戏参与者)自己都不知道的规则”,这里的“知道”其实就是穆勒所追求的那种对科学逻辑的一般化把握。但是,虽然游戏参与者不“知道”这种规则,但是他却身在这种规则之中,用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他与这种规则之间的关系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经历”(leben)与“被经历”的关系,这后一种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处身性的(engaged)实践关联和默会认知。只不过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种规则是由“生活形式”这一术语来表达的,但是他同样承认,理解这种生活形式的最佳途径不是别的,正是实践性地参与到这种形式之中。
正像我们上面论述过的那样,在彼得·温奇的社会学方法论之外,实用主义解释学的实践品格还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解释学本来在狄尔泰那里的规定就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但是到了伽达默尔这里,解释学与实践哲学几乎成了同一个东西,“就人文科学的自我理解而言,这种理解要想从自然科学强加的狭隘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话,实践哲学的科学特征是唯一的方法论模式”[12](39)。伯恩斯坦说:“在伽达默尔看来,不仅解释学是实践哲学传统的合适继承者,甚至连理解活动中所包含的特有的判断、推理都是实践智慧的样式。”[12](40)库恩的科学解释学也表现出同样的实践主义倾向。范式之间的转换诉诸的不是逻辑推理、演绎证明或经验证实(伪),而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判断、选择模式,库恩力图证明这种模式在不同于传统证明方式的同时还具备严格的合理性。伯恩斯坦认为,库恩在这里寻找的新型合理性模式其实就是实践理性模式,彼得·温奇等人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比较宽泛,指的是对某种生活形式的实际投入和参与,而库恩借判断、选择、实验、讨论等指向的那种实践活动,大部分是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探究活动之中的样式,这样的活动样式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限定性和目的指向性,虽然也会出现很多重要的不带这些限定性的环节。
总而言之,伯恩斯坦对解释学效应的考察基本上与哈贝马斯对解释学的评价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将解释学同实践联系起来,极大地恢复和更新了实践哲学传统,使得真理、理性、合理性、知识等概念有望脱离科学主义的约束,真正回到与生活世界的一种实践性关联之中。
三、语言与实践的纠缠
当代解释学在实用主义语境中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以我们上面所述的两个面相来展开的。罗蒂的新解释学思想体现了新实用主义哲学的分析哲学色彩。我们知道,与新实用主义相比,古典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议题不是语言而是经验。在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卡尔纳普等人的努力,以语言分析为特征的分析哲学开始传入美国哲学界,由此实用主义在与分析哲学的交流中逐渐演变成新实用主义,因而新实用主义往往指的就是语言实用主义或后分析哲学。但是,在新实用主义阵营中并非所有人都以分析哲学为背景,伯恩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位,可以说伯恩斯坦的基本立场更接近古典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路径,因而由伯恩斯坦推进的实用主义解释学就表现出与罗蒂新解释学的巨大不同。
虽然说实用主义解释学的这两种基本形态——语言主义(或语言哲学)和实践主义(或实践哲学)——主要源于实用主义哲学本身的复杂性,但是仍需指出的是,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中实践和语言要素的并存同样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如前所述,伽达默尔明确将解释学以及理解中的判断、推理、选择等视为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和实践智慧的继承。但是,与此同时,伽达默尔又一直在凸显一种别具一格的解释学媒介——语言。伽达默尔认为:“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而不是说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并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体验……这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16](489-490)“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并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体验”是古典解释学的要求,伽达默尔当然不会认同这一点,他要求的是通过视域融合来达到更高的普遍性。但是如何来进一步确定视域及视域融合的表现形式呢?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媒介,“我们在前面已把这一点描述为视域融合。现在我们在这里认识到一种谈话的进行方式,在这种谈话中得到表述的事情并非仅仅是我的意见或我的作者的意见,而是一件共同的事情”[16](496)。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的实践性和语言性的双重强调似乎并不矛盾,按照他的理解,语言性是理解活动的首要规定性,既然理解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那么就可以说语言性和语言事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样式,所以在解释学的实践性和语言性之间不存在矛盾。但是,当实践和语言被引入不同的语境之后,尤其是对其中一方的强调走向极端时,问题可能就会显现。这在罗蒂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正因如此,罗蒂才往往会被视为“语言唯心论”的代表。由于其原有的分析哲学背景,语言一直被视为一种比实践更具原始性和优先性的现象,以至于将语言视为一切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可能性条件”。其实这一立场并不仅仅为罗蒂持有,英美哲学传统中的大批成员均持类似的见解。由此,语言与实践的优先性问题就成了一个需要被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1] 罗蒂. 哲学和自然之镜[M]. 李幼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 WILLIAM B. Is Heidegger a representationalist?[J]. Philosophical Topics, 1999, 27(2): 190−191.
[3]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 11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4] LOCKE.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in Ten Volumes: Vol. 1[M]. 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08.
[5] 塞拉斯. 逻辑与语言[M]. 李国山,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6]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London: Methuen, 1966.
[8] RORTY. Strawson’s objectivity argument[J]. Review of Metaphysics 24. 1970(10): 207−244.
[9] 罗蒂. 罗蒂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对批评家的回应[M]. 张国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0]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1] HILDEBRAND. The neopragmatist turn[J]. Southwest Philosophy Review, 2003, 19(1): 8−22.
[12]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13] 库恩. 必要的张力[M]. 范岱年, 纪树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4]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5] 彼得•温奇. 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M]. 张庆熊, 张缨, 郁喆隽,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6]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Language and praxis: On two kinds of pragmatic hermeneutics
WU Sanxi, ZHANG Wenqi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92507, America)
Pragmatic hermeneutics, one of positive results achieved by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n North America, inherits the epistem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anti-representationalism common in pragmatism and hermeneutics, and undertakes profound analysis of and critique at modern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which originated from Descartes. Pragmatic hermeneutics with Rorty as its representative, reconstructs the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of Descartes-Locke-Kant epistemology with representational epistemology, and, by taking language behaviorism as its methodology, launches a severe attack at it, and finally insists that that we should reduce the transcendental norm of condition of our knowledge into our particular usage of language, hence manifesting typical philosophical color of language. Pragmatic hermeneutics represented by Bernstein, however, though starting also with Descartes' epistemology, highlights practical rationality as its key element by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hermeneutics on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tself, hence exhibiting a strong color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se two kinds of pragmatic hermeneutics derive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pluralism of pragmatism, and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double emphasis of language and praxis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
linguistic behaviorism; relativism; objectivism; language; praxis
2018−09−12;
2019−03−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克尔凯郭尔主体性真理观研究”(15CZX031);河北师范大学校内博士基金“新实用主义出场学中的马克思问题研究”(S2017B11);河北省教育厅2018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现代反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研究”(SQ181178)
吴三喜(1988—),男,河北石家庄人,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联系邮箱:wuxizhispring@163.com;张文琦(1988—),女,河北张家口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后现代解释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9.03.004
B151
A
1672-3104(2019)03−0026−08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