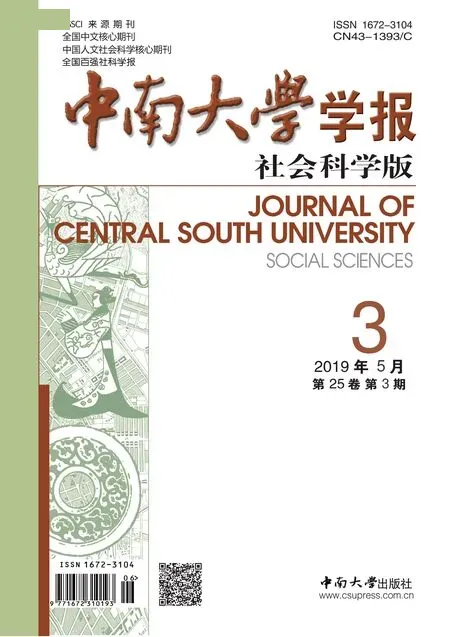宗教在公共证成中的作用:杰拉德•高斯对罗尔斯的修正
2019-01-04夏庆波
夏庆波
宗教在公共证成中的作用:杰拉德•高斯对罗尔斯的修正
夏庆波
(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02)
面对宗教的公共证成作用这一新的“神学−政治问题”,罗尔斯希望他的既有自由共识又有宗教容纳的方案能够实现现代多元社会的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然而亲近宗教的理论家们对其提出了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意见。高斯认同罗尔斯的公共证成抱负,但是不满意他的公共证成方案;同情理论家们的宗教批评,但是不支持他们的某些极端主张。他试图发展一种聚合公共证成模式来回应针对罗尔斯观念的宗教批评。不过,高氏的方案也存在诸多困难。对于这两种公共证成观念,可以秉持一种更符合现代多元主义精神的态度,即无论是罗尔斯的更加强调共识的公共证成观念,还是高斯的更加尊重多元的公共证成观念,都是证成性自由主义家族中不可缺少的合情理的成员,它们能够互补地为实现现代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多元与稳定作出贡献。
罗尔斯;高斯;宗教;公共证成
在对政治秩序的公共证成中,宗教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神学−政治问题”,即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是植根于理性,还是植根于启示?是植根于雅典,还是植根于耶路撒冷?[1]与流行于前现代社会的对政治秩序的神学证成相对照,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更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即我们能够单独基于我们的共同人类理性而不是宗教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公共证成。这样,人为自己立法的世俗化正当性路径取代了神为人立法的神学正当性路径[2]。按照这种启蒙自由主义观点,在理性祛除巫魅之后,宗教在现代世俗社会中似乎顺理成章地沦为一种像濒危动物一样需要受到保护的历史遗迹,进而被私人化,以至于最后彻底丧失对政治秩序的建构力量。例如,理查德•罗蒂认为,“政治可以与有关最重要问题的信仰相分离”,宗教“不构成民主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3]。秉持义务论传统的《正义论》也采取一种与罗蒂相类似的立场。在强调无知之幕论证力量的同时,罗尔斯通过援引阿奎那对处死异端教徒的论证指出,基于宗教信仰的论证方式是错误的,“不能得到公认的理性模式的确认”[4]。然而,人类理性日益遭遇现代性危机,传统的世俗化理论也逐步受到质疑。这样,自以赛亚·伯林以来广受关注的多元论及其与宗教复魅运动的合谋,迫使思想家们重新关注启蒙以后被认为已经由政教分离原则而获得解决的“神学−政治问题”。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神学−政治问题”之“新”在于:如何可能发展出一种面向多元论的公共证成或公共理性理论,这种理论既能摒弃启蒙自由主义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宗教私人化的阐释,又能坚守传统自由主义正当性观念的自由内核。
对于这一新的“神学−政治问题”,当代思想家们纷纷从各自的理论立场进行了思考。其中,罗尔斯的方案与美国哲学家杰拉德·高斯的方案可谓是匠心独运、构思新奇。然而,这两个方案却又风格迥异,存在一定的对峙与分歧。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探讨罗尔斯对宗教公共证成作用的论述以及罗尔斯观点所遭受的宗教批评;第二部分分析高斯聚合公共证成模式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考察高斯方案是否能够回应针对罗尔斯方案的宗教批评。
一、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及其宗教批评
《正义论》之后,由合情理多元论所引发的对稳定性问题的忧虑以及宗教复魅运动所激起的对宗教公共作用的重新思考促成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公共理性转向。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将上述“神学−政治问题”重新定义为:“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情理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与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所组成的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治久安?……那些认可某个基于如罗马教会或《圣经》等宗教权威的宗教学说的人如何可能也同时拥有一种支持公正民主政体的合情理的政治观念?”[5]在《公共理性理念新探》一文中,罗尔斯将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地表述为:“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何可能——以及有无可能——像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化的)人一样,即使其整全性学说在宪政制度之下不能繁荣发展,甚至会衰落,却仍然支持宪政制度?”[6](133)罗尔斯也将这个问题称为社会统一基础问题。在罗尔斯看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主要在于:①社会基本结构受最合情理的政治性正义观念的有效调控;② 这一政治性正义观念能得到社会中由所有合情理的整全性学说所构成的重叠共识的认可;③ 当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发生危机时,公共政治讨论应该总能(或几乎总能)基于最合情理的政治性正义观念或合情理的这一族类性的观念所规定的理由而得到合情理的决定[5](391)。
不难看出,社会统一基础问题即罗尔斯的公共证成问题。罗尔斯的公共证成理念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与三个阶段。两个部分是指对政治性正义观念的公共证成及对罗尔斯所谓的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证成。如果说前一部分是罗尔斯整个公共证成活动的基础的话,那么后一部分则是其目的。同时,这两个部分又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对政治性正义观念的特定程度证成(pro tanto justification)阶段;②对政治性正义观念的充分证成(full justification)阶段;③对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证成阶段。
首先,罗尔斯设想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证成一种族类性的政治性正义观念,以作为公平的正义范例。罗尔斯强调,在无知之幕的背后,原初状态的各方遵守其对知识与推理的限制,从一种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基本理念出发,能够为社会基本结构论证一种自立的政治观念。显然,这种特定程度的证成是一种具有高度共识特质的证成,因为原初状态的各方严格按照相同的基础(即共享的社会观念与个人观念)进行推理[5](386)。
其次,在第一阶段之后,罗尔斯相信,公民们的总体观念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政治性的正义观念;另一个部分是整全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由于在原初状态中所获得的正义观念只是特定程度的,因此,一旦公民们把自己所有的价值观都计算在内的话,正义观念就很可能会被他们的整全性学说所僭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政治性正义观念需要每个公民对其进行充分证成,即检测他们是否能以某种方式把这一正义观念作为真确的或合情理的观念嵌入他们各自的整全性学说中。如果所有公民都将一种共享的政治观念嵌入他们的整全性的宗教、哲学或道德学说中,即对这个政治观念形成了重叠共识(否则的话就只是一种临时协定),那么我们就可以希望,公民们对政治价值的排序通常会优先于与之冲突的非政治价值。这样,政治性正义观念就获得了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对这个观念的公共证成也遂告 完成[5](386−387)。
最后,罗尔斯指出,由于通过前两个阶段获得证成的政治性正义观念是持有不同整全性学说的公民之间的一种合情理的共识,当所有合情理的公民把这种共享的正义观念作为共同的政治基础应用到政治权威的普遍结构中,就能够最终实现对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证成[5](391−393)。罗尔斯用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来表述这种对政治权威的公共证成:政治权力的行使,只有这样才是完全适当的,即它所依据的宪法的根本内容,可以合乎情理地期待得到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按照他们共同的人类理性可以接受的原则和理想——的认可[5](137)。
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三个阶段的公共证成构成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与公共理性理论的核心关切。在罗尔斯看来,这种解决“神学−政治问题”的公共证成模式能够有效地回应合情理多元论及宗教复魅运动的挑战。它既能体现对传统自由主义价值中立论的继承与坚守,又可表明对启蒙自由主义宗教私人化观念的批判与反思。按照罗尔斯目的中立性观念的要求,“国家不得做任何旨在偏袒或促进任何特定整全性学说的事情,或者给予那些追求某一特定整全性学说的人以较大支持”[5](193)。因此,第一阶段对政治性正义观念的证成必须独立于整全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这是一种共识证成观念①。同时,罗尔斯也认识到,这种正义观念要想实现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就必须在第二阶段获得各种合情理的宗教、哲学及道德学说的重叠共识的支持,这是一种具有鲜明主体间特征的聚合证成观念。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共识是正(独立于宗教等学说),第二阶段的聚合是反的话(依赖于宗教等学说),那么第三阶段的共识则是合(既独立于又依赖于宗教等学说)。罗尔斯相信,通过正反两个阶段获得的政治性正义观念能够在第三阶段合成为最深刻与最合乎情理的社会统一基础[5](391)。
与《正义论》的宗教私人化立场相比,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综合了共识观念与聚合观念的公共证成模式把宗教的公共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宗教批评者看来,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仍然由于具有太强的排斥性而对宗教抱有敌意[7]。
首先,批评者认为,从罗尔斯公共证成的两个部分三个阶段来看,虽然在对作为其公共证成基础的政治性正义观念的证成中,信教公民可以在充分证成时自由地诉诸自己的宗教观点,但是在对作为其公共证成目的的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证成中,信教公民只能诉诸所有人共享的族类性的正义观念,他们自己的宗教观念必须被括置。这是因为根据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宗教理由不可能合乎情理地期待得到所有自由平等公民的认可。简言之,从总体来看,罗尔斯的公共证成是一种共识观念,这种共识观念预示了公民性责任及其所带来的类似于宗教私人化的宗教约束原则,即罗尔斯试图克服的宗教私人化依然出现在对根本政治问题的公共证成中。批评者担心公民性责任与宗教约束原则会使信教公民的人格完整性(integrity)被一分为二,即在公共证成中,信教公民应当将宗教信仰深埋心底,而只有在非公共政治空间,他们才能表达真实自我。尼古拉斯·沃特斯多夫这样批评道:“我们社会中的信教人士理应把他们涉及根本问题的决定奠基于自己的宗教信念。他们不认为存在做或不做的选择,因为这样做也是他们的宗教信念之一。他们的信念是,他们应当终其一生地寻求整体性、完整性及统一性:他们应当让上帝之道、《摩西五经》的教义、耶稣的诫命与榜样,或诸如此类,来把他们的存在——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存在——塑造为一个整体。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宗教不是关于某种把他们的社会政治存在排除在外的东西(something other than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existence);它也涉及他们的社会政治存在。”[8]
其次,尽管罗尔斯公共证成理论的起点是出于对公民们自由平等这一道德身份的尊重。但是,宗教批评者认为,尊重公民们的自由平等并不意味强制性法律的正当性要以把宗教信念排除在外的共享理由为基础。相反,这种尊重意味着,当合情理的公民们从构成了自己人格认同的整全性视角出发有充分的理由去认可某项法律的时候,该项法律就能够得到公共地证成。克里斯托弗·埃伯利与特伦斯·库内奥假设了一个场景的两种路径。这个场景是:公民们在对医疗改革问题进行慎议。一种路径是,这些公民采取罗尔斯式的方式,诉诸公共理由;另一种路径是,这些公民基于他们的整全性学说(犹太教、天主教、康德主义、佛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医疗改革问题形成聚合。埃伯利与库内奥反问道,一个自主的合情理的公民会拒绝后一种路径吗?[9]
最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作为公共证成基础的政治性正义观念是完善的(complete),能够为所有或近乎所有的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提供合乎情理的答案。然而,批评者怀疑,在价值观高度异质的现代民主社会,仅仅诉诸公共理由是否能够让整全性观点相互冲突的公民们对存在激烈争论的根本政治问题达成一致。按照批评者的观点,以政治性正义观念为基本内容的公共理性是不完善的(incomplete),它的内容根本不足以对诸如堕胎、干细胞研究、克隆人、动物权利、同性关系的道德等问题达成一个使争论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批评者最后得出结论,要解决这些存在高度争议的根本问题,公民们只有求助于宗教等非公共理由[10]。
针对宗教批评者的质疑,罗尔斯的回应是继续释放对宗教推理的善意。他相继提出了公共理性的包容性观点[5](247)、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5](xlix-l)及宽泛的公共政治文化观点[6](136−138),进一步放宽了公共空间对宗教理由发挥作用的限制。然而,批评者似乎并不满意。例如,戴维·雷迪评论道:“尽管罗尔斯的‘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允许对非公共理由的公开诉诸,但是其目的并非是为了让公民和官员们能以一种合情理的、确定的方式解决根本政治问题……它假定,在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公民和官员将会发现有可能以一种合情理的、确定的方式解决所有或近乎所有的根本政治问题,而不需要诉诸非公共理性来确定解决方案。”[11]然而,“自由公共理性的自主性与完善性达不到罗尔斯所希望的程度,这表明罗尔斯‘公共理性理想的宽泛观点’仍然不够宽泛”[11]。
二、杰拉德·高斯的聚合公共证成模式
作为罗尔斯之后最重要的公共理性哲学家[12],杰拉德·高斯服膺罗尔斯的公共证成理想,他进一步拓展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在高斯看来,证成性自由主义的核心承诺是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原则:自由应该作为准则,尊重人的自由平等要求。强制总是需要某种专门的证成,而未经证成的强制则是错误的。根据自由原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如果人们自由平等的道德身份得到尊重的话,那么,约束他们的强制性法律就必须要对他们证成。因为这种证成能够把正当的集体权威同单纯的强力区分开来。这就得出了证成性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原则——公共证成原则:仅当公众 P中的每一个成员有确定的理由 R承认需要 L的时候,L才是一项得到证成的强制性法律[13](53)。高斯与罗尔斯等证成性自由主义者都同意,为了避免埃伯利所说的证成性民粹主义[14],有必要对作为证成主体的公众 P作某种理想化(idealization)的预设,以克服由于现实公众成员的认知局限与信念缺陷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在关于如何解释理由 R这一问题上,高斯开始与罗尔斯分道扬镳。
如前文所述,尽管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在对政治性正义观念的证成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聚合因素,但是其整体倾向尤其是在对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证成中却体现出共识特征。让我们把上述的公共证成原则重新表述一下:当且仅当公众 P中的每一个成员 x都有充分的理由 Rx去认可强制性法律 L的时候,那么,L在公众 P中就得到了证成。按照共识观念,对于公众P中的不同成员 x来说,他们的理由Rx(R1,R2,R3…Rn)是相同的,即证成强制性法律 L的理由 R对所有公众成员来说必须具有可共享性(shareability)。根据罗尔斯的观点,公众成员在公共证成中运用共享理由是一种公民性责任。高斯描绘了罗尔斯式的公民性责任的共享理由观:如果阿尔夫基于理由 R(在政治论坛中)公开地倡导 L,并且,一个这个公众中的伙伴成员贝蒂,不认为 R是她的理由(她不会共享这个理由),那么,阿尔夫就违背了公民性责任[15](10)。高斯认为,由于宗教理由不可能为所有公众成员所共享,因此共享理由观就预示了罗尔斯的宗教约束原则,即“当讨论宪法根本与基本结构问题时,我们不应当诉诸整全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不应当诉诸我们认为是完整真理的东西,因为它们不能提供公共证成的基础”[5](224−225)。
高斯对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及其宗教约束原则的批评集中在下面三点:①按照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每个人都同等理性,境遇类似,并被同样的论证说服”。这种观念实际上把原本存在分歧的公众成员之间的多人选择问题简化为一个人的选择。高斯的困惑是,“为何证成性自由主义者——他们开始于对作为人类理性自由实践之结果的合情理多元论的坚定承 诺——会接受一种假设我们进行同质推理的公共证成观念?”[13](58)②根据宗教约束原则,公众成员们应该括置他们所深切关心的宗教等整全性承诺,而仅仅基于所有人都共享的然而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却可能是次要的价值去证成一些规则。高斯的疑问是,如果说一个尊重所有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必须要表明,深切关心自己的不同的价值观的人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去认可并遵守道德规则,那么,“当我完全了解我所深切关心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我将会怎么看待这些(基于共享理由的)规则?”[16]③在高斯看来,罗尔斯的公共证成模式排斥宗教推理的实质原因是这一观念对真正多元推理的敌意,因此,他的结论是有必要发展一种聚合公共证成模式。这种聚合模式能够尊重包括宗教推理在内的任何真正的多元推理[13](58−59)。
与罗尔斯相比,高斯的聚合公共证成模式有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高斯切断了公共证成与共享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换言之,高斯认为,公共地证成一项法律或规则并非一定要基于某种共享的理由。如果说罗尔斯要求对于不同的公众成员 x来说,证成强制性法律 L的理由 Rx(R 1,R2,R3…Rn)必须是相同的,即具有可共享性的话,那么高斯则仅仅要求对于不同的公众成员 x来说,证成强制性法律 L的理由 Rx(R1,R2,R3…Rn)可以是不同的——Rx只需具有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即可②。高斯指出,把证成性理由植根于共享标准会潜在地伤害自由主义的公共证成规划,因为这样做会阻止公民们在公共证成中诉诸自己的合情理的具有可理解性的理由。高斯相信,如果每一个公众成员通过不同的但却是可理解的理由对强制性法律 L形成聚合,那么基于法律 L所实施的强制就能够通过公共证成测试。“阿尔夫能够基于宗教考量对同一教派的查理证成 L;贝蒂通过诉诸密尔的理论对多丽丝证成 L;尤金基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弗朗西丝与查理(证成通常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证成 L。最后,来自不同视角的不同理由对 L形成了聚合。这是一种使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富有魅力的洞见。”[15](11−12)高斯设想,通过聚合观念,“即使宗教理由不为公民们所共享,它们也能够进入公共证成网络,使不同的合情理观点交错、重叠,以确保一个全面的公共证成”[13](6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聚合观念允许具有可理解性的宗教理由在公共证成中发挥作用,但是高斯强调,如果罗尔斯的宗教批评者希望单独依据宗教理由证成某种强制的话,那么这种强制是不能通过公共证成测试的,“一个公民不应当认可一项她相信只有宗教理由的法律”。高斯将其称之为罗尔斯限制性条款的最低程度版本。根据这个最低程度条款,“如果公民阿尔夫基于合情理的宗教理由去提议 L,他要想正当地在公共领域认可 L,那么他就必须相信,存在对合情理的非宗教的公众成员合理地证成 L的非宗教理由”[13](61−62)。
其次,高斯的聚合公共证成模式具有“非对称性”(asymmetry)的特点。一般认为,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预设了一种对称性(symmetry)主张,即“运用于提议强制行动的理由之标准与运用于拒斥或否决强制行动的理由之标准是等同的”[17](263)。根据对称性主张,宗教等非公共理由既不能构成公共证成,也不能削弱公共证成。高斯基于两个理由反对这种对称性。一是对称性主张违背了无支配与良心不可侵犯这一自由主义核心承诺。高斯举例说,在教育政策中,我们面临着促进共享民主价值的教育制度之价值与尊重某些公民关于培育孩子方式的宗教承诺之价值之间的持续冲突。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定在世俗化(共享的)价值中,就会存在一个支持共享的民主价值教育的充分理由。然而,信教公民却可以合乎情理地宣称:对他们来说,宗教信念的重要性压倒了共享民主教育的价值。高斯认为,如果因为这个宣称仅仅是基于不被世俗考量支持的宗教理由而被无视的话,那么,这就等于鼓励一些人臣服于其他人的价值观——以公共理性的名义。高斯评论道,对信教公民说“你并没有被强制去反对你的良心,因为你分享相关的证成性世俗理由——尽管鉴于你的合情理的价值系统,你的良心会教导你要反对这项立法”,这虚伪透顶并且是非自由主义 的[13](63−64)。二是对称性主张会使公共证成原则变得毫无意义。高斯的论证如下。一个证成性自由主义者会持有的观点是,仅当接受 L的某个全体一致性条件[U(l)]被满足的时候,L才是得到许可的[L仅当 U(l)]。而如果我们接受对对称性的一个严格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同意,运用于提议的理由与条件必须也要运用于拒斥,所以我们也就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对 L的拒斥(L得不到许可)也需要一个全体一致性条件[U(not-l)]。这样,我们的结论就是:①L仅当 U(l);并且②非 L仅当 U(not-l)。但是,我们常见的情形是,上述结论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往往都得不到满足(不会存在一个接受或拒斥 L的全体一致的公众)。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实施 L将既不是得到许可的,也不是不被许可的。对称性的代价就是大范围的争论,对于这种争论,公共证成原则难以提供任何指导[13](64)。与罗尔斯公共证成观念的对称性主张相对照,高斯强调聚合观念的非对称性特点,即尽管公众成员不能单独基于宗教等非公共理由证成一项强制性法律(除非满足最低程度条款),但是他们可以单独基于非公共理由拒斥一项强制性法律。质言之,如果某个信教公民基于宗教理由拒绝一项法律的话,那么这项法律就得不到公共证成。如果世俗立法者贝蒂现在提议一项法律,对于这项法律,阿尔夫所代表的宗教选区的选民有强烈的宗教理由去反对,那么证成性自由主义应该允许阿尔夫单独基于宗教理由反对贝蒂的提议吗?聚合观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宗教信念能够扮演一种否决者(defeater)的角色。按照高斯的观点,聚合观念的非对称性主张保护了包括信教人士在内的所有公众成员的完整性[13](63)。
最后,聚合公共证成模式的实现方式是发展一种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宪法制度。高斯认为,证成性自由主义采取宗教约束原则的动机是一种作为公共推理的政治原则(the principle of politics as public reasoning):因为①所有法律都必须得到公共地证成;并且②政治(最终)是关于选择哪些法律的;那么③政治应该以公共证成为目标;所以④政治应该是公共推理的一种形式——对那些与我们存在分歧的人作出他们能够合情理地接受的论证[13](65)。高斯指出,罗尔斯式的协商民主正是基于作为公共推理的政治之原则以阻止宗教等非公共理由进入公共证成中。然而,高斯试图论证,在大型复杂的现代社会,与依赖于公民间的民主协商去公共地证成强制性法律的方法相比,通过设计一种开放的宪法制度去实现公共证成的做法明显更为合理。高斯对比了两类选举与立法制度。一类是作为记录器的制度:与问题 i相关的选举与立法制度的任务是精确地记录公民们关于对 i的得到公共证成的解决方案的观点;一类是作为发生器的制度:与问题 i相关的选举与立法制度的任务是接收公民们关于 i的观点(cv1…cvn),并形成一个得到公共证成的对 i的解决方案。高斯借用了乔恩•埃尔斯特关于广场政治与市场政治的著名区分来说明上述两种政治制度。在广场政治中,公民们根据他人的推理进行辩论、讨论并改变自己的观点,而选举与立法制度的任务仅仅是充分地记录广场中讨论的结果;作为对照,市场政治把可能反映各种关切与利益的公民们的观点作为输入(inputs),并设法利用制度把它们转变为一个得到证成的政治成果(outcome)。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念构成了这种市场政治观念——作为得到公共证成成果之发生器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在高斯看来,基于作为公共推理的政治原则的协商民主及相伴的作为记录器的政治制度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贫乏的阐释(a poor account of political life)。这是因为约束原则容易扭曲信息的传播,最合情理的投票者会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自由审查,从而导致对现实问题以及共识的深度与广度的普遍误解。与作为记录器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是,作为发生器的政治制度直接借助公民们最牢固的地方性知识与个人性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生成能够得到公共证成的政治成果。高斯最后得出结论,证成性自由主义者的规划不应当是设法约束公民们 的输入,而是发展一种宪政政府理论——它接受现 实世界的不完美的输入,并产生得到公共证成的 法律[13](66−70)。
三、高斯的聚合模式能够回应对罗尔 斯公共证成观念的宗教批评吗?
面对所谓新的“神学−政治问题”,高斯发现,尽管罗尔斯在对政治性正义观念的充分证成中以重叠共识的方式放弃了自洛克以来的宗教隔离主张,但是在对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证成中,罗尔斯的公民性责任依然把宗教等整全性学说作为非公共理由排除在证成过程之外,即使在罗尔斯的更温和的宽泛的公共理性观点中,宗教也只是公共理由的一个并非必要的补充。因此,虽然证成性自由主义者一直宣称自己认真对待宗教,并强调信教人士按照自己的宗教承诺去生活的重要性,但是罗尔斯式的公共证成观念却已经使得宗教公民成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15](2)。我们已经看到,高斯通过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中的主流公共证成观念的共识的错误(the error of consensus)、对称性的错误(the error of symmetry)及构成证成的协商的错误(the error of deliberation as constitutive of justification)的纠正,试图发展一种不同的能够解决宗教与自由主义之间冲突的聚合公共证成模式,从而回应对罗尔斯公共证成观念的宗教批评。
首先,关于完整性的批评。如上文所述,按照批评者的观点,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造成了对宗教公民人格完整性的伤害。对于这一反对意见,斯蒂芬·马赛多讽刺道:“如果有人因为这一事实——我们中的一些人相信,根据宗教或形而上学主张去塑造基本自由是错误的——而感到被压制或边缘化,那么,我只能说‘成熟一点吧’。”[18](21)然而在高斯看来,一方面,如果证成性自由主义把公民们视作合情理多元论条件下的自由平等者,就应当允许拥有不同善观念的公民们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人生规划。因此,承诺公共证成实际上意味着应当承诺尊重包括教徒在内的所有合情理公民的人格完整性。另一方面,罗尔斯式的公共证成观念不必要地疏远了那些认真对待宗教的人,因为这一观念“错误地坚持认为,强制性法律应当得到公共地证成这一原则必须要奠基于‘公民性责任’或‘宗教约束原则’”[15](3)。与之相反,高斯的聚合公共证成观念从两个层面体现了对公民人格完整性的保护:其一,聚合观念允许合情理的公民基于不同的具有可理解性的理由(包括宗教理由)去认可一项法律或提议(在满足最低程度条款的前提下),从而表达了对公共证成中的价值多元论的承诺;其二,聚合观念赋予宗教公民单独基于宗教理由去拒绝一项法律或提议的权利。不过,高斯提醒我们,在完整性问题中,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唯一有错的一方。如果宗教批评者仍然以完整性的名义拒绝聚合观念的最低程度条款的话,那么这将是在诉诸一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批评的迫害者逻辑——我们可以强迫他人听从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是对的;但是他人决不可强迫我们听从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是错的[13](63)。
其次,关于“尊重”的批评。罗尔斯式自由主义通常假设:①每一个公民都应当作为自由平等的人而受到尊重;②如果每一个公民都作为自由平等的人而受到尊重的话,那么就存在一个有力的反对国家强制的初步预设;③如果这一反对国家强制之预设要被克服的话,那么国家强制就务必要对受其强制的人进行证成;④如果国家强制必须要对受其强制的人进行证成的话,那么任何缺少公共理由支持的强制性法律在道德上就都是不正当的;⑤如果任何缺少公共理由支持的强制性法律都是不正当的,那么公民就不应当基于宗教理由支持某项法律;⑥宗教公民在公共证成中应当避免诉诸宗教理由(即使诉诸宗教理由,也应当满足限制性条款)。批评者认为,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的“宗教约束原则”实质上造成了对宗教公民“自由平等”道德身份的不尊重。高斯高度赞同批评者的主张。按照高斯的观点,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括置策略不仅很难说是尊重了宗教公民的自由平等,而且还难以解释一项法律或提议如何能对每一个公众成员公共地证成,因为该项法律或提议仅仅以他们所接受的一套次要价值为基础。与罗尔斯的公共证成观念相比较,高斯指出,聚合观念不仅能够通过公共证成测试,而且也体现了对所有拥有不同的整全性学说的公民们的真正尊重:如果每个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对强制性法律 L形成聚合,那么以 L为基础的强制就通过了公共证成测试,并且这种诉诸非共享理由的聚合公共证成观念不会是对他人的不尊重[15](11)。
最后,关于完善性批评。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相信,良序社会的公民通过诉诸具有完善性的公共理由就能解决现代民主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而批评者则宣称,排除了太多道德资源的罗尔斯式公共理性是不完善的;对于存在高度争议的社会问题,宗教等整全性学说应当起到比罗尔斯所承认的更广泛的作用。事实上,高斯也是较早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提出完善性批评的理论家之一。在 1996年出版的《证成性自由主义》中,高斯把不完善性分为两类:一类是模棱两可的(inconclusive),即在讨论根本政治问题的时候,诉诸公共理由可能会产生许多相互冲突但却都能满足公共理性要求的答案,而单凭公共理由无法确定哪一个答案更合情理。另一类是没有结论的(indeterminate),即面对根本问题,公共理由有时被耗尽了,其内容过于贫乏以至于不能为该问题提供任何答案,或不足以为公民们从该问题的诸多答案中进行选择提供任何参考[19]。高斯认为,罗尔斯原本试图利用特定程度证成所产生的公共理由来避免公民们相互冲突的整全性学说所造成的模棱两可或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是显然罗尔斯没有成功。而聚合公共证成模式摒弃了罗尔斯的特定程度证成。按照高斯的看法,公众成员通过不同的评价性学说聚合可以形成一个既非“空集”又非“单子集”的“最佳合格提议集”(the set of optimal eligible proposals)。对于这个“最佳合格提议集”中的所有规则,公众成员们都同意它们优于没有规则,但是对于这些规则的排序,公众成员们则存在分歧。在《公共理性秩序》中,高斯力图论证,不同于康德−罗尔斯哲学,“从霍布斯经过弗格森、休谟、斯密到哈耶克及当代博弈理论家们”的思想传统所强调的社会演进过程能够对“最佳合格提议集”中各种规则的排序形成一个均衡的方案[17](42−46)。
总体而言,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限制宗教理由的做法不同,高斯的聚合公共证成模式强调,无论是宗教理由还是世俗理由,无论是整全性理由还是政治性理由,只要处在合情理多元论的范围之内,都应该能够进入证成法律的总体网络中,因为“真正的公共证成事业是制定尊重所有人自由平等的法律之事 业”[13](71−72)。这样看来,高斯的公共证成观念对于宗教批评者来说似乎更有吸引力。然而,我们也看到,高斯的聚合观念在回应了一些宗教批评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批评。
第一,高斯的聚合观念可能违背公共证成的真诚性(sincerity)原则。真诚性体现了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伙伴公民的尊重,它意味着公共推理不可借助于修辞或花言巧语。乔纳森•况恩假设了一个只有两人(甲与乙)的政治选区,他们正面临是否要认可提议 X的选择。按照真诚性原则,甲可以认可 X,仅当下面陈述为真的时候(对乙也一样):①甲合乎情理地相信,在对 X的认可中,他是得到证成的;②甲合乎情理地相信,在对 X的认可中,乙是得到证成的。可以看出,真诚性原则要求双方在公共证成中只把自己能够合情理地相信的论证提供给彼此。而根据聚合观念,假设甲乙两人各自拥有相互冲突的关于提议 X的理由 R甲与 R乙:①甲相信 R甲→ X;②乙相信 R乙→X;③甲不相信 R乙→ X;④乙不相信 R甲→ X。在这种典型的聚合版本中,如果甲想要说服乙去认可 X,他只能诉诸理由 R乙,因为乙相信 R乙能够证成 X而 R甲不能。但是问题在于,甲只能不真诚地把 R乙提供给乙,因为在甲看来,R乙并没有证成 X。因此,况恩指出,聚合观念导致了公共证成的不真诚。
第二,聚合观念可能低估了共享价值的重要性。对于许多理论家来说,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创建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一套价值与原则整合的政体。例如,马赛多声称,政治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在一个多样性社会中能够得到公共地证成,并能够得到合情理的人们广泛认同的政治原则”[18](2)。换言之,公共证成的目的不仅仅是一项法律,而且应该是法律背后的价值与原则,因为共享价值能够加强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并提升政治决策的质量。显然,聚合公共证成模式缺少这种考虑。按照马赛多的看法,信奉个人性(privatism)与偏私性(partialism)的聚合观念形成了一种薄公共理性(相对于共识观念的厚而言),这种薄的政治观念在鼓动公民们寻求社群感的同时,也削弱了公共领域分享共同知识的能力[18](16)。
第三,聚合观念中的公共协商不够充分。按照聚合观念,公共证成不需要根据“作为公共推理的政治之原则”进行民主协商的结果,而是需要选举与立法制度及程序演进与选择的结果。这样,公共讨论的作用仅仅限于发现公众成员拥有何种理由,以确定法律对他们来说是否得到证成。可以看出,公共协商对于聚合公共证成模式并非不可或缺。但是共识理论家如詹姆斯•贝彻认为,协商在公共证成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其一,协商使公民们能够相互交换理由,“从而促进他们的决策及更好地理解彼此的主张、论证以及正义观念”[20](225)。其二,通过协商与讨论,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人论证的力量的话[20](225),“公民们会愿意修正他们的政治判断”。其三,协商的目的就是正义与共同善[21]。同样,况恩对聚合观念的批评是:“如果我们拒绝‘作为公共推理的政治之原则’的话,我们就可能抛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况恩对聚合模式作出了与高斯对共识模式的相似判断:聚合公共证成观念是公共理性价值的一个稍显贫困的观念(a slightly impoverished conception of public reason’s value)⑩。
综上所述,罗尔斯为新的“神学−政治问题”提供了一个包括两个部分三个阶段的后启蒙方案。罗尔斯希望这个在他看来既有自由共识又有宗教容纳的方案能够实现由持有相互冲突的整全性宗教、哲学及道德学说的自由平等公民所组成的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然而,亲近宗教的理论家们并不满意,他们对罗尔斯公共证成观念的宗教约束原则及其理论与实践后果提出了完整性问题、尊重问题及完善性问题等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意见。与他们的立场相对照,高斯认同罗尔斯的公共证成抱负,但是不满意他的公共证成方案;同情理论家们的宗教批评,但是不支持他们否认最低程度条款的极端主 张[15](3)。高斯惊奇地发现,罗尔斯自由主义与宗教批评者之间争论的症结竟然是双方共享一个理论预设,即强制是相当容易的原则。高斯试图发展一种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的聚合公共证成观念来提醒我们记住密尔的洞见:强制是万不得已的补救,是需要节制使用的危险手段;如果个体的良心不是自由地接受法律的约束的话,强制就会导致堕落的奴役[15](24−25)。不过,虽然高斯的方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针对罗尔斯方案的宗教批评,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聚合公共证成模式也存在违背真诚性原则、低估共享性价值及缺少充分的公共协商等诸多令人诟病之处。因此,我们很难说高斯的方案优于罗尔斯的方案,或者相反。实际上,对于这两种公共证成观念,我们或许可以秉持一种更符合现代多元主义精神的态度,即无论是罗尔斯的强调共识的公共证成观念,还是高斯的尊重多元的公共证成观念,都是证成性自由主义家族中的不可缺少的合情理的成员,它们能够互补地为实现现代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多元与稳定作出贡献。
注释:
① 强制性法律的正当性在于它能够向所有人证成。也就是说,每一个合乎情理的公众成员必须有充分的证成性理由——如果他们被自由而平等地对待的话——去认可该项法律。但是由于不同的理论家对如何阐释证成性理由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而出现了两种公共证成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证成性理由 R能够被公众 P中的所有成员所共享。这是公共证成的共识观念。另一种观点认为,公众 P中的不同成员通过各自的证成性理由( R1,R2,R3……Rn)在法律 L上形成聚合。这是公共证成的聚合观念。参见 Kevin Vallier. Convergence and consensus in public reason.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2011(25): 262-264; Fred D'Agostino. Free public reason: Making it up as we go.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② 凯文·瓦利耶与弗雷德·达戈斯蒂诺沿着高斯的思路给出了比较清晰的可共享性与可理解性的定义。可共享性是指:公众成员 A的理由 RA对公众来说是可共享的,当且仅当该公众的成员们根据(在该公众中)共同的评价标准认为 RA对公众的每个成员来说是得到证成的(包括 A)。可理解性则是指:公众成员 A的理由 RA对公众的成员来说是可理解的,当且仅当该公众的成员们根据 A的评价标准认为 RA对 A来说是得到证成的。参见 Kevin Vallier, Fred D'Agostino. Public Justifica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4 Edition), Available at: https://plato.stanford.edu/ entries/justification-public/.
[1] LEO S. Preface to hobbes politische wissenshaft[C]//KENNETH HART GREEN.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7: 453−456.
[2] 任剑涛.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2): 134−144.
[3] 理查德•罗蒂. 民主先于哲学[C]//黄勇, 编译. 后哲学文化.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162.
[4] JOHN R. A theory of justic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15.
[5] JOHN R. Political liber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约翰•罗尔斯. 公共理性理念新探[C]//谭安奎编. 公共理性.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7] PATRICK N. Is political liberalism hostile to religion?[C]//SHAUN P. YOUNG. Reflections on rawls: An assessment of his legacy. Burlington: Ashgate, 2009: 158−159.
[8] NICHOLAS W.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decision and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issues[C]//ROBERT A, NICHOLAS W.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 The place of religious convictions in political debat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105.
[9] CHRISTOPHER E, TERENCE C. Relig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EB/OL].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7 Edition), Available at: https://plato.stanford.edu/ entries/religion-politics/#toc
[10] 夏庆波.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完善性”问题[J].社会科学辑刊, 2016(5): 15−20.
[11] DAVID R. Rawls’s wide view of public reason: Not wide enough[J]. Res Publica, 2000(6): 51−52.
[12] JONATHAN Q. What is the point of public reason?[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4(170): 545.
[13] GERALD G, KEVIN V. The roles of religious conviction in a publicly justified po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convergence, asymmet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09(35): 53−72.
[14] CHRISTOPHER E. Religious conviction in liberal politics[M].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0.
[15] GERALD G. The place of religious belief in public reason liberalism[EB/OL]. published papers.Jerry Gaus. Available at: http://www.gaus.biz/Gaus-ReligiousBelief.pdf. 2009-10-09.
[16] GERALD G. 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M].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9−40.
[17] KEVIN V. Convergence and Consensus in Public Reason[J].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2011(25).
[18] STEPHEN M. In defense of liberal public reason: are slavery and abortion hard cases?[J].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1997(42): 16−21.
[19] GERALD G. Justificatory liberalism: An essay on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al theory[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1−158.
[20] JAMES B. Respect, recognition and public reason[J].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33).
[21] JAMES B. Strong inclusionist accounts of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J].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005(36): 503−504.
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ublic justification: Gerald Gaus’ revision to Rawls'
XIA Qingbo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Facing the theological-political problem of the role that religion plays in public justification, Rawls hopes that his plan of “liberal consensus”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can achieve “stability for the right reasons” in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ies. However, theorists who are sympathetic of religions put forward the criticisms that deserve to be taken seriously. Gaus agrees with Rawls’ ambition of public justification, but he is not satisfied with Rawls’ scheme. He sympathizes with the theorists’ criticism but doesn’t support some of their extreme claims. Gaus attempts to develop a conception of convergence to respond to the religious criticism at Rawl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iculties in Gaus' scheme. In a word, As to the two schemes of public justification, we can hold a more modern spirit of pluralism. That is to say, whether it is Rawls' scheme which puts more emphasis on common sense or Gaus' which pays more respect to pluralism, both are indispensible and “reasonable” members of the liberalism family of public justification, making complementary contributions to realizing freedom and equality, pluralism and stability of the modern society.
Rawls; Gerald Gaus; religion; public justification
2018−08−23;
2018−12−26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罗尔斯宗教思想研究”(15YJA720008);2017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宗教与公共理性关系问题研究”(AHSKYG2017D131);2014年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高校德育的公共性困境及其出路研究”(2014jyxm128)
夏庆波(1972—),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联系邮箱:xiaqingbo2008@126.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9.03.002
C913
A
1672-3104(2019)03−0010−09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