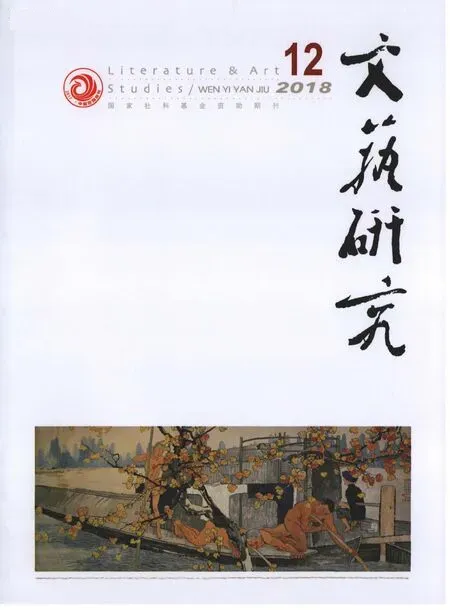追寻美学的现实感
——评玛莎·努斯鲍姆《善的脆弱性》
2018-12-26范昀
范 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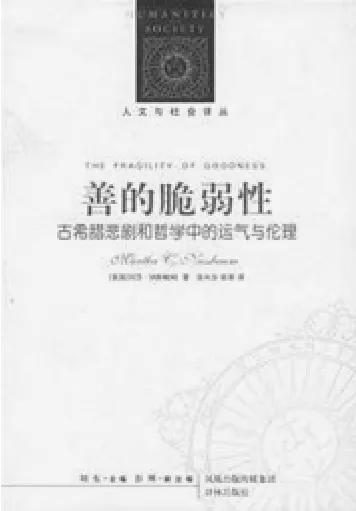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理论话语中,“审美超越”是个常被用来描述文学艺术独有价值的重要概念。将审美体验理解为某种宗教或形而上的救赎力量,是现代美学的主流共识。查尔斯·泰勒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家周围弥漫着这样一种崇拜,它源于这样的意识:艺术能够显现巨大的道德与精神意义;在它之中存在着生活的特定深度、完满、严肃以及强度的关键,或是一种特定整体性的关键。”①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中,特里·伊格尔顿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即便身处“上帝已死”的后现代处境中,人类也依然不会放弃对信仰与超越性的追求,“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使得形而上学的激情再次勃发”②,大部分的美学理念依然不会满足于琐碎的日常性,更愿意将自身定位于“神学的置换性片段”③。这种判断在现实层面可以不断得到印证,“超越”“救赎”“乌托邦”等语汇的确是当代艺术展览与论文频繁使用的关键词。
就国内而言,“审美超越”一直以来同样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自20世纪末文艺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以来,不少学者基于对当下学术风潮的质疑与不满,更加强调“审美超越”的重要价值。虽然这种对人文理念的坚守值得肯定,但学界对审美超越的具体讨论常常流于笼统,缺乏较为细致的澄清。如强调审美活动的形而上学性,认为审美是“超越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式”④,或将审美超越理解为一种“终极关怀”和重建信仰的手段⑤,这些表述并未真正揭示审美超越与宗教信仰的本质区别。此外,对审美的讨论呈现出某种单一性,尤其是对审美超越的个体内在救赎性的强调往往压倒对审美的外在社会性、公共性的重视:如认为审美超越的特质在于实现个体的本真或开启心灵的自由,从而实现拯救人性的目的,而对审美超越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内涵则论述甚少。即便认为审美超越所包含的个体救赎具有社会性,但对社会性的理解也往往停留于理论概念层面,并未将这个概念落实于真正具体的现实实践。对此需要追问的是:除了具有超越性之外,审美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性?除了个体救赎色彩的超越性,审美超越是否存在着具有现实公共维度的超越性?
在一篇题为“超越人性”(Transcending Humanity)的文章中,美国当代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引述了《荷马史诗》中的这一段落:奥德修斯被困于神女卡吕普索的洞府,神女对他一往情深,照应他的饮食起居,答应让他长生不死,奥德修斯却对此毫无兴趣。尽管他深知他的妻子佩涅洛佩在容貌上无法与卡吕普索相比,但在完美永恒的天堂面前,奥德修斯却坚定地站在不完美的现实人生这一边:“我忍受过许多风险,经历过许多苦难,在海上或在战场,不妨再加上这一次。”⑥不可否认,努斯鲍姆是在借助奥德修斯的选择来表达其哲学立场。她的文字体现了一种与时代风潮格格不入的不彻底性,在她的诸多作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不完美”(imperfection)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fragility)。在这个问题上,她的思想与18世纪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写作旨在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能够更好地忍受生活。在努斯鲍姆看来,审美并不仅仅是人们超越现实、追求完美的手段,而且还可能成为人们认识现实、追求良好生活的指南。在当下的艺术与美学语境中,努斯鲍姆所发出的无疑是一种“不同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艺术的进路,值得学界重视。
若要理解努斯鲍姆的这一思想特色及其对美学产生的影响,有必要认真对待她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中译本由徐向东翻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善的脆弱性》,引文凡出自该中译本均只随文标注页码)。在这部广受好评并奠定其学术声誉的作品中,努斯鲍姆基于伦理学的当代困境,对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作了批判性的审视,为诗的伦理智慧进行有力正名,并着力构建诗与哲学的联盟。她对悲剧有关人生脆弱性的洞察所给予的深入诠释,更是暗示了一种以“不完美”为皈依的伦理学与美学思想。针对人为何有必要面对世界的缺陷与自身的脆弱,以及艺术为何需要追寻现实感等问题,她做出了极富洞见的回答,从而对19世纪以来在美学领域占据主导的“审美超越”话语形成了批判与挑战。这些思考也为她此后在《爱的知识:论哲学与文学》(1990)、《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1996)以及《政治情感:为何爱对于正义如此重要》(2013)中所发展的“诗性正义论”思想奠定了基础。为此,本文从美学的视角审视努斯鲍姆的这部专著,并结合其后来的相关作品来讨论其伦理思想为当代美学所作的贡献。
二
《善的脆弱性》看似探讨古代思想,其实剑指当代学术。努斯鲍姆失望地看到当代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在追求抽象化、理论化以及系统化的过程中,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究其思想根源,努斯鲍姆认为这源自于一种追求完美、摆脱缺陷以及追求简单封闭、逃避复杂的冲动,也就是“超越人性”的冲动。这一冲动在古代思想中就已普遍存在,并在当时就引发过争议。
所谓“超越性”(transcendence),即人对克服有限性、偶然性以及流变性的渴求。其在拉丁语中有“攀登,胜过”之义,通常指向神或上帝,因而有强烈的神学内涵。人对超越的渴求与人的有限性密切相关。超越冲动是人类在面对生命的有限性、流动性与不完善性中被激发出来的。人类根据自身的缺陷构想了超越自身的完美形象,以此来摆脱自身的有限性。具体而言,大致存在着两种形式的超越:一为宗教层面的超越,认为在现实之外存在着一种完善之物(神、上帝);二为哲学层面的超越,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如沉思)来摆脱生活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这个层面也常常被称为“形而上学”。在宗教传统中,上帝或神成为了自我救赎的指路明灯;在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中,对世界的理性沉思则促成了灵魂因超越流变不居的现实而走向不朽。但在实际情形下,这两种超越性混合在一起,难以做出清晰的区分。
《善的脆弱性》的重点在于探讨哲学层面的超越性。努斯鲍姆开宗明义,指出该书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古希腊伦理思想中对理性的自足性的热切追求:借助理性的支配力量使一个人类好的生活之真善得以摆脱运气的左右”(第4页)。这一通过摆脱“运气”来追求“自足”(self-sufficient)的沉思哲学传统上承柏拉图,中续斯多葛学派、斯宾诺莎、康德,下接当代道德哲学。该传统一方面体现出“人类存在的被动性以及他们在自然世界中的主动性的一种原始感觉,以及对这种被动性的憎恶与愤怒”,另一方面则认为“理性必须要拯救人类的生存,否则那种生存就是无意义的生存”(第3页)。在这种感觉的影响下,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分享了一种共识:“正确的认识只能来自一个比人类更高的观点,一个能够从外面看清人类本性的观点。”(第184页)努斯鲍姆将这一视角称为“神目(God’s eye)观”,该观点突出体现在柏拉图以《斐多篇》与《理想国》为代表的中期对话作品中:
苏格拉底:“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任何东西的尺度,虽然有时候人们认为那个尺度是足够的,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求。”
格劳孔:“懒散会让他们这样做。”⑦
基于对完美尺度的追求,外在的“神目观”并不认同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目观”,认为“我们应当效法的是那种彻底摆脱了人类需求和兴趣的存在者”(第210页),一种好的生活应该尽量排除或者减小我们最为脆弱和最不稳定的个人牵挂,而全心投入于自足的理性追求。努斯鲍姆借助对柏拉图思想的批判来反思整个沉思哲学的传统。她在论述中很少使用“超越性”而更多使用“自足”,但后者体现了“超越性”的内涵:自足的实现需要以彻底否定现实的变化以及身体的有限性作为代价。尤其在柏拉图的中期作品中,一个好人被视为一种自足的和纯粹理智的存在,不受感情的羁绊与缠绕。高尚的人类生活需要尽可能通过沉思的方式从毫无价值的身体藩篱中解脱出来,不希望有任何偶然的运气影响到不朽的永恒生活。
努斯鲍姆对这种沉思的超越性提出质疑:她认为沉思的生活并不具有吸引力,沉思性的超越往往会以牺牲现实美好生活为代价。柏拉图式的沉思幸福,无视或回避物质资料、社会环境、政治制度以及外部风险和运气对人类幸福的决定性影响,并坚信好人不会受到伤害。然而当一个人先天残废或意外遭遇车祸,即便他拥有善的灵魂,我们能认为他幸福吗?在努斯鲍姆看来,在做一个好人与过一种欣欣向荣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距离。
她引述亚里士多德思想,对这种沉思哲学提出批判,认为这种超越性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对于伦理学而言,这种超越并不合适,因为这种超脱于现实的理性无法为现实实践提供智慧;其次,哲学沉思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具有单一性,但人的完整的生活绝不能被化约为某种单一的生活目标,并为此付出多样性的代价;最后,这种超越会使人丧失现实意识,失去改造现实的动力。当柏拉图告诫我们现实只是幻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认为这样的“影像”世界值得去付出心血,因而对改变现实放弃任何希望与努力。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沉思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立场依然在当代主流哲学(如功利主义哲学)中延续。
努斯鲍姆对沉思哲学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较之于理性主义哲学,宗教的情形更为复杂,需做更细致的区分。她在2002年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有的宗教并不否定现实人性,并能在现实人性的基础上发展出超越性,比如基督的形象是一个卓越的人的形象。在改革后的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中可以看到一种基于人性卓越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宗教。她反对的是那种与人性相对立的宗教,如基于奥古斯丁原罪观念的基督教等。这种类型的宗教常常以等级排序,把野兽置于最低级,上帝置于最高级,人则居于中间,他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本性而追随上帝。这种等级观念以更高级的事物作为超越的标准,否定了每种事物基于自身超越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以上帝的高度去要求人类,因为人的卓越与上帝的卓越不可相提并论⑧。努斯鲍姆充分认同尼采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评,因为这种形式的超越会“摧毁人们的爱,并削弱了为克服局限而作斗争的努力”⑨。
从历史的视野看,尽管对哲学及宗教形而上学的批判已成现代哲学的主流,努斯鲍姆的批判也绝非原创,但其思想的特色在于,对超越性的批判并非出于理论思辨层面的争强好胜,而是基于她对个体伦理生活以及人类公共生活的关怀。因为在她看来,只有走出对现实与人性超越性的否认,哲学才对好生活有意义;只有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哲学才能真正回到它的源头——人应当如何生活。除此之外,她对哲学与宗教超越性的批判思路还进一步地延伸到了对审美超越的批判,这在思想史层面独树一帜。因为对“审美超越”做价值上的反思,在当代学界并不多见。
三
针对神性意义上的超越性,努斯鲍姆提出基于人性视角的“脆弱性”。对于这个概念的阐释,构成了努斯鲍姆《善的脆弱性》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她援引古希腊诗人品达诗歌意象中的植株来描述这种脆弱性,如一棵小树,“独自生长在世上,细弱,无助,时时刻刻需要外界的滋养”(第1页)。人类的生活也可作类似比较:“因为命运无常和我们的价值感使我们总是要依赖外界……外界所助长的,甚至是帮助构建的,是人的杰出或价值本身。”在外界导致人类生活的脆弱性的原因中,运气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在使我们能够或者不能公正地行动,并因此过一种伦理上完整的生活这件事情上,运气看来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伦理角色。”(第3页)努斯鲍姆对于脆弱性及运气的阐发,主要源自古希腊其他思想资源(如悲剧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启发,因为在这些文本中“偶然多变的事物又总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第4页)。
悲剧诗歌让人们意识到人生幸福的不可把握以及追求自足生活的虚妄。通过对公元前5世纪几部悲剧的探讨,努斯鲍姆认识到悲剧在呈现运气之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上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努斯鲍姆指出悲剧常常表现两件事情之间的一种抗争:其中的一件是我们要超越人性的热望,另一件是认识到这种热望所带来的损失(第11页)。其次,悲剧常常展示出价值间的冲突与伦理上的两难处境,向我们展示出一种“难以解释和摆平的情景——通常称为‘悲剧冲突’”(第31页)。埃斯库罗斯笔下的阿伽门农要么做出献祭女儿伊菲革涅亚的痛苦选择,要么就得接受整个远征军全军覆没的代价:“我们是不可以用错误的方法来挣脱冲突的,也就是说,只是单单执著于唯一的一种价值,而摒弃所有其他的价值。”(第88页)除了在个体选择上呈现价值冲突之外,悲剧诗还以个体之间的对峙来呈现生活的复杂性。在对《安提戈涅》的分析中,努斯鲍姆指出悲剧主人公克瑞翁与安提戈涅分别代表两种不可通约的价值选择。这些悲剧主人公因其选择所付出的代价,质疑了那种试图化解冲突、追求完美的企图。其次,悲剧诗还能洞察到现实中的运气对人的幸福生活(包括品格)造成的影响。在努斯鲍姆对《菲罗克忒忒斯》的分析中,索福克勒斯塑造的那位英雄也会因遭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伤痛折磨,而使自身品格受到极大的损害。在她对欧里庇得斯《赫卡柏》的分析中,即便是灵魂高贵的赫卡柏在连续得知女儿和儿子噩耗的情况下,也会丧失理智,“在一个频繁动荡的时代,我们的伦理实践以及成年人的伦理善的本身,可能比赫卡柏所承认的要脆弱的多”(第564页)。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认为悲剧对于伦理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它们“把我们带回到栩栩如生的实践选择那复杂的‘现象’中”,并提示我们:“冲突的危险是实际生活的事实,我们似乎应该接受并且考察这一现实。”(第63页)
如果说诗对现实生活脆弱性的呈现基于一种直观的话,那么在晚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这种脆弱性进一步得到理论上的反思与阐发。努斯鲍姆指出,柏拉图一改早期和中期的立场,在《斐德罗篇》中对爱的解释“深刻地回应了人的脆弱性之美”(第12页)。在这篇对话录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再把人的爱欲与癫狂视为一种恶,这些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反倒是人类美好生活中不可缺失的部分。在《斐德罗篇》中,晚期柏拉图思想与诗之间也建立起了新的联系。
同样基于对悲剧诗歌价值的认识与肯定,诗性智慧在理论层面上被亚里士多德转化为一种在伦理学上的实践智慧。努斯鲍姆首先指出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拯救为沉思哲学所抛弃的“现象”上所做的努力,因为现象是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向我们呈现的,经常充满了直接的矛盾”(第333页)。在她看来,亚里士多德希望把哲学的起点定位于令柏拉图主义者丧失耐心之处,即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性、脆弱性以及流变性:“我们需要哲学向我们昭示回到日常生活的方式,使日常的东西成为兴趣和快乐的对象,而不是成为蔑视和逃避的对象。”(第353—354页)其次,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重视感知与情感。因为正是通过人的感知对特殊事物的辨别,以及人的情感对外界环境的回应,人才能真正意识到外在的善不仅仅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且还可以成为目的本身。再者,与悲剧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强调现实生活中价值的多元与不可兼容性,价值之间的不可兼容性是人类生活无法克服的事实。最后,亚里士多德还重视运气对于好生活的影响。在诸多运气与偶然性面前,生活常常显得脆弱不堪:“一个身材丑陋或出身卑微、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一个有坏子女或坏朋友,或者虽然有过好子女和好朋友却失去了他们的人,更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所以如所说过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⑩
至此,努斯鲍姆对脆弱性的重视与肯定可见一斑:“没有冲突的人类生活,比起充满了冲突可能性的人类生活来讲,无论在价值和美感上都要逊色得多。”(第107页)在另一段文字中,赞赏之情更是跃然纸上:“人性的卓越最美之处,正是在于它的脆弱性。植物之美在于它的柔韧,不同于宝石之美,即它炫目的坚硬。”(第2页)对努斯鲍姆而言,承认脆弱性意味着现实感,缺乏了这一现实感的超越性,只会沦为某种自负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在此,努斯鲍姆思想呈现出了一种独特而强烈的现实意识。
四
努斯鲍姆对脆弱性的肯定,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过于现实”之感,似乎在鼓励人们只认可现实的不完善而不再追寻完美。针对这样的误读,努斯鲍姆也做过回应。在2001年为《善的脆弱性》修订版所写的序言中,她强调了该书写作的目标是为了批判当时的那些主流道德哲学,它们无视人类生活中的复杂性与冲突性,使哲学抽象化、学院化,与真实的生活失去联系。这一理由使她特别强调脆弱性的价值。但她否认自己认同过这样一个浪漫的观点,即脆弱性本身是值得赞颂的。她还进一步指出,很多脆弱性“并不是来自人类生活本身的结构,不是来自某种神秘的自然必然性,而是来自无知、贪婪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癫狂”(第27页)。为此,人们需要通过努力去克服与消除那些明显可以避免的脆弱性,需要某种程度的理想性与超越性。她不仅援引尼采,表示一旦人失去了对超越的渴望,那么“最可轻蔑的人的时代就到了”⑪,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伯纳德·威廉斯的虚无主义,后者在对索福克勒斯《特拉基斯少女》的解读中暗示了人类生活悲剧的必然性,因为这“许多罕见的痛苦,/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宙斯的所作所为”。努斯鲍姆则认为我们不能麻木地认可这样的命运,而应该付诸努力去克服这些邪恶与困难⑫。
由此可见,努斯鲍姆并不希望人们以庸俗的方式理解超越性,尤其反对刻意制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个在《善的脆弱性》中有所暗示但未加以明确阐释的主张,在她2013年出版的《政治情感:为何爱对于正义如此重要》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理想与现实有时候并不一定对立,因为只有现实中的人才会渴望,“他们想象着比现实世界更好的可能性,并且努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在此意义上,这种“理想”就是“现实的另一种形式”⑬。努斯鲍姆同时提醒,当人们的渴求偏离了现实的人性,也会误入迷途。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选择超越性还是现实性,而在于我们如何寻找具有现实感的超越性,因为拥有现实感并不等于世俗意义上的“太现实”。
努斯鲍姆在此后的一篇论文中对“外在超越”(external transcending)与“内在/合适的超越”(internal/appropriate transcending)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地把握超越性。她所谓的“外在超越”即上文所提到的两种超越,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敌视与否定;而“内在超越”则为一种基于日常人性的超越,是一种正视人性局限前提下的超越⑭。在努斯鲍姆的概念框架内,这两种超越存在着对立:我们之所以反对外在超越,就在于它会妨碍我们更好地进行以人性与现实为基础的超越⑮。
努斯鲍姆常常用人的卓越(excellence)来描述“内在超越”。她以体育竞赛为例,指出人的卓越完全不同于神的卓越:作为人的运动健将要比完美的神更具有魅力,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建立在身体的局限性之上。人们之所以会为奥运会百米赛跑世界记录的刷新而喝彩,是因为在这些行动中让人体会到一种因克服身体局限而达到的卓越。“追求卓越就是充分利用这些能力去成功地克服那些局限”,而“越大的局限越能产生伟大成就的可能性”⑯,这点在很多残疾人所取得的成就中得到充分印证。与之相反,人们之所以痛恨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其原因不仅在于它违背了公平竞赛的理念,而且还在于通过药物所达到的卓越毫无魅力可言,它通过帮助人摆脱身体的局限性,“超越了身体的界限”,这样会使“取得的成就不再是一种成就”⑰。因此这是一种与脆弱性相关的卓越,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性的、与外界紧密相关的卓越。努斯鲍姆所强调的“内在超越”是一种基于脆弱性与现实感的卓越,上文所讨论的希腊悲剧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即是这一“内在超越”的典范。
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无法在理性上在“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因为抽象的规则绝不可能成为正确的指针,真正的答案只能源于我们对历史以及当下经验的理解。在努斯鲍姆看来,古希腊词“hubris”(傲慢自大)可以成为我们衡量超越性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这个词常被用来指称丧失对现实的联系,过高估计自身的能力,意味“丧失对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生活的理解,并无法生活于人生的局限(同时也是可能性)之中”⑱。唯有通过避免这种“傲慢自大”,我们才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超越,从而获得一种对待生活的合宜的态度,在超越现实与肯定人性之间寻找微妙、灵活的平衡。在追求合理人性超越的过程中,我们无法机械地按照某种教条或准则行事,而需要“更多的经验与实践,更多在思想与情感上的灵活性与微妙性”⑲。
五
努斯鲍姆对超越性的区分不仅对伦理学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当代美学事业启示良多。在她的伦理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超越性有别于抽象思辨的哲学或否定人性的宗教。文学艺术因其对事物的特殊性、情感以及价值之间不可兼容性的正视,在努斯鲍姆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努斯鲍姆由此构建了一种面向公共生活的“诗性正义论”。努斯鲍姆的关注点主要在伦理学与政治学,因此并未就美学主题做专门系统的阐发。但她对两种超越性的区分以及对相关文艺作品的讨论,暗示出在审美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超越维度。
自19世纪以来,基于信仰的真空以及对中产阶级品味的不满,“审美超越/救赎”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美学与艺术实践的主流话语。如果说在18世纪艺术主要指技艺的话,那么一代人之后,“艺术被抬高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形式”⑳。艺术的伦理维度逐渐为形而上学维度所取代,艺术的教诲模式逐渐退场,人们“不再要求艺术取悦于观众,但却要求它能够提供生活的精神食粮”㉑,审美的价值就体现在席勒的“自由”与黑格尔的“解放”,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需要意识到他们肩负着一个“伟大的宗教与社会使命”,像“热气球一样,把我们提升到更高的空域”㉒。
在“审美超越”的问题上,努斯鲍姆的态度与这一主流有所不同。她对希腊悲剧的阐释明显不同于尼采对悲剧精神的理解。如果说尼采对悲剧的理解基于“艺术形而上学”的话,努斯鲍姆的阐释完全是伦理学层面的。她所赞赏的审美超越不是向非人性的神性超越,而是为了回归人性所做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不脱离现实,而且通过审美的再现以及同情共感的力量来建立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纽带,从而召唤读者去思考生活中严肃的伦理命题,并从情感与想象上激发读者在实践中为改变人类生活的缺陷而努力抗争。
在理论层面,努斯鲍姆对柏拉图式的美学思想提出批评。后者认为我们在观看绘画时不应该从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兴趣和需要出发来关注对象,而是应该采取一种超越人性的方式来观看:“只欣赏纯粹的、简单的线条和色彩之美”,因为“完美的神不可能在这一特殊的个体身上看到任何奇异的地方”;在音乐欣赏上,柏拉图也认为人们“同样也应该放弃对人类的语言、意义和情感的关注,而去欣赏‘流畅和清晰的声音,以及那些把一个单一的和纯粹的音调产生出来的声音’”(第208—209页)。努斯鲍姆在呈现并批判柏拉图上述观点的过程中,也将柏拉图的观点引入现代美学与艺术发展的语境之中:比如她从柏拉图的观点谈到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进而会令人联想到现代艺术的“去人性化”立场(奥尔特加·加塞特)以及当代艺术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对艺术的“剥夺”(阿瑟·丹托)。
努斯鲍姆不仅不认为艺术的价值仅仅体现于某种类似神学意义的超越性,而且还认为艺术的力量恰恰体现在它的伦理性与现实感,甚至还比伦理学更好地激发人们去探询关于人生的问题。她的“内在超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释她对诗的理解。一方面,诗对现实与自我的认识是超越日常的。诗中之所以存在着超越,在于日常生活的麻木已使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认识与判断,诗恰恰是在碎片化式的生活中把握到了现实生活的实质。但另一方面,这种超越并非转向神圣的非现实,而是“转向好的人类活动”(第527页)。因为悲剧不仅能够通过怜悯与恐惧,帮助人们直面现实的复杂性,“从而可以平等地评价当下和未来的人性”㉓,而且还有助于“把某些重要的、有关人类之善的东西向我们揭示出来”(第542页)。因为怜悯意味着我们希望某种邪恶与残酷能够得到改变,意味着一种改变现实的意愿与行动。
除了理论上的阐述外,从其对悲剧的分析来看,努斯鲍姆更注重通过作品个案来阐发其审美理念。《善的脆弱性》中探讨悲剧的思路也在其此后对现代小说的讨论中获得延续。在《爱的知识:论哲学与文学》中,努斯鲍姆援引亨利·詹姆斯对文学的比喻“机敏的羽翼造物”(alert winged creatures)㉔,或普鲁斯特“翱翔于日常的麻木与迟钝之上”的“天使”,来指称文学的超越性,但同时认为这些文学中的天使终究不同于神圣的天使。文学的天使是关注具体的、特殊事物的,而神圣的天使,“因缺乏想象力与观察特殊事物的能力而无法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㉕。她之所以赞赏詹姆斯的后期作品《金碗》,在于该故事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一个处处存在代价的不完美世界,主人公麦琪必须在父亲与丈夫之间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代价。麦琪正是通过真正看到了一个“有裂缝的金碗”而实现了自我的成长㉖。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妇之间的非完美爱情,同样得到了努斯鲍姆的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典范,尽管这种信任也会以付出权力关系作为代价㉗。
近些年,努斯鲍姆还特别关注经典歌剧作品。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以伯爵夫人原谅伯爵这一妥协性的结局收场。努斯鲍姆看到的是,伯爵夫人不仅原谅了伯爵,而且也原谅了那个并不完美的生活:“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爱情,并不总是那么平坦和无忧无虑;人们绝无可能获得他们所渴求的全部。”她还在莫扎特尘世性的音乐中体会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贝多芬音乐的现实感:“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可以感受到的是某种不同于宗教式的幸福:它是喜剧性的,不平静的,不确定的,对超越性的主张怀有警惕。”㉘很多美学家或音乐评论家往往倾向于从一个笼统的“审美超越”观念去理解莫扎特的作品,并未注意到在莫扎特与贝多芬、瓦格纳之间的差异。在她看来,如果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对超越性的渴求弥漫着更多虚无主义的味道,并很可能鼓励人们对着这个世界摆出一张臭脸的话,那么在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人们则能感受到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热忱,会把这个世界看做一个值得我们去投身的世界㉙。
总而言之,努斯鲍姆更重视基于现实感的超越性。她心目中的好艺术,是以复杂性、冲突性以及不彻底性的精神形态示人,与追求极端、决绝与乌托邦的精神气质形成鲜明对照。在此意义上,文学与艺术才真正向其读者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在直面现实的同时超越现实,“要求他们积极地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道德挣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某些情形下,美德有可能战胜各种反复无常的不道德力量,而且,即便不是这样,美德仍然可以因其自身的缘故而闪闪发亮”(第37页)。
六
基于“审美超越”在当下美学话语中的支配性地位与笼统化言说,努斯鲍姆贡献了一种更具辨别性与现实感的美学思想与批评范式。中国文艺学与美学界长期深受欧陆尤其是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㉚,以席勒为代表的“审美超越”成为学界思考美学问题的普遍范式,以此为背景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成为中国艺术教育所致力的主要方向。曾有当代学者试图探讨审美的公共维度,但依然无法摆脱席勒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审美共通感的实现在于超越现代性的分裂,回归被现代—后现代黜退的“真理”与“至善”母体㉛。席勒的美学观看似沟通了三大领域,实现了某种“整全”,但这种“整全”往往只实现于人的“心境”㉜之中,而非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不可否认,这种美学观对18世纪至今的美学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中国学界普遍接纳。无论是后来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还是当代文化激进主义,基本并未摆脱这一以“游戏”逃离(或摧毁)“现实”的思考范式,甚至在现实中产生一定的危险。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的不幸命运尚属个体不幸的话,那么萨弗兰斯基在对浪漫主义的反思中向我们指出某种审美超越在政治上的危险㉝。而当下在国内新一波走红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在展示激进的、不留余地的政治姿态的同时,并不能掩饰其有限而微弱的现实介入感。尽管也有个别学者对此做出批判与反思㉞,但并未动摇国内美学研究的这一基本格局。为此,探寻一种更具有现实感、更有利于社会正义的美学思想,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至少有助于丰富与补充美学研究的维度。努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中对哲学与宗教超越性的批判和对诗性伦理智慧的捍卫,无疑为当代美学提供了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思考路径。
不可否认,努斯鲍姆的这一美学立场很容易遭到质疑。一方面,她会遭到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认为其对审美文化的辩护,暗示了某种形式的非理性情感政治。另一方面,她的审美观还会遭到浪漫主义以及审美主义的质疑,认为其美学观缺乏自主性。比如安·兰德就认为“艺术的关键要点是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㉟。理查德·波斯纳更是指出:“我们不应自作聪明地断言,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最佳路径,便是追问它如何才能够帮助读者指导他的生活。”㊱
一面在抽象的理性主义面前强调情感与想象的价值,另一面则在非理性的情感狂热面前,强调具有现实感的“理性情感”,这不免使努斯鲍姆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尽管努斯鲍姆的思考似乎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不完善性与不彻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努斯鲍姆真正在乎的东西不是自洽的理论真理,而是一种具有现实价值的实践智慧。她曾写道:“我相信,真理永远存在于中间的某个地方。”㊲她的“诗性正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面向培养公民人格与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学。她遗憾地看到传统美学与文学理论在这个公共议题上长期缺席:
经济学理论锻造了人类合理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支配着公共政策的决定,这些决定事关食品分配,社会福利。法理学家和法官们探寻对于基本权利(比如隐私权)以及对这些权利在我们彼此共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理解。心理学与人类学描绘我们的情感生活,我们的性别经验,我们共同互动的形式。道德哲学试图对事关医疗护理、堕胎、基本自由等问题的争端做出裁断。文学理论长久以来在这些讨论上都太过沉默。㊳
从这个意义上讲,努斯鲍姆所倡导的并非基于自我与理想的“青春美学”,而是一种面向现实与公共生活的“成长美学”。“青春美学”关注应然与理想的世界,厌恶或逃避现实世界,而“成长美学”则需要坦然面对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与裂缝。“不管生活多么美好,裂缝总是存在: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㊴苏珊·奈曼的看法表达了努斯鲍姆的心声。
若要实现真正的成长,人们就需要有勇气去超越“青春期理想主义”㊵,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理想主义有时就是一种“病理学上的自恋主义”,是人在心理上的成长受阻的表现,始终无法走出婴儿的心理状态:它们渴求完全地控制整个世界,拒绝放弃这种愿望而去支持一种更为现实的人生㊶。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好人需要“一种面对世界的开放性,一种对超越你控制的、不确定的并会让你心烦意乱的事物有所信任的能力”㊷。人一旦未能发展或丧失这一能力,依然是未断奶的孩子,或如狄更斯笔下的葛雷硬,满足于借助简单的理论来寻求幸福㊸,或如奥威尔笔下的温斯特,最终选择在国家这一巨大的乳房那里寻求安慰㊹。
虽然“使人成长”并非衡量好艺术的唯一标准,但当代的美学理应重视艺术文化的这一维度。有不少优秀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在实现人的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启示人们如何直面现实的复杂与冲突,以及自我的限度,并在承担其社会职责的过程中真正实现自我的成长。努斯鲍姆关于“善的脆弱性”的思考,客观上提示当代艺术与美学不能仅仅停留于愤世嫉俗的层面,以“颠覆”“抵抗”“反叛”以及“革命”的简单姿态来实现自我的价值,而更应以一种直面现实复杂性与脆弱性的方式来唤起人们对生活的责任与担当。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重视与赞赏这位当代思想家为实现艺术的公共性与美学的现实感所做出的卓越思想贡献。
① 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22.
②③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宋政超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第194页。
④ 杨春时:《生存与超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⑤ 王元骧、赵建逊:《审美超越与终极关怀》,载《文艺报》2007年9月4日。
⑥ 《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⑦ John M.Cooper (ed.),Plato Complete Works,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1125.
⑧⑮㉔ Martha C.Nussbaum,“Transcendence and Human Value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LXIV,No.2 (March 2002):445-452.
⑨⑯⑰⑱⑲㉕㉖㊳ Martha C.Nussbaum,Love’s Knowledge: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80,p.372,pp.372-373,p.381,p.378,p.379,pp.125-147,p.192.
⑩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页。
⑪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7页。
⑫ 参见Bernard Williams, “The Women of Trachis:Fictions,Pessimism,Ethics”,in Robert B.Louden (ed.),The Greeks and U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p.43-65;玛莎·努斯鲍姆《善的脆弱性》,第31—38页。
⑬㉘㉙ Martha C.Nussbaum,Political Emotions: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83-384,p.52,p.52.
⑭ 这种“内在超越”与现象学的“于内在性中的超越”有一定的类似性。按照吕克·费希的介绍,这种“价值的超验”建立在“最具体的经验之上,而非以‘上帝’‘天堂’‘共和’等偶像形式出现的形而上虚构”,它是一种“非形而上人本主义所愿意承担的本分”(参见吕克·费希《人生难得是心安——另类西方哲学简史》,孙智绮、林长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页)。
⑳㉒ 蒂莫西·C.W.布莱宁:《浪漫主义革命——缔造现代世界的人文运动》,袁子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5页,第46页。
㉑ 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㉓ 莱昂内尔·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张沫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㉗ 玛莎·努斯鲍姆:《窗: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中对他者心灵的了解》,黄红霞译,芮塔·菲尔斯基主编《新文学史》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㉚ 有关德国文化问题的批判,请参见拙文《致命的深度》,载《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
㉛ 尤西林:《审美共通感与现代社会》,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
㉜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附:论崇高)》,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㉝ “浪漫并不适合政治。倘若它进入政治,就该与现实主义的一种有力附加紧密相连。”(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8页。)
㉞ 比如崔卫平提出建立“世俗世界的美学”(参见崔卫平《建立世俗世界的美学》,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㉟ 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齐译,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㊱ 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㊲ Martha C.Nussbaum, “Romans,Countrymen,and Lovers:Political Lov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Julius Caesar”,in Bradin Cormack,Martha C.Nussbaum,and Richard Strier (eds.),Shakespeare and the Law:A Conversation among Disciplines and Profess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269.
㊴ 苏珊·奈曼:《为什么长大》,刘建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㊵ 格兰特:《伪善与正直——马基雅维利、卢梭与政治的伦理》,刘桉彤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㊶ Martha C.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524.
㊷ Rachel Aviv,“The Philosopher of Feelings”,The New Yorker,July 25,2016.
㊸ Martha C.Nussbaum,Poetic Justice: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Boston:Beacon Press,1995,pp.13-52.
㊹ 玛莎·努斯鲍姆:《同情心的泯灭:奥威尔和美国的政治生活》,阿博特·格里森、玛莎·努斯鲍姆、杰克·戈德史密斯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