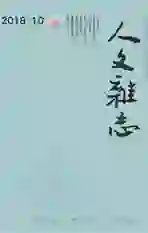“儒”“道”之间:《源氏物语》的女性意识
2018-12-24张楠
内容提要 《源氏物语》意蕴丰富深刻、思想博大精深,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思想史价值。尤其是关于女性的性别意识、心理结构、行为规范、品性修养、婚姻恋爱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都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情节构架之中,既表现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也反映了中国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内含着紫式部对道家哲学“上善若水”之女性特质的深刻领悟,从而成为中国思想影响日本的一个值得分析的典型文本。
关键词 紫式部 《源氏物语》 女性观 水之道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0-0078-07
一
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小说《源氏物语》,堪称日本古典文学巅峰之作。作者紫式部真切关注所处时代的女性命運,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不仅艺术再现了“男女姻缘多歧路”①这一作品主题,更从中体现了超越其时代局限的女性意识。至今为止,中、日学界考察《源氏物语》文本思想之际,往往囿于日本民族独创性之强调(如本居宣长的“物哀说”②),抑或是围绕佛家无常宿命论之集中阐述(如村田升的“神佛融合文艺说”、③叶渭渠的“心性说”④)。对于其中的女性意识,多以人物形象分析为主,兼或肤浅地触及男女社会学层面,几乎未见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对《源氏物语》的女性意识加以阐发,分析其中显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在为数极少的将中国儒家思想与《源氏物语》结合起来加以讨论的研究成果中,尤以叶渭渠先生的著述最为突出,他所概括的“出家”“宿命”和“心性”等诸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却几乎未曾将研究焦点投向更能折射问题意识的“女性”层面,从而忽略了中国道家思想对《源氏物语》施予的另一层关键影响,尤其是紫式部身处儒家与道家观念之间所经历的女性意识的胶着状态。
总结紫式部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柔软、婉转的方式对女性意识的自我表述和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儒、道传统文化的比较解析,对于深化理解《源氏物语》创作的伦理旨向、深入把握《源氏物语》创作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期。处于这种社会背景的中下层贵族知识分子,在从佛家宿命观中寻找自我解脱的慰藉的同时,也开始了自我反省和社会批判的欲求。而当时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婚姻生活中的被动地位,决定了纵然如紫式部、清少纳言等那般博学多才的女官,也只能囿于狭窄的皇宫内感时伤怀、以笔抒情,书写“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日]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39页。的王朝女流文学的辉煌。
正如本居宣长所指出的:“真实的人性就是像女童那样幼稚和愚懦。无论怎样的强人,内心深处都与女童无异。”[日]本居宣长:《紫文要领》,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第44页。紫式部虽处繁华宫廷之中,卑躬屈膝的苦楚境地却使其不得不内省现实与理想间的矛盾对立。因此,她对典籍、宗教的领悟深刻且微妙。而中国文化的熏陶作为蕴藏于其教育根基中的潜在能量,对紫式部的女性智慧、审美趣味乃至性格气质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同千年之后川端康成在随笔中所言:“既然有纯真的声音,又有纯真的形体,就应该有所谓的纯真的精神”那样,紫式部正是融这种女童般的“纯真精神”于文学创作中,以女性的直觉得出“丧失了童心,人就成了‘假人,文就成了‘假文”[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5页。的创作感悟;在《源氏物语》中,她不做装裱门面、矫情做作的说理,不做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的教化,只是细腻而深刻地描绘自然人性、人情。在日本平安时代的男权封建文化结构中,女性只能是屈从于男性的悲剧性存在;紫式部凭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塑造出众多善良素朴、优雅风流而内心却蕴藏着深沉、纤细哀伤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真实鲜明而又不失温婉柔和的女性之美,彰显了平安时代的女性意识。
二
日本平安时代文化深受中国唐文化的影响,“唐”作为一种先进的判断标准和价值体系,在社会意识中具有绝对权威性。而唐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儒、释、道三家并行,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平安时代的日本政治最初以儒学为显学,倡导入世之道。随着天台宗和密宗的传入,佛家出世思想渐融渐深。日后的世俗教化和空无寂寞感使得人们难现素朴的原初本性。才情兼备、深谙中国文化的紫式部不同程度地浸透了三家文化的思想底蕴;其女性观的思维取向则是直接反映出其对于三家思想的接受态度和物语创作的文化源头。
紫式部于《源氏物语》文本中彰显出的女性观,大致呈两种形态:一是蕴含自我意识的语言表述,这些表述最为重要,是考察作者女性观的文本依据;二是艺术典型的灵活再现。对塑造的典型人物的好恶态度,是解析作者审美价值的有效途径。所谓“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紫式部借主人公源氏之口的叙说,就是“自我”与“他者”关系自觉意识的表现。也就是说,源氏这一“他者”形象的塑造浸透了紫式部对“自我”的审视与反思。“夕颜”卷中,源氏言道:“‘柔弱,就女子而言是可爱的。自作聪明,不信人言的人,才叫人不快。”(《源》:75)日语中“可爱”一词,在奈良时代原本是表示骨肉之情,平安时代后引申为对柔弱者的感情。任杰译:《大野晋评〈源氏物语〉》,《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1期。“柔弱”,不仅界定出女性的生命本质,更是考察女性人格、品质、才华、风韵等的原初基点。紫式部在《源氏物语》全书多处强调“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详见“杨桐”卷第226页,“薄云”卷第409页,“少女”卷第436页等。与其说《源氏物语》是集中描绘贵族社会风俗,不对人情作道德伦理的善恶评价,毋宁说隐晦表明了女性的生命本质在于其“柔弱”的自然天性,而非在于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卷入权力角逐或是表现出政治家所应具有的残忍、果断、坚决等性格特征——这些皆有悖于紫式部心目中的女性价值。在“帚木”卷、“少女”卷中,紫式部更是借书中人物之口作出了“一个女子潜心专研三史、五经等深奥的学问,反而没有情趣”,“作者女流之辈,才疏学浅,不宜侈谈汉诗”等评说,表达了女性可爱之处在于知情识趣、察善明恶,如果热衷于道德教化,效仿男人争名逐利,势必压抑自然情感的宣泄,甚至深陷世俗牢笼而难获精神自由的观点。“夕雾”卷中,在刻画女主人公紫姬的心理活动时,作者又进一步言道:
女人持身之难,苦患之多,世间无出其右!如果对于悲哀之情、欢乐之趣,一概漠不关心,只管韬晦沉默,那么安得享受世间荣华之乐、慰藉人生无常之苦呢?(《源》:699)
紫式部认为,女性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最为悲苦,但还是要坚定面对,并执着于父母之恩、荣华之乐、喜怒哀乐等人世间的真情表达,否则便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全部意义。“苦患”“悲哀”等词语在《源氏物语》中反复出现,其中用“哀”字更是多达上千处。这种弥漫全书、挥之不去的忧愁情绪正是源自作者所认为的“女性的悲剧性存在”。
平安时代以后,日本的婚姻制度由“访妻制”逐步转变为“娶妇制”。幻匡兴、陈悼主编:《外国文学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8页。這种“变异的专偶制度”钱澄:《变异的专偶制——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的婚姻形态》,《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访妻制”以男子占统治地位为特征,采取暮合晨离方式,男女双方结婚之后各自居住在自己家中,并不同居,婚姻生活由男子到女家造访实现。钱澄认为,日本平安时代的“访妻婚”虽属专偶制婚姻形态,但因其“独占但不同居”及“父权制时代延续母系氏族社会婚禁规则”等特征,属于“变异的专偶制”。下的女性地位十分卑微,在婚姻中完全丧失主导权,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随着女性地位的日益跌落,处于暗淡和闭锁世界中的贵族女性,更加向往古代母系社会中的自由精神和豁达生活。因此,紫式部于“帚木”卷品评女性,先是总结出三种类型的情人形象,即善于伪装而掩盖瑕疵者、过分风流而令人不安者、好为人师而卖弄风情者,来探究女性的内在本质:“凡应时的卖弄风情,表面的温柔旖旎,都是不可信赖的”(《源》:25),指出女性的美与善应像“高明巨匠的华贵器物”,“著名画家的水墨丹青”,“卓越书家的遒劲大字”一般内敛而不张扬。接着,更是概况出三种类型的妻子形象:勤勉持家而不知“物哀”者、钟情丈夫而常怀妒忌者、感情轻率而遁世逃避者,发表自己对于好妻子的理解:“不讲门第高下,更不谈容貌美丑,但求其人性不甚乖僻,为人忠厚诚实,稳重温和,便可信赖为终身伴侣。此外倘再添些精彩的才艺,高尚的趣致,便是可喜的额外收获。”(《源》:23)从中可见,“性情不甚乖僻”,是当时理想女性应有的天性,体现女性自然生命之“真”;“为人忠厚诚实,稳重温和”,是理想女性应有的修为,体现女性社会角色之“善”;“精彩的才艺、高尚的趣致”,是理想女性应有的风韵,体现女性内外兼备之“美”。任何从审美感受中提炼并升华出的美学理想,都无一例外地包容并彰显出其所处时代所赋予的特定社会涵义。中等贵族出身的紫式部,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不可避免地沾染阶级局限性,但她以女性纤巧细腻、缠绵温和的审美角度观察生活并提出的这一重性重情、不以道德伦理来评判的“真善美”统一的女性标准,是有着进步意义的“理想化”女性观。
遵循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时代特点,紫式部虽将《源氏物语》的主人公设定为男性,却通过主人公情爱生活的描写,将大量笔墨倾注于其周围女性的形象塑造上,从而展示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命运。《源氏物语》中,桐壶帝皇后“弘徽殿女御”,因有强大的娘家后台和皇太子母亲的身份撑腰,恃权斗狠、热衷政治,妒恨源氏生母并害其青春夭亡后,又不甘心“儿子空有皇上的虚名”,抓住源氏与胧月夜私会一事,以莫须有罪名将源氏谪戍须磨,并对藤壶女御多加限制至其出家为尼,后被世人冷漠遗忘,终在尔虞我诈、妒恨恩怨的宫廷争斗中逝去。这一有着高贵血统却排斥异己、迫害贤达的恶人形象,完全异化了女性“柔弱”的生命本质,处处表现出与其权力欲相对称的男性化的刚硬和冷酷。
“‘柔弱这一特征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形象相吻合,在男权意识极强的儒家学说中,它是女性心理特征的突出显现”。李莎:《男人眼中的女人——沈从文与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及女性塑造》,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第12页。所谓“柔弱”,不是软弱、懦弱,更不是男性中心论调的性别歧视理念,而是生命底蕴深厚的女性之德,有着无比坚强的力量和坚忍不拔的特性,而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对男性力量的屈从。例如老子赞美“柔弱胜刚强”。从表面上看,女性是柔弱的,但恰恰却能够成为生殖力量的象征,这种“柔弱”之道是天下万物生生不息之源。“‘柔弱胜刚强,是人类智慧驾驭客观世界的本质体现”,刘绍军:《论老子的柔弱观》,《江汉论坛》2010年5期。唯有以不争强好胜、不刚愎自用的“柔弱”之态来处世为人,才会少掉世俗的烦恼与纷扰,避免心理和人格的畸变。紫式部通过塑造弘徽殿女御这一被权与欲扭曲了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女性内心被异化、被毒害后的悲哀。
源氏正妻“葵姬”性格高傲冷漠,拥有显贵的家庭出身,受过正统的儒学教化,给人以“气品高雅,毫无半点瑕疵,然而又觉得过于端严庄重,似乎难以亲近”(《源》:164)的印象。稳重自持、万事隐忍的葵姬,熟悉仁义礼智道理,懂得三纲五常人伦,符合当时衡量女性修养的全部标准,其作为牺牲品在与源氏的政治联姻悲剧中最为无辜,被六条妃子生灵作祟难产而死的凄惨结局更是令人同情。而紫式部对其塑造的这一恪守礼仪、循规蹈矩的世俗“上品女子”形象,却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在她借源氏之口的评说中可窥端倪:“这个人不肯开诚解怀,一味疏远冷淡,相处年月越久,彼此隔阂越深”(《源》:92)。在日本传统封建文化结构中,女性处于被男性所支配的地位,毫无主体性可言。波伏娃有言,女人不是天生而是被变成女人的。[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89页。女人的自然性被女人的历史性及社会性所压制,女人仅成为依附男人的“第二性”。以男权为中心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形态固然是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但经女性自身加以内化的附属意识则有效地配合了外在环境带来的压迫。周青:《倾覆末世的一叶方舟——解读〈源氏物语〉中的一个“另类女子”》,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紫式部塑造的葵姬这一失落和泯灭了女性自主意识的悲剧形象,是对波伏娃观点的有力阐释。
公元五世纪初,儒家学说东传日本。见《日本书记》卷10“应神天皇十六年二月”记载。至平安时代,儒学的理性精神极大满足了统治阶级需求而成为皇室贵族之显学。当时日本学令规定:国家设立大学,以养成官僚群臣。大学开设“大经”,即《礼记》和《左传》;“中经”即《毛诗》《周礼》和《仪礼》;“小经”即《周易》和《尚书》,此外还需兼学《论语》和《孝经》。[日]吉本隆明、[日]梅原猛、[日]中沢新一:《日本人は思想したか》,新潮社,1995年,第43页。对此,“夕雾”卷有着明确描述(《源》:364)。儒学非常重视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宣扬学习儒家经典,遵循等级礼法,是提高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道德境界的根本动力。因此,平安时代的日本,钻研“三史五经”,实践儒家礼仪,不仅成为上流社会男子的主体行为,更成为贵族女性侍奉宫廷和博取宠爱的唯一出路。
藤式部丞的情人,“书牍写得极好,一个假名也不用,全用汉字,措辞冠冕堂皇,潇洒不俗”(《源》:32),枕上私语时都教诲为官出世之道。这种所谓的“贤德淑女”最令紫式部反感,被她评为“下品之人,真是可厌。”(《源》:33)正如《紫式部日记》中她对清少纳言的那段著名评论一样:“脸上露着自满,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总是摆出智多才高的样子,到处乱写汉字,可是仔细地一推敲,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原文见[日]紫式部:《紫式部日记》,[日]池田亀鑑、[日]秋山虔校注,岩波书店,1964年,第52页。紫式部深谙汉学却十分讨厌女性卖弄学问,她注重以原初本色格物识人,认为女子过于嫉妒不可取,为人轻浮不可取,木头木脑不解风情不可取,过度展示独到见解也不可取。若是囿于儒家学问而不能自拔,必然会因过度重视礼仪、关注名分,而丧失恬淡、虚静的真实性情。儒学主张“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序”,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76年,第3289页。将个体生命活动严格控制在社会等级名分乃至血亲遗传秩序之中。其所宣扬的孝悌忠恕、仁义礼智之说,归根结底是为维护“尊卑别序”的权力地位服务,限定着人的自然天性,禁锢了人的意志尊严。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以及《紫式部日记》)中反复流露出渴望女性自然天性的思想情绪,批判了众多贵族女性掩盖于娴雅背后的病态心理,从女性社会性格的悲剧中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文化根源。
三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儒家思想极其重视社会生活的理性精神,而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儒学的过程中,受以“诚”为中心的伦理观影响,显示出较少的中国儒家道德。姜文清:《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8页。“诚”,是指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制的感情并将感情付诸行动。日本上古人对事物自然形成的“诚”的意识,具有现实性、素朴性和明朗性。紫式部于《源氏物语》中并没有伦理道德的说教,她“只追求朴素自然的真情,而淡化儒教伦理的思想,很少受到中国文学儒教言志、追求高远精神境界的影响”,叶渭渠、唐月梅:《中国文学与〈源氏物语〉——以白氏及其〈长恨歌〉的影响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换言之,她对于女性的评说更多趋向于非理性主义,只将心与情统一,几乎无视理的作用。譬如在集中发表女性观的“帚木”卷,紫式部先是借“雨夜品评”细致分析了世俗流行的三种以儒学为旨向的女性标准,并逐一加以否定,即以出身门第断言女性人品是偏见,以贫富状况判定女性教养是谬论,以血亲遗传推及女性姿容是妄言,表达了其“女性的生命本质应如水般柔弱纯净、婴儿般质朴天真,若是醉心于儒家教化,就會丧失本有的自然秉性”张楠:《谈“源”论“道”》,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2页。这一核心观点。
女性在社会人伦中的角色是“妻子”,如何评价“理想妻子”,关系到对女性生命的认识。紫式部通过大篇幅论述“理想妻子”应有的人品详见《帚木》卷第22页,[日]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39页。得出判断:评价妻子比评价一般女性难得多。妻子要具备一般女人的天性和品格;妻子又是丈夫的终身伴侣,在情感上要不离不弃、厮守一生;妻子更是家庭主妇,需负担起与之身份相适应的全部职责。对于理想妻子的标准,左马头等男人的看法是,妻子好比“真能称职的人才”去“辅相朝廷”,“居上位者由居下位者协助,居下位者服从居上位者,然后可使教化广行,政通人和”。这种观点正是当时日本贵族阶层流行的“以顺为正”的儒家夫妇之道的反映。人伦观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儒家认为,夫妇之伦乃“五伦”之首,最为重要。夫妻关系的实质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婚义》),强调妻子的社会行为仅囿于家庭领域,妻子的品德修为要顺于纲常秩序,恪守理家治内的本分。孟子曰“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滕文公下》)。《礼记·礼运》对此诠释曰:“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道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也就是说,儒家规范妻子恪守“以顺为正”的妇德,是以家族的利益为主要考量的,旨在维护和延续家族的兴旺,巩固和加强“尊尊亲亲”的等级礼法。对此,紫式部提出质疑:
主妇职务中,最重要者乃忠实勤勉,为丈夫做贤内助。如此看来,其人不须过分风雅;闲情逸趣之事,不解亦无妨碍。但倘其人一味重视实利,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是一个毫无风趣的家主婆,只知道柴米油盐等家常杂物,则又如何?(《源》:22)
相对于男性体现在公共领域的道德品质,儒学更加关注女性在私人领域的品德培养。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私人领域主要指家庭生活领域,女性被规训、教导成为温良、顺从的“贤内助”,体现了男性主导社会的伦理要求。如同夫妻关系既是人类对源于内心的情感的体会,又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性需要一般,妻子对丈夫的关系同样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体现伦理纲常的家庭主妇的职责,这是礼仪制度所赋予的趋于功利性的社会属性;二是维系两性之间自然情感的天性需要,这是体现夫妻间平等关系的非功利的自然属性。紫式部探究理想妻子的标准,与她从整体上探究理想女性的标准是统一的。她以女性的自然生命为基础,以夫妻间的情感生发为纽带,认为生活中的妻子必须加强自我人格修养,保持女人柔弱虚静的本性,“凡事不要装模作样,卖弄风情”(《源》:34),才能达到理想妻子“性格不甚乖僻,为人稳重温和,有精彩才艺和高尚趣致”(《源》:23)的“真善美”的统一。可以说,紫式部不是站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审视,而是以“知物哀”作为判断善、恶的基准,因为“物哀就存在于善与恶的调和之中”。叶渭渠:《中日古代文学意识——儒道佛——以〈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比较为中心》,《日本学刊》1995年第1期。日本“物哀”中的“物”与“事”,完全是与个人情感有关。所谓“知物哀”,就是因物动情,因物感哀。王向远指出,“知物哀”的“知”是一种审美性感知观照,其等同于审美,并且是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审美活动。王向远:《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江淮论坛》2012年第5期。“知物哀”既要保持自然人性,又要具有情感教养,不需有教诲、教训等任何功用或实利性目的,而要有贵族般的超然与优雅、女性般的柔弱与细腻,[日]本居宣长:《紫文要领》,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第61页。是一种高于礼仪规范的情感人格修养。
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的第一要义是确立人的性格,即尊重人的自然情欲。她以淡淡的笔调,在趋于日常的描绘之间,反映人的本质意味,表达有别于中国文学中的儒家教义倾向的独特文学判断和审美价值取向。她所主张的大智若愚、谦逊谨慎的处世哲学映射出她对所处时代思想意识的洞察和省思。
四
日本文化史上最辉煌的平安时代,伴随着儒学东渐日本,道家思想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513年)记载:“夏六月、百济遣姐弥文贵将军、洲利即尔将军、副穗积臣押山、贡五经博士段杨尔。”见《日本书纪》卷第17“继体天皇”记载。“五经”中包含《易经》,可见,作为道家谶纬思想的基础,“阴阳五行学说”已于六世纪初传入日本。儒家和道家分别是父权制和母权制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反映,二者都是关注人,把自然看作生命大化过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阴阳”,在自然界指天地,在社会人群则指男女。《周易·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明确阐释了儒家与道家分属于男性和女性生命智慧:儒家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尚刚知雄崇阳,是古代父权制氏族文明的理论升华;道家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贵柔守雌主阴,是母系氏族文明的理论升华。胡孚琛、牟钟鉴等主编:《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道家是从个体生命中体验出来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以“阴阳平衡”“贵柔守雌”的原则为指导,它不主张像儒家那样将为私为亲之心扩大到为公为国之上,从而实现“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而是肯定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应打破“尊卑别序”的礼仪制度禁锢而“独善其身”,保持人性的自然素朴和精神的虚静自由。道家“崇阴尚柔”的女性哲学被日本贵族阶级误读为 “以独善为宗,弃父背君,无爱敬之心”。《日本古典全集·经国集》,新树制版印刷社,1926年,第192页。所以,道家文化虽然在日本平安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却没有像儒学那样被上流社会奉为政治显学。但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却充分体现着“道法自然”的生命本性,它与崇尚自然素朴的日本民族文化相契合,尤其是“道”内涵的尚阴、贵柔的女性色彩和女性生命智慧,更得到日本贵族文人特别是宫廷才女们的青睐。以紫式部为杰出代表的平安时代女性作家,以女性生命特有的品格和智慧体悟到了“道”的本质,从“道”的生命智慧中发现了女性应有的思想境界,并试图在等级社会礼仪教化的牢笼中释放出自由灵魂,追寻返璞归真、上善若水的生活乐土。可以说,《源氏物语》的创作就从根本上领悟了道家哲学的真谛,这从主人公“光源氏”之名是由“高丽相士”观相占卜得出,主人公一生际遇遵照“三段预言”命定安排等物语构思中可见一斑。张楠:《源氏物語における道学的な発想》,创价大学《日本语日本文学》2012年第1期。《源氏物语》没有表现为君、为国的英雄壮举,没有宣传人伦教化的大道理,全書只是深入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真实描绘人性、人情的自然。
文学叙事的重要功能在于,以某种故意经营的思想内容来对人物和行为进行安排,从而为铸就的思想模式提供基础。[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源氏物语》即是如此。如上文所述,紫式部于集中阐述女性观的“帚木”卷开篇,并未做长篇累牍的分析,而是渲染自然环境来隐喻女性的生命本质。“梅雨连绵,久不放晴”的日子里,“一日,下了整天的雨,黄昏犹自不停。雨夜异常岑寂”(《源》:18),源氏等四位无聊的男人开始品评女人。“梅雨连绵,久不放晴”,“雨夜岑寂”,这些物象都和女性阴柔的生命气质吻合。道家对其核心概念“道”的意象表征,直观地指向女性,这其中最重要的透视立场即是以女性的气质性情和处世经验模拟“道”的情状。《道德经》中,静、雌、柔、牝、母、水等阴柔词汇反复出现,它们直接与“道”相贯通,例如老子认为母是根,女性是本,将“道”称为“天下母”,又比喻为女阴——“玄牝之门”,称谓为女性生殖神——“谷神”。表述道家学说中所遗存的原始宗教中的女性崇拜信仰。“雨”即是“水”,道家体悟女性生命大化之“道”的概念,更深一层的意象就是“水”。“水”与“道”同质异构,“水”性即“道”性,与天地相连、润物无声,“绵绵不绝,用之不勤”,水的意向体现出的柔弱品格,更是女性最显著的特征。《道德经·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是道家观察自然万象所体悟出的“水之道”。[美]艾兰(Allan S.):《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张海晏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2页。因此,在“雨夜品评”中,“雨”的意喻被情境化和观念化,超越了其本身的自然属性。“夏季的雨夜”这一特定环境设置的出现不仅符合作品中自然描写和人物刻画的需要,其所引发和照应故事情节之功效,也符合审美主体的情感需求。可见,紫式部精妙苦心构思出的“雨夜品评”,明确表达了其体悟道家哲学智慧,质疑儒家正统女性观的思维基点。
胡孚琛认为,道家学说蕴含的女性崇拜有着极深的寓意,其根本旨意在于肯定与之对应的谦下、静笃、柔弱、无为等属性最接近“道”的规定性。《源氏物语》中,紫式部成功塑造出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女性形象——紫姬,即是领悟了道家“水之道”的生命智慧,彰显着柔弱、素朴的自然本性。作为全书第一女主人公,紫姬对源氏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意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紫式部笔下的紫姬“相貌艳如花月”(《源》:565),“气度高雅、容颜清丽,似有幽香逼人。教人看了,联想起春晨乱开在云霞之间的美丽山樱”(《源》:459)。可以看出,紫式部探究女性风韵,并不注重矫饰后的妩媚,而是内涵“道法自然”的智慧,强调人的生命律动和自然亲和,把对日出月落、四季更替、花草树木、昆蛉鸟虫等自然形态的审美感受,全部渗透在女性生命的内在灵性中,形成了对女性生命淖约如水的美感体验。紫姬“为人异常谦恭……一举一动,无论何等些微,都受世人赞誉……应付各种场合都很诚恳周至”(《源》:721)。这种安情适性的人格操守所透视出的美好心灵,显现的是“体道如水”般的精神境界。道家以“水”喻人,强调如水之“德”皆源自“道”。人若有德,就会保持自然本性和禀赋,从自我中心的局限中超脱出来,开拓心性灵明的精神空间。做到既不受世俗功名利禄的诱惑,又不因情感好恶而内伤其身,始终顺其自然,心境平和。紫姬温柔宽容,对源氏的风流韵事虽忧思满腹,却“竭力抑制,外表若无其事”(《源》:565),“虽然心中不能没有蕴藏,但善于因人因事而运用亲疏两种态度”(《源》:611),是执著于源氏心目中的“十全无缺”的“完美女性”。道家认为,人的生命展现出的勃勃生机,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促成的中和结果。《庄子·天道》云,“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因此,有着水性生命的女子如何在行为举止中处理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宣泄,在性格养成上处理内在精神机理与外在表现的和谐,从而谨慎得体地表达自身情趣和情感,是最能体现女性虚静如水的“至善”风貌的根本所在。
然而,紫姬这种为世俗所普遍称道的“善”,恰恰是用压抑其人性之“真”而换来的贵族阶级淑女之“美”。这样的极品女子,虽赢得源氏的极致爱恋,终也无法成为皇室贵族正妻,无奈地发出“女子持身之难,苦患之多,世间无出其右”(《源》:842)般的悲叹。隐含在其享受的荣华富贵背后的,乃是被扼杀了的生而为女人的自然本性。可以说,紫式部赋予紫姬这一形象以超脱的心灵和柔弱的美质,其命运却揭示出:越是美好的自然特质,在“世之浑浊”的人间越要被玷污甚至毁灭,这是等级社会女性逃脱不了的悲剧。《源氏物语》所描写的社会世相,紫式部对女性的种种见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受当时社会地位的制约而在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表现出社会局限性,但却深刻地表达了其夹杂于儒、道两学之间所演绎出的独特女性观。
结语
作为日本王朝物语的代表之作,《源氏物语》中蕴含的女性思想不仅折射出紫式部自身的价值追求,某种意义上也反向映射了其所处历史语境的性别伦理取向。紫式部自觉地(尽管以某种隐晦的叙述策略)将平安朝的时代精神融入自身特殊的人生阅历中;其女性观的思想底蕴,绝非表面上所展现的对于儒学道德伦理意旨的屈从,而是立足于“与世俗处”的现实,将其性别政治取向投入艺术创造,通过体悟道家“法天贵真”的性情论,将女人自然人性的情感和社会人性的情态统一起来,揭示“上善若水”的生命内涵,彰显“如水之道”的生命智慧,从而追求既超越现实又返璞归真的自然化人格——恬淡优雅、绰约婉娈的风韵,浊以澄明、莫若以明的心灵,安情适性、谦让恭谨的品质,思虑周谨、平易温柔的性格,知情察理、审慎圆通的智能。紫式部以女性之心体悟女性之痛,并给予这种感受以更加明朗的批判性表征。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无论身份高贵还是卑微,无论个性理智还是冲动,也无论行为逆来顺受还是富于反抗,虽然都难逃平安时代男权社会烙上的磨难印迹,但源于自然的女性精神,往往试图超越世俗教化的樊笼,与天地逍遥游,吟唱如水的生命赞歌。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