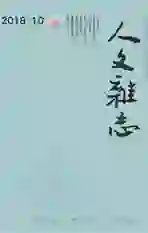透视主义哲学视角下鲲鹏之重言
2018-12-24陈赟
内容提要 《庄子·逍遥游》鲲鹏寓言被置放在全书开端,它又是在三层重言中展开的。传统在借重、重要、重复的内涵上理解重言,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未能注意到重言所包含着的透视主义哲学的预设,这一预设将真理的显现与主体自身的转变关联起来,并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基本条件。根据透视主义哲学预设,鲲鹏的三次出场,各有自己的内涵,它们结合起来,形成自由主体的成长历程的完整步骤。
关键词 透视主义 鲲鹏 自由主体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0-0021-07
古人慎始,其立言写作,特重开端。鲲鹏之喻,意味着三重开端:《逍遥游》的开端、《庄子》内篇的开端、《庄子》全书的开端。作为《逍遥游》的开端,鲲鹏之喻以自然之物的角度引出了自由问题,从而为进一步思考人的自由提供了背景视域。作为内篇的开端,鲲鹏之喻与内篇的结局——《应帝王》中的浑沌之死——构成义理上的对应关系:不仅《逍遥游》中关键词语“北冥”“南冥”与《应帝王》中“南海之帝”“北海之帝”构成对应,“冥”与“浑沌”构成对应,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同样具有深层的呼应关系,自由图景在《逍遥游》中以自然世界的鲲鹏开启,而在政教社会中则由浑沌之死终结。《庄子》外篇以《知北游》终篇,文本中的“知北游于玄水”“反于白水之南”“反于帝宫,见黄帝”的寓言,既与《逍遥游》的鲲鹏寓言形成对比,也与《应帝王》的浑沌寓言构成对应。除去作为全书自序的《天下篇》,《庄子》全书的终篇实际上是《列御寇》,《列御寇》篇末关于知、明、神三者关系的探讨,正与《逍遥游》的核心概念“神凝”、《齐物论》的“以明”构成义理上的深层对应。①由此,鲲鹏之隐喻在《逍遥游》全篇、乃至整个内篇,以至《庄子》全书,具有开端立始的基调性意义。在《庄子》的整体视域中解读鲲鹏寓言,实在是一项重要但却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充分尊重历史形成的内、外、杂篇的划分,这一划分的题中应有之意在于,以内篇为主干,外篇则可以视为内篇的注解,而杂篇则是对内外篇的引申与发挥。因而,以内篇为主体,以外杂篇为羽翼,在内外篇的互文见义及其構成的总体思想脉络中理解内篇,理解① 《庄子·列御寇》云:“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夫!”钟泰释之云:“常人验之以明,明者人知也。而人知不足据以为验也。以人知验,是为‘以不征征,故曰‘其征也不征,言其征不可得而终信也。盖人知而听命于天知,则人知亦足以效其用。若人知为主,而天知退处于其下,即上文所谓‘受乎心,宰乎神者,则内外之刑并至,欲善生以善死,难矣,故曰:‘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明者唯为之使,言可为使不可为主也。‘神者征之,言用为征者,唯神为可也。‘明之不胜神,即人之不胜天也。‘不胜者,不及也。”参见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52~753页。
《逍遥游》,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方法。事实上,明代学者潘良耜《南华会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各以类从,分附七篇之后。如以外篇《缮性》《至乐》,杂篇之《外物》《让王》附于《逍遥游》之后;以外篇《秋水》,杂篇之《寓言》《盗跖》附于《齐物论》之后;以外篇之《刻意》《达生》附于《养生主》之后;以外篇之《天地》《山木》,杂篇之《庚桑楚》《渔父》附于《人间世》之后;以外篇之《田子方》《知北游》,杂篇之《列御寇》附于《德充符》之后;以外篇之《骈拇》,杂篇之《徐无鬼》《则阳》附于《大宗师》之后;以《马蹄》《胠箧》《在囿》,杂篇之《说剑》附于《应帝王》之后。潘雨廷谓:“此书编目之义似可推敲,而內七篇足以概括全书之旨,未可谓之无理。……唯庄子之所以成庄子,似当以內七篇为主。”(潘雨廷:《论庄子内七篇》,《易与老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的确,以外篇之《缮性》《至乐》为《逍遥游》之注脚,不如外篇之《秋水》之与《逍遥游》之相似也。陈志安《南华真经本义》谓:“《秋水篇》与《逍遥游》局相似也。”王夫之《庄子解》云《秋水篇》“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参见方勇:《庄子纂笺》第4册,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662~663页。这种互文性的理解方法乃是对《庄子》一书传统编排之意的恰当回应。这里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透视主义哲学的视角,展现鲲鹏隐喻的三次重言逐层展开的思想意蕴。
一、鲲鹏隐喻作为“重言”
鲲鹏寓言在《逍遥游》中出现了三次,是典型的重言式写作方式。关于鲲鹏的三次出场,笔者曾有论述,参见陈赟:《〈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寓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但本文所作,立意重在重言的叙述机制,并由此叙述机制揭示鲲鹏寓言的未尽之意,故而本文与曾有的论述甚有不同,颇有另撰此文之必要。第一次是鲲鹏的直接、正面出场,第二次与第三次则分别通过“齐谐”与“汤之问棘”间接引出:“鲲鹏之说既言之,重引《齐谐》,三引汤之问棘以征之,外篇所谓‘重言也。”王夫之:《庄子解》卷1《逍遥游》,《船山全书》卷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2页。曹础基将重言别具一格地解释为“重(zhòng)言”,即“庄重之言,亦即庄语,是直接论述作者的基本观点的话”,并将《寓言篇》的“重言十七”解为重言占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都是寓言。这样,重言与寓言相对(参见曹础基:《庄子浅注》修订重排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0页)。然而,这样的解释未能把握重言中的重复之意,而且,这种解释还不得不改变《寓言》原文,将“重言十七”改为“重言十弌”。
重言似乎意味着重复之言,即一再地说、再三地说,但重言也意味着为世人推重的重要(厚重、郑重)之言,因为重要,所以被推重,因为被推重,所以需要重复、反复言之。郭象注《寓言》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成玄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显然本质上以为重言即为世人推重之言,即主观上被重视、客观上很重要的话。陆德明《经典释文》“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世人推重之言,往往由为世人所推重之人所说,由此重言往往是老者(耆艾)之言、圣贤之言。然而,郭、成所谓的“十言而七见信”,又包含重复之意,即反复被道及的话,郭嵩焘:“重,当为直容切。广韵:重,复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郭云世之所重,作柱用切者,误。”这其实是以重言为重复之言,而非世人推重之言。(以上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830~831页)其实,重言同时包含重要、重复两个层面。魏光绪以为重言即重复之意,但却否定重言之重为轻重之重的含义:“而得重言者,古人有言,庄生重复言之,如伯昏瞀人、吕梁丈人等十余处,皆见《列子》;《庚桑楚》一段,见《亢仓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等语,见《老子》。其他杂引诸圣贤,及自所论著,前后重复者亦多,若曰苟可借以发挥理奥,启人信从,不必自己出也。而诸家乃训为‘轻重之‘重,谓借重古人,岂其然与?”(魏光绪:《南华诂》,转引自方勇:《庄子纂要》第6册,第497页)然而杂篇《寓言》云:“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显然,在《寓言》看来,借重古人之言乃是重言的题中应有之意。郭象、王雱、吕惠卿、陈景元等多数学者都是这样主张的。就此而言,重复之言与重要之言这两重含义均应包含在重言的内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重言”之“重”似乎同时包含着两个方面即重复与重要。但《寓言》对重言、寓言功能的认识,仅仅限于赢获读者的信从。但庄子的重言更近于托古言说,即借他人之口而说自己之意,如刘凤苞就注意到:“重言十居其七,杂引古人问答之词,而参以己意。虽不必实有其人其事,当凭空结撰之时,以准乎数典不忘之例,见非自我作古,古人已先我言之也。”(刘凤苞著,方勇点校:《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年,第723页)这里的要点是参以己意,其实笔者认为重言以参以己意更甚之,而是托古言说,皆作者借着他人之口而自我言说。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透视主义哲学预设下多角度、多音调、多层次的立体性写作方式,即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等等,呈现同一个对象的多重面向。这跟《逍遥游》中藐姑射山神人是通过接舆、肩吾、连叔、尧等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加以呈现的方式是一致的。郭象注《寓言》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成玄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这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说“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相互发明。⑦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830~831页。显然,三人均以为重言即为世人推重之言,既然主观上被推重,那么在客观上也就很重要,唯有重要的东西才能被世人所推重。然而,郭、成所谓的“十言而七见信”,又包含重复之意,即反复被道及的话,郭嵩焘云:“重,当为直容切。广韵:重,复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郭云世之所重,作柱用切者,误。”⑦郭嵩焘以重言为重复之言,固然合理,但却否定重言为世人推重之言,这就有问题了,没有看到重言兼具重复与重要的含义。世人所推重的重要之言,往往由为世人所推重之人所言说,由此重言之重又可以引申出另一种含义,即借重,林希逸云:“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431页。同样地,陆树芝认为:“所谓‘重言十七者,托于人所尊重之人以言之,所以止人之争辨也。如书中所称引古昔,皆人所素重之前辈,以有经纬本末,在人心目是以推为耆艾者也。”陆树芝:《庄子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6页。的确,庄子中不少话往往借助于老者(耆艾)、圣贤、古人来言说。但借重古人以自重者,仍然要强化所言说者之重要性,这与通过重复之言的方式以增强所言之重要性,异曲同工。就此而言,借重之言、重复之言与重要之言这三重含义均可逻辑地包含在重言的内涵之中。
然而,仔细思考,即便重要之言的展开往往借助于两种言说方式——一是借重古人、圣贤之言,一是重复地言说——但仍然可以追问:无论重复、反复地言说,还是借重古人、圣贤之言来说自己之意,是否每次重复都是同一道理的重复,是否每次借重在内容的呈现方面都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追问实际也是在探究重言的功能。传统的理解,或者认为,借助于世所推重之人,比通过自己之口说出,可以增加内容的可信性,如刘凤苞所谓“取老成硕彦之言,以见信而有征,则群言可息”;刘凤苞著,方勇点校:《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年,第723页。或者认为,反复地言说、再三地致意,“重言之不倦,提撕警惕,人道于是乎存。”⑤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832、831页。然而,在实际上,《逍遥游》中“齐谐”就不是这样的“耆艾”:一方面,“齐谐”增加的是内容的诙谐与幽默,隐喻齐谐之言是戏说,而非庄语或正说;另一方面,对于本来就是寓言的文字,无须增加字面上的可信性,因为在字面含义成为隐喻内涵的“具身”或“体现”时,字面内涵的可信并不意味着隐喻内涵的可信,否则人类所需要的叙述机制中就需要将寓言、隐喻之类的排除出去。就此而言,将重言的目的理解为增加可信性,以达到止息纷争从而让人更加信服地接受,这一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并没有触及重言的真正意义与功能。再如,在《逍遥游》中,从斥鴳之眼看鲲鹏,与从蜩鳩之眼看鲲鹏,本来就意味着一种重言,然而无论是斥鴳,抑或蜩鸠,都不能在传统的重言意义上加以理解,毕竟,蜩鸠与斥鴳不但不是为世人所推重的角色,相反,它们相对于鲲鹏,似乎更多地具有贬义的色彩,那么,以它们的出现重言鲲鹏,当如何理解?这些都关系着对重言本质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重言是一种值得再思的叙述机制。当郭嵩焘以“庄子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⑤来阐发重言的功能时,在一定意义上道出了重言这一叙述机制的奥秘。就叙述机制而言,有让对象直接出场与间接显现两种方式。所谓直接出场,意味着对象在直接描述中出场,而不是通过他者之口、他者之耳被转述,如鲲鹏的第一场出场,这样的叙述方式属于《庄子》叙述结构中形式上的正言,尽管正言本身也可能是寓言或隐喻。如果被叙述的对象或事件并不是直接出现,而是经由他者之口或他者之眼而得以显现,那么这就是间接叙述,例如鹏的第二次出场是通过“齐谐”这一中介,鲲鹏第三次重言则是被置放在“汤之问棘”的情境下。间接叙述的逻辑意味着庄子在未被明言然而又一直被遵循的类似于“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哲学预设下展开自己的叙述。所谓视角主义的哲学预设,意味着事物的显现并不能无遮拦地全面地一次性完整地自我呈现,而总是在一定的角度或视域中进行侧面性的或间接性的显现,一定的视域对应着呈现事物的一定侧面,而且随着视域的转变,呈现的侧面也有所不同。换言之,事物的呈现受制于显现的机制,而这一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条件,它使得事物的自我呈现源初地卷入到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中去:其一,某物A总是对着某物B而显现,其二,某物A总是在C的情境下(对着某物B)而显现;而在C情境下,某物A总是不可避免地勾连着一个某物的系列,换言之,A1与A1、A2、A4……共同构筑了情境C;不仅如此,当A对着B的不同层次或不同界面显现时,情境C中的A仍然具有相对于这些不同层次或界面的不同内容。无论是某物B,还是情境C,都构成了某物A显现自身的限制与条件,这两者不仅参与了某物A的呈现,而且也影响着某物A显现的内容。换言之,事物的每一次视角主义下的显现,其实都是立足于某个立场与情境下的观看,立场与情境等深刻地影响了某物A的什么方面得以显现。而且,具有不同性格、气质、思想、境界、精神取向的某物B,即观看者个人,也是视角主义下事物显现的一个重要要素,因而存在与真理向着不同层次的人而有不同维度的显现,即便对同一个人,在其学习与成长过程的不同瞬间或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显现内容。故而《大宗师》强调,只有对真人而言,真知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真理不会对着某个对象自发地作为给定之物或完成之物而显现,真理的显现本身就内蕴着主体性的条件,即主体需要做出某种对应真理显现的自我转变,如果主体转变自己,升华自己,提升自己的存在层级,存在与真理的更高维度、更多侧面也就可能得以向他敞开。庄子不离人而言道,其所言之道,为具体到人格中的道。王邦雄注意到,“庄子从来没有孤离的、概念式的去讲一个‘道;他只讲天人、至人、神人、真人、圣人,所有的道,内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做一种全幅整体的展现,庄子的主要精神就在此。”王邦雄:《中国哲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2004年,第201页。又该书第202页:“把老子的‘道落在生命人格的修养中,所以庄子不讲道,他讲人,天人、至人、神人、真人、圣人。”在视角主义的预设下,重言本身意味着这样的叙述机制,通过不同的情境与不同的主体这双重的视角,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重言中将会显现不同的内容。故而重言,表面上是重复,当然确实是包含了重复,即被重言的对象在不同重言中依旧保持着同一性,但更重要的是显现的差异性,即每一次出现,由于立场或情境或主体改变了,故而同一个对象也就伴随着这一改变而显现出不同的内容。更进一步地说,随着言说对象与言说方式的转换,被重言的内容本身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不同的内容。而庄子正是通过这种不断迁流变化的语境与视角来层级性地呈现所要表述的真理的内容,事实上,这种随物流转而又不留滞于某个现成之物的言说方式,正是卮言的精髓。
二、鲲鹏三次重言的不同寓意
在字面上,我们可以发现《逍遥游》中鲲鹏有三次出场,每一次出场中,鲲鹏当然仍然是鲲鹏,但每一次出场被敞开的总是鲲鹏的不同层面。第一次出场以直接显现的方式进行,在这一次显现中,我们获得的信息有三:其一,鲲、鹏为二,一者为鱼,一者为鸟,但通过一个“化”字,两者连接为一,即作为“鱼-鸟”的“鲲-鹏”;其二,最深的深渊(北冥)与最高的高度(作为天池的南冥),通过“鲲-鹏”得以连接,分别成为“鲲-鹏”的出发点与目的地,因而在这里南冥与北冥是两个不同地方,其中只有南冥才是天池;其三,作为鱼的鲲与作为鸟的鹏,二者共有的特征是“大”,另一个隐含的特征是“化”。总体言之,“大而化之”是鲲鹏在第一次显现中呈现的品质,正是这一品质使得鲲与鹏被视为同一个自由主体的不同侧面,鲲-鹏则成为自由主体的隐喻或象征。换言之,正面出场的鲲-鹏从开篇就获得了作为自由主体之象征的肯定性意义。
通过“齐谐”的视角,鲲鹏第二次出场,而“齐谐”的视角内部又包含了另一个视角,即蜩鸠的视角,故而鲲鹏是在这双重的视角中出场的。在第二次出场时,通过齐谐之眼的叙述对象不仅仅是鹏的有待性,这与鲲鹏第一次出场作为自由的象征就有不同的蕴含,而且蜩鸠笑飞鹏的故事也来自齐谐。而在这之间却交织了庄子的正面评论,例如“齐谐者,谐之言曰”一句、“生物之以息相吹……而后乃今将图南”一段、“适莽苍者不亦悲乎”一段。刘凤苞正确地指出:“引《齐谐》至‘六月息句已住”,蜩鸠一段“此节又引《齐谐》之言”,参见刘凤苞著,方勇点校:《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年,第3~5页。同样,宣颖在蜩鸠一段注云:“此又齐谐之言也。引齐谐始毕。”参见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这意味着鲲鹏第二次通过蜩鸠之眼而出场,鲲鹏的有待性由此而被引出,并由此而有蜩鸠之笑。这一次出场值得注意的显现内容是:其一,有鹏而无鲲;其二,蜩、鸠之笑鹏;其三,通过这一嘲笑,第一次出场中的鲲鹏之“大”,由正面出场中承担的能“化”的肯定意义,在这里却转变成为一种“有待性”的限制。蜩鸠之眼中看不到沉潜的鲲在北冥的沉潜与修为,是其能大能化的条件,故而第二次出场有鹏而无鲲,其重点不再意味着鲲鹏作为自由的体现者,而是鲲鹏之有待,通过蜩鸠视域呈现的有待,与正面叙述中的自觉的修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鲲鹏第二次有鹏而无鲲的出场,鹏的来源以及何以飞翔的可能性即“化”在蜩鸠那里被隐没了,这本身恰恰呈现了蜩鸠的不“化”。而且,通过“齐谐”这一本身也颇具寓言意味的载体出场,交代着与第一次出场的正说不同,这一次叙述是谐说,在形式上不是一本正经的庄语,而是寓诙谐滑稽于其中的戏说。对齐谐的另一种理解是,齐谓齐物,谐为和谐,因而通过齐谐而出场的是,鲲鹏与蜩鸠虽然表面上大小不一,然而实质却是各适其性的“齐”与“谐”。如王雱《南华真经新传》云:“夫齐者,齐其所不齐;谐者,谐其所不谐……均为物则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极于齐谐也,故曰‘齐谐。”参见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4页。这里的谐说正好与第一次出场的正言不同,正言将鲲鹏视为自由的象征,谐语乃正言若反,恰恰揭示了鲲鹏有待的限制性。
通过“汤之问棘”的视角,鲲鹏第三次出场,这一视角还内嵌着斥鴳的视角。在这双重的视角下,显现的内容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其一,对于斥鴳而言,沉潜的鲲与飞翔的鹏为二,在这里并没有“化”所带来的鲲与鹏的连接;其二,鲲鹏的行程出现了与第一次出场完全不同的变化,虽然同样是从北冥到南冥,但由于北冥位于“穷发之北”,并且是天池,由此,对鹏的飞翔而言,成为从天池出发的行动,原先的目的地变成了出发点;其三,嘲讽鹏的斥鴳在这里出现了,但这一出现与蜩、鸠的出现由于其本身呈现的视角不同——一是对着汤之问棘出现,一是对着“齐谐”出现——而在文本中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与意义。
鲲鹏三次出场的上述差异,仍然是现象层面的,它需要被解释,不经过解释,就无法被问题化,无法被吾人进一步理解。而且,这些差异并不能被如下的观点所误导,即三次出场内容本来完全相同,只是由于修辞的缘故,出于行文简洁而或省或略,或简或繁,此中并无深意。这样的观点其实是一个逃离问题的解释,它已经是一种解释,一种回避问题化、逃离进一步反思的解释。吾人所需要的是面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更何况,古人行文,书法谨严,惜墨如金,“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是对《春秋》书法的总结,《春秋》寓价值褒贬于历史书写中,法度极严。杜预《春秋左传序》云:“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可以看作此一意思的发端,后来它渐渐凝练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但其最初出处,已经不得而知。 明代邱浚《大学衍义补》卷84、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卷260、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上陈大中丞请修明史纲目书》、清王嘉谟纂修《康熙徐沟县志》(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前附阎开泰《序》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一说法。就此而言,我们不能放过文本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必须将任何一个细节问题化,就好像面对一个“寓言十九”的文本,如果仅仅停留在文本字面的理解上,而不能将寓意的发掘进行到百分之九十的程度,那么,寓意也就会是隐藏的。对于习惯于命题性论述的现代读者而言,通常面对的问题不是诠释的过度,而是诠释之不及,即达不到其寓意与深度,甚至回避对寓言及其哲理之深层内涵的思考。
何以正面出场的鯤化鹏,在第二次、第三次出场中便不再出现,这就与第二次、第三次出场所基于的透视主义的特定视角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逍遥游》所给出的这两次显现的视角都是复调性的,皆是两种视角的交织重叠。就第二次出场而言,它立足的视角有两个:一是齐谐之眼,一是蜩鸠之眼。虽然,在这次出场过程中,引入了作者的评论,这些评论在通过“齐谐”所呈现的两大内容之间形成了逻辑上的连接:所引“齐谐”内容的第一部分,就是“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第二部分则是“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齐谐”的引入意味着对鲲鹏的述说,立足的是不同的视角,因而也就呈现了鲲鹏不同于前者的侧面。问题是“齐谐”之言的两个部分,它们之间的逻辑如何?这一问题正是要点所在。“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是鲲鹏的第二次出场所呈现的东西,而这一呈现是向着蜩鸠呈现的,因而被叙述的乃是蜩鸠之眼所见的鲲鹏。鲲、鹏被化约为鹏,而鲲在此缺席,完全是蜩、鸠在其自然主义视角中透视的结果。蜩鸠的飞行不需要工夫及其过程作为条件,更多地是出于本能,因而在沉潜(冥于北冥)中修养自己、由小而大的变化历程中的鲲鹏完全被忽略了,它所能看到的只是飞翔在天空的鹏,并把这种飞翔的条件视为类同于自己“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的飞行,这一飞行几乎完全立足于当下之本能,由此而自行在自己与鲲鹏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理解上的隔膜。更重要的是,在正面出场中被视为鲲鹏之“大而化之”能力之标志的翱翔九天,在蜩鸠这里被视为对条件的依赖,即有待性的限制性表现。由此,鲲鹏第二次出场时,其情境与意义和第一次相比,已经具有极大的不同。蜩鸠对鲲鹏的嘲讽在此显示了“下士”面对真理与大道时的特征,《庄子》与《老子》在思想上具有互文性,蜩鸠之笑之所以呈现蜩鸠的“下士”特征,是因为《老子》第41章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通过这种嘲弄,尽管鲲鹏的有待性这一侧面得以真实地呈现,但其在与蜩鸠的对比中仍然彰显了值得肯定的正面性。换言之,蜩鸠视角下的有待鲲鹏固然受制于蜩鸠的小知视野之限制,从而使得其之正面意义不得呈现,但这绝非意味着蜩鸠所见鲲鹏相对于鲲鹏所传达的隐喻性真理是不真实的幻象,相反,它仍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真理性,只是这一真理性不是全部,而是必须被看作视角性或层次性的真理,或者是鲲鹏所传达的隐喻性真理的特定层面或侧面,只不过不是全部,甚至不是真理的主体或核心而已。事实上,蜩鸠之眼透视下的“鲲鹏”(无鲲而有鹏)乃是对第一次出场的鲲鹏(鲲鹏的正面向度)之补充,将它们结合起来才更可看出,通过立足于本能的自然主义方式无法达到“大而化之”的自由主体的生成,自由主体只有在工夫的积累过程中才能展开自身。就此而言,第二次出场的鲲鹏虽然传达的是鲲鹏的限制,而不再是鲲鹏作为自由主体的象征,然而通过鲲鹏的限制给出的是自由主体的生成条件,鲲在北冥的沉潜相对于蜩鸠立足本能的飞行的对照,传达出鲲鹏之为鲲鹏,自由主体之为自由主体,并非是现成的,而是在工夫的历程中生成的,换言之,自由并非仅仅可以理解为先天赠予之物,而必须理解为自由主体通过工夫历程而得来的获得物,更确切地说,自由本身是获得性的,而不是给定性的。
鲲鹏的第三次出场以汤之问棘(夏革)为中介。汤问夏革从“古初(太初)有物乎”到“物无先后乎”,再到“上下八方有极尽乎”,夏革以不知答之,而后对言“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杨伯峻:《列子集释》卷5《篇汤问》,中华书局,2012年,第140~141页。通过汤之问棘的这一背景所欲呈现的是对南冥与北冥的理解,在这一背景下“穷发之北”,一个似乎无极无尽的“不毛之地”便成了后文“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寓言性表述,所谓“天池”不过意味着“造物者无物”之境,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天地之一气(未分化为六气),也就是未始有物、唯有有者的本原。鲲鹏从这样一个不是地方的地方开启其自由的历程,此与第一次、第二次出场的以天池为目的地的叙述截然不同,它意味着原来的目的地构成了新的出发点。鲲鹏这一次高起点的出场由古圣人汤为背景引出,在此,背景视域与隐喻内容之间形成了对应,也正是在古圣人那里,鲲鹏作为不同于蜩鸠所见的有待性才得以呈现。由此,斥鴳之笑,彰显的不再是鲲鹏通过与斥鴳对比而显现的大,而恰恰是鲲鹏作为自由象征的不充分性,这种不充分性只有通过汤这位圣王的视角才得以呈现。如果没有汤之问棘,而只是在蜩鸠与斥鴳的视角下,鲲鹏作为自由主体的象征性的不充分性就不可能呈现,因为汤作为古代的圣人,本身已经意味着自由的更高层次,只有在自由的更高层次,鲲鹏的自由的限制才可以给出。
三、鲲鹏的隐喻与自由主体的成长之路
鲲鹏的第三次出场,与此前的第一二次出场合在一起,构成了自由历程的完整步骤。从大地上北冥至于作为天命象征的南冥,抵达天命之后,南冥适成北冥,无一处不是天命之地,于是鲲鹏由第一次第二次出场的道路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相对)再继续上升,这个由天命高度而开始的上升之路反而与下降之路同一,它是从未始有物,即无走向有,走向和光同尘的有,走向让事物各正性命的生生之有,这一次的南冥之冥,是冥极于有,而北冥之冥则是冥极于无。因而鲲鹏完整的路线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北冥到南冥的上升之路,即从冥极于有到冥极于未始有物的天,这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历程;二是从北冥的未始有物之天到人与万物共居之有,这是从形而上出发到形而下的万有中去的道路,是下降之路,而这一下降是主体上升自己的新形式。如果说孔子由十有五而至于学到五十而知天命对应第一个阶段,那么从五十而知天命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对应的是第二个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历程,那么第二阶段便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历程。第三次出场中斥鴳之笑与第二次出场中蜩鸠之笑,便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如果说蜩鸠之笑是形而下视域内对形而上行程的嘲笑,是满足甚至沉沦于形而下的有限自足的表现;那么,斥鴳之笑从侧面传达的却是鲲鹏的局限性,鹏之图南,则南冥仍然是目的地,北冥则为其出发点,因而南冥与北冥之间的距离恰恰彰显的是鲲鹏存在境界的局限,虽然鲲鹏抵达了形而上高度,但却尚未完成第二个阶段,因而北冥与南冥为二,还不是南冥即是北冥,与此相应,鯤也就不是鹏,而是鲲是鲲、鹏归鹏。换言之,虽然鲲鹏走向了更高的高度,可以乘自己的性命之正,却不能御六气之辩,因而不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斥鴳之笑,就成为鲲鹏不能化之的表现,此与鲲鹏为二、南冥与北冥不能为一等所彰显的内涵是一致的。而鲲鹏在这里的有待性对应着的是后文列子的有待性,这一有待性不同于蜩鸠所见的有待性,即那种形而下的有待性;正如列子的有待性只有在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至人、神人、圣人的视域下或与后者对照的情况下才能显示,鲲鹏的由无而有的形上历程只有在作为古圣人的汤那里才能被彰显。
《逍遥游》中鲲鹏的三次重言,意味着鲲鹏分别在不同的视角下以不同方式出场,然而这三次出场的是否还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鲲鹏呢?这里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鲲鹏在不同的视角下对不同的观看者显现了不同的内容,但当我们这样表述的时候,我们假设了为现成性所规定的鲲鹏,即鲲鹏在这三次出场中的差异仅仅是对观看者而言的差异,而不是对鲲鹏自身的差异。但《逍遥游》中的鲲鹏却不是这样,不仅随着观看者的不同视角而有鲲鹏的不同显现,而且,鲲鹏在不同的视角下自身相对于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庄子用鲲化鹏点出了第一次出场中的变化,虽然化字没有出现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文本中,虽然从蜩鸠、斥鴳的眼光中看不到鲲鹏自身的变化,因为它们所见的鲲鹏犹如电影胶片上的一个片段,但当我们将这些片段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鲲鹏的变化。事实上,隐含在文本中更深层的叙述机制在于,正是鲲鹏自身的变化导致了不同视角的可能性,这些不同的视角并非平行的并列关系,而是由小而大、层层上达的递进关系:汤之作为古圣人的视角出现在最后,天池从目的地变成出发点的转换,都是随着鲲鹏自身的变化,即鲲鹏向着更高的可能性上升,而得以可能的。就此而言,鲲鹏的三次出场,实际上刻画了鲲鹏的蜕变与成长的历程,通过鲲鹏的蜕变与成长,《逍遥游》所昭示的是自由的历程。自由并非给定的东西,也并非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获得的东西,也不是步步接近但永远都不可能抵达的高悬着的理念,而是展开为一个发展着的历程,自由的主体便是在这个历程中蜕变、升华与成长。
不难看出,在《逍遥游》中,透视主义的叙述机制与隐喻的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间接叙述与直接叙述交织,正面出场与侧面出场叠加,使得《逍遥游》的表达机制充满了深刻的迷魅性质。《逍遥游》的真理不是在字面上现成性地给予,而是以读者必须真正地展开思想为条件,对《逍遥游》本身的阅读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字面性意义就可一次性获得其所欲传达的内容,而必须穿透字面内涵,辨识隐含在字面背后的道理,读者本身的从小知到大知的视野转化以及下学而上达的自我提升,对于《逍遥游》的阅读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的主体性条件,也只有我们站在更高层次,才能看到更高层次的道理。透视主义叙述的前提,实际上与古典哲人的如下体知有关:真理的呈现离不开主体的条件,主体层次的高低决定了真理呈现的层级。而小知之人正是以其小知的视域体验真理,真理对它所呈现的内容虽然是真理自身的有在于是者,但却同时也遮蔽了真理的其他方面甚至更主要方面。因而必须从小知进于大知,获取更大的视域,才能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接纳真理的自身呈现。由于人的存在层级不同,因而同一事物在不同个人那里有着不同的显现,最高意义的大知之人,并不自用其知,而是向着各种视域之知敞开自身,接纳它们,从而在间接性的前提下形成关于真理的最大限度的相对完全体验,《孟子》所谓集大成、《齐物论》所谓的“参万物而一成纯”、《荀子·解蔽》所谓“兼陈万物而中县衡”、方以智所谓“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都意在描述这种相对完全的真理体验。《逍遥游》寓言之中又有寓言,此寓言之中又内蕴彼寓言,在寓言的连续重言中,构筑了一个真理藉由间接显示而综观的大知性真理。而这种层级性的大知要求对不同层次的知行主体予以不同层级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在《庄子》中,尤其是在《内篇》中,越是重要之人越是以间接方式出场的原因;与此相应,越是重要的真理,越是以多重间接性的迂回方式呈现出来。正是这样的在意蕴上具有“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庄子·天下篇》)意义的文本,才要求以自我参与、自我转化和自我提升的方式作为阅读它的条件,因为这样的阅读方式本身必须成为读者成长的方式。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