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变迁史
2018-12-19顾玉雪
顾玉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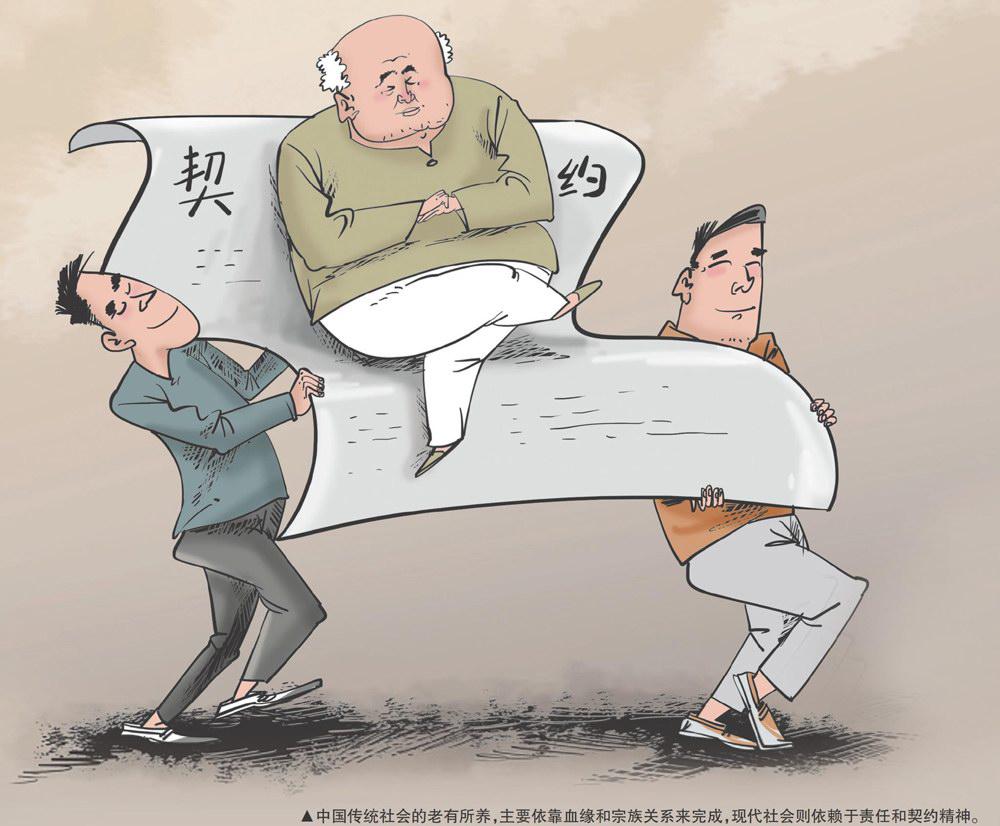


老有所养,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目标。《礼记》描摹的理想社会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孟子则希望看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从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年代,到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再到迈向老龄化社会之时,中国的养老制度一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修订,经过一次次艰难博弈。
血缘、宗族和国家福利:“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古代启示录
中国传统社会的老有所养,主要依靠血缘和宗族关系来完成,现代社会则依赖于责任和契约精神。
为支持家庭养老,古代许多朝代普遍施行了“侍丁”与“权留养亲”两项制度。“侍丁”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礼记》的记载,“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是指政府对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减免其税收与徭役。明清也一样,如《清律例》规定,“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
“存留养亲”则是中华法系中一项比较特别的缓刑制度:犯罪之人(重罪除外),如果父母年迈、无人照料,政府可不立即执行判决,允许犯罪人回家赡养父母,候赡养结束后再执行判决。这一制度正式形成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之后唐宋明清,历代相沿。
尽管“存留养亲”是一项迄今已消失多时的古老法律制度,但对于今人并非没有可借鉴之处。
按中国现行缓刑制度,法庭在决定缓刑的适用时,一般只是考虑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因此有学者提出,“可以将犯罪人家庭情况作为缓刑适用条件的考虑因素。由犯罪人所赡养、抚养和扶养的直系亲人,若确实有待照顾且非犯罪人再无可托付的情况,应被纳入缓刑适用的考虑因素。”
家庭养老模式当然也有着内在的缺陷——那就是,家庭贫寒的老人及孤寡老人由谁来养,将成一大问题。不过,古代传统社会对此也并非毫无办法,主流的家庭养老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辅助性的宗族养老系统。
宗族救济古已有之,到了宋朝,宗族福利开始制度化,那就是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义庄就如一个公益基金,定期向族人或族中贫困、孤寡人口发放钱米:每一位五岁以上的族人,都可以从范氏义庄领米,每口每日一升。族中若有老人去世,也可以从义庄申领到15贯至25贯钱的丧葬费。
范氏义庄创立后,宋朝及后世的士绅纷纷效仿,成立义庄赡养族人。有了义庄救济的机制,族内的贫寒与孤寡老人便得以“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不致沦落到老无所依的凄凉境地。
不过,宗族共同体的救济毕竟是基于血缘,族外人无法获得义庄的福利。那么古代有没有超越血缘关系的养老机制呢?
南宋《夷坚志》中记载,至迟在南宋时期已出现了民间慈善人士创办的公益性孤老院。 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更为发达,其中公益性养老机构通常叫做“普济堂”,类似于今天的福利院,以收养“老疾无依之人”为主。如清代康熙四十五年,“京城广宁门外,士民公建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司其事者,殊為可嘉”。
在家庭养老、宗族养老与公益养老覆盖不到的地方,还有福利性质的国家养老。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传统社会已经出现了养老福利。当时刚传入中国未久的佛教带来了“布施”的观念,信奉佛教的梁武帝在其都城建康(今南京)建立“孤独园”,收养孤儿和贫困孤寡老人。其后唐王朝则在京师设立“悲田院”收容乞丐、孤老。
宋朝时候,跟“孤独园”“悲田院”功能类似的福利养老机构已经遍布天下,为全国贫困、孤寡老人提供“老有成养”的保障成为常设的国家制度。后来的明朝与清朝,基本上都保留了宋代的居养院建制。
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养老系统是多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主流的家庭养老;第二个层次是辅助性的宗族养老;第三个层次是民间的慈善养老;第四个层次是国家的福利养老。
安身与立命:
养老变迁与国家角色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质变,依靠血缘和宗族构建的社会关系和安全网络,很大程度上被现代政治和意识形态取代。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养老制度的起源是在东北。1948年,在哈尔滨等地方试验的基础上,根据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发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从铁路、邮电、矿山、军工、纺织等七大行业开始,劳动保险制度逐步在解放区推行。
“劳动保险”这个词,是时任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创造”的,后来在中国取代了世界通用的“社会保险”而被沿袭下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出台共同纲领,“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被写入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便由时任中央劳动部长的李立三牵头,展开了《劳动保险条例》的起草,到1951年初时由政务院(国务院前身)颁布,这也是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出台之前的六十年里,中国唯一的社会保障法规。
建国初期,公务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除了配发衣服、伙食,简单的生活用品外,每月发6元钱津贴。当时的农村,养老虽有集体之名,但核心其实仍在家庭。集体经济时代,一方面,国家设立了教养院、敬老院,初步建立了“五保”(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供养的福利制度,但面对整个社会庞大的养老需求,这些举措仍是杯水车薪。
已被世人淡忘的是,早在那时中央就在“考虑”如何将两个群体包括养老在内的保障体系“并轨”的问题。
中国自1958年起便实行干部和工人统一的退休、退职制度,事业单位和企业的退休制度并无本质差异。两者均实行单位统筹下的现收现付制,由单位直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费用,退休后的待遇差别也微乎其微。变化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此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制度渐行渐远,如今已经几起几落。
1986年,国务院下发多个文件,改革劳动制度,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民间被叫做“打破铁饭碗”。
借此,在新中国历史上,个人首次成了养老保险的缴费者之一,养老制度开始朝由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承担的方向前进。
中国养老保障政策的变迁历史十分清晰地展现了“国家”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扮演了一个全能的、父爱式的社会保护角色;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收缩,个人和社会的责任开始凸显;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社会建设时期之后,国家开始重新回归,积极干预社会福利。
新时代的养老实验
2017年年初,杭州余杭区的张浩阿姨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抱团养老实践——她致电当地报社,自发在社会层面征集,要在杭州131平方米公寓里探索抱团养老。引发应征热潮之后,宣告“失败”,两位室友陆续搬离她家。
之后,瓶窑镇的朱荣林和王桂芬找张阿姨取完经“干了一票更大的”,招募了11位陌生老人一起住进了自家别墅,开始了一场对抗晚年孤独的集体实验。半年之后,入住7户共13位老人,其间有小幅人员流动。
所有人都明白,这次抱团养老,放之于老年岁月长河之中,只是一个“不能一步到位的驿站”。但我们却可从中发现当下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养老需求与真切心境。
这种经济乃至生活理念“共享”的养老实验,已经并不鲜见。
近年来,日本开始尝试研发护理机器人以替代人工。2018年,北海道的道央、道北、道东、道南四个地区开始全面推广护理机器人,试图寻找出路。
借鉴发达国家解决养老问题之道,养老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組织和个体共同的努力——人们发明一系列办法,从资金、医疗到养老机构,想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美好些。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养老意识的变迁,即从依靠个人到依靠公共;以近30年来看,对公共的依靠也在逐渐转换方式,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开始不断出现。
2018年8月10日,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由直辖市试点推广到全国。顾名思义,这是一款将住房抵押给保险公司以换取养老金的保险产品。
在此之前,幸福人寿作为全国推广前唯一一家真正开展了“以房养老”业务的保险公司,参保者仅有寥寥98户家庭、139位老人。
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自有其局限性,可也有其合理性。面对不确定性时,血缘是人们最后的依靠。然而,在曾经长期铁板一块的人口政策下,“儿子”愈少,“老子”愈多。两拳难敌四手,血缘与家庭甚至有可能成为养老的拖累。
业内人士普遍将“以房养老”商业上的“低存在感”归咎于目前产品本身不完善、市场有待教育及中国房价波动。但这种自觉自愿的保险产品,也引起诸多争议。拒绝或抵抗“连根拔起”的,不仅是老人,更是一个又一个中国家庭。
不独以房养老,甚至不独商业保险,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对任何养老方案及资源的渴求,宛如黑洞。
加拿大的养老制度,可简要概括为“社会福利养老为主、互助养老和商业化养老为辅”。中国未来应该也是这个趋势,但起步晚、基础差,养老制度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局限于养老本身,而必然与社会方方面面相结合、牵一发而动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