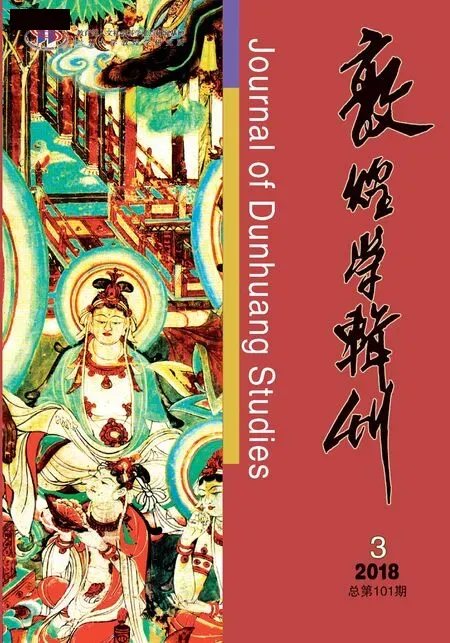敦煌变文疑难字词辨释
2018-12-18张小艳
张小艳 冯 豆
(复旦大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自上世纪初发现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孜孜努力,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注举其荦荦大者即有: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简称《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六版增订本后收入《蒋礼鸿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项楚《敦煌变文选注》(简称《选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本文据后者征引。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编《敦煌变文集补编》(简称《补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2016年第2版,本文据后者征引。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简称《新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简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但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前人所据多为不清晰的缩微胶卷或黑白图版,致使以往的校录本中仍留有一些疑难之处。近年来,藉助于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公布的彩色照片,笔者将前人的整理本与相应的彩色照片对读的过程中,对某些不易理解的字词产生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兹不揣謭陋,择取其中数条进行辨释,敬请读者指正。
一、汝
S.2204《董永变文》:“郎君如今行孝仪(义),见君行孝感天堂。数内一人归下界,暂到浊恶至他乡。帝释宫中亲处分,便遣汝等共田常(填偿)。……董仲长年到七岁,街头由喜(游戏)道边旁。小儿行留被毁骂,尽道董仲没阿娘。遂走家中报慈父:‘汝等因何没阿娘?’”(《英藏》4/41A—B)[注]“《英藏》4/41A-B”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简称《英藏》,共14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第4册41页上栏至下栏,下仿此。本文引用的其他敦煌图录版本信息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简称《法藏》,共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简称《俄藏》,共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称《国藏》,14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日]磯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蔵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书集成》(简称《中村》,共3册),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ァ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总括班,2005年;财团法人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集《敦煌秘笈》(简称《秘笈》,共9册),大阪: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団影印杏雨书屋,2009-2013年。
按:“汝”,《变文集》(111-112)、《新书》(927-928)照录,《选注》(301、308)前字照录,后字下注:“汝等”句,谓汝等因何使我没阿娘。《敦煌变文集校议》认为:“汝等”当校作“奴等”,“奴”为董仲自呼[注]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简称《校议》),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91页。。《校注》(174-175、178)径录作“奴”,注云:奴,原录作“汝”,此处为天女所述,“汝”当作“奴”,为天女自称;下文董仲所问“奴等因何没阿娘”,“奴”原卷亦作“汝”。《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一卷两句中的“汝”均照录,出校称《校注》改作“奴”[注]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简称《释录》)卷11,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录文见第303、304页,校记见第307页[一六][二四]。。马国强指出:《校议》《选注》所解可商。“汝等”句并非董仲询问其父之语,“汝等”是董永对小辈的称号,犹言“汝”,“等”字不为义,属人称代词单复数同一形式。前文“便遣汝等”中“汝等”亦表单数,都是父母辈对子女的称呼。“汝等因何”句是董永听了儿子诉说后,自问自答、以问启答的过渡语,即:“你为什么没有娘呢?”接着即追述往事,告诉其母的来去踪迹[注]马国强《敦煌变文校注商榷》,《周口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第69-70页;同作者《敦煌变文词语校释》,《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18页。二文观点大抵相同,后文补充了例证,此据后者征引。。
综观各家之说,《选注》所解与董仲作为儿子向父亲询问的口吻不合。《校议》《校注》读“汝”为“奴”,表示女子、小儿的自称,切于文意,但未举出“汝”借作“奴”的实例[注]“汝”(日纽语韵)与“奴”(泥纽模韵),二字韵相近而声略远。P.2187《破魔变》“库内绫罗,任奴糚束”(《法藏》8/179)的“奴”,《校注》(547)疑当读作“汝”,此解于文意较切,但敦煌文献中“奴”“汝”通借颇为罕见,远不及“汝”“儿”通用习见。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才提出“汝”当读为“儿”。,难以令人信服。马说认为“等”字不为义,“汝等”表单数,可从;但将董仲所问“汝等”句视为董永以问启答的过渡语,却与原卷的行文脉络相忤,恐不可信。窃以为上引两句中“汝”皆当读为“儿”,“儿等”就是“儿”,分别用为仙女与小儿董仲的自称。
读音上,“汝”《广韵》音人渚切,为日纽语韵遇摄;“儿”音汝移切,属日纽支韵止摄,二字声同韵别,但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遇”“止”二摄读音混同无别[注]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收入作者《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4页。,故敦煌文献中“汝”“儿”通借之例较为常见。如S.1477《祭驴文》:“教汝托生之处,凡有数般:莫生官人家,轭驮入长安……莫生和尚家,道汝罪弥天;愿汝生于田舍汝(儿)家,且得共男女一般看。”(《英藏》3/79B)S.1392《孔子项托相问书》:“吾以(与)儿(汝)捨(—掘)却高山,塞却江海。”(《英藏》3/6A)是其例。此外,敦煌写本中还有“汝”与“饵”、“汝”与“尔”、“儿”与“如”、“如”与“儿”通借的例子,它们的语音关系跟“汝”与“儿”一样,均属声母相同,韵母为遇、止二摄混同者。如S.4629《文样·患文》:“时则有坐(座)前厶公奉为小娘染患,经今数旬,药汝(饵)频施,不蒙(减)退。”(《英藏》6/178A)P.2187《破魔变》:“魔王当汝(尔)之时,道河(何)言语?”(《法藏》8/177)S.2922《韩朋赋》:“使者答曰:‘我是宋王使来,共朋同有(友)。朋为公(功)曹,我为主薄(簿)。朋友(有)松(私)书,寄回新妇。’阿婆回语新妇:‘儿(如)客此言,朋今事(仕)官(宦)且得胜常。’”(《英藏》4/256B)后例中“儿”,异本P.2653(《法藏》17/109B)作“如”。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如(儿)今痛切更无方,业报不容相替伐(代)。”(《英藏》4/121B)“如”字异本BD.3789(《国藏》52/385A)作“儿”。皆其例。
词义上,“儿”作为女子自称,无论敦煌文献还是传世典籍均多有其例。如S.1441V《云謡集·破阵子》:“寂寞长垂珠泪,焚香祷尽灵神。应是潇湘红粉継(系),不念当初罗帐思(恩)。抛儿虚度春。”(《英藏》3/49)P.5039《孟姜女变文》:“姜女悲啼,向前借问:‘如许髑髅,佳(家)俱何郡?因取夫回,为君传信。君若有神,儿当接引。’”(《法藏》34/156-157)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又有妇人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注][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5页。本文援引传世文献用例,首次出现详注其出处,再次引用则于引文后括注其页码。首例“儿”为家中思念夫君的女子自称;中例“儿”为孟姜女自称;末例一、三句中“儿”表雄性;二、四句中“儿”为告状妇人自称。至于董仲询问自己的父亲而自称“儿”,则属合情合理,无烦举证。
若将“儿”此义施于上引“汝等”两句,前句为仙女向董永转述帝释之语:“便派儿来与你一起偿还债务”;后句系董仲向父亲董永询问的话:“儿为何没有阿娘”,文意顺适无碍。可见,校“汝”作“儿”,不仅切于文意,也合于当时西北方音的用字习惯。
二、何碓无觜 孤碓无觜




表1:“何碓无觜”“孤碓无觜”中各本相关字形比对表[注]表中卷号后括注的文字,系《变文集》所据原卷与校本序码的标注,以便互参。



回到上文所引《相问书》中那段文字,可知“何雄无雌”“孤雄无雌”两句,出现在孔子与项托问答的语境中。从内容看,孔子所问大多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具体而习见现象的特例,所涉物象的关系都非常紧密,如山与石、水与鱼、门与关、车与轮、牛与犊、马与驹、刀与环、火与烟、树与枝等。其中体现的特色及所涉物象的密切关系,可从“何门无关”“空门无关”中窥豹一斑:“门”为生活中常见之物,“关”是“门”的必要构件。按理,凡“门”皆有“关”,无“关”则属特例,即唯有发生特殊情况时才会出现“无关”的特例。而项托回答的“空门”恰好就属于这种特殊情况,“空”者,无也,“空门”指没有门而仅存门框的情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无关”的特例。
以此来衡量“何雄无雌”“孤雄无雌”两句中所涉“碓/雄”与“觜/雌”这两组异文,可以看出:“碓、觜”与“门、关”之间的类比关系更近。首先,“碓、觜”属日常生活中习见而具体的物事;其次,“碓”与“觜”关系密切,“觜”即“碓觜”,是“碓”的必要构件(详下文),无“觜”之“碓”属特例。相反,“雄、雌”与“门、关”之间却不具备这种相似的类比关系。首先,“雄、雌”属抽象概念,非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具体物象,用在孔子与项托之间的问答场合不合适;其次,“雄”与“雌”的关系并不紧密,它们只是两种独立的性别特征,“雌”并非“雄”存在的必要条件,“无雌”于“雄”属正常现象,“雌”“雄”同体才真是特例。因此,从上下文的语境看,“碓、觜”较“雄、雌”更切于文意。
就“碓、觜”的词义来看,“碓”是一种舂米的用具,简式的碓仅由杵、臼构成,因以手执杵而舂,或称手碓;复式的碓则用支架撑起一根木杠,一端装石头或木椎(有的还在木椎下端套有铁质椎头),用脚踏另一端,连续起落,脱去下面臼中谷粒的皮(参图1、2)[注]“碓”的释义参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7卷“碓”条,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1056页。“踏碓图1”参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刘玉权撰“踏碓图”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踏碓图2”参[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卷9农器图谱集之九“图125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07页。,因以脚踏木杠而舂,俗称踏碓。《玉篇·石部》:“碓,所以舂也。”[注][南朝梁]顾野王著,[宋]陈彭年等增订《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5页。《广韵·队韵》:“碓,杵臼。”[注][宋]陈彭年等编撰,周祖谟校勘《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页。“觜”本指鸟嘴,《广韵·纸韵》:“觜,喙也。”(245)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角部》:“觜犹,锐词也,毛角锐。凡羽族之咮锐,故鸟咮曰觜。”[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觜”亦可指尖如鸟嘴之物,如舂碓的杵,其末梢略尖,形如鸟嘴,故称“碓觜”,也写作“碓嘴”,“嘴”为“觜”的后起增旁字。如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宋令文者,有神力……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得四十字诗。”[注][唐]张鷟著,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5页。P.3234V《净土寺西仓司麦豆布绁粟油等破历·油破》:“油三胜,梁内买碓觜用。”(《法藏》22/244B)宋释惟一《环溪惟一禅师语录》卷下《禅人请赞》:“赤土画簸箕,冬瓜作碓觜。”[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64页。明陈铎《嘲人盖屋》套曲:“椽子是累年积下锄头柄,地磉是到处搬来碓嘴石。”[注]谢伯阳编《全明散曲》(增补版),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第657页。汪曾祺《冬天》:“踩碓很好玩,用脚一踏,吱扭一声,碓嘴扬了起来,嘭的一声,落在碓窝里。”[注]汪曾祺《人间草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相关的歇后语有:“碓嘴舂碓窝——准着”[注]白维国主编《现代汉语句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由此可知:简式的碓由杵、臼合成,“碓觜”指碓杵末端略尖的部分;复式的碓由支架、碓杠、碓觜和臼组成,“碓觜”指碓杠末端装插的石头或木椎,故又称“碓觜石”或“碓头”。
明白了“碓”“觜”之义及其内在关系后,再来看“孤碓无觜”,就不难理解其中的意藴了。“孤”者,独也,碓杠一般总是与碓觜相配,“孤碓”指仅存碓杠而无碓觜的碓。上文所举《朝野佥载》例中,富有神力的宋令文以五指“撮”着碓觜写字时剩下的碓,应该就是项托所说仅存碓杠的“孤碓”[注]文献中也有“孤碓”之例,如宋刘子翚《屏山集》(明刻本)卷十二《谕俗十二首》之十:“寒堤孤碓在,废圃鸣泉出。”(叶五)元贡奎《云林集》(明弘治三年范吉刻本)卷四《居庸关蚤行》:“涧深孤碓响,山暗数灯明。”(叶十二)二诗中“孤碓”均用以突显环境、气氛之幽静、荒凉。前例中“孤碓”既可能指独立而完整的一座碓,也可能指没有碓觜仅存碓臼的废弃不用的碓;后例中“孤碓”应指山中独立的一座水碓。。以此所解“碓”“觜”之义,还原到“何碓无觜”“孤碓无觜”的语境,文意顺适无碍。孔子问:“什么碓没有碓觜?”项托答:“(仅存碓杠的)孤碓没有碓觜。”唯有如此直白显豁的回答,方才切合项托的孩童身份。相反,若据异本作“何雄无雌”“孤雄无雌”,不仅与上下文并列的语句格格不入,而且语义表达也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很难想象,这样的语句会出现在孔子与项托问答的场合。
由此看来,在“碓/雄”与“觜/雌”这两组异文中,不论从上下文语境显示的文意还是文字本身的词义来看,均当以前者为是。异本作“雄”者,当是“碓”之形近讹误;作“雌”者,应是“碓”讹作“雄”后,抄手觉得“觜”于义不谐而作出的臆改(即为使它与“雄”在文意上相对,而将“觜”改作“雌”)。就像以往的整理本将“碓”误认作“雄”后,不顾原卷作“觜”,而据异本改作“雌”一样。总之,以往整理本中有关“何雄无雌”“孤雄无雌”两句的校录,均当作“何碓无觜”“孤碓无觜”。唯其如此,方合于文意,才能真切地揭示出孔子所问与项托所答的神韵与智慧。

图1 榆林窟西夏第3窟踏碓图(刘玉权绘)

图2 元王祯《农书》卷九所附踏碓图
P.3883《孔子项托相问书》:“夫子曰:‘汝知屋上生松,户前生苇,床上生蒲,犬吠其主,妇坐使姑,鸡化为雉,狗化为狐,是何也?’小儿答曰:‘屋上生松者,是其椽;户前生苇者,是其箔;床上生蒲者,是其席;犬吠其主,为傍有客;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鸡化为雉,在山泽也;狗化为狐,在丘陵也。’”(《法藏》29/84B)
按:“初来花下”,P.3833(《法藏》28/287B)、P.3255(《法藏》22/314B)、S.5529+Дх.1356+Дх.2451(《俄藏》8/113B)、S.395(《英藏》1/181B)等4卷同;S.1392(《英藏》3/6A)作“初来花夏”;S.5674(《英藏》9/63A)作“初来化下”;P.3754V(《法藏》27/351A)作“物来化下”。比较可知:“夏”为“下”之音借字;“化”系“花”之省借;“物”是“初”之俗写形讹。“初来花下”,作为变文校理中的疑难词句,向来备受关注。综观学界相关的校释意见,主要有如下两种:
1.结婚,或新妇刚过门。张鸿勋于“花下”注云:“指结婚。”[注]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8页。《选注》(480)将“初来花下”释为:“指新妇刚刚过门。”刘瑞明指出:张鸿勋、项楚之注不误。“花下”当作“他下”,意为他家。“花”字下部的“化”是“他”字成误,又误加草字头。敦煌文书中,“某某下”的说法与“某某家”相同,如S.525《搜神记》:“父母叹曰:‘我儿未得好学。’遂遣向定州博士边孝先生下入学。”(《英藏》2/3A)即“边先生家之意”,异本中村139号作“边先生处学”(《中村》中/335),下、家、处,三者义同。唐王建《新嫁娘词三首》之三:“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注][唐]王建撰,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08页。前二日便是姑作饭,新妇坐吃现成。清孙枝蔚《新嫁娘》诗之六:“从今愁妇职,人莫羡三朝。”[注][清]孙枝蔚《潜堂前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下栏。即三朝之后勿复“妇坐使姑”了[注]刘瑞明《〈敦煌变文校注〉刍议》,《文教资料》1992年第2期,第88页;类似的观点亦见于同作者《〈孔子项托相问书〉再校议》,《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18-19页。后文论证更周备,本文据以征引。上文所引《搜神记》及《新嫁娘》的两首诗,皆源自刘之后文,笔者复核标注出处。。
2.用佛典,指妇女生小孩。郭在贻、黄征、张涌泉认为:“初来花下”乃俗文学作品暗用净饭王夫人临产来到无忧花树之典,其义为“生小孩”。“妇坐使姑”中“妇”是新妇,“姑”是婆婆。媳妇使唤婆婆,只有在生小孩时才有可能,故云“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注]郭在贻、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释词》,《语言研究》1989年第1期,第70-71页;类似的观点又见于同作者《〈敦煌变文集新书〉校议(下)》,《文献》1989年第3期,第211-212页。本文在参考前文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后者征引。。后《校注》(363)明确释为“妇女做产”。吴浩军以为:据旧时生活状况及习俗,媳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唤婆婆。这种特殊情况除了新妇刚过门外,还有生孩子、坐月子时。若作此解,则为暗用佛典摩耶夫人于花下攀枝而生悉达太子的故事。推究事理,后说更为妥帖[注]吴浩军《敦煌赋三篇注释商订》,载氏著《酒泉地域文化丛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由上可知,学界对“初来花下”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指新妇结婚、刚过门时;二是用摩耶夫人于无忧花树下攀枝生子之典,表示女人做产、生孩子。尤以后说影响较大,或以此为据探讨敦煌变文词汇的“造词法”,认为“花下”乃化用“净饭王夫人临产时曾到无忧花树下”的佛典故事,这里特指“临产分娩”[注]陈明娥《敦煌变文词汇计量研究》“变文词汇的造词法考察”节,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然上引二说对“花”的解释及校读,均嫌推测成分过重,难以令人信服。“花”究竟当如何校读,成了准确理解这句话的一大症结。
2009年10月,李盛铎旧藏后为日本杏雨书屋收藏的羽33号《相问书》残卷,正式刊载于《敦煌秘笈》第1册231页,使我们能一睹其真容。张涌泉指出:该卷可与Дх.2352缀合。其中异文亦有可为校勘之资者。如“何谓‘初来花下’?众说纷纭,乃本篇校勘的一大难点。查本卷,‘花’字作‘往’,或许能为我们校读此句提供新的线索”。[注]张涌泉《新见敦煌变文写本叙录》,《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34页;随文附有缀合图,可参。所言诚是!此则新异文的出现,确为我们校读“花”字指示了新的方向。


由此看来,羽33号《相问书》中“初来往下”当作“初来家下”,则项托所答应为“妇坐使姑,初来家下也”,其句意谓新妇坐着使唤婆婆,是因为她初来家中。文意顺适无碍。以此反观上揭写本中的“初来花下”,可知“花”应为“家”之音借。“花”《广韵》音呼瓜切,为晓纽麻韵,与“家”(见纽麻韵)声近(晓、见分属喉、牙音)韵同,应可通借。如“贺”从“加”声、“霞”“遐”“暇”“瑕”“虾”诸字从“叚(假之初文)”声等,均属喉、牙音相谐之例。是知上述有关“初来花下”的两种解说中,自当以“新妇刚过门”之说最为恰切,然刘瑞明谓“花”系“他”之误,“花下”当作“他家”则属猜测之词,但他援引文献论证“下”与家、处义同及列举新妇初来三朝可坐享现成的文例,均为我们的校读提供了文意理解的支持;而解作“妇人做产、生小孩”之说,本据“花下”立论,而今已知“花”为“家”之借,则其说犹无根之木,不攻自破。
四、博
龙谷大学藏《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大臣见大王别要苦楚,遂奏云:‘将耶输母子卧在床上,向下着火,应是(时)博煞。’”(《补编》212A)
按:“博”,《补编》(98)校作“缚”,《新书》(545)、《校注》(473)从之。例中只说将耶输母子卧在床上,下面燃火,即可将其“博”杀,并未提及绑缚之事;且若仅是“缚”,恐怕也不可能即刻致死。故以往整理本将“博”校作“缚”,于义不谐,于理难通。那么,其中的“博”当校作什么字呢?
萧旭以“博”当读“爆”,二字同音通借[注]萧旭《群书校补(续)》第六册《敦煌文献校补》,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4年,第1340-1341页。下引《集韵》《龙龛手镜》《齐民要术》的书证、文例均引自萧文,笔者重新复核标注出处。。“爆”或换旁作“煿”,《集韵·铎韵》:“爆,火干也……或作煿。”[注][宋]丁度等编《集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影印《宋刻集韵》,第208页下栏。《龙龛手镜·火部》:“煿,补各反,迫于火也,与爆亦同,出《川韵》。”[注][辽]释行均编《龙龛手镜》,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5页。《齐民要术·作酢》:“有薄饼缘诸面饼,但是烧煿者,皆得投之。”[注][北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从所引文献看,其说可从。值得注意的是,“爆/煿”此义在唐宋文献中常用“迫”来表示。
读音上,变文中“博”与“爆/煿”均属帮纽铎韵,“迫”为帮纽陌韵,“迫”与之声近义通。如S.5437《汉将王陵变》:“将士行莫营数里,在后唯闻相煞声。”(《英藏》7/66B)前句异本P.3627作“二将蓦营行数里”(《法藏》26/138B)。其中“莫”为“蓦”之借字,“莫”为铎韵,“蓦”属陌韵,即为铎、陌二韵通借之例。
词义上,“迫”本指逼近,用在有“火”的语境,即可表示用火气熏炙、烘烤,其义犹“煏”。《玉篇·火部》:“煏,火干也。”[注][南朝梁]顾野王著,[宋]陈彭年等增订《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9页下栏。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伐木》:“凡非时之木,水沤一月,或火煏取干,虫则不生。”缪启愉校释:煏,指“逼近火旁烘炙”(379—380)。“迫”这种用法习见于唐宋典籍,如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八“八角玉升”条(出《逢夏记》):“宣帝时,西夷怛陀国贡八角玉升,夏以水浇之则无暑,冬以火迫之无寒,异事甚众。”[注][唐]冯贽《云仙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页。《云笈七签》卷六九金丹部引《英砂诀》:“又文火养一七日,候干,紧固济,武火迫之一日,其砂涌出于宝锅之上,而红黄映彻,光耀不可言。”[注][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535页。宋王谠《唐语林》卷六补遗:“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注][宋]王谠,周勋初点校《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6页。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图画碑帖:“玉炉一枚,其文云龙,盖思陵旧物也。惜乎经火迫坏了。”[注][宋]周密《志雅堂杂钞》,清粤雅堂丛书本,叶六。以上诸例中“迫”与“煏”及萧氏所论“爆/煿”的音义皆近。
将“迫”此义施于上引“应是(时)博煞”句,可知大臣所奏“苦楚”,原来是用火将耶输母子活活熏烤致死,可谓残忍之极。由此看来,在实际使用中,“爆/煿”或借“博”“迫”等常用字来表示“火干”义。
五、沿寮

读音上,“沿”《广韵》音与专切,为以纽仙韵;“员”音王权切,属云纽仙韵,二字声近韵同。据邵荣芬研究,唐五代西北方言“云”“以”二纽不分[注]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氏著《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第218页。。也就是说,“员”“沿”二字的读音在当时混同无别。且敦煌文献中即有它们展转相通之例。如P.3128V《解座文》:“初定之时无衫袴,大归娘子没沿房。”(《法藏》22/353A)P.2564《齖齒可新妇文》:“且与缘房衣物,更别造一床毡被。乞求趁却,愿更莫逢相值。”(《法藏》16/14B)前例中“沿”为“缘”的同音借字,“沿房”即“缘房”,指嫁妆、妆奁。“缘”又可用为“圆”的音近借字,如P.3270《儿郎伟》:“兄供(恭)弟顺,姑嫂相爱相连(怜)。男女敬重,世代父子团缘。”(《法藏》22/333A)句中“缘”显为“圆”之借,而“员”乃“圆”之古字,既然“圆”与“缘”、“缘”与“沿”可以相通,那么“员”自然亦能跟“沿”通用。
词义上,“员寮”即“员僚”,泛指官吏,习见于唐五代文献。如BD3024《八相变》:“是时太子车驾及诸侍从员寮,才出南门,忽尔行次,不逢别事,见一老人:发白如霜,鬓毛似雪。”(《国藏》41/127)P.2652V《诸杂谢贺》中有一首题为“自身得官谢诸员(寮)”(《法藏》17/106B)。《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员僚,但驰走从行而已,忽与介胄奋命之士,俱号功臣,伏恐武臣愤惋。”[注][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97页。皆其例。故上引例中“(沿)寮”当作“员僚”,指官吏。
六、复制
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罗卜自从父母没,礼垃(泣)三周复制毕。”(《英藏》4/116B)
按:“复制”,《变文集》(714)、《新书》(685)、《释录》卷十三(2)均照录,《选注》(850)释云:“指复墓之礼。亦云‘覆墓’。”《校注》(1040)从之。曾良指出:《选注》所解疑未确。“覆墓”是在“殡后三日”,而变文中是“礼泣三周复制毕”,“三周”即三年,时间不吻合,“复制”应非覆墓。“复”有除义,“复制”指除丧制,父母之丧,三年而毕[注]曾良《敦煌文献语词例释》,《文献》1996年第3期,第170-171页。。曾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复”恐不当以“除”义解之。其句谓罗卜父母去世后,他依礼制守丧满三年。窃以为“复”当读为“服”,“复制”即“服制”,指服丧之制。
读音上,《广韵》“复”“服”皆音房六切,二字音同,可以通借。且敦煌文献中即有“复”借作“服”的实例。如P.3833《王梵志诗》:“古来复丹石,相次入黄泉。”(《法藏》28/282A)BD62V《患文》:“唯公乃四大假合,尪疾缠身;百节酸疼,六情忄尧忽(恍惚)。虽复人间药饵,世上医王、诸佛如来为种种疗治,未蒙诠(痊)损。”(《国藏》1/282A)前例“复”,项楚谓“通作‘服’”[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后例“复”,黄征、吴伟校作“服”[注]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676页。,是其证。
词义上,“服制”谓服丧制度,文献多有其例。如《风俗通义·十反》:“(范滂)父字叔矩,遭母忧……三年服阕,二兄仕进。叔矩以自替于丧纪,独寝坟侧,服制如初,哀犹未歇。”[注][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18-219页。《魏书》卷五二《张湛传》:“兄怀义,闲粹有才干。遭母忧,哀毁过人,服制虽除,而蔬粝弗改。”[注][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54页。S.343《脱服文》:“慈颜一去,再睹无期,堂宇寂寮(寥),昊天罔极。但以礼章有[限],俗典难违;服制有终,除凶就吉。”(《英藏》1/143A)皆其例。
从文意看,在BD2496《目连变文》中,与上引“礼泣三周复制毕”句近似的内容作:“目连葬送父母,安置丘坟,持服三周,追斋十忌,然后舍却荣贵,投佛出家。”下文相应的唱词为:“目连父母亡没,殡送三周礼毕。遂即投佛出家,得蒙如来赈恤。”(《国藏》34/408)可见,所谓“三周复制”即“持服三周”,也就是服丧三年,其中“复”显然当读为“服”。前贤以本字解之,释“复制”为“复墓之礼”或“除丧制”,恐不可从。
七、悬沙
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娘娘见今饥困,命若悬丝,汝若不去(起)[慈]悲,岂名孝顺之子?生死路隔,后会难期。欲救悬沙之危,事亦不应迟晓(晚)。”(《英藏》4/121A)
按:“沙”,《变文集》(739)径校作“丝”,《校注》(1035)、《释录》(13/29)从之;《新书》(710)径录作“丝”,《选注》(931)从之,注云:悬丝,形容极其危殆。例中上文有“命若悬丝”之语,以此来看,前贤有关“悬沙”的校、注,似颇切于文意。但考虑到“沙”与“丝”形音皆不近,应无形误、音借的可能。考佛教文献中有“悬沙”之说,指悬挂沙袋以缓解饥饿,犹望梅止渴。如北魏菩提流支译《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爱乐佛法味,禅三昧为食”北魏昙鸾注:“此二句名庄严受用功德成就。佛本何故兴此愿?见有国土,或探巢破卵为饛饶之膳,或悬沙指帒为相慰之方。”(《大正藏》T40/P830B11—B14)元云峰集《唯识开蒙问答》卷下:“问:请举思虑为食之事。答:如悬沙疗饥,望梅止渴。”(《卍续藏》X55/P365A23—A24)明广莫《楞严经直解》卷八:“三者思食……思是思量,以希望心,任持不忘,如彼悬沙望梅,能止饥渴,皆思食义也。”(《卍续藏》X14/P835A14—A17)“悬沙”也作“悬砂”,如宋延寿《宗镜录》卷七三:“古师义门手钞云:思食者,如饥馑之岁,小儿从母求食,啼而不止,母遂悬砂囊诳云:‘此是饭。’儿七日谛视其囊,将为是食。其母七日后解下视之,其儿见是砂,绝望,因此命终。”(《大正藏》T48/P826A3—A7)可见,所谓“悬沙”本指悬沙袋以疗饥,上揭变文中用以形容目连母亲在阿鼻地狱中经受的极度饥困的状态,故称“救悬沙之危”。
八、椷


上举“每椷三两句”中,“椷”位于“每”与数量短语之间,用为名量词。“椷”这种用法亦见于押座文,如S.3491V《破魔变押座文》:“直饶玉提(缇)金萧(绣)之徒,未免于一椷灰烬。”(《英藏》5/107)“一椷”即一盒。弄清“椷”的词义及用法后,再来看“偈子每椷三两句后云云是”的意思。“偈子”本谓偈颂,此特指变文中的唱词;“椷”本指盛放物品的盒子,“每椷”就是“每盒”,因变文写本为卷轴装,不用时或卷束存于盒中[注]这可从敦煌愿文中“启金函”之语得到证明,如S.5957《文样·邑文》:“是日也,开月殿,启金函,转大乘,敷锦席。”(《英藏》9/241)说明斋会上转读的经卷原存放于金函中。,故以“椷”来称量用“盒”装盛的变文写卷。具体到P.2319《目连变文》中的偈颂,“椷”则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段”[注]此处以“椷”指称成段的唱词,可能与变文讲唱时以图与诗相配有关,这从P.4524《降魔变》写卷中可得到很好的说明。该卷正面绘舍利弗与劳度叉斗圣的彩图,背面则是与图画相配的诗句(即P.2319所谓“偈子”),讲者按正面的图画演说故事,一段讲毕,即由唱者依背面的诗句吟唱。如是按照故事情节逐段讲唱,直至将整卷讲唱完毕。因是按图配诗逐段讲唱,便临时用表整卷经文的量词“椷”来指称部分段落的唱词,可视为以整体指代部分。此处对“椷”这种用法的解释,获益于研究生邓博方的提示。另,关于P.4524《降魔变》中以图配诗的讲唱方式,参[美]梅维恒著,杨继东、陈引驰译,徐文堪校《唐代变文》,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14-117页。;“云云”指行文有所省略。“偈子每椷三两句后云云是”句,意谓该卷变文中每段唱词抄几句后即缀以“云云”,表示后面的内容省掉了[注]以“云云”表省略,文献习见。如《汉书》卷50《汲黯传》:“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颜师古注:“云云,犹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辞耳。”[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7页。。这在S.2614与P.2319两件写本的唱词中有清楚的体现,此举一段为例比对如下:

表2:S.2614与P.2319唱词比对示例表
由表2所列S.2614与P.2319两件写本中唱词的差异,即可直观地领会后卷首题下小字注“偈子每椷三两句后云云是”的具体内涵。反观上引川口久男与砂岗和子关于“云云”的理解,可知前者是而后者非。
附记:初稿承梁春胜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后又提交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2018.4.25)讨论,得到余欣、张金耀、唐雯、仇鹿鸣、夏菁等同仁及研究生邓博方的指正,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