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时期的河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
——以P.2942卷末所存三牒状为中心
2018-12-18杨宝玉
杨宝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唐代宗统治时期(762-779),因安史之乱后已攻占河陇大片疆土的吐蕃的阻隔,河西及伊西庭地区与唐廷的联络极为困难,致使中原史官对两地史事的记载断续零散,因而若仅据传世史籍已无从准确全面地了解那段历史。而在此期间,有两任河西节度使曾兼领伊西庭,故在留存于敦煌藏经洞的河西军文书中,可以检出一些有关两地的非常重要的记述,这当中内容最为丰富重要的便是法藏敦煌文书P.2942。该卷卷末第190-216、217-226上、226下-228行抄录有三件牒状,各牒状,尤其是第一件的内容具体繁复,三件之间又有内在联系,均围绕副帅长泉遇害事件展开,共同揭示了这场发生于伊西庭地区的政治变乱的主要过程,而这场变乱对伊西庭和河西地区均影响深远,因而这三件牒状历来备受相关学者重视。不过,由于这三件牒状用典频繁、部分文字行文晦涩、牵涉的问题隐秘复杂,可参照比对的相关史料却极少,同时P.2942这一长卷中的部分其他相关文字也颇为费解,故研究者对这三件牒状的解读异见迭出,对其所涉史事的阐释分析更是大相径庭。数年前,笔者因整理敦煌尼僧史资料而追索至该卷,最初的感觉也是迷惘困惑,遂在认真拜读学习前辈时贤相关论著的基础上,从不避繁琐不求时效的重新校录和详尽注释入手,结合相关敦煌文书、石刻墓志及传世史籍逐一探讨该卷各疑难问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今试就这三件牒状及其记述的唐代宗时期的河西与伊西庭节度使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P.2942卷末牒状校录
以前曾有多位学者做过P.2942全卷或部分文字的录文,但多未注释,笔者已重新校录该卷并进行了详尽注释[注]详参拙文《敦煌文书P.2942校注及“休明肃州少物”与“玉门过尚书”新解》,《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3-124页。。由于笔者的释录结果与前贤录文之间存有较大差异,亦为下文行文方便,今试略去注释部分,仅录三牒状于后。为便于阅读,不依原卷行款而据内容分段校录。
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
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奸回不轨,在法攸书。
副帅巡内征兵,行至长泉遇害。军将亲观事迹,近到沙州具陈。建谟出自中权,纵逼方凭外寇。逐兔者犬,可矜愚于小戎;指踪者人,宜责智于大匠。览三军之状,已辨淄渑;听两道之词,了分曲直。馆中毁玉,曾未谇于守持;衙内攫金,何遽受于旌节?承伪便行文牒,凭虚莫畏幽明;侮法无惧三千,搏(抟)风妄期九万。尚书忠义,寮属钦崇;生前人无间言,殁后状称矫诏;假手志诬为国,披心恨不显诛;岂惟名行湮沉,实谓奏陈纰谬。将士见而愤激,蕃虏闻而涕流。咸谓煞国之忠良,更兴谤讟,屏王之耳目,使不聪明。伏寻表草之言,却似首陈之状。上书自然不实,下策何烦漫行。此乃欲盖弥彰,将益反损。既知指的,方敢奏闻。又伪立遗书,躬亲笔削;恣行贪猥,莫顾章程。况随使资财,尽知优赡;供军玉帛,众委丰饶。人虽非命薨亡,物合却归府库。今者,马承官印,货被私收;杂畜全留,家僮半放。语亲殊非骨属,论义正是血仇。更何因依,独擅封植?且煞人求饷,尚召初征;害使贪荣,能无后患?离心速寇,当即非赊;夺魄丧名,期于不远;事复彰露,迹甚猖狂。匪直紊乱二庭,亦恐动摇四海。察其情状,法所难容。宜绝小慈,用崇大计。
彼道军将,早挹忠贞;数州具寮,素高节操。前车既覆,已莫辩于薰莸;后辙须移,可早分于玉石。事上固能剿绝,临下岂惮锤埋。请从曲突之谋,勿误焦头之祸。
周逸非道,远近尽知。理合闻天,义难厘务。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
某乙谬司观察,忝迹行军,欲宽泉下之鱼,有惭弦上之矢。公道无隐,敢此直书。
各牒所由,准状勘报。当日停务,勿遣东西。仍录奏闻,伏待进止。
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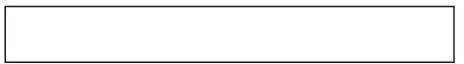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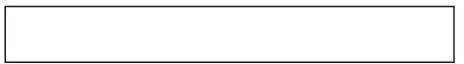
周逸与逆贼仆固怀恩书
推亡固存,《商(尚)书》所重;去顺效逆,《春秋》则诛。周逸猖狂,素怀悖乱。辇毂[后残]
二、唐代宗时期的河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
笔者以为,发掘上录三件牒状的史料价值,应以正确和充分理解其文字含义为前提,而三牒状中最令后人纠结的是以官称表述的人物关系,故下面试以各官称为线索,论述笔者对当时河西与伊西庭节度使的认识。
1.“使主”、“副帅”、“元帅”:三称所指为同一人,即接续杨志烈统领河西军的杨休明,因杨志烈为两镇节度,杨休明及其率领的河西将士遂将他赴伊西庭视为“巡内征兵”,而这却触碰了伊西庭留后周逸的权利
“使主”、“副帅”均出现于上录第一件状牒中,从所记事迹遭遇看,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之所以用两称,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因为该状牒之题目的后半句“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中提到了矫诏而成的“河已西副元帅”,而那是另一个人(详后),为了避开“副帅”与“河已西副元帅”的中心词“副元帅”之间有可能出现的模糊不清,更为了说明构逆者周逸与被杀害的两镇节度使之间具有从属关系——被杀者乃是杀人真凶的上司,本有主从上下之别——故文题中用“使主”代称正文中的“副帅”。“副帅”则是状牒作者在“各牒所由”时对自己属下说的,也应是河西军内部对当时的节度使的习惯称谓[注]关于节度使可被称为“副帅”,唐长孺先生已做过精彩论证,详情请参氏著《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3-11页。不过,在此我们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赞同该文将“尚书”与“副帅”比定为同一人的做法。。至于下一则牒状中“一昨亲巡”的“元帅”当然也是这位河西节度使,作者是在致书安西四镇的统领者,以请求对方派发援兵的情况下说的。关于这三称在本卷中的互通性,唐长孺先生已有论证:
所谓“巡内征兵”,“元帅一昨亲巡”,也好解释为他兼领河西和伊、西、庭两镇。更因为他虽兼领两镇,通常驻节河西,所以伊、西、庭置留后,对周逸而言,他是“使主”。[注]唐长孺《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第3-11页。
因而,关于这三称,的确可以简单等同为一个人,牒状在不同情况下分用三称,各有道理。
关于这位被害于长泉的节度使究竟是谁,学界一直存有巨大争议,唐长孺、安家瑶先生等主张为杨志烈,史苇湘先生等推断为杨休明。笔者认为只能是杨休明。
其一,杨休明的最终官职与被害副帅相符。传世史书和杨休明后人的墓志对杨休明的最终职任多有记载。例如:《册府元龟·帝王部·旌表三》、《全唐文》卷51等均收录了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五月所颁《赠杨休明等官诏》,对杨休明终官的记载为:
故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太保杨休明。[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0頁。[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39,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84页。后者将“检校”书为“简较”。
再如,《千唐志斋藏志》所收《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丹州诸军事守丹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弘农杨公墓志铭并序》的志主杨乾光为杨休明之孙,志文云:
祖休明,河西伊庭节度使,赠司空。[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31页。
是知杨休明终于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任上,而据P.2942卷末牒状中“使主”“两道”“巡内”等语,被害于长泉的副帅无疑也是兼领河西与伊西北庭两镇的节度使,与杨休明的最终官职正相符合。
其二,杨休明的郡望与被害副帅相符。上引《杨乾光墓志》有云:
公讳乾光,字耀卿,其先弘农人也。
是知其家族为弘农杨氏。近年陈晓伟先生揭出明人胡广(谥号文穆)曾于永乐十三年撰作《记高昌碑》一文[注]陈晓伟《胡广〈记高昌碑〉与高昌麴氏、唐李元忠事迹丛考》,《文献》2016年第6期,第53-61页。该文考出胡广所得拓片当来自永乐年间通使西域的著名使者陈诚,认为陈诚“第二次出使西域,途经火州城时摹拓了这六种高昌旧碑”,火州曾是唐朝伊西庭节度使管辖的重镇。,抄录了其所见《大唐故伊西庭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刑部尚书宁塞郡王李公神道碑》(以下简称《李元忠神道碑》)拓片的部分内容,该碑文相当详尽地记述了碑主李元忠为长官复仇的忠义之举,而其长官正是P.2942卷末牒状中的副帅。其文曰:
李元忠,河东人也,本姓曹,字令忠,后以功赐姓改名,祖考以上皆负名称。元忠……及弱冠,从军……故恒遇战,勇冠□□□□河西、伊西庭节度使、工部尚书弘农杨公之亚将。及弘农公被屠害,元忠誓报酬(仇),乃以师五千,枭周逸,戮强颙,雪江由之耻,报长泉之祸。义感四海,闻于九重,解褐授京兆洭道府折冲都尉。[注][明]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19《记高昌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59页。
其中明确提到被周逸屠害的节度使是弘农杨公。
其三,杨志烈、周逸、杨休明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合理解释被害副帅为杨休明而非杨志烈。这三人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其对河西与伊西庭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更值得深究。
首先看杨志烈与周逸。关于杨志烈,王小甫先生已指出:
伊西庭节度观察由河西兼起自广德元年(763)杨志烈,起因是宝应元年吐蕃陷伊州后,是杨志烈率河西军将收复的。[注]王小甫《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57-63页,亦收入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5章《东争唐地、西抗大食的吐蕃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本文所据为后者,下引文见该书第199页。
故据吐鲁番阿斯塔纳第509号墓所出《西州使衙牓》[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6-127页。该牓文签署“使、御史中丞杨志烈”,年代题记为“建午月四日”,唐长孺先生等已考出此处的“使”即伊西北庭节度使,时当宝应元年(762)五月四日,故知其时杨志烈正在伊西北庭节度使任上,所带宪衔为正五品上的御史中丞。及唐长孺、王小甫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杨志烈曾在伊西北庭地区大有作为,当时其麾下必然有一些得力干将。东调河西时,杨志烈仍兼任伊西北庭节度使,但因伊西庭与其时的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相距遥远,故有留后之设。上录第一件状牒题目为“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很显然,状牒作者即便在谴责周逸罪行时仍然承认其伊西庭留后的身分,说明周逸的留后之位应是名正言顺的,当初也应是得到了其长官杨志烈认可甚至荐举的。正因为这样,一方面,倘若前来征兵的是杨志烈,作为杨志烈部下并曾受主政伊西庭期间的杨志烈提携的周逸一般不会顿起杀心。另一方面,当杨志烈于甘州遇难后(详后),周逸自认为当是杨志烈的接班人,也就并非全无来由了。
再看杨志烈与杨休明。杨志烈遇难前虽兼任两镇节度使,但身处河西已至少一年多,在当时战乱路阻的情况下,在此期间他的主要活动范围与联系紧密的部属就主要都在河西了,而他自己也身死甘州,故杨志烈遇难后,紧急情况下的代任者自然会在河西军将中产生,是以杨休明以侍御史判凉州长史等身分接任[注]此据P.3952。该文书形成时间为永泰元年秋冬至永泰二年(765-766)前后,所书“前侍御史判凉州长史杨休明”是今日可知担任河西节度使之前的杨休明的唯一官称,该语颇有深意,解析之后可知:杨志烈突然被杀后,杨休明临时被推举出来领导河西军,而当时战乱路阻,杨休明无法及时获得唐廷的任命,至已移衙沙州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是尽其责而乏其名,在给唐廷上报民事的奏状中只得署在凉州时的前官。详参拙稿《两件度牒相关敦煌文书复原整理与再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多元宗教”学术研讨会论文,敦煌,2018年5月。。那么杨休明及其河西部属自然会认为他承袭的是杨志烈的全部职任,是河西与伊西北庭两镇的共主,伊西庭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巡内”,西去征兵为其权限之内的事情。
最后看周逸与杨休明。早已充任伊西庭留后的周逸可以顺服于杨志烈,却未必对杨休明心悦诚服,不会轻易服从后者的约束。当杨休明进入了周逸实际掌控的势力范围并要从中征兵时,遭周逸设计谋杀便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了。并且,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事件发生时,唐廷对杨休明的任命很可能还没传达到伊西北庭地区,这也给了周逸可乘之机[注]据后面结合明人胡广所记《李元忠神道碑》等进行的推算,副帅长泉遇害一事当发生于大历元年(766)或稍早些时候。而《资治通鉴》卷224代宗大历元年条记:“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可知当年五月唐廷才终于接获奏报,认可并记录了杨休明继任河西节度使和已率军移镇沙州的既成事实。但是,授官诏敕和节度使旌节送达漫漫关山阻隔的沙州敦煌和伊西北庭地区却还需要不少时日,按当时的交通实况推理,最快也要到半年之后的秋冬年末。。
总之,笔者认为,P.2942卷末牒状及其记述的事件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河西与伊西庭各执各理的结果。
2.“河已西副元帅”:系周逸的矫诏自称,唐廷并未设置过该职,由这一子虚乌有之称引申的“唐廷构建了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体制”的观点值得商榷
P.2942卷末牒状中最惹眼的官称可能就是“河已西副元帅”。
曾有多位学者注意到无论是在传世史籍中,还是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河已西副元帅”均仅此一见,更找不到唐廷设置该职的任何记载。不过,学者们多以“失载”来解释,进而认为此官曾真实存在,杨志烈和杨休明都曾出任。唯独唐长孺先生有过怀疑,谓:
题有“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一语不知何指,或是周逸矫诏自称此官,所以在下面又有“承伪使[注]此字原卷所书为“便”,唐先生所录有误。行文牒”一语。[注]唐长孺《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第3-11页。
但是唐先生仅提此一句,并未深究,后来的研究者也没有认真对待唐先生此一疑问。
考“河已西副元帅”所属原句为:“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该句是对周逸逆乱事件的扼要概括,语法简单,语意清晰。显然,矫诏的主体是周逸,状牒作者谴责控诉的周逸的罪行不只是他勾结突厥杀害使主,还有矫诏自称“河已西副元帅”,状牒作者承认其时周逸的身分是伊西庭留后,但认为其“河已西副元帅”则是矫诏而来,根本就不认可。
据前引《李元忠神道碑》,当唐廷获知李元忠诛杀周逸之事后,表彰了李元忠并授予官职。那么唐廷对周逸当然是完全否定的,根本不可能认可周逸的自称。
有无可能周逸矫诏是想承袭杨志烈或争夺杨休明的权位,即唐廷曾任命杨志烈、杨休明为“河已西副元帅”呢?先看杨志烈的情况。据前面已经提及的吐鲁番阿斯塔纳第509号墓所出《西州使衙牓》,宝应元年五月杨志烈任伊西庭节度使时所带宪衔仅为正五品上的御史中丞,而两年后的广德二年(764)杨志烈即被沙陀杀害于甘州,这当中他虽迁为尚书,但对于所谓兼领河西、伊西庭、安西的河已西副元帅来说资历仍浅,而杨志烈的最终结局(详后)也足以说明他与“河已西副元帅”无涉。至于杨休明就更不可能了,不仅资历更浅,他还是在杨志烈突然遇害,群龙无首的特殊时期临时接管河西军的,因途遥路阻,烽火战乱,很可能至死都没能接获节度使诏命旌节(朝廷任命并遣使册拜和朝命送达之间必有时间差,而在军情政况瞬息万变的战乱时期,这种间隔或曰滞后有时是致命的[注]仍以P.2942所记为例,该卷中竟有7则判文或牒状明确记述或直接提到甘州刺史张瓌对抗杨休明的变乱,推其事发时间,也可证明正式任命及旌节送达的滞后是当时河西与伊西庭变乱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有甘州刺史张瓌之乱,西有伊西庭留后周逸之叛,这期间杨休明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详参拙文《永泰元年甘州刺史张瓌之乱索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8辑,即刊。),更别提“河已西副元帅”的任命了。并且,遍查现存各类史料,对杨休明终官的记载明确而一致,均为河西节度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如果唐廷真的曾任命其为“河已西副元帅”,如此重要的官职,史书不应缺载,杨休明的后人杨乾光等更不会遗忘漏记。
因而,所谓“河已西副元帅”不过是谋逆的周逸企图“搏(抟)风妄期九万”,即为对抗河西军公意而自壮声势的矫诏冒称,是子虚乌有之称,只会出现在对其罪行的控诉中,却不可能得到任何史料的印证。
正因为当时的唐廷根本就没有设置过“河已西副元帅”,由此称引申出来的所谓唐廷通过设置河已西副元帅构建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体制的说法就失去了凭据。该假说不仅没有可信史料支撑,更与当时唐朝总体政治形势不符。彼时中原激战正酣,唐廷疲弱被动,哪里有空暇和能力远瞻西顾。
3.“尚书”:与“使主”“副帅”“元帅”并非同一人,而是杨志烈,广德二年他已于甘州被沙陀人杀害,因以前杨志烈曾主政伊西庭,故当周逸为维护旧有势力谋逆作乱时自然会盗用他的名义为自己背书
关于P.2942卷末状牒中的“尚书”与被害于长泉的副帅之间的关系,自唐长孺先生始,相关研究者一直想当然地将他们等同了。笔者认为本卷中他们根本就是两个人。
其一,按正规官文书的行文习惯,在上录第一件状牒这同一件公文的正文中,对同一个人物是不应该用两种官称混称的,这与前面论及的题目与正文分用两称的情况不同:题目中的“使主”主要是从被害者与凶手之间的主、从关系说的,而“尚书”与“副帅”却都是实有所指的正规官称,混用容易致乱,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古人为文一般都会避免的。
其二,状牒中有关他们的叙事完全不同。“尚书”与“副帅”在状牒中所处的语言环境及遭遇各异:“副帅巡内征兵,行至长泉遇害”等语表明副帅是现任使主,是在征兵过程中被杀;而“尚书忠义,寮属钦崇;生前人无间言,殁后状称矫诏”等语则是说尚书于死后被别有用心的人盗用了名义以谋取私利。被杀害与被盗名诬陷性质迥异,不能简单等同,显然并非同一人。
其三,对P.2942所抄各公文作者的考证[注]详参拙文《法藏敦煌文书P.2942作者考辨》,《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第62-67页。拙文反驳了以前学界将P.2942第47行“休明肃州少物,今请回易皮裘”理解为“肃州的杨休明缺少物资,现在请求博换皮裘”并进而以杨休明身在肃州不可能在沙州判案为由来否定判文作者为杨休明的做法,认为该句语意乃是“休明留在肃州的少许物品,现在就请用来换取皮裘吧。”“休明”是判案者的自称,虽然其时他已在沙州主持政务,但并不妨碍他派人处置自己留在肃州的物品。据P.2942第92行“甘州请肃州使司贮粮”,河西节度使司就曾经在肃州存留物资,那么途径肃州时杨休明留下一些东西是很正常的。该则判文表明,当已处抗蕃斗争最前线的甘州兵健缺少冬装而难以筹措时,杨休明一边敦促肃州、瓜州尽力援助,并派押衙前去妥善处理,一边令该押衙先以自己以前留在肃州的少许物品换取皮裘帮助甘州兵健。在当时的情境下,此一做法虽属杯水车薪,但总是聊胜于无,其以身作则的姿态应能收到暂且安抚人心的效果。也可证尚书与使主、副帅、元帅并非同一人。P.2942共抄存40馀则判文,其中第1-5行判文自题“尚书判”,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该则判文的作者为尚书。而第11-14、34-38、86-88、145-148行四则判文所判之事均与尚书有关,判案者显然不是尚书本人而是另有其人,且后者应是本卷所抄大多数判文的作者,他判署了大量与州刺史、军使有关的文书,断非撰作上录第一件状牒的行军司马可比,却与该状牒中可以统理两镇军政事务的副帅相符。换言之,P.2942所存40馀则判文的作者至少有两位,此二人均有节度使权责(各判文均以节度使口吻判署),而当时的河西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位节度使,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有前任与后继之别,后继者尊称前任为“尚书”,自己则被属下称为“副帅”。
上文已经论证了副帅为杨休明,他的前任非杨志烈莫属。其实关于尚书为唐代宗时期的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学界一直没有异议,笔者亦认为其说有据可信,笔者极力主张的只是应将“尚书”与“使主”“副帅”“元帅”进行区分,也只有这样才能客观正视传世史籍对尚书事迹的记述。
考《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二年十月条记:当反叛唐朝的仆固怀恩南寇时,杨志烈曾派出河西精锐攻打仆固怀恩的老巢灵州以缓京师之困,此举有力地支援了唐廷。但是,当伤亡惨重的残军归来时,杨志烈沉浸于“此行有安京室之功”的欣慰,没能充分体恤属下将士的悲苦,一句“卒死何伤”招致“士卒怨其言”,兵将的不满情绪开始积聚。不久,吐蕃围困凉州城,将士们的不满被迅速引发,“士卒不为用”,以致:
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68-7169页。
同书卷224代宗永泰元年(765)条亦有注文云:
杨志烈死见上卷广德二年。[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4,第7185页。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对杨志烈西奔情形更具体而形象地记为:
广德二年,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守数年,以孤城无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于寇。[注][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9页。
此处之“守数年”是指杨志烈守卫河西而非被围后的凉州。关于凉州被围与陷落的时间,传世史书与敦煌文书等均记为广德二年。于此,还有一条相关史料也当注意,即《资治通鉴》卷223于上引第一条史料处还引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曰:
十二行本“杀”下有“凉州遂陷”四字。
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中所说的十二行本《通鉴》乃是刻印精良的宋本,该本明言杨志烈被杀在先,凉州陷落在后,也可证杨志烈殁于凉州陷落之前的广德二年。
这些史籍对杨志烈自受困凉州,至西奔甘州,再至被沙陀杀害的记述完整、清晰、一致[注]唯独《新唐书》卷6《代宗纪》于永泰元年记:“十月,沙陀杀杨志烈。”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录传世史书对杨志烈被杀时间的记载,即为证明广德二年说有多条记载可相互支撑,而《新唐书·代宗纪》所言为孤证,恐有误。况且,《资治通鉴》卷224代宗永泰元年条记:“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灵武初复,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倘若杨志烈真的是亡于永泰元年十月,郭子仪和唐廷不可能一月之内就获知消息。当时战乱路阻,信息传递极其困难,西北与中原的沟通往往需要数月以上,本文后文所引各例均可提供佐证。,据此,杨志烈于广德二年被沙陀杀害于甘州应是不刊之论,那么他也就不可能二次亡殁于伊州与北庭之间的长泉,与长泉遇害的副帅绝非同一人。
行文至此,笔者必须回应学界流传多年的一种说法:将P.2942第145行“玉门过尚书”一语译解为“尚书经过了玉门关”,并进而推论尚书弃凉州西奔后并未死于甘州,而是一路西行,经沙州玉门关,远赴伊西庭征兵,至长泉遇害,从而将文书所言被杀副帅等同于尚书,又将其推断为杨志烈。
笔者认为,上述一连串假设均建立在“玉门过尚书”是“尚书经过玉门关”之意的基础上,但问题是原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上述解读连续出现了三个疏误:将“玉门”理解为玉门关、将“过”解作经过、将原句的主语与宾语颠倒而成“尚书过玉门”。以下略作解说。
通观P.2942所抄40馀则判文,其判处的均为军、州事务,是知判案者只面对军、州层级,各县政务尚且不会直接干涉,更不可能跨越数级去过问处置小小关隘玉门关的事情了,因而此处的“玉门”绝非玉门关,也不是玉门县,而是玉门军,其简称“玉门”与建康军简称“建康”的道理是一样的。“过”也非“经过”之“过”,而是“过丧”[注]过丧原本是丧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送葬、路祭等关系密切,具体指逝者的亲知友朋等于丧车经过时举哀致祭。之“过”,于此处可译为祭拜。至于句子结构,依古汉语语法,主语、谓语、宾语各有其固定位置(倒装句也只能是主谓倒装或谓宾倒装,而不可能是主宾倒装)。具体到这个句子,位于谓语“过”字之前的“玉门”才是主语,之后的“尚书”乃是宾语。因而,“玉门过尚书”一句的意思系谓作为河西节度使属下的玉门军的将士祭拜已逝的前任节度使尚书。玉门军驻守于肃州境内,与上举传世史书所记杨志烈的遇难地甘州毗邻,玉门军举行祭奠尚书杨志烈的活动十分正常。该件判文中“尚书当过”一语,字面意思是应当祭拜尚书,整件判文则是说虽然应该祭拜尚书,但是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不应该动用过多的资财,逾制过奢不合时宜。
关于P.2942现存近50件公文的排序规律,笔者已考出这些公文可略分为军需相关、军政相关两大序列,各序列内部均按各文形成时间先后(也就是相关史事发生时间先后)抄列[注]详参拙文《法藏敦煌文书P.2942文本解析》,刘中玉主编《形象史学》2017上半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6-169页。。“玉门过尚书”一语抄于卷子中部,可证该卷所涉史事大多是在玉门军为尚书举办祭仪之后发生的,卷末牒状所言副帅长泉遇害事更远在尚书亡殁于甘州之后。
尚书已逝,但其影响仍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杨休明职位和周逸自称的正统性合法性都要依赖各自与杨志烈的关系。P.2942卷末状牒所书是杨休明部属对周逸的控诉,其中涉及尚书的文句主要是:“尚书忠义,寮属钦崇;生前人无间言,殁后状称矫诏”系谓杨志烈的忠义深受下属钦仰,其生前没有受到过非议,岂料殒殁后却被周逸盗用名义矫诏欺世。这是从状牒作者,即副帅的部下的角度说的,指责周逸既杀害了副帅,又玷污了另一位重要长官——尚书——的名誉;“又伪立遗书,躬亲笔削”则是说周逸命人伪造了尚书遗书,并亲自动手修改,以欺世盗名,利用尚书为自己的矫诏背书。状牒作者之所以撰作这些与尚书有关的语句,就是想以此阻止周逸利用尚书为自己造势。
4.“留后”:P.2942卷末状牒之正文中的“留后”乃单纯指这一职位,其所属“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等语系谓应以贤能之人充任伊西庭留后,这正揭示了以后两镇分别设立节度使的起因
“留后”两字在P.2942卷末状牒中曾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上录第一件状牒的题目中,与上下文紧密地组合在一起而成“伊西庭留后周逸”,语意明确,兹不赘述。第二次则是在该状牒的正文中,从字面上看并未指某人而是谓该职位,其所属语句“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很值得仔细分析,因为这与以后的河西与伊西北庭不再兼领密切相关。
前已言及,宝应元年时的伊西庭节度使为杨志烈,稍后他赴河西,在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同时仍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又因两地辽远,伊西庭同时设立了留后。以后两地的实际状况是,当杨志烈兼任两使并主要以凉州为中心治军时,两地相安,但当杨休明接手并将河西军治所西移沙州,甚至径直赴伊西庭征兵时,冲突便不可避免了,最终酿成了节度使被害的惨祸。P.2942卷末牒状作者在控诉周逸罪行时,一方面强调副帅具有两镇职权,周逸谋杀使主是犯上作乱,另一方面,针对撰作状牒时两地的客观情况,明确提出“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表明副帅长泉遇害事件之后,河西将士对当时两地的客观形势有清醒认识,明白在伊西庭设留后的必要性,期待的乃是以选用贤良有才干的人担任伊西庭留后来取代大逆不道、欺世盗名的周逸,而不是由治所已移至沙州的河西军完全统摄伊西庭。
根据前引《赠杨休明等官诏》称杨休明为“故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唐廷确实给了杨休明两镇节度的名义,但是以后的河西节度使却不再兼领伊西庭。例如,大历七年(772)八月之前[注]《喻安西北庭诸将制》中有言“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使用的是李元忠的原名,考《旧唐书·代宗纪》曰大历七年“八月庚戌,赐北庭都护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是知《喻安西北庭诸将制》当颁布于曹令忠赐姓改名之前。颁布的常衮撰《喻安西北庭诸将制》即称杨休明的后任为“河西节度使周鼎”[注][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16《政事·慰抚中·喻安西北庭诸将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06页。《全唐文》卷414亦收,第1876页。。再如,《赠杨休明等官诏》所述周鼎的官职也只是“故河西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侍御史大夫周鼎”。这说明杨休明死后两镇已的确无法共管了,此前杨志烈兼领两节度乃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杨休明没有杨志烈那样的背景资历,徒有其名的结果是祸乱加身,其后继者周鼎更是连虚名都不再有了。
今知周逸被诛杀后伊西庭即由率领五千将士前来为杨休明复仇的原河西军将李元忠等实际管领,至大历二年(767),唐廷更是正式任命李元忠为伊西庭节度使,以后还多次为其加官。《李元忠神道碑》在上引文之后紧接着写道:
大历二年,遣中使焦庭玉,授伊西庭节度兼卫尉卿、瀚海军[押]蕃落等使。大历五年九月,中使将军刘全璧至,加御史中丞。大历八年四月,中使内寺伯卫朝王巷至,加御史大夫,赐姓改名,赐衣一袭。
关于此后的李元忠事迹,胡广《记高昌碑》记录和考释曰:
碑云:“建中三年二月廿七日,加刑部尚书、宁塞郡王。”《会要》云:“建中二年七月,加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北庭大都护。”与碑不合。岂二年为遣使之日,三年乃至塞之日也。所加官爵不同,不审何者为是。……《唐书·回鹘传》云“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鹘乃得至长安,帝进元忠为北庭大都护。”此史之失也。碑云:“建中五年五月五日,公薨于北庭之廨宇。六年,葬前庭东北原火山南面。”然建中止四年,明年为兴元元年,又明年为贞元元年。无五年、六年。则是没于兴元而葬于贞元,岂建中以后使路阻绝,惟知有建中,而不知有兴元贞元也。
是知大历二年至兴元元年(784),伊西北庭一直在李元忠治下。大致同时段的河西节度使则是周鼎,史书常将二人并提。
因而,笔者认为,大历二年河西与伊西北庭两镇正式分别设立节度使的举措与此前周逸谋害杨休明事件大有关系,该恶性事件集中暴露了当时河西与伊西庭官员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P.2942卷末状牒的作者身处其中,明晓利害,故建言“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而其对留后人选恐怕也已有倾向性。
5.“行军”:“行军司马”的简称,系牒状作者的自指,其人应即是继杨休明之后统领河西军的周鼎,在长官突然遇害的特殊时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危局,以后又在河西节度使任上固守敦煌,但最终也死于非命。
P.2942卷末牒状的作者自称“某乙谬司观察,忝迹行军”,表明节度使不在使司期间是由他临时代理军政事务,至于其原来在河西军中的官职,则为节度使下的首僚——行军司马。据传世史籍、敦煌碑铭、藏经洞文书等对杨休明遇害后河西沙州史事的记述,此人就应是接续杨休明掌理河西军的周鼎。
杨休明突然遇害后,周鼎面临的局势也相当艰难,必须“孤馆自裁”[注]曾有学者将此语解作副帅是被迫自杀的,恐非是。孤馆:本意为孤寂的客舍,此处殆因状文作者是受形势所迫而随河西节度移镇沙州的,故以此自称。自裁:此处谓自作决定。,即自行决断。今日可知行军司马周鼎至少采取了四项应急措施:其一,立即发布牒文揭露声讨周逸,并劝谕河西和伊西庭将士,以稳定军心,控制局面。上录第一件状牒“各牒所由,准状勘报”等语即可为证。其二,迅速修表状上奏朝廷。上录第一件状牒行文明显具有奏状特征,稍事修改即可用于上书奏事,即文末所言“仍录奏闻,伏待进止”。第二件牒状也要以牒文的形式晓示相关人员,并据此状修表上奏,即“各牒所由。准状修表录奏”。这两项措施正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相关责任者需要上报下达的状况相合。其三,派遣部将李元忠领兵严惩凶犯。据《李元忠神道碑》所记碑主诛杀周逸后因功解褐得授京兆洭道府折冲都尉,彼时李元忠在河西军中的职位不会太高,其剿灭周逸一举必然是听命于周鼎。其四,差遣属下郑支使携其书状(内容当即P.2942《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所述)前往安西四镇,请求对方火速派兵救援突遭变乱的河西军。这两项实际行动果断及时,积极主动。从后续结局看,周鼎的这些举措收到了良好成效,周逸谋逆一事被迅速压制,以后河西和伊西庭皆又为唐廷坚守多年。
据上引《喻安西北庭诸将制》和《赠杨休明等官诏》等,后来周鼎也获得了节度使正授。关于具体时间,参照《李元忠神道碑》所记“大历二年,遣中使焦庭玉,授伊西庭节度兼卫尉卿、瀚海军[押]蕃落等使”,周鼎至迟也当同时获旌节。考虑到周鼎的资历及当时河西与伊西庭局势,很可能他获任更早,或许李元忠“解褐授京兆洭道府折冲都尉”时周鼎即迁升为河西节度使,至于其大致时间,当距离杨休明长泉遇害事件不远。
考《李元忠神道碑》记:当诛杀周逸的消息传到唐廷后,李元忠先是因功解褐,得授京兆洭道府折冲都尉,至大历二年,唐廷才再遣使拜其为伊西庭节度使兼瀚海军使。其时吐蕃已占据河西陇右大片唐土,关山阻隔,军情朝命的传递极其困难,伊西庭与中原往来需要至少半年时间。例如,前引《旧唐书·代宗纪》明确记给曹令忠赐姓改名的时间为大历七年(772)八月庚戌,而据《李元忠神道碑》,中使将诏令送到已是次年四月,耗时长达八个月。那么,副帅长泉遇害及P.2942卷末牒状的撰写时间就当为大历元年(766)左右。由此推算,周鼎任节度使有可能就在那之后不久。
无论是大历元年还是二年获正授,实际上自杨休明遇害后,周鼎就已经担当起了河西节度使的责任,在宋璟之子宋衡[注]《全唐文》卷338所收大历十三年(778)三月颜真卿撰《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云:“第六子衡,因谪居沙州,参佐戎幕,河陇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节度行军司马,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是知周鼎任河西节度使后,宋璟之子宋衡迁任周鼎原来的职位行军司马,与周鼎共守敦煌。等的辅佐下,周鼎治下的沙州还曾有过一段较为安宁的时日。莫高窟第148窟前室存留有一方《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简称《大历碑》,P.4640、P.3608有抄件),记录了该窟建成之初河西节度使周鼎曾来巡拜一事,谓:
时节度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爰因蒐练之暇,以申礼敬之诚,揭竿操矛,闟戟以从,篷头胼胁,傍车而趋,熊罴启行,鹓鸾陪乘,隐隐轸轸,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也……时大历十一年龙集景辰八月有十五日辛未建。[注]转引自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可知至大历十一年(776)八月沙州尚称安定,人们还在进行开窟造像活动。
关于周鼎的个人结局,《新唐书·吐蕃传下》记:
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踰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注][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1页。
是知周鼎是在固守沙州城数年,历经艰难困苦之后,认为沙州城已无法再守,考虑弃城率众东奔时被部下阎朝缢杀的,此一个人结局着实令人唏嘘。据《新唐书·吐蕃传》随后所记,那位缢杀周鼎后自领州事的阎朝,在率众又坚守数年之后,因“粮械皆竭”不得不出降,最终却也被吐蕃“置毒靴中而死”。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将唐代宗时期(762-779)及稍早或稍晚一些时候的河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或留后的任职情况归纳为:
河西:
约宝应元年[注]戴密微等学者据P.2555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考证认为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至宝应元年(762)河西节度使为吕崇贲。详见[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6-217页;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4-1225页。至广德二年(762-764),杨志烈任节度使;
永泰元年至大历元年(765-766),杨休明任节度使;
大历元年至大历十一年八月之后某年(766-776年八月之后某年),周鼎任节度使;
再后阎朝自领州事。
伊西庭:
宝应元年至广德二年(762-764),杨志烈任节度使;
约宝应元年至大历元年(762-766),周逸任留后;
永泰元年至大历元年(765-766),杨休明任节度使;
大历二年至德宗兴元元年(767-784),李元忠任节度使。
这当中杨志烈和杨休明兼领两镇。关于这些节度使或留后的个人结局,今知除李元忠寿终正寝外,皆死于非命,当时河西西域抗蕃斗争之惨烈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