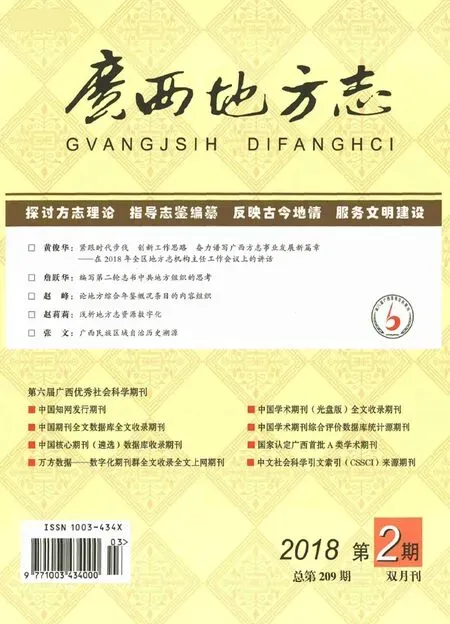明清广西方志所见儒家祠祀体系
——以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2018-12-13王群韬
王群韬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明清时期的广西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各级政区境内儒家祠祀和社会礼俗的相关信息,反映出儒家礼仪传统主导的祀典体系和祭祀场所在这一地区的历史格局。那么,明清广西地方社会的儒家祠祀体系具有怎样的基本内容和区域特色?本文主要依据明清广西各府志中关于儒家祠祀的相关记载,围绕地方性的祠祀体系特征、社会礼俗图景及其与当地文化教育体系的关联进行简要的分析与探讨。
一、祀典:儒家礼仪传统主导的国家祠祀制度
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说及其礼仪传统逐渐占据了中国官方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体系的主导地位,儒学、儒教成为礼法社会之正统。此后历代的国家祭祀制度,皆以儒家礼仪为主导,一般称为“祀典”。这套国家祀典制度,主要依据《周礼》《仪礼》《礼记》等经籍,在两汉礼制实践中逐渐成形,以后历代又根据具体情况有所损益,至隋唐时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架构,宋元明清又各有局部调整与总结,至清代形成一个极为成熟和完备的制度化体系①吴飞.从祀典到弥散性宗教[A].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第三辑[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按照正统儒家士大夫的说法,国家祀典的主干部分包括对天地、日月、风云雷雨山川等的祭祀礼仪,这是从周代延续下来、由历代儒家尽力维持的传统,具有完整的“祭统”“祭义”和“祭法”②李天纲.三教通体:士大夫的宗教态度[J].学术月刊,2015(5).。这套祭祀制度,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君主统治和教化的重要手段。儒家礼仪与祭祀制度构成了国家礼乐教化与信仰传统的重要内容,“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邦有祀典,治明治幽”③(清)魏笃修,王俊臣纂.同治浔州府志卷七[M].同治十三年刻本.。这一儒家礼仪主导的国家祀典与祠祀体系,实际上具有“宗法性宗教”的特质,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和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①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明清时期,从中央到各省府州县皆建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文庙、乡贤祠、名宦祠、武庙、城隍庙等“天下通祀”的坛壝祠庙,并由官府定期派员致祭,以示礼敬。这套祀典落实到地方上的具体情形,则体现在各地编纂的方志里。明清时期各地方志大多专门辟出一部分,或名“祀典”,或称“祠祀”“秩祀”,或为“坛庙”“祠庙”等,作为记录当地儒家祠祀庙宇相关内容的篇目。方志编纂者多为官员或儒生,他们在《祀典》《祠祀》篇目中首先记录境内由官方颁定的重要祀典和各类具有“赐额”的祠庙(官祀、正祀),其次记载民众建立的祠庙(私祀)。记载的具体内容包括祀典和祠庙的名称、祭祀规格、地理位置、修建沿革及存废现状等信息。有些方志还会在祠祀篇目起始处列出境内的祠庙总数、方位分布特点等整体信息。还有一些方志会更细致地在《祀典》《祠祀》篇目之下再分设《坛》《祠》《庙貌》等子目,然后根据坛庙祠宇的具体形制进行分类记载。
二、明清广西府志所见儒家祠祀体系
现存的明清广西方志,多以《祠祀》《祀典》《坛庙》《祠庙》等篇目记载祀典和祠祀的相关信息。从这些方志的《祀典》《祠祀》篇目的序言或引语看,作为编纂者的地方官员和儒生十分重视对祀典、祠祀的记载。例如乾隆《柳州府志》卷17《坛庙》开篇云:
昔圣王治天下,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故□郊宗祖而外,凡日星风雨山川百物及前哲令德之人,有功烈于民者,虽在遐荒,必令有司建坛壝、崇庙貎,以岁时奉牲币尸祝而社稷之,所以明报嘉也。柳郡信巫尚鬼,与楚同风,而祀典所载、赫赫照人耳目者,正不可废;岁遇水旱、疾疫,有求辄应,有祷必灵,其为功于兹土也大矣!倘祠宇不修,执事罔恪,何以答神贶乎?②(清)王锦修,吴光昇纂.乾隆柳州府志卷十七坛庙[M].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再如雍正《平乐府志》卷14《祀典》的序言说:
中宪大夫广西平乐府知府胡醇仁重修祀典。祀典之设,以为民也。故《祭法》曰: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以此为祀典,亦重矣!③(清)胡醇仁纂修.雍正平乐府志卷十四[M].雍正四年刻本.
根据明清时期广西各府志《祠祀》部分的内容,可以发现其记载的祠庙主要包括城隍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纛神庙、先师庙(文庙)、文昌祠、名宦祠、乡贤祠、伏波庙(伏波祠)、陶使君祠、关王庙(关帝庙)、天妃庙、玄帝庙(真武庙)、火神庙,以及各州、县的城隍庙、旗纛庙、名宦祠、乡贤祠、怀忠庙、厉坛、风云雷雨山川坛、社稷坛、先农坛、八蜡庙、龙王庙、药王庙等。
具体来看,儒家祠祀体系首先遵循国家祀典的基本框架,记录了纳入国家祀典的祠祀,包括敕建的或由儒家礼制直接统摄的官方祠祀,包括社稷坛、山川坛、厉坛、文庙(先师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等。这类官方祠祀级别较高,往往有配套的祀典加以维持,例如府级城隍庙的祀典就有一套高规格的祭祀礼仪。【要求作者补充时代信息】《南宁府志》卷5《祀典志》记载:社稷坛,在府城外东北二里,坛如制,其主各为一牌,题曰府祀之神、府稷之神,春秋卯酉上戊日致祝文行礼各见仪计。再如府级社稷坛的祭祀规格,据乾隆《梧州府志》卷7《建置志·坛庙》记载:“(梧州)府社稷坛,祀五土、五谷之神,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五土也。稷、稻、麦、菽、黍五谷也。郡坛建于洪武七年,在大云门外,元至元二年颁诸路立社稷坛壝式,贞元二年议社稷二坛,方广视太社、太稷杀其半,三献,官以州长贰为之。明初颁降图式,国朝之制,坛高三尺四寸,陛四级四方,各二丈五尺,以北为前,南为后,缭以垣而丹雘四门,由北门入,神以柱石为主,长二尺五寸,方一尺。”①(清)吴九龄修,史鸣皋纂.乾隆梧州府志卷七[M].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再如光绪《镇安府志》卷14《坛庙》记录了当时县级社稷坛的祭祀规格:“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帛二,俱黑色,豕一,羊一,鉶一,簠二,簋三,笾四,豆四,尊一,爵六,先期致斋三日,祭日主祭及陪祭各官俱朝服,行三献三跪九叩首礼。春秋二祭。”②(清)羊复礼纂修.光绪镇安府志卷十四坛庙[M].清光绪十八年刊本.这类规格最高的祭祀,都是国家祀典的内容,需定期派遣地方官员致祭。
其次,是为曾在桂任职、颇有善政的人物修建的祠宇,属于官方祠庙(官祀)。这类祠庙奉祀的神灵多为历代贤臣、名士,当地民众因感念其功德而立庙奉祀礼敬。这类庙宇包括乡贤祠、名宦祠和其他一些经由国家批准,获得赐额甚至纳入祀典的专门祠庙,例如柳侯祠在柳州府城东,祀唐刺史柳宗元;陶使君祠在南宁府城内,祀宋知州陶弼;廉州府学名宦祠,祀汉伏波将军马援、汉合浦太守孟尝等,廉州府祭祀前代或当朝贤良之祠,还包括郭公祠(祀明太史郭廷良)、游公祠(祀明太守游日章)、冯公祠(祀明太守冯盛典)、沈公祠(祀明太守沈纶)、戴公祠(祀明谪官戴士衡)、罗公祠(祀明石康县令罗绅、罗鉴父子)等。这些祠祀崇奉的人物皆为历史上在当地有惠政的官员。
再次,广西地区还有大量与江河水系环境息息相关的祠庙,多为朝廷赐额的“正祀”,包括真武庙(玄帝庙)、龙王庙(龙神庙)、丁王祠、水神庙等。正是由于广西地区河流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出现了大量奉祀各种水神以祈求水运平安、风调雨顺、农渔丰收的庙宇。在这类水神祠祀中,祭祀规格较高的当数真武庙。真武帝君(玄帝、北帝)是北方玄冥水神,为宋代以后的朝廷所重视,同时也是道教崇祀的神灵,常由道士和道教信众参与礼仪实践。明代以后,中央和各级政区主要的真武祠庙都被纳入国家祀典,采用儒家祠庙礼仪进行崇奉,得到皇室、地方士绅民众的普遍奉祀,在广西地区亦十分盛行③参见王群韬.明代桂林府真武信仰与崇祀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5(11).。因此,方志编纂者多将真武庙列入儒家祠祀系统的《祠祀》《坛庙》,而不列入佛道信仰系统的《寺观》。例如雍正《太平府志》卷18列有《坛庙》和《寺观》,即把太平府城内的真武庙列在《坛庙》之下④(清)甘汝来纂修.雍正太平府志卷十八坛庙[M].清雍正四年刻本.。另一个典型的水神祠祀是丁王祠(丁王庙)。“丁三郎,不知何时人也。相传一日庐舍忽沉,举家尽为冯夷所劫,其地化为百寻深潭,因名丁塘(在今灌阳县新街镇虎坊村),秋水澄澈,乡人偶有见其庐舍者,志若显圣,洞庭楚人像祀附于湖之龙王庙者,本系三国吴丁奉,非灌之丁三郎也明甚……故乡人祀之,遂谓三郎殁为水神,嗣是全灌渡湖者,具名投祠瞻拜,从无风波之险。商舟有搭全灌人,亦私窃喜,清封为靖江王,立有专祠。”⑤于凤文等.灌阳县志卷二十三[M].民国年间刻本.
此外,明清广西方志中还记载有一些富有地域特色的祠祀,如岑土府祠(祀岑氏土司先祖)、武婆庙(祀地方俗神)、盘王庙(祀瑶族祖先盘王)等。这类民间祠祀种类繁多,遍布各府州县及乡村地区,或许与“百越之俗尚巫”的传统有关。然而这类民间祠祀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官方的正式赐额,例如岑土府祠,可以视为儒家礼仪主导的地方祠祀;其他的一些民间祠祀,虽然被记载在地方志中,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处于儒家祠祀体系边缘的民间私祀。
三、明清广西方志《祠祀》书写体例的特征
明清广西方志之《祠祀》书写,一般包括祀典规格、祠宇名称、地理位置、创建沿革、存废状况等内容,有的方志还会在祠祀的基本信息之后附以碑记或简要的考证。儒家祠祀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场所——佛教的寺庙庵院和道教的宫观,方志多以《寺观》记载之。儒家礼制主导的祠祀与佛道教的寺观庙宇,在方志的书写过程中一般有着程序化的区分,不会相互掺杂,体现了明确的条理性。从笔者所见明清时期广西各府志的具体情况来看,《学校》《祠祀》《寺观》的卷次安排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兹列为表1。

表1 明清广西各府志中《学校》《祠祀》《寺观》卷次一览表
据表1可知,明清广西各府志之《学校》篇目通常居于志书中靠前的位置,多以《祠祀》继其后,因而《祠庙》部分所处卷次位置往往与《学校》篇目存在一定的联系,内在地构成了“文教—祠祀”的体系框架。甚至在许多广西方志中,文庙(先师庙)、启圣祠等祠祀一并记载在《学校》类下,而不列入《祠祀》。这种“文庙不列祠祀”的现象,显示出“重道”的观念。例如崇祯《廉州府志》卷5云:“名宦祠、乡贤祠,俱见学校。”①(明)张国经纂修.廉州府志卷五礼教志[M].崇祯十年刻本.光绪《镇安府志》卷14《坛庙》也说:“名宦祠在学宫内,乡贤祠在学宫内。”正是由于这类祠庙与学校、书院等儒家文教机构紧密相关,形成了一种“庙学复合”的体系。实际上,自隋唐以来,广西各地逐渐设立文庙,文庙依靠政治的支持和科举制度的激励,与各级官学在某种程度上合而为一。相比之下,除了少数方志将《寺观》与《学校》《祠庙》列于同卷,大多将《寺观》安排在靠后或接近志书末尾的位置。这种卷次篇目与书写体例,是明清时期方志中较为常见的固定模式,以显示儒家祠庙及学校的地位尊于佛道寺观。
这种书写体例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可以比较详实客观、条理清晰地记载该区域的祠祀状况。广西方志的编修者多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官员或儒生担任,他们熟悉儒家礼仪传统和国家祀典仪式,并掌握地方信息,对境内祠祀进行过踏访,加之编修方志所依据的历史材料多来源于政府公文、地方档案等,可信度较高,因而对当地祠祀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广西方志记载的儒家祠祀中包括大量祭祀名宦、圣贤、节孝的祠庙,即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准则的记载,具有昭示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淳化风俗的现实意义。通过呈现人文教化和崇德报功的观念,具有淳化风俗、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广西方志所见儒家祠祀体系,呈现了儒家礼法主导的地方祀典体系的基本格局,并与中央祀典相呼应,是国家祠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国家官僚制度、文教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一套以“尊贤重教”“崇德报功”等宗法原则和伦理观念为基础的政治教化与礼制框架。
在祠祀的具体内容上,广西地区的儒家祠庙不仅具有国家祀典的一般模式,还体现出许多地方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广西各府州县的祠祀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例如伏波祠集中于桂林府,柳侯祠多分布于柳州府,土司庙宇主要在桂西地区等,这种格局体现了地方祠祀在区域内的差异性。从进入地方志记录体系的祠祀种类来看,许多是获得前代或当朝正式“赐额”的“正祀”,具有浓厚的儒家祠祀礼仪元素①“赐额”即由朝廷正式赐予庙额及封号。唐宋以后,赐额(赐号、册封)制度成为将民间祠庙纳入国家祀典的主要途径,广西社会形成了一套具有强烈地方性、民俗性的基层祠祀体系,是否持有前代或当朝赐给的庙额,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祠祀的兴衰。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在对宋代以来地方神祇获得赐额的研究中发现,儒家士大夫、地方精英和当地民众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8—92页。。此外,还有很多民间社会建立的祠祀,处于儒家祠祀体系的边缘,有时甚至被官方视为荒诞不经的“淫祀”。祠祀的建立,主要是出于儒家忠孝仁义等道德伦常,尤其是中国民众“崇德报功”这一核心观念②张志刚.“中国无宗教论”反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乾隆《梧州府志》收录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陈天植所作原序云:“崇祀典以报功德。”③(清)吴九龄修,史鸣皋纂.乾隆梧州府志原序[M].清同治十二年刊本.自古有功德于民者,民众往往感念其恩德,而尊奉其为“神”,立庙祀之。此种“崇德报功”的观念,发乎人心公义,构成了中国古代民间祠祀的重要基础,通常能够得到儒家士大夫的认可。这也是《国语·鲁语》中“圣王制祀”传统的基本内涵:“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④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61.换言之,一些地方神祠即使不在国家祀典、无朝廷赐额,但因“有功德于民”,而为当地民众自发祭祀或具有悠久的崇奉传统,地方志编纂者往往记录之。
在方志编写体例上,文庙(孔庙)、启圣祠、乡贤祠等与儒学机构(学校、书院)紧密相关的祠庙往往归入《学校》篇目记载,而且《祠庙》篇目多位于《寺观》之前,都是明清时期方志编写体例相对固定的模式。总体来看,由于方志编纂者主要是地方官员、士绅、儒生,因而方志的书写方式蕴含着政治教化、宗法制度、宗教信仰与社会礼俗的内在框架,也是儒家知识精英文化与地方社会文化包括民众文化之间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体现了广西方志编纂者对地方祠祀文化的整体认知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