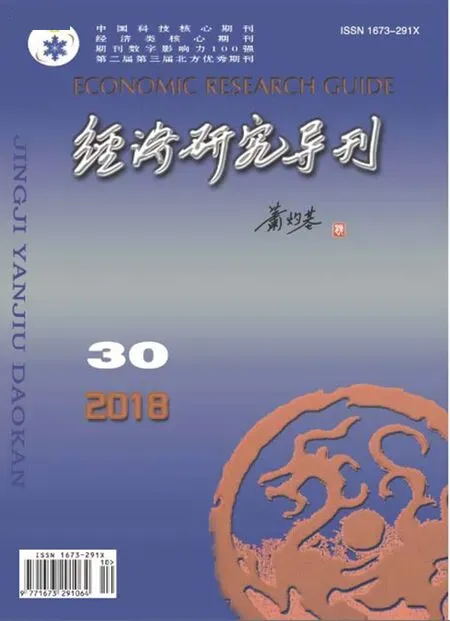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路径构建
2018-12-06杜良杰
杜良杰,周 怡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提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新背景下,如何管理好流动人口群体、实现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贵阳作为贵州省内唯一的大型城市,外来农民工不断增加,其住房、就业、收入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2017年,贵阳市委、市政府提出开展城市“三变”改革,以此全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目前而言,贵阳推行的城市“三变”改革,更多的还是市民的加入,如白云区的“梵华共享”项目,实际上作为收入低微的流动人口还未能参与进来。因此,为顺利实现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本文拟从理论层面探讨贵阳市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可能性。通过探索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影响因素和路径,以期为政府构建促进公平分配、先富带后富的有效手段提供思路,力推城乡融合发展。
一、文献综述
当前,具体从城市“三变”改革这一视角研究流动人口的文献还没有,但针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社区参与等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深入。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城市流动人口迁移决策主要受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1]。流动人口的差序格局会影响其城市融入[2]。个体层面的性别、婚姻年龄等因素及家庭层面的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状态有显著影响[3]。除个体特征外,有学者认为对法律规范以及现代城市组织有较多的了解、家庭经济收入高以及有正能量的流动人口相对容易融入城市[4]。
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研究。通过提升公民素养、提高社区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自身建设、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能有序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5]。有学者基于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探寻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途径[6]。学者认为,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制度性身份是影响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核心变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受其所居住的社区场域的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城市意愿和本地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7]。
二、贵阳市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可能性分析
(一)“推—拉”理论: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双向性
就“推—拉”理论来看,流动人口往往是从成本和效益角度进行流动决策的[8]。因此,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往往同时源自于外部的机会和个体层面的发展诉求。首先,作为城市“三变”改革载体的社区组织要承认并重视居民流动人口参与的权利,为流动人口提供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平台和机会,鼓励流动人口参与改革,从而提升流动人口的社区组织归属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流动人口需要树立参与城市“三变”改革集群发展的意识,作为行动者而不仅是成果的接纳者参与其中,在参与过程中实现权力并获得自身发展。
(二)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内因:流动人口的能动性参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显著,而性别和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有一定影响[9]。据此,笔者推断贵阳市流动人口参与城市可能性与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有一定关系。其中,流动人口年龄阶段的不同,思想有所不同,其追求梦想可能有较大差异,参与城市“三变”改革可能性也不同。其次,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等级越高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思想层次就越高,理解能力越强,这部分流动人口也就更可能主动参与到城市“三变”改革。较高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较为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其生活圈也就较稳定,也更可能参与到城市“三变”改革。就性别而言,女性受家庭、婚姻因素影响大,其受到的约束或就更强,所以性别对于其参与城市“三变”改革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另外,已婚流动人口更趋向于成熟和落户城市,所以参与城市“三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流动人口在流入时间长短和个人月均收入对城市融入影响显著[10]。所以,贵阳市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工作时限与工作收入也可能对其参与改革有影响。在城市待时间较久的流动人口,自身积累的资源可能更为丰富,也就有更多资源入股企业、合作经济组织,获得更多收入,因而更倾向于参与城市“三变”改革。而有较高收入的流动人口,也有更充裕资金可入股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企业等经营主体,预期收益更高,所以也就更愿意参与城市“三变”改革。
2.外因:外部环境的导向性。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受到结构约束的影响[11]。良好的结构整合主要是指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协同契合:政府政策规范、许可、激励与引导,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市场机会公平、创造、拓展与丰富;社会多样性且包容力大,共容性空间大。政府系统、市场系统、社会系统内部整合良好,三个系统之间契合度高。如果三系统的力量较为协调,整合资源的能力较强,共同作用形成较好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风险机制、退出机制,更好的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形成良好的外部条件,流动人口就更可能参与到城市“三变”改革。反之,如果上述三个系统之间或者内部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结构整合比较差,外部环境堪忧,流动人口对参与到城市“三变”改革会有诸多顾虑,其参与的可能性会受到消极影响。
三、贵阳市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路径探讨
(一)贵阳市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原始路径探讨
原始路径,即流动人口—市民化—城市“三变”改革,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流动人口—市民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2];二是市民化—城市“三变”改革,即通过市民化后获得相应的市民权,也就恰好符合城市“三变”改革中提出的“市民变股东”。如此,流动人口就能更广泛和稳定的参与到城市发展中,参与到城市“三变”改革。总体而言,此路径属于渐进性的参与过程。
1.流动人口市民化。基于现实的制度困境,笔者提出贵阳市流动人口市民化的三个途径:其一,顺应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把握贵阳加速发展的阶段特征,科学选择城市化发展战略,走多元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把城市圈发展与城镇城市化发展相结合,构筑科学的城市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等级城市吸纳和承载人口的作用,如贵安新区的打造。同时,培育就业取向的城市主导产业,扶持城市非正规经济主体的发展,并通过城市间纵向产业链的联结和延伸,为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定居融入城市提供机会。如贵州黔中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的打造,立足黔中经济区大背景下做出的一项加快融入黔中经济核心圈,实现与贵阳同城化发展的战略举措。其二,以农民工权利复归和制度重构为途径,进行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农村退出的土地制度、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城市融合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住房、教育等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创新,优化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制度环境。其三,以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为途径,增强流动人口市民化所需要的城市进入的职业转换能力、城市生存的获取稳定就业和收入的能力、城市融合的发展能力,包括反映其经济地位变化的比较收益的决策能力、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谈判能力、交易能力、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反映其政治地位变化的参政议政能力、自我组织能力、自我维权能力;反映其社会地位变化的社会交往并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自我抱负与人生目标实现的能力,以及改变歧视的“可行能力”。
2.流动人口市民化后的城市“三变”改革参与。本路径的第二阶段,首先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城市“三变”改革中,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进行顶层设计,坚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引领发展。政府整合流动人口分散的资源、激活资源活力、释放资源红利,政府资源和资金向这一群体倾斜。同时,政府聚集分散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改善城市环境、完善社会功能,提升城市供给质量。
然后,社区经济组织和市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创新完善基础治理体系,激活基础社会活力。将政府依法依规配置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事业资源和政策资源等公共资源使用权,以及发展资金通过股份投入享有股份权利。发展壮大社区经济,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增强基础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使得市民化后的流动人口更为自愿的将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知识产权等,通过与社经济区组织、市民合作经组织订立协议等方式,入股经营主体。
(二)贵阳市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绿色路径探讨
1.绿色路径:直接参与。绿色路径是流动人口—城市“三变”改革,即直接参与的过程,此路径可以理解为突发式参与。首先,让流动人口在参与城市“三变”改革后,再考虑其市民化的问题。通过上文对城市“三变”改革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简要分析,此处可理解为先让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就是在促进其市民化,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绿色路径相对原始路径可能更为省时有效,但同时需要认识到的是,此路径对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社区经济组织的治理体系要求更高。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基础党组织的管理体系,完善社区经济组织基础治理体系,是走此路径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需各参与主体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发展。
2.流动人口参与的多样化模式。在有政府、企业、市民、经济组织、流动人口等多主体参与的城市“三变”改革中,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可呈现“三变+”多样化模式。社区经济组织等主体为载体,流动人口参与发展分享红利。如“三变”+政府+企业+流动人口、“三变”+流动人口、“‘三变’+……”等。无论任何模式,其实都需政府扶持。流动人口参与城市“三变”改革的模式可能是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同,运作方式也各有不同,但究其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增加流动人口收益。
四、结语
原始路径、绿色路径是两条有区别性的参与路径,原始路径主要考虑从市民化这一渐进实现途径,流动人口—市民—股东。绿色途径则是考虑让流动人口直接变股东,跨越户籍制度的约束。两种途径各有优劣,但发展条件亦各有差异。不可否认的是,两条路径的具体推行以及发展条件需要基于实践作进一步研究。同时,不管是流动人口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城市“三变”改革,都应关注其内外部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