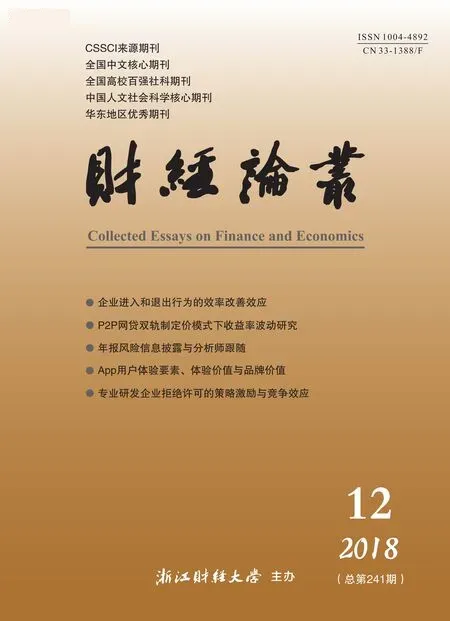基于赛斯模型的最优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研究
——以工资、薪金为例
2018-12-04李香菊郑春华
李香菊,郑春华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引 言
公平和效率是税制设计永恒的主题,不同的税制结构往往是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期对二者权衡取舍的体现,常因不同的政策意图发生变化。个人所得税由于其税基广泛、税率累进等优点,在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筹集财政收入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自1980年设立以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其不足之处常常引发社会热议,包括分类税制难以体现量能负担、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导致的税负不公、累进税率级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等等。税率高低是个人所得税的核心,税率过低影响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过高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拉弗曲线告诉我们过高或过低的税率都会影响财政收入,因此税率是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的关键,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最高边际税率也备受关注。为避免税率设计的随意性和武断性,需要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理性、严谨的方法进行计算。那么,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应该如何选择呢?本文将结合我国改革方向,应用赛斯的非线性所得税理论对其进行研究,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最优所得税理论的研究逻辑严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认为,最优所得税理论研究始于埃奇沃斯(Edgeworth,1897),他选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界定了社会效用(即个人效用之和)最大条件下的税收为最优所得税,其研究表明最优所得税下的人均税后财富相等,所得税应使用多级次高税率的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应为100%。其理论虽然考虑了社会福利和公平问题,但缺乏对效率的考量使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埃奇沃斯之后,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同时兼顾了最优税率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其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资源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得到了三个结论:(1)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线性所得税率表(对不同的人应用不同税率组成的税率表),并且政府应实行负所得税制度(政府补助那些低于免税水平的人);(2)所得税并不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工具;(3)应当进行与所得税搭配的税制设计,从而弥补所得税的缺陷。米尔利斯的理论启发了诸多学者,之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转向研究线性所得税模型,如斯特恩(Stern,1976);二是放松米尔利斯模型的假设继续研究非线性所得税模型,如戴德蒙(Diamond,1998)、赛斯(Saez,2001)等各自提出了理论模型,在米尔利斯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完善。其中,赛斯(Saez,2001)将劳动供给弹性引入到最优所得税的理论中,并用1992年和1993年美国纳税申报资料报道的年度薪金收入拟合出最优边际税率曲线。他认为用劳动供给弹性对最优边际税率的研究可以准确表明不同的经济效应如何影响最优边际税率选择,其计算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和收入分布的形状,借此拟合最优边际税率曲线,而其方法也能用于其他税种[1]。
我国最优所得税的研究主要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应用的。郭庆旺(1995)对最优所得税理论进行了基础理论阐述[2][3]。杨斌(2005)对西方最优所得税理论及进展进行系统评论、评析和论辩[4][5]。彭海艳(2014)分析了社会福利函数、技能分布、效用函数以及劳动供给弹性等最优税率的影响因素,对最优所得税理论进行深入评析[6]。郝春虹(2006)阐述了其对米尔利斯模型和斯特恩模型的理解,借鉴斯特恩模型的方法及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经验,认为我国最高边际税率还可以适当下调到36%左右[7]。邓子基、李永刚(2010)介绍了斯特恩模型并估计了我国和部分国家所得税最优税率,认为毋须严格按照这些模型来设计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但其税制设计理念或思想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8]。杨武、刘振亚、李升(2014)在赛斯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高收入者收入的帕累托分布现状,并使用我国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对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进行了测算,显示我国当前“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税率45%偏高,应适当降低至35%~40%[9]。诺敏、张世伟、曙光(2016)根据最优税模型计算出最优税率,并以此计算新的模拟税率表对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进行改进[10]。
通过整理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的解读拓展、定性分析、部分模型应用及改进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表上。然而,将收入分布相关数据应用于赛斯模型计算我国最优税率的文献较少,存在较大空白,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研究的文献更是寥寥。本文在赛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下,使用CHIP2013项目提供的数据作为收入分布数据,结合我国个税改革方向,计算最优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我国个税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三、赛斯非线性所得税理论简析
赛斯认为,对于某个给定收入水平,其边际税率τ的增加会引起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税率增加使收入水平高于的纳税人支付的个人所得税增加;另一方面,税率增加导致劳动力减少劳动时间,致使劳动收入减少。当边际税率τ的微小变化引起的这两方面效应相等时,此时的τ即是最优税率。为了计算τ,他引入了弹性方法。
将包含个人技能的效用函数设为消费c和收入z的函数:U=U(c,z),假定个人面临一条线性预算约束:c=z(1-τ)+R,其中边际税率为τ,非劳动收入为R。则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1-τ)uc+uz=0,其可以推导马歇尔(非补偿)收入供给函数z=z(1-τ,R),且可得非补偿弹性定义为:
(1)
收入效应为:
(2)
补偿弹性为:
(3)
根据斯拉茨基方程有:
ζc=ζu-η
(4)

(5)
税率增加导致劳动力减少劳动时间,从而使劳动收入减少。个人收入变化量为:
(6)
其总效应为:
(7)

(8)

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税制设计在公平和效率上的权衡取舍问题。赛斯在他的模型中以高收入纳税人的社会边际效用与政府公共资金的边际价值的比值作为公平理念的体现,是社会福利函数的量化选择,引入劳动供给弹性表示增加边际税率导致纳税人工作时间减少的效应和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效应相等,以此作为效率理念的体现,计算最优的最高边际税率。相比于前人,赛斯将劳动供给的非补偿弹性和补偿弹性引入最优所得税公式的推导,从而简化最高边际税率的计算,他还依此用美国数据拟合出最优边际税率曲线,其方法具有通用性,适用于影响纳税人劳动供给的所得税,而不受具体税目影响,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四、数据来源和处理
使用赛斯模型计算适用于我国国情的最优最高边际税率,需要针对国情对数据进行处理。税制设计中,准确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实现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的出发点。赛斯的理论中,所得税改变了劳动收入从而影响劳动供给弹性,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反映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应纳税额,而不是具体税目。本文的目的在于结合个税改革方向提出政策建议,因此并不严格按照现行税制而是选择更能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包括以家庭代替个人为纳税单位、以年收入代替月收入作为收入分布等,这也符合最优所得税理论对公平和效率进行权衡取舍的思想。
(一)纳税单位的选择
我国个人所得税采取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它具有简便、容易征管的优点,在我国设立个人所得税制之初是符合国情的做法,但弊端在于忽略了不同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和实际负担,并不能体现量能纳税的原则,在征管过程中造成一定的不公平,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如今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过高,迫切要求对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纳税单位进行改革。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细胞,是经济行为、社会行为的基本主体。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纳税人的生活质量、消费水平受家庭成员的收入结构、年龄阶段、子女教育、健康情况等影响,个人的收入差距、福利水平不能代表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相同收入、不同家庭结构的个体,其经济负担不同,纳税能力也不同。例如,同为月收入5000元,一个单身纳税人和一个三口之家的男主人,其经济状况、生活质量和税负情况显然不同。从这一角度来讲,相比于个人,纳税人的收入和支出以家庭为单位更有利于保证纳税人的生活福利均等,体现公平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另一方面,家庭观念是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础,汤洁茵(2012)认为,在家庭这个共同体之下,配偶双方必须根据家庭的总体成本——收益的分析,决定包括市场工作、家务劳动、家庭闲暇、人力投资在内的家庭活动的安排以及不同家庭成员之间在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并最终决定家庭的总收入和总支出[11]。在我国,家庭成员的行为决策以家庭总收入为依据,而家庭收入极少区分来自哪位家庭成员,以个人为纳税单位事实上与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相冲突。除此以外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包括婚姻中性原则和女性职业自由的争论,婚姻家庭的保障、申报程序的简化以及家庭养老负担等视角进行讨论,认为以家庭为纳税单位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二)年收入和月收入的选择
数据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年收入与月收入的选择。一方面,按月计征的方式有诸多缺陷:除行政单位和部分事业单位外的纳税人,由于行业生产经营的月度差异和周期性导致的淡旺季或工资制度改革导致的月度工资差异明显,由此造成年工资总额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税费不同;同时,按月计征比按年计征更耗费成本,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偷税漏税行为的诱因;工资按月发放或某月集中发放的形式不同也会造成纳税人缴纳税费的差异[12]。另一方面,我国工资和年终奖在我国采用了不同的征税方式,造成年收入相同而月收入不同的纳税人存在税负差异,同样有悖横向公平原则。朱为群(2017)认为对年终奖按年计征有利于解决月收入波动导致的税收不公平问题,按月计征的税制,对于年收入相同的两个人,收入波动大者所纳税额大于收入稳定者,造成了横向上的不公平[13]。学术界也存在不少关于工资和年终奖分配方案的研究,但笔者认为将年收入代替月收入,不仅有利于简化税制,更有利于消除工资和年终奖因不同征税方式带来的税负差异,贯彻横向公平原则。因此,笔者选择按年计征的方式处理数据。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另一呼声是由分类所得税制转向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本文是以我国工资、薪金为例进行计算,但由赛斯的理论可知其方法具有通用性,在综合所得税制情况下依然适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鉴于以上原因,笔者选择CHIP2013项目提供的数据进行收入分布数据的系数计算。
CHIP2013项目的样本来自国家统计局2013年城乡一体化常规住户调查大样本库。该项目中住户成员是指居住在一个住宅内,或与本住户分享生活开支或收入的所有人员,包括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还包括:由本住户供养的在外学生,未分家的外出从业人员和随迁家属,轮流居住的老人,临时外出的人员,以及其他长期居住在一起并共享收支的人。对于具有事实婚姻关系的同居者,应算入家庭成员。由此可见该样本能满足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要求。本文以工资、薪金为例,选择家庭收入的工资性收入作为研究对象,剔除工资性收入为负值的,取得样本量18198个,将数据依据当前税制还原为税前收入。
五、最优税率设计
(一)相关系数取值




(二)结果与分析
运用上述系数取值计算可得:

表1 税率表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赛斯的最优所得税理论,结合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以年收入为研究对象,以工资、薪金为例,计算了不同收入分布情况、不同社会福利函数下的最高边际税率,认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目标下,现行的45%最高税率仍有下调空间。在分类所得税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方向下,该方法仍然适用。具体结论如下:
赛斯的非线性所得税理论引入了劳动供给的非补偿弹性和补偿弹性,选用合适的社会福利函数,以此兼顾公平与效率。本文虽以工资、薪金为例,但其适用范围不局限于税目,在我国由分类所得税制转向综合所得税制的改革进程中,依然适用;计算适用于高收入人群的最优边际税率时,还需要考虑到整体纳税人的收入分布状况,而不能仅仅通过划线定义高收入人群;社会福利函数是公平理念的体现,其选择对最高边际税率影响很大,对高收入人群赋予的权重越高,最高边际税率越低。
赛斯在该模型中对效率原则的体现仅在于高收入人群提供的税收收入的最大化,是政府税收收入和劳动供给的权衡取舍,但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问题,也没有将获取信息的成本、行政成本考虑在内。最优解的计算是依托于严格的数学方法计算极值得到的结果,其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可能存在偏差,考虑到为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人才在经济发展中带头作用,直观上认为实际结果应比表1所示更低;赛斯的理论模型依然存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缺陷,是建立与在一系列严格假定条件上的推导,在难以满足假定条件的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的税制改革。
在中国贫富不均加剧的社会环境下,高收入人群往往代表更高的生产能力,过低的税率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过高的税率则影响生产效率,如何赋予其适合的社会福利函数实现全社会对公平和效率的权衡抉择是设定最高边际税率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赛斯的最优所得税理论并不能完美解决实践问题,而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