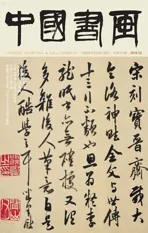中国艺术的理想(第十四讲)
2018-12-03主讲人刘墨
◇ 主讲人:刘墨
◇ 时 间:2018年9月10日15:00—17:00
◇ 地 点:《中国书画》美术馆

第十四讲主讲人
“艺术”是什么?西方说到“art”的时候,指的只是和手工有关的—手做出来的叫艺术,用嘴唱的在舞台上表演的,都和“art”不是一回事。《论语》里面讲孔子“吾少也贱,故能鄙事”,以及“吾不试,故艺”,这个“艺”,就是技术或手工艺的意思。《晋书》里面有《艺术列传》,但那里没有王羲之,没有顾恺之,收在里面的人是算命的、看相的、搞建筑的、做园林的、治病的。所以在中国,最早的“艺术”就是“杂艺”(役),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完全两回事。
艺术确实是从一门技术开始,不断地向一个人的学问、一个人的修养和智慧靠近,尤其是向一个人的情绪靠近,艺术慢慢和人性有了非常大的关系。
英国人赫伯特·里德,写了一本书《艺术的真谛》,他讲,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艺术表现的是“永恒的人性”。他说:比起历史学,比起哲学,比起其他学术,艺术是检验人类精神幻相的确切证据。这句很有意思。我们看画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真山真水,但从里面会获得很多真山真水所没有的东西,看到诗,看到笔墨,看到风格,看到个性。但它是一个幻相,它只提供一种幻相。
如果仅仅是一个幻相或者毫无意义的墨迹,艺术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但是,它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的精神幻相最直接的证据。
中国艺术的理想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传统有两部分,一部分叫作“大传统”,一部分叫作“小传统”,当然,“大传统”不等于很大,“小传统”不等于很小,它只是人类学家的划分:大传统属于思想传统,比如我们经常说中国思想里面儒、道、释;小传统是民间信仰,巫术。我们的艺术理想,是由“大传统”决定的。
儒家首先有原始儒家,就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孔子设定了“仁”。这个“仁”和元旦的“元”有什么联系?从文字学角度看,“元”字也是两个“人”。在儒家的经典里,我们说这个人很仁爱,这是仁的根本。元气的“元”是“气”的根本,因而这个根本的东西,在自然界里叫作“元”,在人类就叫作“仁”。这个“仁”不仅仅是仁慈,是道德,还是人和天地之间的生机。我们把果核叫果仁,它是一粒种子,一种生机,一种能够成长的力量。所以当你说“仁”的时候,不仅仅是德,不仅仅是慈爱,更多是一种来自天的力量,是一种生机。到了宋代,有程朱理学,有朱熹、陆象山,然后明代有王阳明。王阳明了不起,他认为他的学问直接从孔子那里来,甚至直接从朱熹那里来。他讲“良知”,这个“良知”实际是孟子讲的。孔学里有一种是向外的,有一种是向内的。向外的是,你要一条一条去认识世界的道理,比如竹子是怎么长的,松树是怎么长的,桃花什么时候开花。所以宋人特别具有科学精神,因为他几乎要把每件事情都弄清楚。朱熹的教导,就是要把每一件事都弄清楚了,才会成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接近于圣人的人。王阳明年轻时和他一个朋友说朱熹的“格物”,竹子究竟怎么回事,我们来“格”一下。中国人最早把物理学译成格致学。“格物致知”,就是你要到生活那里去调查,然后你才会获得知识,这就是格致学。王阳明就对着这个竹子不停在那里“格”,不吃不喝,也不睡,晕头胀脑,后来终于病了。他开始回到自己的内心,他相信自己的内心有真正的力量,而且他正是因为从心的角度判断人,或者判断事物,就有了很多新的发现,或者说,发现了“心”的力量。
北宋的《溪山行旅图》《早春图》为什么到了元朝会变成《富春山居图》那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倪瓒那个两岸一河、寥寥几笔几棵树,一个小亭子,几块石头?为什么慢慢又会变为后面的册页和小手卷?如果从纯粹绘画史的角度上来讲,它可能是一种“视觉的退化”,如果我们把绘画仅仅认为是一门视觉艺术,它的确是一个“视觉退化”,但是当我们离开技术,离开视觉,回到内心,回到中国思想最高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减低视觉,恰恰是为了突出心灵的意义,而且恰恰是为了能够让人的情绪得到一种更充分的发挥。所以,我在写《中国艺术美学》的时候曾经提出,它是为了削减迹象以增加意境,拉低视觉以提升心性,解放心性。因此文人画,它不是一个退步的过程,它是一个把自己的情绪完全释放出来的过程,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得到更自由发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如果读朱熹的书,你会发现,朱熹格物致知,偏向于“自然之性情”,郭熙、范宽这些人都偏向于自然山水的性情,就是春夏秋冬的四季山水,类似于人的种性情。可是朱熹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回到人本身,回到内心,回到生命的时候,他说“性情之自然”,人的喜怒哀乐也如春夏秋冬。这个转换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换,就是从把自然比成人,到把人比成自然。这从思想史上,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宋代的山水画从那种严谨、科学开始向南宋以后尤其是元代的松动和性情过渡。
这一点不仅仅有儒家在里面,更有道家的思想在里面。
说到道家和儒家的区别,有一个小故事:当老子在洛阳做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曲阜的孔子千里迢迢去拜访老子。等孔子走了之后,据说老子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不要去学那个家伙,满脸都是功名利禄,整天得不到安宁,想干这个想干那个,千万不要去学—这个小故事很好说明了儒家和道家的本质区别。中国文人从本质上讲,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失意的时候是道家,既不得意也不失意,是儒也是道,苏东坡就是这么个人物,高兴了就儒家,不高兴了就道家,能做事就做事,不能做事就不做事。所以中国人骨子里面,就融合了道家和儒家两种天然的成分,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儒道互补”。
从哲学角度说,我们总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古人不这么问的,古人不下定义—这是中西哲学思维非常大的区别。有人总问什么是“仁”?“何为仁?”孔子不答。禅宗更明显体现了这一点,“不可说”。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思维尤其是哲学思维里面一个很有趣、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追求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一直否定,一直追问到不是什么,这才问到本质。它里面有某种高妙的、玄妙的东西。所以在道家思想里,它一直在追问你,不是让你回答“道”是什么,而是回答“道”不是什么。
这种思维也影响到禅宗,你说是这个,是那个,都不是,所以总是“非也,非也”。印度哲学也这样。所以你读佛经,法,非法,非非法,非法法也……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很绕,可是它不停给你否定那些你认为的东西,一直到你认为不是了,可能才是真正的东西。听起来比较拗口,但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去思考这些问题时,很快乐,很有趣。
道家思想在老子那里,就是要否定一切人为的规定,因为所有的“是”和“不是”都是人为的规定,都是概念,而我们往往是因为规定和概念而吵架,道家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打掉。到了禅宗,打得更彻底。
如果老子让我们去寻道,到茫茫自然、宇宙中去追寻道的话,到了庄子那里,已经把这个“道”安放在我们内心。“道”太远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庄子却告诉我们,“道”就在你的内心,“心斋”—只要心里面有这个东西,实际上就等于已经靠近了道,甚至道就在你的内心里。
当庄子把这个道安放在人的内心的时候,内心的体验就变得无比重要。我们可以从《富春山居图》上看出来。现在很多专业画家,比如说备战全国美展,先收集素材,再考虑主题,接着至少用半年时间不停地画,然后送展,希望得奖。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而言,这只是一个制作或创作的过程,它不是生命的审美体验过程。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画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境,那种体验,那个过程,所以《富春山居图》迟迟画不完……
古人审美体验的过程,远比结果重要。苏东坡不能喝酒,大概端起小杯子三两杯,然后找个地方就酣声如雷,睡得快醒得也快,醒了之后就找纸,要么写要么画,一会儿扔一地,“不计工拙”,好坏无所谓,谁愿意拿谁就拿走。苏东坡的作品如此精彩,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下创作出来的。他就是要这种感觉,以一种审美游戏的态度来完成他的审美体验。我们现在的绘画,已经忘了这一点!
世俗有很多诱惑,但是道家会告诉你远离这些诱惑,而且道家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推崇“妙”,不推崇“巧”,推崇“奇”,不推崇“怪”。这人长得很怪,那不行,长得奇,是称赞。说他的画很丑,可以;画得很怪,就不行。除了推崇妙,推崇奇,还推崇拙,推崇朴,推崇重,推崇大,始终向最厚重的那一面去发展。
我们总想用技巧达到技巧达不到的境界,实际上我们想达到的恰恰是小孩达到的境界,即所谓的“天真烂漫是我师”,小孩表现的就是这个境界,他不需要任何技巧作为中介。
技巧越多,离我们的本性越远;会的越多,离我们自己的本心越远;我们的技术越熟练,离本质越远。所以道家始终让你不要去忘记这个本性,甚至要你放弃任何技术,以完成这种本质性的表现。
今天很多中青年画家,从小就学,然后一直到硕士到博士毕业,他们都受过很好的训练,可是当你把他们的画和那些八九十岁的人去比的话,你会发现在艺术里面,技术的作用真的非常有限。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说,他在四五十岁的时候,知道了物体的构造;等到六七十岁的时候,笔下稍微有一点生机。它不仅仅是一个外形,不仅仅是一个构造,它还能够活起来,能动起来。但是他又说,如果我能够活到90甚至活到100岁的时候,我相信我笔下的一点一线,“皆是生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从一开始的画外形到画构造,到它能够活起来,到最终能够充满生命,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有多少人能进入到这种生命里面去呢?
当一个人把他的技巧打掉,把他有限的知识打掉时,他才可能接近无限,才可能接近于道,这个才是道家所给予我们的一种教导。
中国艺术进行到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它开始追求“老境美”,即开始追求一种高古。中国绘画从南宋以后,开始表现一个人的晚年境界,这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书画家的年龄普遍往上提了,王羲之、王献之,苏东坡、米芾,这些人的年龄平均60岁不到,可是到了南宋尤其到了元,70岁,80岁,90岁,近现代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这些人差一点到了百岁。
禅宗给了中国艺术另外一种表现。
如果说儒家过于庄重,过于庄严,道家又过于散漫或者说过于质朴,禅宗则给了我们一种空灵,或者说一种缥缈,更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力量。道家要把人为的规定和人为的概念一点一点打掉,到了禅宗这里,它打得更彻底,甚至连整个自己都要否定掉。朱熹讲“读书要于不疑处有疑”,就是读书要从没有怀疑的地方开始怀疑,就是始终要不停去质疑,去接近事物的本质。禅宗把一切都要打掉,否定到什么都没有了,才是所说的“究竟”。“究竟”这个词就是由禅宗那里来的。艺术也是这样,如果说道在“虚”,在“无”,在“淡”,中国绘画从元以后就不停地向“虚”“淡”“无”走,这个走的过程实际上是为了接近道的过程。从绘画的角度可能会觉得是一个“退化”,是一种“衰弱”,但从艺术哲学的高度,它却是不停向道、向道的本质靠近。所以,像徐悲鸿、康有为等人认为中国艺术没办法和西方去比,这个比法本身是成问题的。
中西艺术区别不是优劣问题,是差异,是不同。中国艺术除了儒家,除了道家之外,我觉得禅宗艺术和西方是最可以拿来比较的。凡・高曾经有自画像,在写给他弟弟的信里面说,他故意把自己的耳朵画得往上面提了一点,以便像一个日本的和尚。我想那个时候凡・高大概还没有见到中国和尚的东西,他只见了日本的浮世绘和日本禅僧的东西。
禅宗会让你在疑惑当中寻求一种觉悟,进而寻求生命的解放,让你打破许多惯例。儒家让你追求对称的庄严之美,比如故宫,它就是对称的,天安门两边一定要对等,中轴线展开,这是儒家的。如果你一看这边有那边没有,那可能是某个道教或者禅宗建筑,它讲究奇。日本千利休的老师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创始人,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集会,刚好路边有一个卖花瓶的,一个双耳的瓶,村田珠光拿起来看了一看,觉得太完美了。等他集会回来,发现瓶子已经不在了。过了几天,千利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要办一个茶会。村田珠光想,没准儿那个花瓶是被千利休买走了,他到了千利休那儿,一进房间果然看见那花瓶,但是花瓶有只耳朵被敲掉了。村田珠光就说:“我就知道这花瓶是被你买走的,当初我也看见了它,我觉得它太完美了。我今天来,本是为了帮你把这个耳朵敲掉的。”他从怀里面拿出小锤子,说:“我连锤子都带来了,可是你并没有让我用上这个锤子,你可以独立门户了,我不需要再教你什么了。”
所以,禅宗追求一种残缺美,不要那种均衡,它要打破这种均衡,在这种打破均衡的过程当中追求一种奇趣。我们看八大山人,尽管他学董其昌,可是董其昌的画里没有八大山人的味道,八大山人的画里也没有董其昌的味道,如果把八大山人和董其昌做一下比较,会看到一个是禅宗画风,一个完全是儒家的画。
但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是禅宗,他们所启示的艺术,都是表现人性的,而且他们承认,只要是自己用心做的东西,它一定会表现永恒的人性。伟大的或者复杂的人性,才是艺术里面最终要追求的理想。
艺术的理想是什么呢?艺术的理想是人,一定是以人为中心。一张画可以去买一座别墅,买一辆汽车,但那些都是艺术以外的东西。
艺术的本质一定是人,一定能够看到人的精神,看到人的修养。艺术也是一种解放之路,它让你摆脱一些世俗的束缚,让你飞升到人类的精神能够抵达的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