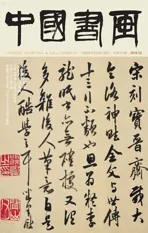南画与文人画之辨
2018-12-03周敏
◇ 周敏
关于“南画”“文人画”及“南宗画”概念的讨论应该说是一个老问题了,从20世纪初〔1〕开始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2〕,再到现在依然不断有讨论的声音出现,然而各方莫衷一是,并未达成共识。说“南画”大体等于“文人画”者有之,说“南画”就是“南宗画”的简称有之,说“南画”是“南方画”者亦有之。这种概念的不确定使得我们在使用“南画”这个名词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有人出来批评说不对,这是日本“舶来品”,并不能等于“文人画”之类云云。现代学术讨论交流的前提即是概念的准确界定,而对此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确实令人颇为困扰,故笔者在此欲重新来梳理这个问题,试图对它的讨论有所推进。
一、 中国语境中的“南画”
中国从何时开始使用“南画”这一概念?古代偶有出现,如“北画病在重坡,南画伤乎多水,以其习熟而然也”(南宋李澄叟《画山水诀》)。这里应是从南北地域来分,北方的画病在重坡,南方的画伤乎多水,这时“南画”尚未形成一个专有名词。有学者〔3〕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过专门的考证,指出是在民国时期受日本绘画影响,才逐渐使用开来。但是其内涵在一开始被使用时就不太确定。
俞剑华对日本绘画颇有研究,并对此问题有敏锐警觉,他曾说:“日本初学中国马远、夏圭之水墨苍劲一派,以水墨之渲染,笔法之劲力见长,颇与浙派相似。后始知有南宗画,又竭力模拟,日本之所谓南画,即中国之南宗画也。”〔4〕他把“南画”看成是“南宗画”的简称。郑逸梅在其文章中曾这样归类:“南画虽多类别,然据朱应鹏之归纳:分三大系统,一人物画;二山水画;三花鸟画。”〔5〕虽然他是借用了别人的观点,但他自己是赞同的。这种分类显然是传统中国画的三大科,文人画主要也是这三科。“南画”在此应是用来指代“文人画”。陈小蝶在1929年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一文中,按画风分了六个流派,其中“南画”专门列为一派,“南画派,金拱北以摹古得名,专以宋元旧迹,输送日本。及其归也,乃为北平广大教主”〔6〕。金城的画从中国的语境来看当属于明清以来的文人画典型风格,流入日本后,被日本人视为南画正宗,陈小蝶在此直接继承了日本的“南画”概念,将之理解为等同于文人画。童书业在《南画研究》新序中说“所谓‘南画’,大体说来就是中国的‘文人画’”。他将“南画”这一概念等同于“文人画”,但是同时他又察觉到“南画”在日本人的语境中有不同的风格内涵,指出“以‘南画’名家的日本画家所写的作品,总是近于杂有‘北画’技术的吴门派绘画,面对于南画的松江派以后的明清画家技术,总有些距离”〔7〕。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朱良志先生的著作《南画十六观》标题就用了“南画”一词,他主要接受了郑逸梅、童书业的说法〔8〕,把“南画”直接当作“文人画”来用。但我们看该书正文就会发现,提到“文人画”“南宗”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使用“南画”来代替,可见他只是在标题上借用了“南画”而已。
从上面各家学者对“南画”一词的使用可知,在中国的语境中说“南画”就相当于“文人画”或者“南北宗”,这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那么问题就转换成“文人画”和“南北宗”是不是同一个所指?显然不是,两者乃属于不同层级的概念。文人画是相对于院体画来说的,最初其标准并非某种特定风格,而是指业余士大夫之画,元代之后确立了自己的图式类型。所谓院体画,一般指画院职业画家之画。画院的设置来自五代,梁唐蜀皆设待诏,两宋画院蔚为鼎盛,如宣和、绍兴画院。晋唐之“衣冠贵胄”的画家以及五代两宋的画院画师们凭着专业而精湛的技法握住绘画的话语权,但随着五代两宋之后体现人文精神特征〔9〕的文人绘画逐渐强大,职业画师与文人画家之间评判尺度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他们(职业画师)对绘画所倾注的毕生精力,是那些本位意义上的文人士夫所不屑付出的。过度沉湎于绘画,不仅有为物所累的危险,对体悟至道更会构成极大的妨碍。”〔10〕宋代文人画价值观的确立,就凸显了其不同于院体画的存在,必然也带来风格、技法上的不同。
“南北宗”论的说法则要等到晚明的董其昌〔11〕,在《画禅室随笔》中他分别论述了“文人画”和“南北宗”的系谱(限于篇幅在此不引),通过分析两个系谱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点:1.文人画包括南北宗;2.董氏尚南贬北。“南北宗论”一出,影响巨大,时人及后人皆以此为据言说画史,尚南贬北则更是变本加厉,把喜欢的画家都加入“南宗”,不喜欢的都贬斥为“北宗”,使得“北宗”大有被清理出文人画直接归入院体画之倾向,“南宗”甚至变成了文人画的代名词。随着现在我们对传统认识的深入,观看视域的扩大,尤其高居翰、徐小虎等西方学者对非文人画的价值再发现,“南北宗”说已属勉强成立,再要独尊“南宗”实在不无过激之处。
抛开一些时代偏见,我们可以看到“南北宗”其实是“文人画”的一个下属概念,特指“文人画”山水科的两种不同风格,所以“南宗画”与“文人画”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要追溯“南画”何以在中国语境中内涵模糊之缘由,还不得不从其原生国之语境进行考察。
二、日本语境中的“南画”
谈日本“南画”须从中国画传入日本说起。中国绘画传入日本主要有两次浪潮,时间间隔既长,性质亦各异〔12〕。在这两次浪潮之间,中国画的传入亦未尝中断,文人画就是在这两次大浪潮之间传入,时间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江户时期。那么这里会有个问题,从第一次输入浪潮的12世纪开始,为何文人画要迟至17世纪才传入日本?〔13〕可能有两方面原因:1.元代文人的交流“雅集”仅限于狭窄的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封闭的世界;2.对于钟爱南宋院体风格的日本人来说,新兴的以干性用笔为主要技法的文人画与他们的审美趣味有所隔膜。
直到17世纪元明文人画才传入日本,有几个契机:一个是德川幕府大兴儒教,培养了一群能接受文人画品味的文化人〔14〕。一个是日本本土大和绘如狩野派、土佐派等陷入因陈相袭毫无生气的境地,需要外来画种以刺激当时沉寂的画坛。晚明吴门画派以及《芥子园画谱》〔15〕、《八种画谱》等明清画谱一进入日本即被不断翻刻,广为流布,江户画坛绝大多数成名画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这前后延迟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到16世纪晚期,日本艺术家已能充分掌握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的“诗意式着色山水”〔16〕。艺术,并延伸到整个画面、渐层极端细腻的渲染技巧,深刻影响了日本画的走向,所以它们面对一种完全新式的以线性用笔为主的元明文人画,是感到非常陌生且难以准确理解的。明清画谱的盛行除了展示历代经典图式之范例,为有志于画学而苦无名师指点者提供了门径之外,其价值还在于帮助日本人更新了以往的审美趣味和理论观念。《芥子园画谱》中包括“六法论”“南北宗论”等画论,使得日本人在文人画的价值追求层面能更深入理解文人画的价值所在。在此之后的日本画论中,关于文人画、南北宗论的说法比比皆是〔17〕。
由于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社会背景的不同在一开始便使得当时的日本画家很难在精神内涵上真正理解中国文人画,结果是文人画在日本演变成一种不同于本土传统的风格样式,作为一种新鲜的图式画风被接受。日本人所画的文人画不同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笔耕墨戏,而只是少数儒学者或文化人、职业画家的重要谋生手段〔18〕。囿于卖画、趣味、身份等原因,他们的作品在文人画的核心—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等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这种情况在当时就有人提出批判,如江户时代画家金井乌洲在《无声诗话》中尖锐指出:
吾人今日,幸遭升平,身在草莽,笔耕生活,龌龊终年,故士气流成匠气,乃所以今之学者为人也。〔19〕
造成风格上的偏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前面已有提到,在于日本画家借以理解文人画的背景依然停留在唐宋着色山水所奠定的渲染风格,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理解中国已经经历了宋元演变而来的线性用笔风格的背景资源。徐小虎指出:18世纪的日本评论家所了解的中国文人画是自由挥洒的、自发性的、才气横溢的、简略的、渲染导向的与非线性的〔20〕。也难怪俞剑华曾批评道:“(日画)仅能袭取中国画之皮毛,柔弱单薄,无复韵味。”〔21〕因为毫无笔法。基于这种背景,日本人在当时就不怎么用“士夫画”“文人画”这样的概念,而用“南画”来指代这一类富有文人趣味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他们不直接用“南宗画”而要造一个“南画”出来呢?很显然,这种杂糅的风格也并不是“南宗画”这个已有的概念所能全部指涉的。
至此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日本语境中“南画”的特征了:以明清画谱中的图式为主要样本,取法明清文人画之外还吸收院体画、浙派及朝鲜画风格〔22〕;主题不仅限于山水,还包括花鸟、人物、竹石等题材;技法上则以湿润渲染、粗率减笔、非线性为主,置骨法用笔于不顾;整体上没有明确的形象轮廓,充满诗意空间。由此观之,似是文人画,又兼院体画、浙派甚至朝鲜画,似是南宗山水,又包括花鸟人物等丰富题材,似是主流风格,又是被中国评论者斥为“粗恶”毫无笔法的禅画、墨戏之作。借用吉泽忠先生的一句话来说颇为准确:“关于日本的南画,最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江户时代后半期,以南宗画为主的被中国元、明时代的绘画所触发的一个画派。”〔23〕故狭义上讲“南画”应是日本的一个独立画种。

[唐]王维(传) 江干雪霁图(局部) 31.3cm×207.3cm 现藏日本
三、南画家及文人画家对西洋画的态度
考察“南画”与“文人画”的区别还可以从它们与西洋画的关系来看。18世纪初,德川幕府对闭关锁国政策稍有放松,西方书籍可以从长崎进入日本,书内插图、版画都成为日本人争相临摹的对象。西方写实主义对日本画家学习文人山水画的影响便是产生了日本艺术中的折中主义。前面提到文人画进入日本的一个背景是日本本土画派的僵化疲弊,文人画作为一种新鲜的刺激能够被取法,那么稍后进入的西洋画,亦同样可以成为被学习取法的对象。所以一个日本南画家同时学习西方写实派画法,完全没有什么不适,并且还能保持强烈的热情。但是在中国,情况则截然不同,西洋画虽然也受到清代皇室以及一部分开明人士的喜欢,但大多数文人画家对此却不以为然,明确表示出拒绝排斥的态度,认为西洋画透视等技法皆非高雅“不知底蕴,则喜其工妙,其实板板无奇”(松年《颐园画论》),为“好古者所不取”,虽工亦匠。
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日本江户时期的画家司马江汉(1747—1818),一个是中国清代画家邹一桂(1686—1772)。司马江汉早年学过浮世绘,之后又学南画,最后转向了西画,回过头来对南画展开激烈批判,对西画的写实透视法赞叹不绝。他在《西洋画谈》中说:
东方绘画不讲究细节的准确性,但是一幅图画如果没有细节的准确,便算不上图画。客观真实的绘画,是将所有的绘画对象—山水、花鸟虫草、牛羊、树石等—完全按照它们本来看起来的样子画出来,这样画出来才活泼生动。唯有西洋技法才能取得这种真实效果。东方画家的作品在西洋画家眼里就像儿戏,简直谈不上是绘画。〔24〕
类似司马江汉的学画经历和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大有人在,如与谢芜村〔25〕的学生松村吴春,将南画带到江户的第一人谷文晁,将南蘋派技法与西洋写实技法结合开创圆山四条派的大家圆山应举等。
作为“清六家”之一恽寿平的女婿邹一桂,绘画颇得恽氏真传,同时又是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可谓典型的文人士大夫画家。他在《小山画谱》中对西洋画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价: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缁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一,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26〕
最后一句是关键,毫无笔法且有匠气,在那个时代这几乎是对一张画作最坏的评价了,故西洋画很难进入传统文人画家之眼,西方技术和绘画多局限于皇族宫廷及民间世俗的范围。
日本南画家与中国文人画家对西洋画截然相反的态度,耐人寻味,似可见出两者之区别还不仅仅在于表面视觉上的样式,若要探究其背后之根源,则涉及中日两国的哲学思想背景,而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不做展开。

[日]室町雪舟 四季山水轴之一 149.2cm×75.5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四、南画及文人画的价值
谈了那么多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会发现这种区别更多地表现在图式风格上。不论南画大致等于“文人画”“南北宗画”还是独立成科,总之都还是在“文人画”这一范畴之内,若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虽不能完全对应上,但相较而言把日本“南画”翻译成中文的“文人画”当是最接近的词了。对此徐小虎曾提出过一个新的英文词“理想型绘画(idealist painting)”,她以这个词来统称中日两国的文人画,认为文人画是受到特定理想的激发,这些理想强调精神与智能的价值,胜于装饰甚至描绘的价值〔27〕。“南画”因“文人画”而触发,日本人虽在理解把握上有所偏差,但在笔墨趣味、人文价值方面的追求上基本同其母体“文人画”保持着一致。江户时代日本南画家大多都有一定的汉学修养,他们的南画理论也接受了中国的文人画理论〔28〕。内藤湖南说“日本的艺术只不过是中国艺术传入乡村时添加了一些浓厚的地方特色而已”〔29〕。此话不无谦卑之意,但说“南画”是“文人画”的一个支脉,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内藤先生对南画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南画代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的时代精神,会对当今的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30〕。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且不说外国人,即使我们自己要准确理解文人画的价值也非易事。关于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前人讨论颇多,大体有两层含义:态度和功能。前者是主体的行为取向,指无功利、无目的性的自适,如“墨戏”“自娱”“无意于佳”“逸笔草草”等;后者是主体行为及其结果的效用,如“成教化,助人伦”“为工农兵服务”等。两者一般呈平衡状态,但有时也出现主从关系,如苏轼、米芾等墨戏一派为功能从属于态度。近现代中国画,则多是态度从属于功能。尤其20世纪50年代后政治功利观的进一步强化,以大众化取代精英化的革新运动,将文人画推上极“左”乃至反文化的巅峰,日趋失落的形而上精神,已经很难为人们的意识所感知了〔31〕。
朱良志先生曾指出传统文人画之核心在于“真性”,它不以视觉感官的愉悦为目的,而以真性显现为根本之追求,重在“呈现”而非“看见”,超越外在形式上“似与不似”的怪圈,直达生命之内核〔32〕。然而,在有识之士已经抛出“文人画终结”〔33〕的背景下讨论如此形而上的价值是否略显苍白无力?“文人画符号表现日益强化而话语阐释日渐退场的发展趋势,在近代城市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海派绘画的催化下,出现了价值与形式的分裂化局面。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和运用文人画的表现形态及其形式趣味,却越来越不可能继续贯彻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取向了。”〔34〕传统文人画形而上的哲学品格在此显得格格不入,图式沦为标签符号,日本南画也同样面临这种状况,在明治维新全盘西化的背景下节节败退,20世纪初出现一个讨论小热潮,但也仅仅是日本人确认自身的一个回光返照,迅速在高昂的军国主义面前冷却。
结语
中国绘画在中唐之后出现了水墨“逸品”画风,被朱景玄称为“格外逸品”的王墨、李灵省、张志和,意在指这种特异画法超出六法的范畴。到北宋之后,苏轼等士大夫群体举起“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墨戏”大旗,绘画要在笔墨之趣味,“不当问工拙,放笔一戏空”,这种价值追求与唐以来的“逸品”之趣不谋而合。士大夫评论家们遂推“逸品”一格以配合时代风潮,这使得“逸品”被纳入文人画系统,内涵也发生转变。这次转变,日本人已经滞后了。到了元代赵孟頫的登高振臂,使得文人画又出现一次重大转变,从强调自由挥洒和创造的宋代绘画理论,转向一种明确的学者态度,将干的线性笔墨在纸上的潜能爆发出来,元代的山水、花鸟文人画在绘画方面打开了一条通往历史决定论的道路,笔墨第一次依照书法的原则来撷取形式〔35〕。这次重要的转向,日本因为各种原因完全未能跟上,致使时隔四五百年,转向后的元明文人画传入日本,日本人只能带着对唐以来的“逸品”及所谓“诗意式着色山水”的框架去阐释,由此产生的“南画”风格必然是带着唐以来的“逸品”印记,未能得到文人画的“清逸”滋养和收束,最后走上近于中国“禅画”的粗减狂逸风格,而这些却是在中国绘画史的演变当中沉淀为被遗忘的“古层”。
追溯日本南画的形成脉络,的确可以勾勒出中国绘画史在历史的演变中被遗忘的存在,这种存在即是另一种可能。徐小虎在《南画的形成》一书中所做的工作,其价值即在于此。以中国之立场来看,日本“南画”多半都是粗恶无笔法不足取,但本文努力揭示出“南画”与“文人画”之间的异同,还意在提示:仅仅一个粗率的价值判断,或者一个相对主义的两可态度都将掩盖原可重估中国绘画史进路的“可能性”。传统文人画的生存土壤虽已时过境迁,或者说文人画运动已经消歇了,但文人画的人文精神早已内化为东方艺术中最具辨识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