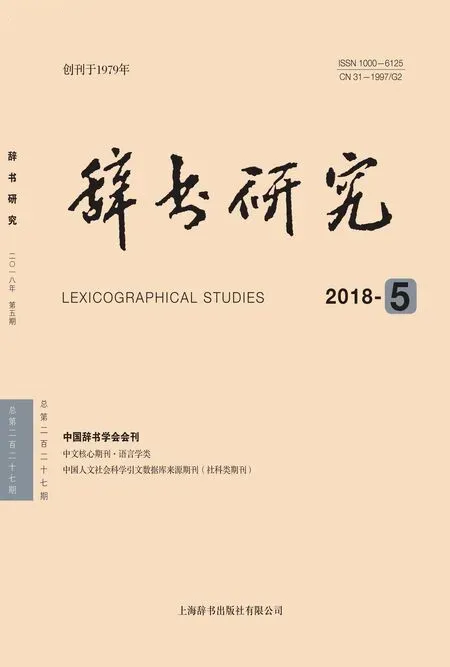古典拉丁语辞书编纂史述略: 从西方到中国*
2018-11-29黄瑞成
黄瑞成
拉丁语(Lingua Latina)起初是古代意大利西部拉丁族罗马人所使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拉丁语以罗马字母书写,深受埃特鲁里亚语(Lingua Etrusca)、尤其是希腊语(Lingua Graeca)影响而形成,以至于古典语文学家认为,“罗马字母只是希腊字母的一种形式”(Wheelock 2005)。拉丁族罗马人起初居住在以罗马城(Roma)为中心的拉替乌姆地区(Latium),随着罗马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直至发展为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拉丁语也成为罗马帝国治下所有民族通用的语言。从公元前6世纪讫于公元8世纪,古代拉丁语文学发展经历了“早期”(550—250BC)、“共和国早期”(250—80BC)、“共和国晚期”(80—30BC)、“帝国时期”(30BC—476AD)、“晚期”(476—800AD)五个时期。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Carolus Magnus)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此开启卡洛琳王朝的文艺复兴(Renovatio Carolingiana),这是由古代拉丁语到中世纪拉丁语的转折点。广义的“古典拉丁语”,指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600年之间的古代拉丁语,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古典拉丁语”概念的。(Kramer 2013)
一、 古罗马三大拉丁语辞典
古典拉丁语辞书的编纂,最初是古典希腊语辞书编纂传统的延续,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早期,由希腊语学者制定,用于罗马人学习希腊语的“希腊语—拉丁语”或“拉丁语—希腊语”双语词汇表,如今只有纸莎残篇传世。(Stathi 2006; Corréard 2006)从公元前后到公元7世纪,古罗马出现了三位有重大影响的辞书编纂家,成就了古罗马三大拉丁语辞典: 1. 古罗马语法学家弗拉库斯(Verrius Flaccus)的《辞义》(DeVerborumSignificatu);2. 古罗马语法学家诺尼乌斯(Nonius Marcellus)的《约言》(DeCompendiosaDoctrina);3.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主教(Isidorus Hispalensis)的《辞源》(Etymologae)。(Lindsay 1901)
(一) 弗拉库斯的《辞义》
最古老的拉丁语辞典,是由活跃于公元前后的古罗马语法学家弗拉库斯编写的《辞义》(Kramer 2013),弗拉库斯是奥古斯都皇帝(Augustus)养子暨执政官盖优斯(Gaius)的保傅。《辞义》词目广泛,以字母顺序排列,规模有40卷之巨,惜仅有残篇传世: 卷Ⅳ存近1页文本;卷Ⅴ存5行文本;卷Ⅵ存未经证实的4页文本,以“Bellitudinem[美]”起首,涉及I、M-V字母下约60个词目。(Augustus 1826)公元2世纪,罗马语法学家费思图斯(Sextus Pompeius Festus),大量参考弗拉库斯的《辞义》,将其缩编为20卷同名辞书,该书广泛流行,从某种意义上使弗拉库斯的《辞义》获得新生。然而,费思图斯缩编的《辞义》也未能完整传世,“Manare[流动、流传]”以上词目全部失传(Thewrewk 1889; Lindsay 1901114-115)。公元8世纪末,本笃会执事保罗(Paulus Diaconus)在费思图斯缩编的《辞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缩编这部辞书,略去出自古代文献的引例,(Kramer 2013)成就了《辞义精粹》(PauliExcerpta/Epitoma)一书。值得一提的是,保罗出身伦巴德王国(Regnum Langobardorum)贵族,曾为戴西德里乌斯国王(Desiderius)宫廷秘书,任阿黛尔佩嘉公主(Adelperga)保傅,公主嫁为贝内文托的阿莱奇斯二世(Arechis II, Benevento)公爵夫人时,他随从前往辅佐其应对意大利复杂的政治局面,还应公爵夫人之命,续写了欧特洛皮乌斯(Flavius Eutropius)的《罗马简史》 (BreviariumhistoriaeRomanae)。保罗后应邀造访查理曼大帝宫廷,作为语法学家在此停留。保罗认为,他的《辞义精粹》必将对查理曼大帝图书馆有所增益。(Glinister & Woods 2007)
可见,古罗马首部拉丁语辞书《辞义》的文本传统,是由跨越700年历史的三位辞书编纂家弗拉库斯、费思图斯和保罗共同成就的,其中费思图斯缩编的《辞义》是承前启后的桥梁,该书尽管并非以主题作为划分依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古罗马随后两大拉丁语辞书之形制规模奠定了基础。弗拉库斯创始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辞义》,首先是作为皇储和他主持的语法学校中贵族子弟的教科书。所以,他要通过大量引述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为贵族子弟传达对民族文教传统的深远记忆。研究表明,《辞义》与拉丁语语言学的奠基人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的《论拉丁语》(DelinguaLatina)关系密切(Glinister & Woods 2007),弗拉库斯引述了瓦罗已失传的《人神古迹》(Antiquitatesrerumhumanarumetdivinarum),而他的《辞义》复又为百科全书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的《自然史》(NaturalisHistoria)广泛引用,由此可见《辞义》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的古罗马文教传统中的重要位置。
然而,弗拉库斯《辞义》卷帙浩繁,也许正是导致其大部失传的原因。费思图斯缩编弗拉库斯的《辞义》,词目基本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在拉丁语辞书乃至西方全部语文辞书编纂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对弗拉库斯《辞义》的词目和内容做了调整,略去生僻旧词,加入自己的评述,但保存了词源和语法解释,大量引述自公元前3世纪史家法比乌斯(Quintus Fabius Pictor)以降的古罗马作家,对研究古罗马政治、文化、宗教和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Glinister & Woods 2007)保罗《辞义精粹》的重要性,尤其在于保存了费思图斯《辞义》前半部分词目内容,使得后人可略窥费思图斯《辞义》之全貌: 1913年,英国古典语文学家林德赛(W. M. Lindsay)编辑的《辞义》权威校勘本,就是以勘费思图斯《辞义》和保罗《辞义精粹》为基础构建的辞书文本。弗拉库斯于公元前后始作《辞义》的影响,通过费思图斯和保罗的两度缩编,一直持续到了中世纪早期。不仅如此,21世纪以来,有鉴于《辞义》之于古罗马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启动“费思图斯《辞义》计划”(Festus Lexicon Project),以期校勘出版更为完备的研究文本和现代语言译本与评注本。
(二) 诺尼乌斯的《约言》
公元4—5世纪间,古罗马语法学家诺尼乌斯编成《约言》20卷,是为古罗马第二大拉丁语辞书。对诺尼乌斯其人,我们所知甚少。相较于基本按照字母顺序安排词目的古罗马第一大拉丁语辞书《辞义》,《约言》以“主题”方式分为20卷,在现代西方辞典编纂学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约言》20卷主题分类如下: Ⅰ. “言辞本义”(De proprietate sermonum);Ⅱ. “雅言”(De honeste set nove dictis per litteras);Ⅲ. “各性名词”(De indiscretis generibus per litteras);Ⅳ. “一词多义”(De varia significatione sermonum per litteras);Ⅴ. “同义辨析”(De differentia similium significationum);Ⅵ. “喻义”(De inpropriis);Ⅶ. “反常动词”(De contrariis generibus verborum);Ⅷ. “变格”(De mutatis declinationibus);Ⅸ. “数与格”(De numeris et casibus);Ⅹ. “变位”(De mutatis coniugationibus);Ⅺ. “副词”(De indiscretis adverbiis);Ⅻ. “特殊用法”(De doctorum indagine);. “航海之属”(De generibus navigiorum);. “衣着之属”(De generibus vestimentorum);ⅩⅤ. “器皿之属”(De generibus vasorum vel poculorum);ⅩⅥ. “鞋履之属”(De generibus calciamentorum);ⅩⅦ. “颜色”(De coloribus);ⅩⅧ. “饮食之属”(De generibus ciborum vel potionum);ⅩⅨ. “兵器之属”(De generibus armorum);ⅩⅩ. “亲属词汇”(De propinquitatum vocabulis)。
1901年,英国古典语文学家林德赛研究诺尼乌斯《约言》的专著《诺尼乌斯的罗马共和国拉丁语辞典》,取得重大成就,并在两年之后出版了《约言》的校勘本。林德赛研究表明,《约言》的文献价值首先在于,它通过引例保存了大量如今已失传的古罗马作家,如悲剧家阿奇乌斯(Accius)、讽刺诗家卢奇里乌斯(Lucilius)、史家西森纳(Sisenna)等人的作品片段。就辞书结构而言,以“一词多义”为主题的《约言》卷Ⅳ最符合现代辞书观念,占据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卷Ⅱ—Ⅳ中的词目,按字母顺序排列,但在各次属部分,词目又并未按字母顺序排列。整体观之,《约言》20卷中的最大篇幅在于广泛引述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作为例句,每个词目下出自这些作家的引例,遵循同样的次序——始于普劳图斯(Plautus),终于瓦罗或卡图(Cato),而且主要出自从普劳图斯到阿普利乌斯(Apuleius)的古罗马作家的41部作品,每个词目下出自这41部作品的引例,按时间先后排列。若我们据此认为,在全部古罗马作家作品中,诺尼乌斯最钟爱这41部作品,当非过分之辞: 他使引例次序完全符合这41部书作品问世的先后次序,正是为了展示这41部作品之概貌。
古代流传下来的诺尼乌斯《约言》一书的全名是: 《图布斯库的漫步学派诺尼乌斯约言示子》(NoniiMarcelliniPeripateticiTubursicensisCompendiosaDoctrinaadFilium, 1480),林德赛等西方古典学家,没有忽视这个书名所指示的诺尼乌斯的学问传承(“漫步学派”)和家乡何处(“图布斯库”),却忽视了这个书名所指示的另一重要内容“示子”(ad Filium),这一指示表明: 《约言》原本是诺尼乌斯为自己儿子编写的辞书,用途就是作为学习古罗马作家作品的辅助工具,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约言》引例何以完全符合所引41部古罗马作家作品问世的先后次序。古哲著述,目的当然是为了教化,辞书编纂也不例外: 教化世人之前先教化自己的儿子,想必在情理之中。
(三) 伊西多尔的《辞源》
公元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主教编写完成《辞源》(Etymologae)20卷,是跨越古代和中古最重要的拉丁语辞书,它涵括了古希腊罗马作家和教父的大部分学识,被德国古典学家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誉为“整个中世纪的基础性著作”(Grundbuch des ganzen Mittelalters)。(Barney, Lewis, Beach,etal. 2006)3。伊西多尔由兄长、塞维利亚大主教雷安德尔(San Leandro de Sevilla)抚养长大,后者是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ius I)的密友,与西班牙国王利奥维西尔多(Leovigildo)的两个儿子“反叛者”埃尔梅内西尔多(Hermenegildo)及后来的国王莱卡来多(Recaredo)交好。雷安德尔死后,伊西多尔继任塞维利亚大主教,主持塞维利亚和托勒多(Toledo)两次公会议,与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西南的维西哥特(Regnum Gothorum)的国王西塞布托(Sisebutus)建立了“理智上的”友谊,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与兄长、一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后都被天主教封圣,伊西多尔本人于1722年被天主教会封为“教会博士”(Doctor Ecclesiae)。
据伊西多尔的同僚、后来的萨拉戈查大主教布劳洛(Braulius Caesaraugustanus)称,伊西多尔是应他的请求编写的这部《辞源》,其20卷的形制,最终也是由他编定的——然而,无论如何,伊西多尔本人首先得同意布劳洛的请求;其次,由伊西多尔编纂的《辞源》内容本身,可以按20卷形制来编排。《辞源》20卷的编排形制绝非出于偶然。布劳洛盛赞伊西多尔:“我们时代的确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与古代知识的相似,在他身上古代本身的某些事物重生了。”(Barney, Lewis, Beach,etal. 2006)7-8伊西多尔平生大部分著述的主题,都成为其《辞源》各卷主题乃至词目,《辞源》可视为他平生著述之精粹,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布劳洛上述评价意味着,伊西多尔“与古代知识的相似”就体现在《辞源》中,正是在《辞源》中的“古代本身的某些事物重生了”,当非过分之辞。
布劳洛认为,哲人西塞罗(Cicero)《论晚期学园派》(AcademicaPosteriora, 1.3)中的一段话,完全适用于评价伊西多尔:“因为,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漫游和迷失,就像异乡人,正是你的书,好似引领我们回归家园(quasi domum deduxerunt),让我们能够时时知道,我们是谁又身在何处(qui et ubi essemus)。你展示了(aperuisti)我们祖国的时世,你展示了对时代的描述,你展示了神圣事物的正义,你展示了祭师的正义,你展示了家政学科,你展示了军事学科,你展示了诸地域的状况,你展示了所有神圣和人类事物的名称、种类、本分和原因。”(Reid 1874)布劳洛的这段引述,是西塞罗在瓦罗的庄园中,听游历归来的瓦罗自述其哲学著述风格之后,当面称赞瓦罗的一番话——如果说古代哲人的追求就是“自我认识”,所谓瓦罗的书“让我们能够时时知道我们是谁又身在何处”,无疑是对语言学家瓦罗的至高评价。布劳洛引述西塞罗这段话,表明他眼中的伊西多尔与西塞罗眼中的瓦罗是等而同之的哲人——如果说瓦罗是古罗马文教传统的奠基者,伊西多尔就是古罗马文教传统的集大成者,《辞源》就是古罗马文教传统的集大成之作。
我们来看伊西多尔《辞源》20卷的主题: Ⅰ. “语法”(De grammatica);Ⅱ. “修辞与辩证”(De rhetorica et dialectica);Ⅲ. “数学”(De mathematica);Ⅳ. “医学”(De medicina);Ⅴ. “法律与时代”(De legibus et temporibus);Ⅵ. “书籍与教会之责”(De libris et officiis ecclesiasticis);Ⅶ. “上帝、天使和圣徒”(De deo, angelis et sanctis);Ⅷ. “教会和宗派”(De ecclesia et sectis);Ⅸ. “语言、种族、统治、军事、公民和血亲”(De linguis, gentibus, regnis, militia, civibus, affinitatibus);Ⅹ. “词汇”(De vocabulis);Ⅺ. “人及其部分”(De homine et partibus eius);Ⅻ. “动物”(De animalibus);. “世界及其部分”(De mundo et partibus);. “地及其部分”(De terra et partibus.);ⅩⅤ. “建筑和田野”(De aedificiis et agris);ⅩⅥ. “石和矿”(De lapidibus et metallis);ⅩⅦ. “农事”(De rebus rusticis);ⅩⅧ. “战争与游戏”(De bello et ludis);ⅩⅨ. “船只、建筑工艺和衣着”(De navibus, aedificiis et vestibus);ⅩⅩ. “房屋与家具”(De domo et instrumentis domesticis)。
瓦罗已亡佚的《学科要义》(Disciplines),为西方古典文教初阶所谓“七艺”制定了规范,也是古罗马乃至西方百科全书之滥觞,这也是他被视为古罗马文教传统奠基者的重要原因。《学科要义》这部书共9卷: 卷Ⅰ—Ⅶ主题分别是“语法”“修辞”“辩证”“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卷Ⅷ主题是“医学”,卷Ⅸ主题是“建筑”。(杨祖希,徐庆凯 1992)。伊西多尔《辞源》卷Ⅰ—Ⅲ主题是“语法”“修辞与辩证”“数学”,他将“音乐”“天文”归入“数学”,正与瓦罗《学科要义》卷Ⅰ—Ⅶ主题对应;《辞源》卷Ⅳ主题“医学”也与《学科要义》卷Ⅷ主题“医学”完全对应;《辞源》卷ⅩⅤ主题“建筑和田野”和卷ⅩⅨ主题“船只、建筑工艺和衣着”,又与《学科要义》卷Ⅸ主题“建筑”对应,且比后者更为丰富。这表明,伊西多尔《辞源》的内容和结构,与由瓦罗制定规范的古罗马文教传统一脉相承,且规模远超瓦罗的《学科要义》。
伊西多尔《辞源》20卷,内容涵盖了从格里高利一世(Gregorius I, 540— 604)上溯至老卡图(234—149 BC)800年间的古罗马文教传统。《辞源》按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后各10卷: 前10卷广泛采用“教育进阶”“百科全书”“字母顺序”体例编写,后10卷则主要采用“百科全书”体例编写。《辞源》兼采语词性释义和专科性释义方法,释文主要由“注释词”“种差”“辞源”构成。正如《辞源》书名所示,“辞源”追溯是这部辞书释文的关键所在,“注释词”描述和“种差”辨析服务于“辞源”追溯,而“注释词”“种差”“辞源”三者之间显然存在进阶次序。伊西多尔编纂《辞源》的最高意图是语法和语文学,他让全部高阶学科如医学、法学、哲学乃至神学从属于语文学。拉封丹(La Fontaine)因此称其为古代晚期文化的“泛语法的”丰碑(Barney, Lewis, Beach,etal. 2006)22。
如前所述,古罗马首部拉丁语辞书弗拉库斯的《辞义》,以及弗思库斯缩编的《辞义》和保罗的《辞义精粹》,都基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词目。但古罗马后两大拉丁语辞典诺尼乌斯的《约言》和伊西多尔的《辞源》,都主要以主题方式排列词目,且形制都是20卷。诺尼乌斯的《约言》和伊西多尔的《辞源》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们都是完整传世的拉丁语辞书: 毋庸置疑,任何一部以传抄为传承手段的古代文献,传世越完整,证明它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越大;我们若据此认为,诺尼乌斯的《约言》和伊西多尔的《辞源》在西方拉丁语辞书编纂史上的影响,超过了弗拉库斯的《辞义》,当不是过分之辞。尤有进者,由《约言》和《辞源》的20卷形制规模及其主题,我们即可联想到我国辞书的开山巨作《尔雅》。东西古哲可谓心心相印,《尔雅》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亦有20篇;传世19篇《尔雅》中,前3篇“释诂”“释言”“释训”,堪比诺尼乌斯《约言》卷Ⅰ—Ⅻ和伊西多尔《辞源》卷Ⅰ—Ⅱ;《尔雅》后16篇堪比诺尼乌斯《约言》卷—ⅩⅩ和伊西多尔《辞源》卷Ⅲ—ⅩⅩ。然而,《尔雅》作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固非诺尼乌斯的《约言》和伊西多尔的《辞源》所能企及。就辞书内容而言,《尔雅》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是辅助理解六经的字书,故而没有必要引述六经作为例句。《尔雅》仅以3篇涉及“训诂”,倒是与和伊西多尔《辞源》仅以2卷涉及“语法”和“修辞与辩证”有相似之出,但无法比拟诺尼乌斯《约言》20篇以12篇专注于“词法”或“语法”。
在古罗马三大拉丁语辞典中,伊西多尔的《辞源》对后世拉丁语辞书编纂影响最大。5世纪以降,直至古代晚期,古罗马语法学校中还出现了很多仅以“注释词”简释词汇的“词表”(Glossarium),8世纪晚期编成的《词表》(Liberglossarum/GlossariumAnsileubi)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它将伊西多尔《辞源》的大部分内容纳入其中,是西方辞书编纂史上首次完全以字母顺序编排的辞书,也被视为中世纪首部辞书。11世纪意大利辞书编纂家帕皮亚斯(Papias)的《学说初阶》(ElementariumDoctrinaeRudimentum),大量采用了伊西多尔《辞源》释义中的“种差”和“辞源”。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费拉拉(Ferrara)主教叙古提奥(Hugutio)编写的《语源》(Liberderivationum)和多明我会修士亚努恩西斯(Johannes Januensis)编写的《普世辞典》(Cathlicon),是中世纪拉丁语辞书编纂的双峰,这两部辞典都大量引用或采用了伊西多尔《辞源》。非但如此,文艺复兴三杰但丁(Dante)、薄伽丘(Boccaccio)和彼得拉克(Petrarch),都深受伊西多尔《辞源》影响——伊西多尔《辞源》早在古代晚期就为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
二、 文艺复兴以降的古典拉丁语辞书编纂
文艺复兴开启了拉丁语辞书编纂的新纪元。1502年意大利奥古斯丁修会修士卡勒皮努斯(Ambrosius Calepinus)编成附有例句和文献指引的《词典》(Dictionarium)一书,这部辞书第二版扩编为《最简明拉丁语和希腊语词典》(DictionumLatinarumetGraecaruminterpresperspicacissimus),是为西方首部拉丁语双语辞书。在此基础上,16世纪末甚至出现了多达11种语言(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匈牙利语、英语)的拉丁语多语辞书。(Kramer 2013)1531年,法国古典学家斯泰帕努斯(Robertus Stephanus)以前者为基础,编成一部全新的《词典或拉丁词库》(DictionariumseuLatinaelinguaethesaurus),1536年修订后大规模纳入始于普劳图斯和泰伦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的古典拉丁语文献;1579年,这部辞典的校对员斯卡普拉(Johannes Scapula)将其缩编,删去引例,但更为严格地按照字母顺序编排,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直到18世纪晚期,这部辞书一直是西方最权威的拉丁语辞书之一。
1771年意大利语文学家佛尔切利尼(Egidio Forcellini)编成《完全拉丁语辞典》(Totiuslatinitatislexicon),这部辞书的重要性在于,它首次严格区分了每一词目的核心含义和派生含义,展示出义项之间的含义关联,为18和19世纪西方拉丁语辞书编纂树立了模范。1783年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席勒(I. J. G. Scheller)编成《拉丁语德语详解辞典》(Ausführlichesundmöglichstvollständigesdeutsch-lateinischesLexiconoderWörterbuch)。1835年,英国学者里德尔(J. E. Riddle)将席勒这部辞书翻译为《完全拉丁语英语辞典》(LexicontotiusLatinitatis)。1835年,德国语文学家弗洛伊德(W. Freund)以佛尔切利尼《完全拉丁语辞典》为基础,编成《拉丁语德语词典》(WörterbuchderLateinischenSprache)。1837年,德国古典语文学家盖奥尔格斯(K. E. Georges)在席勒辞书的基础上编成一部全新的《拉德和德拉双向详解辞典》(Ausführlicheslateinisch-deutschesunddeutsch-lateinischesHandwörterbuch),双向释义,解词精准,尤其附有希腊语同义词,2012年的第16版修订版,收录“词目”5.4万条,“义项”20万条,“例句”30万条,迄今仍然是德语学界最具权威的拉丁语辞书,也是西方古典学术界最具权威的拉丁语辞典之一。但该书词目规模仍然有限,举例简略,且少有完整例句。就在同一年,美国学者勒夫莱特(F. P. Leverett)以佛尔切利尼《完全拉丁语辞典》和席勒的《拉丁语德语详解辞典》为基础,编成《新足本拉丁语英语大辞典》(ANewandCopiousLexiconoftheLatinLanguage)。1850年,美国词典编纂家安德鲁(E. A. Andrews)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将后者的《拉丁语德语词典》翻译成英语,1879年由里维斯和绍特(C. T. Lewis and C. L. Short)修订完成的《拉丁语大辞典》(ALatinDictionary,FoundedonAndrews’EditionofFreund’sLatinDictionary),使安德鲁的译本更加完备,收录了发端至3世纪以后的教父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词目”和“义项”或“子义项”十分广泛,成为19世纪通行的标准拉丁语英语辞典,至今西方古典学界仍在广泛使用。
1857年,德国拉丁语学者吁请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us Ⅱ)支持编纂一部全新的“拉丁语词库”(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名称缘起于法国古典学家斯泰帕努斯《词典或拉丁词库》(DictionariumseuLatinaelinguaethesaurus)。1884年,古典语文学家沃尔弗林(Eduard Wölfflin)开创《拉丁语辞典学和语法档案》(ArchivfürlateinischeLexikographieundGrammatik),为“拉丁语词库”奠定了基础。1894年,巴伐利亚科学院设立“拉丁语词库”(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工程,计划囊括自拉丁语创始以来,至公元7世纪伊西多尔《辞源》之间,见于所有文献载体的拉丁语词汇。“拉丁语词库”于1900年首发分册,2010年发行字母P所属词目分册,目前正在编纂N和R的词目,计划于2050年完成全部工程。“拉丁语词库”目前由25个国家的33个古典学术机构组成“拉丁语词库国际学术委员会”,西方以外的学术机构仅有“日本学士院”,委员为前院长久保正彰(Masaaki Kubo)教授。“拉丁语词库”无疑将成为西方古典学术史上词目最为完备的拉丁语辞典,是西方乃至世界古典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浩大工程。
1934年,法国语文学家伽菲奥(Félix Gaffiot)编成出版《插图拉丁语法语辞典》(DictionnaireIllustréLatin-Français),是法语学界最具权威的拉丁语辞书,2016年修订新版后,收录7万多条词目,涉及近20万个词汇,5万多条引例,引用500多位拉丁语作家的近900种文献,成为西方古典学术界最具权威的拉丁语辞书之一。伽菲奥《插图拉丁语法语辞典》的最显著特点,一是为重要名物附有插图,二是词目收录宏富,三是文献举例广泛,四是引例全部译为法语。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法语辞书自1934年初版,就得到日本和歌山大学欧洲文学教授小栗栖(Hitoshi Ogurisu)等的学术支持,成为东方学者参与西方古典拉丁语辞书编纂之先例。这部法语辞书2016年的修订版,得到日本国家高等产业科技研究院工程师大久保克彦(Katsuhikokubo)的技术支持。
1931年5月,牛津大学出版社代表委员会(Delegates of the Press)启动编纂了一部全新的拉丁语辞书,规划既不同于里维斯和绍特修订完成的《拉丁语大辞典》,也不同于巴伐利亚科学院的“拉丁语词库”,这部拉丁语辞书拟收录从发端至公元二世纪末的古典拉丁语。1933年秋,《牛津拉丁语大辞典》(OxfordLatinDictionary)的编纂工作全面展开,由牛津大学的所有古典学者与50多位校外志愿者组成编纂委员会,即使在战火纷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辞书编纂仍未中辍,先后历经苏特教授(Professor A. Souter)、贝利博士(Dr. Cyril Bailey)、怀利先生(Mr. J. M. Wyllie)、格莱尔先生(Mr. P. G. W. Glare)四任主编。从1968年起,该书按字母次序分卷出版,每两年出版一卷,整个编纂工作历经50年,1982年合卷出版,2012年修订再版,收入约4万个词目, 10万义项,涉及3世纪以前几乎所有拉丁作家的全部传世作品,引例较前述所有拉丁语西语辞典远为丰富,惜未将例句译为英语。这部辞典是英语学界最权威的拉丁语辞书,也是西方古典学术界最具权威的拉丁语辞书之一。
三、 我国拉丁语辞书编纂学术史略
我国的拉丁语汉语辞书编纂,可以上溯至明代来华耶稣会士。万历三十二年(1605),利玛窦(Matthaeus Ricci)编成《西字奇迹》,并与郭居静(Lfizaro Catfino)合编《拉丁词汇: 按欧洲字母通例排列,以汉字注音》(Vocabulariumordinealphabeticoeuropaeomoreconcinnatum,etaccentussuosdigestum),便于传教士识读汉字。天启六年(1626),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编成《西儒耳目资》,以拉丁语“字父”(辅音)和“字母”(元音)拼音法为汉字注音,明代著名思想家方以智《通雅》对此书多有引用。据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记述,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恩理格(Herdtricht)编写的《拉中大辞典》印行,惜未有传世。明清之际,中国人修习拉丁语,主要限于天主教范围,拉丁语正式用于中国官方书籍,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交涉官文。至雍正朝,清廷延聘法国传教士在宫廷中教授拉丁语,令“通四夷馆”编成《华夷译语》98卷,其中《拉氏诺语》5卷,每页列拉丁词4个,每一拉丁词之下,列对译汉字单字,汉字下再以数目不等之汉字为每个拉丁词注音,这已然是音义兼备的拉丁语汉语词典。(方豪 1969)
明清两代,由天主教传教士编写的“拉丁语汉语词典”或“汉语拉丁语词典”,乃至拉丁语多语词典,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者,多达50种以上,这些都是我国最早的拉丁语汉语词典。其中,咸丰元年(1852)由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康萨维(Joach Alph. Consalves)编写的《辣丁中华合璧辞典》(LexiconManualeLatino-Sinicum)具有代表性。这部释义十分简略的拉丁语汉语词典,1937年由西什库教堂印行至第六版,1970年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据此影印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广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编成多种拉丁语藏语辞书,民国五年(1916)康定地区主教倪德隆(RR. D.D. Gireaudeau)汇集此前所有拉丁语藏语辞书,编成《拉丁语法语藏语词典》,在包括藏学在内的古典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明清以来,这些发生在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拉丁语辞书编纂,主要由西方来华的天主教士主持,可视为西方拉丁语辞书编纂在中国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自然科学学者编纂出版了大量拉丁语汉语专科辞书,如《拉汉汉拉两用医学词汇》(上海当代医学出版社,1953)、《拉汉孢子植物名称》(科学出版社,1954)、《拉汉无脊椎动物名称》(科学出版社,1966)、《拉汉医学词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拉汉海洋生物名称》(海洋出版社,1982),《拉汉科技辞典》(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拉汉植物学名辞典》(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等。这些自然科学专科辞书的编纂,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自然科学学者厚积薄发的成果,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晚近30年来,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拉丁语汉语专科辞书编纂渐衰,无新成果问世。
1957年,香港保禄印书馆出版了由天主教圣言会苗德秀(Theodoro Mittler)和彭加德(Ernesto Böhm)司铎编写,由张维笃主教和甘增佑司铎校勘,并由彭加德司铎增订的《中华拉丁大辞典》(MagnumLexiconSinico-Latinum),正文规模近2000页,采用《辞海》和《辞源》的词目体例,1983年修订再版,这部由西方和中国天主教学者共同编纂的大型辞书,是我国迄今最具权威的“汉语拉丁语辞典”。1965年,台湾吴金瑞神父主要参考伽菲奥《插图拉丁语法语辞典》编成《拉丁汉文辞典》,由天主教光启社出版,这部辞书收录词目约3万条,释义古朴典雅,引例多取自古典拉丁语,注明拉丁语作家人名,并附有插图,但释义仅举词组或片语,无完整例句,亦未标注文献来源,仍为简明辞书之属。1985年,谢大任先生编成《拉丁语汉语词典》(DictionariumLatino-Sinicum),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4.5万条词目,释义举例丰富,但无完整例句,书证未标注拉丁语作家人名和文献来源,只是一部“中型语文工具书”。1986年,彭泰尧先生主编《拉汉词典》(DictionariumLatino-Sinicum),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3万条词目,释义仅有“注释词”,无引例,属一部“简明拉丁语综合词典”。2002年黄风教授编成《罗马法辞典》,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罗马法律制度的法学专业辞书,共收录与罗马法相关的词目约2600条,绝大部分是法律术语,同时包括一些以拉丁文形式表现和流传的法律格言(谚语)和短语,还有一些罗马法历史人物词目,是一部“小型专科辞典”。2006年以来,在中国学成并长期任教的奥地利学者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先后编成出版《拉丁成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拉-英-德-汉法律格言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拉丁语桥·拉丁语/英语/汉语修辞学词典》(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多部拉丁语辞书,并将于近期出版一部200万字的中型拉丁语辞书,对我国拉丁语汉语辞书编纂事业居功甚伟。但时至今日,我国尚无一部符合时代要求的多学科、综合型《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两方面的卓绝努力,都是在“如何应对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强势”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时至今日,真正化解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强势的任务尚未完成,如何深入认识西方文化传统之根本,仍然是中国学术的首要任务。自严复1898年翻译出版《天演论》以来,我国学界引介西方学术思想,主要局限于西方现代思想领域,要真正深入西方思想传统,必须推进西方古代经典汉译工作,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掌握西方古典语言是关键,编纂词目宏富、释义精审、例句充实的西方古典语言辞书,是亟待推动的学术任务。
拉丁语文学史,发端于公元前6世纪,绵延2500年,直至19世纪末;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经典文本,主要用拉丁语写成;近代西方通用学术语言就是拉丁语,西方古典文献校勘与注疏都使用拉丁语;拉丁语至今仍为罗马天主教和梵蒂冈的官方语言。从公元前6世纪讫于公元600年的“古典拉丁语”是古罗马文化的载体,有鉴于“古典拉丁语”在拉丁文学传统中的基础地位,特别有鉴于以“古典拉丁语”为载体的古罗马文化,是从古希腊讫于现代的整个西方文教传统的重要枢纽, 编纂《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应为西方古典语文辞书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6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MagnumLexiconLatino-Sinicum)编纂”获准立项。根据项目规划,这部辞书将依托我国和西方学界已有古典拉丁语辞书编纂成果,博采我国和西方最具权威的古典拉丁语辞书之所长,参照百年来我国古典拉丁语文献翻译研究资料,借鉴国内外古典辞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积极利用语料库词典学最新成果,编成一部词目收录宏富、语义系统完备、文献辑录广泛、校勘精准详实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型古典拉丁语汉语辞书: 计划收录词目8万条以上,预计规模600万字。
编纂《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不仅是对以古典拉丁语为载体的古罗马文献的全盘梳理,也是对近代以来我国古典拉丁语文献翻译成就的全面清理: 对于我国古典拉丁语教学乃至西方古典语言教学,对于将古典拉丁语文献乃至西方古典文献翻译和研究引向深入,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开展西方古代研究乃至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对于深入认识现代西方根植于其中的西方古典文教传统,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