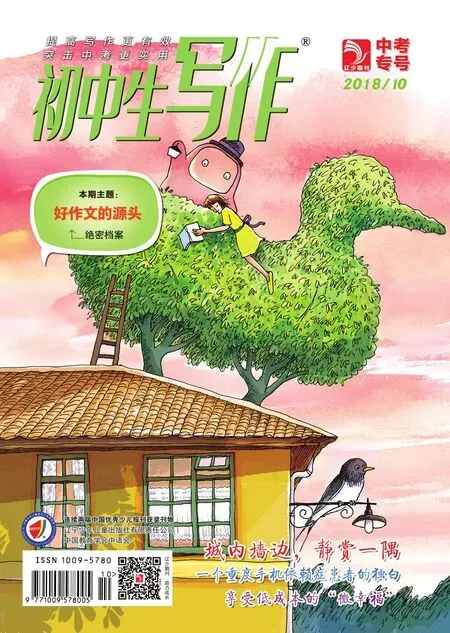一生如诗
2018-11-29◎于丹
◎于 丹
人生总有几个时刻与诗结缘。
第一时刻,是小时候唱儿歌。“你拍一,我拍……”清脆明亮,天真自由,儿歌是诗意的开始。女儿很小就能背杜牧的《清明》。有一天,她问我:“妈妈,什么是词?”我说:“你看这首《清明》,我们要是重新断一下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如此缤纷错落,就是词了。”诗的格律,词的词牌,如果懂得了情感的起伏跌宕,它就是可以信手拈来的一种形式。童年诵读诗词,它点燃了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心,让我们学会了语言的节奏。
第二时刻,是我们恋爱读情诗。所有爱情都是诗人情怀,所有恋人都酝酿着芬芳诗意。千愁万绪说出来,写下来,就活在诗里了。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几年下放到印刷厂,做一些永远都看不见字的体力活,归来的日子遥遥无期,生出好多寂灭和绝望。有一天,我推着单车下班,偶然飘来罗大佑干净的声音:“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原来在我的生命中,好多诗意的东西还活着,似乎顺手拽过来的太阳,一下就把心照亮了。
第三时刻,人到中年,诗歌抚慰我们疲惫的心灵。中年离角色很近,离生命很远,人会活成小说,活成散文,已然淡忘了诗歌。然而,“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在涉世既深又饱经忧患之余,这些多而深的愁,有的不能说,有的不便说,“识尽”而说不尽,说之复何益?浓愁淡写,重语轻说,耐人寻味。
下一时刻,是暮年。“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爱尔兰的叶芝和终生女友茅德·冈妮的爱情故事,和这首诗一起成为后世佳话。那一年,叶芝向他的爱人表白:“我曾以古典的方式爱过你。”也有诗人说:“我所相信的,只是那些从来没有被说出来的爱情。”当你老了,如果还能与诗做伴,就能活出一生的如诗岁月,让我们外在的、琐碎的、无奈的年华多多少少有一点儿梦里的颜色。
同样一首诗,不同的年纪,念法也许是完全不同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果然,一生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