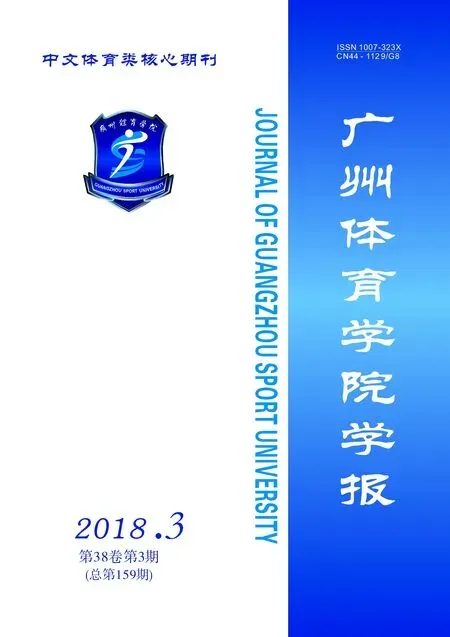传统武术文化内涵下新时代“文化自信”构建路径探索*
2018-11-26冯素琼
冯素琼
(四川农业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继承革命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这一段表述清晰而准确的点明了当前时代的重要任务——在物质文明充分丰富、国家实力普遍增强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国内精神文明建设,构筑中国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才能够在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站稳脚跟,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文化自信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发展。武术文化在我国发展已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写就的《左氏春秋》中就已经有“武术”一词的记载。武术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却并非一成不变,武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2],在春秋时代,武术是杀伐之术也为战争之术;在三国时期,华佗的“五禽戏”使武术成为综合防身与健身双重功用的运动;在民国,武术成为民间义勇抵御外侮的重要手段;在当代,武术是一门关于身体技艺的艺术,是具有保健功能的运动项目,是中国五千年哲学思想的外化展示。武术从表象到本质都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和,武术运动是新时代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是对外展示中国“民族自信”的重要桥梁,是中国当代弘扬红色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文化动力。
1 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表征样态分析
1.1 古代劳动实践的凝练浓缩——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武术
武术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武术来自于古代征战时战士身体格斗经验的总结;有学者认为武术是古代祭祀中“舞”的实用化,是从祭祀行为演变的一种形体技巧;有学者认为武术来自于古代人民对动物形体动作的模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相关研究者则认为武术是古代人民劳动生活实践的产物,武术是劳动者劳动动作的抽象化。最初的武术来自于先民狩猎时的身体动作,如拳打脚踢、躲闪、跳跃、摔跌等,是拳术的萌芽,劈、砍、扎、刺、撩则是武术长短器械使用方法的萌芽。换言之,当代的武术动作是对先民劳动动作高度抽象化、集中化的展示与总结[4]。
作为古代劳动实践产物的武术,也具有注重现实实践的特点。三国时代华佗创立“五禽戏”,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强身健体,也在于帮助人们在动荡不安的时势中保全性命。明朝末期戚继光著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莅戎要略》《武备新书》等武学军事著作,发明、改良戚氏军刀、狼筅等武器,其本源目的在于抵御东南沿海地区倭寇的袭击和骚扰。目前留存的武术成果包含着中国五千年劳动人民生活实践的智慧,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结晶。
1.2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外化体现——作为形而下的中国哲学映射的武术
武术以其高度统一的文化气质超脱于西方体育项目,成为具有浓重东方文化色彩的运动项目,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来自于武术文化与中国古代哲学内涵的深深契合。中国武术和西方竞技体育所强调的“力量、勇气、胜利”相比,更为调和与自然,其世界观也更具有朴素与辩证的特点[4]。《老子》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5]则充分反映了这种参差对比,相辅相成的观点。武术中对“力”的描述是双向和对照的,出拳这一动作是施力的行为,更是被动受力的行为。拳头虽然可以打击对手,但在打击的同时,拳头也将受到被打击物的冲击与反弹。在这种辩证的哲学观念引导下,中国武术自古就有“以德为先,以德帅武,止战于武,武即和平”的观念,并在此观念下衍生出了“点到即止”、“以和为贵”的比武规则。习武的目的在于停止争斗,而非在争斗中取胜。这种观点从古流传至今,与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出自同源,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扎根于文化深层结构的爱好和平的观念意识[6]。
除了参差对照、朴素辩证的武学观念,武术也反映了中国人崇尚道德的民族文化气质。中华道德中又以儒家所提倡的“恭、敬、惠、义”为理论基石。《论语》中有著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此理念衍生下,出现了“抱拳礼”。展开比赛之前,比武双方通过抱拳的方式表达对对手的尊重,也表示对武术的敬意,更表示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圆融。《论语》中“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等描述,逐渐演变成传统武术对习武者道德的要求,仁爱是习武者行事的根基和标准,恃强凌弱、以武犯禁则被武术界视作是习武者的武德低下的表现。明代内家拳法、湖南巫家拳、峨眉枪法等都明确提出了对入门弟子武德考察的要求[7]。
1.3 洒脱与秀丽融合的中国体育艺术结晶——作为审美与实践双重价值凝聚的武术
中国传统武术继承了“舞”的特性,在其形体动作、兵器器械、武术套路编排、动作名称等各个方面都具备了审美的特性。武术经历五千年中华历史的洗礼,逐渐成为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形体艺术。以太极拳为例,太极拳兼具形态美、神态美、文化美三美。形态美包括“逢上必下、前发后塌、刚柔并济、内外兼练”的对称美,“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的节奏美,“非圆即弧,丹田内转”的曲线美;神态美则以阴阳并存、虚实相生、动静结合三地充分呈现。太极的文化美感主要由风格流丽的武术套路编排和各个精准又具有画面感的招势名称组成。风格流丽的武术套路编排表现为连绵相续,气贯始终的动作衔接与情理统一、动静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圆融的展示;精准又具有画面感的招势名称则有金刚捣碓、白鹤亮翅的形意结合,玉女穿梭、青龙出水的洒脱出尘,懒扎衣、高探马的写实生动[8]。
除却审美功能,中国传统武术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因素则是其强身健体、防身御侮的多重现实价值。
2 武术与文化自信的内在联系与文化呼应
2.1 民族自豪视野下的文化自信:传统武术对民族特点的展示与弘扬
中国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劳动人民的日常实践,更离不开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思考、改良与传播。换言之,中国武术从产生与传播层面反映了中国千余年的历史时间变迁,是中国文化浓缩提炼的结晶。在武术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的礼让谦逊、可以看到中国独有的“点到为止、见好就收”的平和态度、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外圆内方、固守原则的正直秉性。修习武术本身就是参与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观看武术则是从武术抽象化的动作行为中观赏中国文化。我国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表演的北京八分钟,就通过武术向世界展现东方文化中刚健、灵秀的文化特质。
武术作为一项可以修习和训练的运动,其影响显然不止于文化欣赏层面。武术对于国人来说是一项极具民族性和地缘性的运动[9]。咏春拳展示南拳拳术的灵秀与敏捷,少林长拳则展示中原拳术的疏放与刚猛。国人通过观看武术、修习武术,往往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深刻的历史底蕴,并且将自发的从内心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到骄傲。这种自豪感产生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对中国人谦逊平和的人格气质的自我认可,也有对其生长地域的依恋与认同,更有对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历史的深切认同。武术凝聚的民族认同感也使得武术与一般西方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和马拉松、足球等传统西方赛事相比,国人在从事武术锻炼时除了运动带来的快乐之外,还将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以及根植于血缘内的民族召唤,进而形成对中华文化、对中国这一概念的深切认同[10]。
2.2 国家自豪视野下的文化自信:传统道德与古代哲学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与规训
武术除了民族性的特点之外,武术也具备着哲学性的特点。武术既能够强健群众的身体,也能够构筑人民的精神世界。武术从创立之初,就被用于战争,“春秋无义战”到“荆轲刺秦”的历史演变,无一不体现了武人对社会公义的重视与坚守,武术不仅仅是一种身体实战的技巧,它更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外化表现。武术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体认,通过修习武术,人们可在武术文化中感知中国古代哲学对人的道德要求,受到古代文化的道德熏陶、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在当代,武术也将继续发挥人格建构作用,唤醒国人的爱国情怀,塑造国人的国家认同感。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群道德习惯的改良、对国人国家意识的唤醒两方面。
武术对人群道德习惯的改良主要表现为唤起国人的道德羞恶心,促使其知行合一,改变拜金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在西方消费文化的侵袭下,国人越来越多的沉溺于金钱和消费带来的短期快感,拜金风气也进一步导致国内出现金钱至上、矫饰伪善、权利崇拜、媚上欺下等现象出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在消费主义与拜金观念的影响下,呈现出一种消极、负面、颓丧的态势[11],中国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丧”文化就是这些不良观念影响的集中表现。武术自强、奋发的精神显然与这些负面流行文化格格不入,也正因为武术的正气、传统与固守才能够矫正当下出现的这些不良风气,改变社会环境,以武术的正气改换“拜金”、“丧”的负面影响,唤醒国人的价值自觉、人格自觉、文化自觉。
武术对国人国家意识的唤醒主要通过武术的体认功能完成。在近代,武术是和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10年霍元甲于上海创办的精武体育会,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爱国群众性武术团体之一,精武体育会的成员多次击败日本、美国等地的力士与拳手,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中华武术优秀文化,增长了国民的文化自信、国家自信,打击了近代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除霍元甲外,民国知名武术家李景林、李书文、尚云祥、张策、杜心武等也都为中国近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代人在修习武术的同时,也是在学习武术中深刻蕴藏的爱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武术本质上与文化自信、国家自信有着深深连结。
2.3 文化殖民与反殖民视野下的文化自信:武术文化的世界性流行与生发
随着网络传媒的发展,国内接触国外文化的方法和途径不断增加,国外糟粕文化对我国文化结构正常发展逐渐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在于国人的欣赏审美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对国内文化存在自卑心理,对外国文化盲目崇拜,全盘接受不加思考;一方面也在于国外糟粕文化包装比较隐蔽,国人缺少警醒识别的意识,也较为容易被西方糟粕文化迷惑[12]。国人迷恋美国对外输出的好莱坞大片,就是糟粕文化侵入中国文化结构的重要例证,好莱坞影片的艺术价值不高,画面充斥暴力、恐怖等内容,价值观念上输出美国的救世主情节,然而国人却趋之如骛。其本质还在于国内没有形成一套正向、积极、高尚的价值观念。武术的体认规训与武术的价值流变,显然可以起到推动国人精神文明价值正向发展的作用,也能够间接提高国人的审美情趣,抵御西方糟粕文化的侵袭。
武术文化除了抵御西方文化糟粕,对西方文化内容殖民加以辨别外,武术文化的发展与弘扬还将起到文化的反倾销、反殖民的作用。2018年2月17日,中国外文局首次发布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显示外国人认知度排在前100名的中国词中,文化类的词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少林”、“阴阳”、“功夫”、“气功”等武术文化相关词汇分别位列于第一、二、六、八名,可见武术文化强大的海外影响力。近代以降,武术文化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形象认知。早在20世纪初,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人是“黄祸”,在电影、舞台上的中国人是身穿清朝官员服装、留着鼠尾辫,身材消瘦神情阴郁的“傅满洲”形象,“傅满洲”形象也充分表达了西方人对东方充满误解、敌意的文化潜意识。然而这一形象也最终被上世纪6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电影所刷新,李连杰、成龙等功夫演员在国外的影响力也间接掀起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风潮,从武术到中医,从汉语到汉字,中国文化通过武术这一路径,实现了“走出去”的文化革新,实现了海外文化面貌的革新与生发[13]。武术文化本质上蕴含的民族性、文化性、国民性特点也促使中国人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豪感、文化自信感。
3 基于武术现实应用层面的文化自信构建路径探索
3.1 文化意识层面:发掘武术中的民族元素,创新性继承和发展传统武术文化,扩大武术在群众中的接受度和实践度
中国武术的发展是人民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暗合着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唯物史观。因此,传统武术在当代的发展也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春秋时期的“尚武精神”塑造了一批批身体素质有意、人格精神健康的优秀人才,间接推动了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发展,在当代,也可以通过弘扬武术文化,提高武术文化在当代群众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来达到影响群众文化趣味,激活民间思想活力的目的。
相关部门对介绍和弘扬的武术文化也应该做出一定的价值取舍、筛选和创新。重义轻利、尊师重道、孝悌正义等优秀的武德思想在当代也应该被大力弘扬,这些武德思想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不谋而合,是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优秀文化思想。传统武术中也包含着一些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思想与行为,如唯我独尊的“宗派之争”、逞凶斗狠的“比武”等就需要被及时的修正,武术价值观念也需要被及时的引导[14]。从文化基底到文化内涵多方面,实现国人对武术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可与自豪,真正从狭义的文化层面出发,走出实现“文化自信”目标的第一步。
3.2 文化应用层面:发挥传统武术的实践价值和体认价值,使其应用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武术需要被修习和实践才能够发挥其根本的体认作用,仅仅从文化理解层面理解武术是不充分的。因此基于武术实现“文化自信”还需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其积极参与到武术运动中去,进而获得完整的武术文化体验,实现这一图景,首先就需要通过政策调节,来引导群众的运动选择与运动取向。从近年来马拉松、滑雪等运动逐渐升温的态势来看,我国群众并不缺乏参与运动的热情、也不缺少运动保健的意识,只是缺少合理的价值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习近平总书记“全民健康观”的思想启发下,开启全民武术运动的推广和拓展,将能够极大地推动传统武术在人群中的接受度,扩大武术文化影响的人群范围,激发群众参与武术运动的热情。文化层面上,融入于全民体育的武术运动也必然会因为群众的日常实践焕发新的活力,武术的体认功能也将得以发挥。通过群众的实践和体验,武术中“止战于武”、“点到为止”、“以和为贵”等思想也将获得新的生发空间,得到符合新时代价值观念的阐发。武术中正向、昂扬、康健的开阔价值向度与高亢豪迈的人生价值观念[15]也将发挥作用,引导国人走出拜金主义的阴影,帮助国人从武术优秀文化中汲取精神精华。“健康中国”层面上,也因为武术或急或缓、或收或放、自我内练、多范围适应的特点,进一步放其保健功效,提高群众身体素质,实现当代人健康生活的目标。
3.3 文化塑造层面:挖掘武术文化中人格道德建构的重要作用,以爱国主义为根基,以武术为推广手段,构建全社会的国家自豪意识
传统武术的着眼点是个体的“人”,更是群体的“国”。不同武术流派对待国家和个人的认知与阐发不尽相同,但武德修养体系中,始终将国的概念放置于习武者道德标准的最高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念也贯穿着武学系统。推广武术文化,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唤醒群众的爱国自觉、民族意识。要达成唤醒群众爱国自觉与民族意识的目的,首先就需要进行武术国族意识的宣传和建构。武术文化的宣传和建构依旧需要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其具体展开可以利用城市、乡村的基层宣传展板,宣传太极拳、太极剑等群众熟知的武术项目的好处与作用,循序渐进地在宣传展板中加入近现代爱国武术家的生平事迹,有条件的地区甚至可以聘请有相关武术练习经验者为社区群众讲学、演示,激发群众对武术文化的热情。
此外,武术对人的教化作用、爱国主义情怀的宣传作用也适应于中小学生群体。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成长的重要阶段,传统武术文化的调和、均衡与道德教化必然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生的人格建构,对校园的德育教育起到辅助作用。
4 总结与展望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小康即将建成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推广、发展、构建、引导。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实践的宝贵遗产,是人民历史实践的重要成果。武术既可以对个人道德修养、个人审美情操加以构建、也能够催化修习武术者形成深刻的民族国家情怀。武术兼具强身健体的养生功效、古代哲学文化的审美熏陶等作用,它也契合着当代国人的自我完善与身份认同的渴求,这些因素都使得传统武术在当代构建“文化自信”的综合背景下,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学理论,2017(11):1-12
[2] 沈小乐.文化自觉视野下的武术传播变迁[J].新闻界,2014(4):40-44
[3] 戴国斌,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2
[4] 尹海立,刘跃军.中国传统武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自觉[J].武术科学(搏击·学术版),2004(2):29-32
[5] 老子.老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
[6] 冉学东,刘帅兵. 从国家文化软实力视角看中国武术的价值使命[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3):251-253
[7] 张峰.武术本质的文化审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8):142-144
[8] 王岗,张大志.从“体育”走向“文化”: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必然选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6):1-7
[9]王俊奇.武术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关系[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12):37-40
[10]刘帅兵,李鸿,吉灿忠.从“自卑”到“自信”:实现中国武术自强的文化反思[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4(1):63-65
[11]李继高.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66-170
[12]方国根.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选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8-28(B07)
[13]张燕中,刘宏,王静.文化焦虑与认同:中国武术异域传播中的文化错位[J].体育与科学,2014(4):51-54
[14]王维,胡凯.武术价值观变迁的回顾与反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11):141-144
[15]李亚晴,吉灿忠,丁晓鹏,等.文化生态学视域下传统武术的传承创新[J].中华武术(研究),2013(8):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