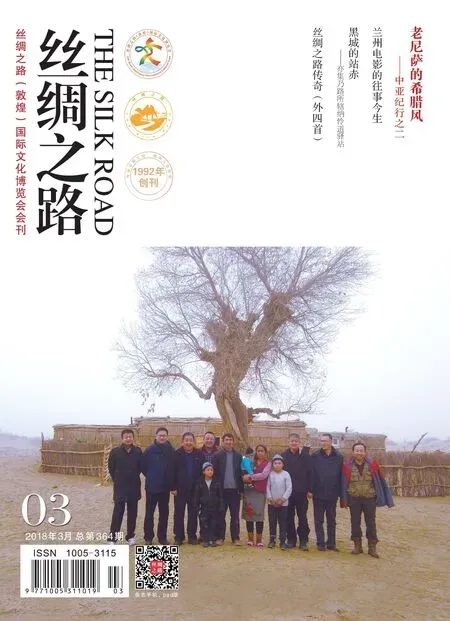陶然逸兴颂乡风
2018-11-21何茂活
文/何茂活
与李中峰先生相识已10多年了。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甘肃省民乐县组织的一次活动上,我与同事朱瑜章教授应邀参加,活动的发起者正是海潮诗社创始人、《海潮诗词》主编李中峰先生。会后小聚,几位民乐的文友在酒酣之际竟能脱口吟诵出中峰先生的一些诗句,如“千年古刹几成尘,又见今朝塑佛身。泥土由来无贵贱,莲台一坐便成神”(《游圣天寺》),“携手同登百尺楼,人生达命欲何求。纵然醉倒眠床底,也在高高最上头”(《迁居六楼戏作示老伴瑶琴》) 等。这样的诗句,我听过一遍,也便大体记住了。说实话,时下很多人在写旧体诗,但像这样过耳成诵而又能启人深思的实在不多。因此我想,中峰先生的诗,能够在一个地方被人记诵,并且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地方的文学生活,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后来许多年,又有多次机会与先生晤面,或作为作者参加政府部门主办的采风征文活动,或作为评委参加旧体诗词、辞赋征文的评奖活动,或因朋友相约小聚,10多年里大概也有八九次之多。最近一次是2017年3月24日,参加张掖旅游文化全民宣传行动颁奖会,我们同为获奖作者,并且邻席而坐,先生说正在编辑个人辞赋集,编好后要我作序。我则自知谫陋,婉言相辞。月余之后,朱瑜章教授转来《李中峰辞赋集》校样,说中峰先生嘱我代为校阅并为之作序。这样一来,我便再也没法推辞了。
5月下旬,遵嘱将辞赋集作了逐字逐句的校读,在文字、标点及注文所引书证等方面作了一些改订。拜学之下,感触良多。愚以为中峰先生的辞赋创作,可资学习者多多,但举其要者,约有如下数端:
一是浓郁乡情与时代精神。辞赋集收录赋作72篇,或咏名物,或颂乡风,或怀古迹,或赞时贤,无不立足地方,胸怀家国,歌咏时代,弘扬传统。正如作者自言,“览山岳之雄奇,叹人事之兴废”(《扁都口赋》),“感天地之变化,看万象之新生”(《民乐公园赋》),表现了作者对家乡山水、人文的一腔挚爱,以及对家国变迁的由衷感怀。就题材而论,除对地方风物的歌咏以外,或写抗震救灾,或写旅游开发,或写农税免除,或嘲官员贪腐,均为有感而作,因时而发,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济世情怀。全书诸作,以颂赞为主,格调高昂,启人奋进。这一方面是由辞赋这一文体的传统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者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判断,来源于作者对时代精神的概括与挖掘。在这些精心结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优秀党员干部的敬仰,对乡村文化教育人物的称颂,以及对文朋诗友的追思,对兄弟子侄的忆念,从中可以窥见作者追贤崇善、乐观豁达的内心世界。在《芨芨草赋》中,他写道:
秉性刚健,何惧雨疏风狂;处身随和,遍居旷野僻乡。汲天地之灵气,吮泥土之乳浆;纳大地之云雾,凝塞上之春芳。情牵沟壑,甘与红柳为伍;远离尘俗,不羡花木称王。逆寒流而秀色,沐冷月之清光;苦修身以济世,固漠土而守疆。
这是作者对芨芨草的描摹,也是对西部人的礼赞,更是作者人格修养和崇高追求的真实写照。
在《霁雪楼赋》中,他以此自勉:“扬中华之文明,历沧桑而不弃;承职守之责兮,虽皓首而不疲。身居小楼,心志常怀国事;人届晚景,眼光仍注寰宇。”在《自费出书赋》中,他以此自嘲:“自愧无才犹立志,冰心一片老庸夫。闲来偏有伏枥志,彩笔犹描盛世图。”凡此种种,都是作者诗人气质与家国情怀的自然流露。
二是盎然诗意与隽永哲思。辞赋集中的赋作基本都是骈赋,而骈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因此赋须有诗的意境与韵味,否则便可能只是辞藻的堆砌。那么,诗意来自哪里?来自生活中的观察,来自诗人的慧眼,来自对世界的关爱和理解。中峰先生的辞赋集中,不乏这样具有浓厚诗意的作品,如《黑河调水赋》:“晴空万里远山低,大漠无垠落日迟。穿过千里大戈壁,河水潺湲到额旗。毕竟真情浓于水,一河波浪一河诗。”“一河波浪一河诗”,这是对张掖人民顾全大局、为下游分水这一时代壮举最为热情豪迈的讴歌。再如《芨芨草赋》赞曰:“一根芨芨一杆枪,漫天青缨筑绿障。莫嫌出身贫且贱,勿哂身瘦貌不扬。自古寒门多将相,须知伟大出平常。”这些描写和议论,都准确地捕捉了芨芨草的形象特点及所蕴含的审美价值,与作者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新诗《芨芨草》 (见该赋注文) 对比阅读,更见其对这一物象的深刻理解与钟爱。
辞赋虽有“诗”性,但毕竟属于“文”的范畴,因此在行文上比起诗来便自由了很多,适当的议论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这种议论不可能像议论文那样完全铺开,因此常常表现为含义隽永的哲思妙句,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中峰先生的赋中也常常给人以这样的阅读体验。如《土塔赋》:“积沙可以成塔,抟土即能造人;莫道沙土松散,凝聚就是力量!”又如《童子寺赋》:“心即是佛,求佛莫若求自己;禅心难问,问禅何如问心旌。”“红男绿女拜佛来,求名求利费疑猜。菩提不是摇钱树,明镜应非钓誉台。积德利民当避祸,贪赃枉法必成灾。甘霖难泽无根木,善种心田花自开。”无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都显得自然畅达,合情合理。而其所以能够臻于此境,莫非得益于诗意与哲思的巧妙结合。
三是秉承传统和大胆创新。辞赋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基本规律必须遵循,基本特征亦须保持,如擅于铺陈、富于辞藻、善用故实、讲求音律等,今人作赋,亦须如之。若非如此,便有悖体制,影响美感。中峰先生早年爱好新诗,中年转攻旧体诗词,老来醉心辞赋。因有诗歌创作的经验和良好的文史素养,因此他在辞赋创作中运用语言得心应手,使用典故信手拈来,属对押韵活泼自然,作品受到当地文学爱好者的推崇,也得到辞赋学界专家的好评,这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继承传统方面,中峰先生师古而不泥古,敢于尝试和创新,根据作品的需要采用适当的语言和灵活的形式。以语体风格而论,作品中不乏以时语入赋者,如《抗震救灾赋》描写地震时的情形:“当其时也,高楼甩头,狂摆疯扭;大地着魔,筛糠颤抖。天隆隆兮如雷怒吼,地绉绉兮似蛇疾走。”文末赞曰:
地塌陷了,天塌不了;房屋倒了,精神不倒。
人民有情,党恩浩浩;重建家园,河山再造。
自力更生,不等不靠;丽日高天,阳光普照。
这显然是地震亲历者的真实描述,也是灾区群众最真切的内心感受和强烈心声。在这些辞句中,我们看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和谐统一,也看到了作者创作时内心的律动。
就用韵而言,这些作品均不拘泥于古韵,而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主要依据,间或参以方音,采用较为灵活的方式进行押韵。对仗方面,注意句子结构的大体相似,不过分追求严整工稳。因此整体而言,韵律和谐,节奏明快,读来朗朗上口。
就篇幅及句式特点而论,全书诸作可谓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篇幅长者,至于千言;短者则仅有寥寥数十字。句式多为杂言骈偶形式,但也有纯用四言或七言者。《四君子赋》:“梅品德,竹精神,傲霜秋菊溢清芬。碧叶嫩青青,寒来犹自荣,清香飘广宇,清廉启众生。千千结,万万心,动若龙须灿若金。骨似铁,气如霞,不屑争添锦上花……”这样错落有致、节奏鲜明的造句形式,显然兼取了格律诗及长短句的句式特点,打破了辞赋与诗词之间的界限,这样的探索值得肯定。作者于2015年创作的《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赋》,全篇采用四言句式,文意畅达,铺陈自然,无疑也是锐意创新、寻求突破的成功之作。同年所作《张掖湿地楹联集句赋并序》,“集联为赋,独出心裁”,虽为集句,但创意独特,内容亦隽永可喜。
最后要说的是,大约在10年以前,应中峰先生之约,曾为其《霁雪楼辞赋集》中的部分作品写过几则简短的评论文字,有幸续貂于相应各篇之后。于今匆匆10年过去,再承谬爱,重评宏文,既感先生之高才雅意,复叹时光之匆促无情,故亦略缀拙句以附庸于兹,祈祝先生笔耕不辍,康乐年年——
陶然逸兴颂乡风,放眼山川夕照明。
一叶一枝观兴废,半忧半喜叹枯荣。
耄龄犹奋登高志,佳韵常含济世情。
椽笔汲来黑河浪,笙歌不倦伴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