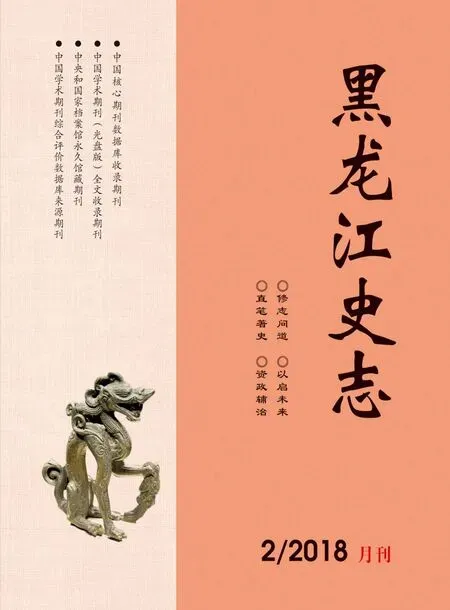清华简研究述评
2018-11-18林东梅
林东梅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清华简于2008年7月入藏至清华大学,系清华大学校友向母校捐赠。经过碳14测定与专家组鉴定,清华简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晚期楚地简册。竹简共计2388枚,是迄今为止战国竹简中数量较大的一批。这批竹简包罗宏富,内容则以书籍为主,其中囊括了对研究中国上古史以及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的“经”“史”类典籍,并且简册内容多为已往发掘先秦时期简牍之所未见,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一、清华简研究综述
清华简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于秦朝焚书余火中幸免,因此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典籍之原貌,不仅对了解中华文化初期面貌以及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的发展都将有所助益。
经过十年的释读研究,清华大学已陆续将照片及释读情况公诸于世,至今已出七辑。其中囊括:2010年12月出版第一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涉及九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皇门》《祭公》和《楚居》;2011年12月第二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此辑收入了一部已经失传两千余年的历史著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其命名为《系年》;2012年12月第三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此辑收录《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一篇、《芮良夫毖》一篇、《良臣》一篇、《祝辞》一篇、《赤鹄之集汤之屋》一篇,共六种八篇;2014年1月第四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此辑包含《筮法》《别卦》《算表》三篇文献;2015年4月第五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此辑包括《封许之命》《厚父》《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六篇;2016年4月第六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此辑包括《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产》《管仲》《子仪》五篇文献;2017年4月第七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此辑包括《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赵简子》四篇文献。
清华简的问世,是先秦史研究领域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清华简问世迄今,学界曾召开多次学术会议,发表相关论文若干篇,并已出版多部专著。其中包括论文集两种:(1)《清华简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2年),(2)《清华简研究(第二辑)——清华简与〈诗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5年)。个人著作二十种:(1)《走近清华简》(刘国忠,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2)《初识清华简》(李学勤,中西书局,2013年),(3)《楚简书法探论——清华简〈系年〉书法与手稿文化》(邢文,中西书局,2015年),(4)《清华简〈系年〉初探》(孙飞燕,中西书局,2015年),(5)《清华简〈系年〉集释》(李松儒,中西书局,2015年),(6)《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李守奎,中西书局,2015年),(7)《清华简〈系年〉辑证》(马楠,中西书局,2015年),(8)《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型研究》(李守奎、肖攀,中西书局,2015 年),(9)《〈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许兆昌,中西书局,2015年),(10)《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贾连祥,中西书局,2015年),(11)《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比较研究》(刘光腾,中西书局,2015年),(12)《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叙事比较研究》(侯文学、李明丽,中西书局,2015年),(13)《清华简〈系年〉所见春秋战事考释》(李充、张相森、钟周铭,四川辞书出版社,2016年),(14)《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姚小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5)《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李守奎,中西书局,2016年),(16)《清华简与古史甄微》(刘成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7)《清华简与儒家经典》(江林昌、孙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8)《楚国官制与世族探研:以几批出土文献为中心》(陈颖飞,中西书局,2016年),(1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书法选编》(李学勤,文物出版社,2016年),(20)《竹简上的经典:清华简文献展》(冯远,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关于清华简释读研究的学术文章则不胜枚举,在此不作赘述。
二、清华简的出土及入藏过程
清华简的发现晚于郭店楚简和上博简,它于2008年7月入藏至清华大学。关于清华简的准确出土时间,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在2013年4月24日于首都师范大学关于《清华简与古典文献》的发言为依据,清华简应该大致于2006年冬天之前出土,因为在2006年冬香港某学术会议上已有关于这批竹简的线索,因此可以断定清华简在2006年冬天以前已经到达香港。关于出土地点问题,因为清华简系被盗掘出土,因此至今仍无法获悉它的确切出土地点[1]。
清华简于2008年7月15日入藏至清华大学图书馆三层竹简保护室,这里恒温恒湿,能够为竹简提供较好的保存环境。7月19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两位研究员开始主持对清华简的清洗保护工作,因之前文物市场对清华简的保存措施不当,故清洗工作困难重重。清洗工作的大致流程是清洗、去污、去霉、杀菌、浸泡保存,这项工作从7月19日一直持续到10月初才告一段落。出于对清华简更好地保护、整理和研究的目的,2008年8月,清华大学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担任中心主任,2009年冬季之后,对清华简的全部拍照工作完毕,清华简的释读研究工作随即正式展开。
三、清华简的内容
清华简与郭店楚简、上博简不同,它的内容是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主要是关于经、史一类的古籍。兹分述如下:
《尹至》简共5支,简长约45厘米左右,存三道编痕,满简可写二十九至三十二字。原无篇名,释读小组根据“惟尹自夏徂亳,逯至在汤”句试拟。简背有具体编号,文字清晰可辨,惟有第二支简上端首字残损。《尹至》篇是记载商汤克夏的重要著作,对于研究伊尹在辅佐商汤灭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重要的价值。清华楚简《尹至》篇也是目前所见关于伊尹的传世文献的最早版本,其文字典雅,叙事完整,是战国中期较为流行的版本。《尹至》篇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够与传世多部典籍契合参校。篇中主要载录商汤与伊尹的对话,不曾见于传世文献,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商代文献。[2]《尹诰》简共4支,竹简长约45厘米,三道编痕。本无篇题,释读小组根据《礼记》与郭店楚简、上博简《缁衣》篇所引确定篇名。简背存次序编号,文字清晰,惟第四简上部首字缺损。《尹诰》篇编联以竹简背后划痕为依据并参校《慎大》叙事顺序而定。《尹诰》亦称《咸有一德》,是《尚书》中的一篇,但是简文内容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大相径庭。据释读小组专家廖明初教授所讲,当时已经有建立在“君权天授”、“天人合一”基础上的民本思想,这也可以理解为孟子思想的源头,简文价值极高。[2]《程寤》简共9支,简长45厘米,三道编,保存完好。全篇原无篇题,亦无次序编号,释读小组依据传世文献曾引用《逸周书·程寤》篇的若干文句,并将其与简文内容相对照,可知本篇简文即失传已久的《程寤》篇,故将其命名为《程寤》。《程寤》篇记载了周文王与太子发因太姒梦见“商廷隹棘”而领受天命之事,可与典籍中关于文王、武王受命的相关记载相印证,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程寤》简的重新发现,使我们得以了解《逸周书·程寤》篇的真实内容,而篇中周文王的有关言论,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商朝后期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2]《保训》简全篇共有11支简,完简长28.5厘米,编痕上下共两道,简文皆顶头书写,简尾一般留一个字距的空白,每支简二十二至二十四字,其中第二支简上半残失约十一字。《保训》简文主要载录周文王文对太子发的训诫之言。周文王对太子发讲述了上古时期的两个传说,第一个是关于舜如何求取中道,第二个传说则是讲上甲微假中于河伯以胜有易,并将“中道”之德传贻子孙,最终商汤得天下的史事,文王以此告诫太子发治政时要善用“中道”。[2]《耆夜》简全篇共14支,简长约45厘米,其中四支有残缺,每简字数不等,背面均有次序编号存系,第十四支简背面有“夜”二字,故以此为篇题。“”字古书作“耆”或“黎”,故现称“耆夜”,其内容弥足珍贵。简文载录周武王伐黎获胜之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君臣饮酒赋歌之史事。因其内容与《尚书·西伯戡黎》《诗经·唐风·蟋蟀》等传世文献关系密切,同时涵盖了文学、史学、礼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自整理报告发布以来,颇受学术界关注[2]《金滕》简全篇共14支,三道编痕,完简长四十五厘米,其中第八支与第十支简的上端均有部分残缺,简背有次序编号,在竹节处书写。第十四支简背下端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文内容与《尚书·金滕》篇较契合,当为《金滕》篇的战国写本。《金滕》篇见于西汉初年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但自西汉以来,学者对其理解颇多歧异。清华简《金滕》篇内容与传世今本《尚书》篇也有些重要的不同,如武王生病的年份问题,周公居东的年份问题。[2]《皇门》简共13支,简长40厘米左右,三道编痕。字迹可辨,书写工整,惟第十简上端残损两字。简文主要记载周公训诫群臣的内容,在周初政治文献中弥足珍贵。简本所用语词多与《尚书》中的《周书》诸篇雷同。简本《皇门》与今本相比有诸多歧异,今本讹脱衍误现象多见,文义晦涩难解,简本相较之则文通字顺,显优于今本。[2]《祭公》简共21支,简长44.4厘米,三道编痕。每支简文字不等,无编号。原有篇题五字,记于第二十一简正面下端,除第二、三、四简两端端稍略有残裂,第十九支简稍模糊外,全篇保存较好,文字可辨。清华简《祭公》篇被释读小组认定为传世本《逸周书》所载《祭公》篇的祖本,以简文与今本内容相互参照,可了解今本的讹脱衍误情况。简文中较为重要的内容当属三公毕、井利、毛班的名号,这不仅澄清了今本的诸多舛误,也对西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楚居》简共16支,简长约47厘米左右,其中有四支下部残去三至四字,其他简文皆完整。完简三十七至四十八字不等,书写工整,是典型的楚国文字。《楚居》所记楚人之起源与世系可信度较高。但简文亦有多处与《楚居》内容相异,可结合其它典籍记载加以勘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系年》简共138支,竹简长度约在45厘米左右,竹简背面原有序列编号,但据释读专家鉴定有一处系误记,故进行厘正,并重新加以排序,尾简未进行编序。原无篇题,因篇中纪年较多,文字体例的诸多内容又与西晋汲冢周书《竹书纪年》颇为相似,故拟题为《系年》。竹简保存较好,仅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有二十三个段落。与《竹书纪年》不同,《系年》的记事自周初始,第一至四章载录西周史事,对周王室如何衰落,以及晋、郑、楚等诸侯国如何代兴加以说明。第五章以后则具体叙述春秋至战国前期的相关史事,叙事详尽。《系年》简诸多内容可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可与《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典籍互校。特别是西周部分内容多处可与青铜铭文相印证,战国部分内容则多为传世典籍所阙,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傅说之命》简共23支,简长45厘米左右,竹简分为上中下三篇,简文笔迹一致,系同一写手撰写,每支简背有次序编号,每篇篇末皆书有“傅说之命”,故以此命名。清华简《傅说之命》主要记述了商王武丁发现傅说的过程,对傅说失仲的战争情况也有说明,其中武丁对傅说的训诫内容约占简文一半篇幅。此篇竹简的发现将为《尚书·说命》中的某些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史料与研究视角,对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发展也意义重大。[4]《周公之琴舞》简共17支,除第15支简略有残损之外,其余均保存完整,其主要内容为成王嗣位承袭大统的盛大典礼,其中包含周公儆毖众士、成王自我儆毖以及祈求上天庇佑这两部分内容,共计十篇诗作。这十篇诗作除了周成王所作的第一首可见于传世文献之外,其余九篇均为逸诗。《周公之琴舞》简文的发现及其完整性,为我们研究《诗》《周颂》以及探究周代的礼乐文明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5]《芮良夫毖》简共28支,竹简长约45厘米,其中后半部分有残断,满简书写三十字左右,简文语意连贯,文辞古韵,主要内容是周厉王时的大臣芮良夫针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所作的训诫之诗。简文首先叙述周厉王时的形势,然后再载录芮良夫所作毖的内容,其中涉及君王治政应敬畏天道、体恤百姓、德主刑辅、任人唯贤以及君臣莫贪利享乐等方面。芮良夫谏言厉王、训诫百官之事于典籍当中多有记载,可与清华简《芮良夫毖》对照参阅。[6]《良臣》简共11支,内容完整,原无标题,今之题目系研究者根据简文内容后加。简文叙述黄帝至春秋时的股肱之臣,属于一篇载录多位贤臣能人的晋系古文献。《良臣》中所列举上古贤君与《墨子·尚贤》篇中列举的贤才能人虽存在部分重叠,但两篇文献在叙述语句及语言风格上相差悬殊。简文叙述时代最晚的当属春秋末期的鲁哀公,简文成文也必定不会早于这个时间。据释读专家研究,《良臣》中的黄帝更接近人帝,并且与尧、舜、禹、文王、武王这样的人君并列,说明作者未将其神话,由此可知,《良臣》的成文时间应该在战国中期。[7]《祝辞》简共5支,每支简撰写祝辞一则,因为第一、二两则均标有“祝曰”,故整理者取名为“祝辞”。[8]就内容可知,这五则祝辞全为原始巫咒之辞。五则中每段均包括祝辞以及与念诵祝辞相配合的仪式或行为规程,第一段是与“恐溺”相关;第二段是关于“救火”的;后三段都是与射箭有关,射箭祝辞因弓名相异而区分为三种,三弓之名、祝辞及相应姿势动作的记述,反映了当时弓的种类与使用情况,这不仅印证了《周礼》所载弓按功能、长度分类的可信,而且记述了当时用不同类型的弓射箭的姿势细节,填补了这方面文献记载的空白。《赤鹄之集汤之屋》简共计15支,三道编痕,简长约45厘米,其中第一支和第二支简末端略有缺残,各损失一字,其它各简保存较好。简背有序号,书于竹节处。篇题写于第十五支简的简背下端,整篇竹简背面偏上方还有一道斜的划痕。《赤鹄之集汤之屋》在第三辑当中备受瞩目,因为这篇简文符合小说特质,极具奇幻色彩,在战国简帛资料中甚是少见。[9]《筮法》简共63支,简长35厘米,每支简尾正面均有简序编号。《筮法》简保存良好,没有明显残损,入藏时全篇大致维持在原来成卷的状态,只有外层小部分竹简散存。需要注意的是,简上除有绳痕之外,背面还有用丝织物粘贴过的痕迹。简文原无篇题,因详细记述占筮的原理和方法,并包含大量以数字卦表现的占例,其中数字卦的形式与楚简中的实际占筮记录较为一致,故将简文篇题拟定为《筮法》。[10]《筮法》简以载录古人占筮的诸多事例为主要内容,并且还对八卦的方位问题以及某些数字所象征的意义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人的筮占体系,从而对先秦易学有进一步的认识。此外,这种三画卦的筮占方式正好与近年流行的数字卦相呼应,有利于研究者对数字卦有全面的解读和认识,也有利于易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别卦》简共7支,阙1支。简文内容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联系甚详,《别卦》的卦名和《归藏》亦关系颇深。《算表》简共21支,其中完整简17支,另外4支上端残缺。完整简长在43至44厘米之间,宽度与同批简相比宽1厘米左右。入藏时已散乱,今所见简序系整理者根据形制与内容编排整理而成,简面均有朱砂渍。原册以三道绳编联,但编绳已佚,仅存编痕。原无篇题,因简文内容与运算息息相关,故整理者将其定名为《算表》。[11]《算表》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算具,其内容实际上是数字构成的表格。据释读小组专家研究,《算表》大致形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比此前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表更早。《封许之命》简共9支,简长约44厘米,宽约0.65厘米,简背标有序号,现第一、四支简已阙,第三、七、八、九四支简上端存在不同程度残损,第九支简背面写有篇题《封许之命》。《封许之命》是周成王封吕丁于许的命书,属于“命”一类的题材。“命”一般被认为是《尚书》“六体”中的一体,故从体裁角度看,《封许之命》应该属于《尚书》逸篇。《封许之命》的面世,对于研究先秦时期《尚书》的基本面貌以及西周时代的政治格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2]《厚父》简共13支,简长约44厘米,简宽约0.6厘米,第一支上下两端残缺,其余完整,简背存有顺序编码,第十三支简背面有“厚父”二字,故以此为篇题。[12]该篇简文内容系君王与厚父的对答,谈论的内容则是夏王的明德事迹和对夏朝民众的治理策略。清华简《厚父》篇经释读小组专家研究,认为简文内容与《尚书》类典籍相似,后经进一步考定,认定其极有可能就是《尚书》中的《商书》,是商汤在灭夏之后以史为鉴,拜谒夏朝贵族厚父的史学作品,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命训》简共14支,竹简长度约在49厘米左右,三道编。竹简各支均存在不同程度残损,其中有八支简的简文受到一定损毁。除最后一支简外,每支简的简背均有次序编码。竹简本无篇题,经释读发现,简文内容与《逸周书》的《命训》篇大致相合,因此释读者以“命训”为篇题。[13]《命训》篇是继《程寤》《皇门》《祭公》诸篇之后,在清华简中所发现的又一篇《逸周书》文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汤处于汤丘》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收录整理的一篇早已佚失的先秦文献。本篇文献主要记载了商汤和伊尹间的史事,极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五十一篇中的佚篇。文中所强调的“敬天”“尊君”“利民”思想与黄老刑名思想相近,对研究黄老刑名之学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14]《汤在啻门》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的篇目,简文内容主要体现了对鬼神的敬重,这篇文献的风格与《殷高宗问于三寿》极为接近,均以对答的形式记载,故被归类为“帝师”类文献,全篇用韵文写成,文章结构较为简洁,但内容却甚是晦涩,不易理解。[15]《殷高宗问于三寿》篇简文文辞浅显,属于战国时代流传的商代传说,与战国时代兴起的儒学政治化关系密切。简文内容则主要是通过殷高宗武丁与三位年龄迥异的老者的对答,阐述了战国时期人对自然、社会以及自我修养的多层理解。简文虽援引殷代史事,却以战国的现实形势为立足点,在说理的同时,字里行间也表露出对家国存亡盛衰的忧虑。[16]《郑武夫人规孺子》简共18支,有多处文义不相联属,疑有阙,但首、尾简俱存,全篇结构大致完整。《郑武夫人规孺子》位于清华简第六辑篇首,对于郑国史事以及春秋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此篇所载内容为研究者探究周代诸侯国统治者的决策程序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范例,使后学者得以了解决策过程的诸多特点,也会对上古时代国家政治中的贵族民主制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简文内容对春秋初期政治演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17]《郑文公问太伯》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郑史三篇之一,涉及到郑桓公、武公、庄公三世的史事。简文载录了太伯对郑文公的训诫之言,其中太伯历数了郑国自桓公、武公、庄公以来东迁启疆,昭公、厉公斗阋斩伐的史事,最后劝诫文公当追慕先君、克己节欲、任用贤良。简文可与《左传》、《国语》等诸多典籍记载相印证,也可补充相关传世文献史事记载之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8]《子产》简26支,简长约45厘米,简宽约0.6厘米,保存相对完好,但有多支简存在一端折残的情况。原简无篇名,因其系讲述子产个人修养以及治政功绩之论说,释读者故以《子产》拟为篇题。《子产》属于论说文形式,主要是论述子产执政史实和相关施政举措,《子产》篇可与《左传》有关篇章相参校,以加深对子产铸“刑书”的背景以及内涵等相关问题的认识。[19]《管仲》简共30支,简长约44厘米,简宽0.6厘米,三道编。全篇原无篇题,每支简的简背亦无次序编号。竹简保存大致完好,但是第28支简下半部残损,第29支的上半部亦阙,这两支简之间是否还有缺失的其他竹简,尚不易断定。第29支简与第30支简之间内容不相衔接,应该是缺失了一支简。因此,整篇简文总共缺失了一至二支简,另外还有两支简有所残损。简文对于深入理解《管子》一书的思想意蕴以及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20]《子仪》简共20支,简长在41至42厘米之间,简宽约0.6厘米,简背无编号,无篇题。每简保存基本完整,经编联,内容大致相贯,其中四支竹简之间内容跳跃较大,疑有缺简。本篇简文讲述秦晋之战后,秦穆公为与楚国交好,主动送归子仪之史事。简文对送归过程,特别是秦穆公与子仪的对话有详细描述,是了解之战前后秦、晋、楚三国关系和春秋外交辞令的重要史料。《子犯子馀》和《晋文公入于晋》皆以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为主角,记载了重耳早年流亡国外,后借助秦国势力返国,以及重耳归国后整顿内政,一战而霸的史事。《越公其事》简共75支,详细记载了勾践灭吴的过程。简文不仅载录了大量的对答话语,而且把勾践卧薪尝胆,一举灭吴的过程概述为“五政”并依次叙述,属于“语类文献”。本篇竹简基本完整,结尾有篇题,内容与《国语》之《吴语》和《越语》密切相关,残缺处之内容均可依据《国语》相关内容补出。《越公其事》前三章详细记载了勾践退保会稽后,吴越两国媾和的具体过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21]
四、清华简的学术价值
对于清华简的价值,李学勤教授曾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综合评述清华简的学术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清华简的发现对于先秦史乃至整个古代文明的研究都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前七辑当中所载文献共三十四篇,其中可见于今本的主要集中在《尚书》和《逸周书》等传世文献当中,如《金滕》《皇门》《祭公》等。研究者可将清华简简文与传世文献相对照,这对于厘正今本中的错误以及古籍原貌的恢复重现都具有重要意义。清华简也可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春秋战国史史料之不足,其中书类、诗类文献对于西周史的重写意义重大。
其二:清华简提供了多篇前所未见的佚书,提示了大量前所未知的历史真相。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为例,其中《尹至》等九篇,大多是传世文献《尚书》以及《逸周书》所亡佚的篇目,使《尚书》等先秦原典得以重现,这为商周史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澄清了诸多学术史上的疑难问题。从古典文献研究角度来看,清华简的发现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先秦文献的形成以及流变历史意义重大。已公布的七辑材料,为我们先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我们可以此为据,重新审视传世文本,以探讨文献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字与内容的变异。
其三:清华简的发现推动了楚文字研究的发展,对整个古文字学的发展也有所助益。清华简多达两千余枚,皆为古文字,我们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对照,进而识别出过去未能识别的楚国文字;清华简中也出现了多处古文字的新字形以及新用法,一些词语亦可与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传世文本相互佐证,这对于汉字发展史以及古文字学的研究发展都弥足珍贵。
其四:清华简的出现深化了我们对楚文化的认识,加深了我们对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22]清华简《楚居》篇载录了楚国起源的传说与历代君王的迁都情况,这对我们深入了解楚国文化意义重大。清华简简文涉及的诸多古籍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凝聚着古籍整理者的心血。清华简使得经典得以重现,我们可以此为据审视以往古籍整理工作的得失,也为将来古籍整理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五、总体感受和评说
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3]清华简目前已出七辑,共包含经、史类文献三十四篇,关于清华简的学术文章更是擢发难数。关于清华简的学术价值问题,目前在学界更是基本达成共识,早已不遑具言。笔者不揣谫陋,现就“研究”层面发表几点浅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其一:对竹简的形制、书写等关注不够,以补史、证史研究居多。现在学者的治学路径多以地下出土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关于论证“二重证据法”价值的学术文章亦不可胜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关于清华简的文章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补史、证史之作。因而,在清华简的研究释读方面,我们需要走出“补正”文献的老路,把握简牍的独立价值,重新发现甚至是复原其中原有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之上,再去添补以往历史的空白,而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传世文献的某处记载。我们要立足竹简本身内容,自下而上观察,发现消失已久的历史侧面,最终还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真实历史。
其二:竹简的出土地点决定了竹简的性质。清华简2008年问世伊始,学界对其研究价值毁誉参半。部分学者对其出土时间以及出土地点提出质疑,认为清华简系后世伪作,研究价值不大。在清华简的研究释读过程之中,又有学者陆续发布了多篇文章,如姜广辉先生先后发表的《〈保训〉疑伪新证五则》《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与《“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等文章就是针对清华简的真伪问题阙疑。文章中旁征博引,推理缜密,颇见功底。竹简的出土地点不同,其性质也大不相同。如果出土地点为遗址,如边塞烽燧遗址、遗址中的古井、宫署遗址,则多属于无意间保留下来的;如果出土地点为墓葬,如两湖、山东、江苏、河北地区,则多是有意保存下来的。目前,仅以碳14测定作为清华简的防伪措施,并非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保障。研究者还需在清华简的出土时间与出土地点上多下气力,从而为清华简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保障。
虽然对清华简的质疑之音时有发声,但清华简对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则是毋庸置疑的。后学者在运用清华简相关简文之时要作好史料甄别、考定记事、校勘文字等工作,若因为客观条件或者主观原因,有无法解决的问题,须存疑待证,切忌主观臆断,更不要牵强附会。
[1]李学勤.清华简与古代文献[R].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2013:108.
[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北京:中西书局,2010:127-149.
[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北京:中西书局,2011:135.
[4]金鑫:清华简《傅说之命》考释及初步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文,2016:2.
[5]王薇.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2.
[6]朱德威.《芮良夫毖》集释[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1.
[7]杨蒙生.清华简(叁)《良臣》篇管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59.
[8]江林昌.清华简《祝辞》与先秦巫术咒语诗[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54.
[9]刘国忠.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伊尹间夏 [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64.
[10]高险峰,杨效雷.清华简《筮法》研究述要[J].中原文物,2016(2):65.
[12]黄凌倩.清华简《厚父》《封许之命》集释[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1.
[13]刘国忠.清华简《命训》初探[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37.
[14]魏栋.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校读记[J].管子学刊,2016(1):104.
[15]曹峰.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3.
[16]刘成群.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揆中”思想与战国时代的政治化儒学[J].史学月刊,2017(7):24.
[17]李守奎.《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丧礼用语与相关的礼制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6(1):11.
[18]马楠.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J].文物,2016(3):84.
[19]王捷.清华简《子产》篇与“刑书”新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7):53.
[20]刘国忠.清华简《管仲》初探[J].文物,2016(3):88.
[21]李守奎.《越公其事》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J].文物,2016(6):75.
[22]刘国忠.走进清华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56-157.
[23]刘梦溪.陈寅恪的学说[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