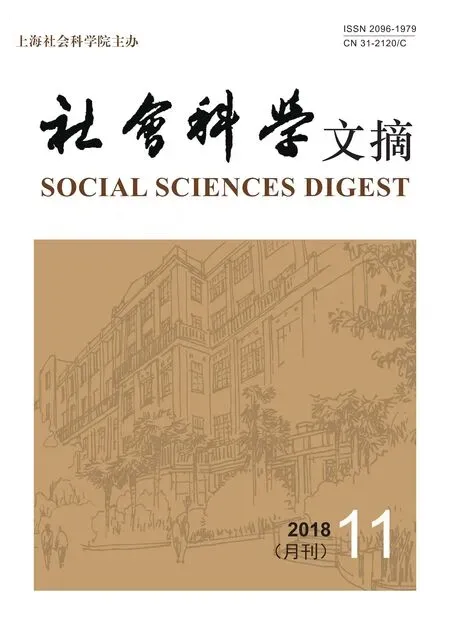从分化到整合: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
2018-11-17
我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一路走来,也实属不易。其间,有一些失误和曲折,也有一些矛盾和风险,还有一些外部世界的挑战和压力。而所有这些,并没有改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相反,“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因此,要继续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顺利展开,对40年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就是一项十分必要的任务了。在这里,笔者仅打算从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动力转换的角度作一简要解读。
打破整齐划一:改革开放的原初动力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国家性格”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建构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把人民组织起来的体系”。这一组织体系,不仅包括了本身就已经有良好组织基础的工人阶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把整个国家组织起来自然有组织起来的好处。例如,团结就是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事实上,这种组织起来的优势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的确也有相当出色的发挥。例如,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民动员,激发广大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我国就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热情会慢慢地消减。因为这样一种把全民组织起来的体制,带来了一个结果是相对的整齐划一,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既然改革开放前的整齐划一(尤其是分配体制上的整齐划一)无法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并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到了近于崩溃的边缘,因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不进行改革就没有出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而要进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首要的就是要打破整齐划一的体制,以分化“板结”了的社会,而这种分化反过来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原初动力。
在农村,打破整齐划一的体制束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在于实行集体化的生产,农民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则解除了生产关系的束缚,肯定了农民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自主性,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总之,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推动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业集体逐渐式微了。
在城市,打破整齐划一的体制束缚是从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开始的。当然,城市改革不能像农村那样把企事业单位一分了之,直接可行的改革路径就是改革分配体制,打破平均主义,通过收入上的分化来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总体上看,城市改革从分配体制改革入手,打破了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壁垒,虽然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诸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乱象,使人们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但是改革开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开启了的城市改革为1992年十四大决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作了物质和精神上的铺垫。
“到体制外去”:改革开放的动力增能
社会分化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但是,自1978年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的10多年间的社会分化只能说是简单的、停在表层的、未触动计划体制的社会分化,它所产生的动能远远不能适应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行进中,现实的生产关系已经和发展变化了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通过调整现实的生产关系,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以推动社会分化向纵深发展,才能为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输送能量。因为只有分化了,才会有竞争;有竞争了,才会带来繁荣。
于是,“到体制外去”就成为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的社会反应。“到体制外去”俨然成为了一个政治口号,呼唤着包括农民、工人、干部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到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去。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则可以看作是对“到体制外去”的民众呼声的政治回应。无疑,“到体制外去”为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进而推动社会变迁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对于90年代初的中国来说,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如何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答案是“到体制外去”。本来,对于农民来说,无所谓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问题,但是,由于农民的本质特征是从事农业生产、束缚在土地之上的,因此,那些离开家乡和土地、到城市或厂矿企业打工的情况,就是离开农业体制,即本文所说的“到体制外”。“农民工”就是到了农业体制之外的农民。“无工不富”对于农民来说是自不待言的,因而“进城务工”自然成为了农民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选择。而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在加快对公有制经济改革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由此迎来了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城市改革与私营经济的发展自然为农民到体制外就业提供了平台、机会和空间。农民“到体制外”就业意味着农村社会分化的加速。
在城市,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都有一个“撑不死,也饿不着”的铁饭碗,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多少的竞争关系,人们虽有怨言,但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制度安排中还算相安无事。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计划体制下进行的分配体制改革,打破了人们收入上的整齐划一,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但总体水平有了提高的收入很快又被80年代末的通胀所击破。冲破计划体制,加速社会分化,才能使城市真正步入改革的轨道之上。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随后召开的十四大,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改革的开启——城市开始打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城市中人开始有了放弃铁饭碗而“到体制外去”的勇气和决心。在市场经济改革伊始,应当说,体制内的铁饭碗不再有昔日的风光,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因而“下海”经商、到非公单位就业在一时之间成为不少城里人的主动选择。据报道,现在的很多知名企业家,就是在当时的市场经济大潮下“下海”。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是倾向于体制外的民企、外企等。因为国企竞争力不大,自然对大学毕业生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而自1993年以来处于“国退民进”红利期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总值,而且有较国企高出许多的收入,因而成为“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在90年代末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国企大量出现亏损、倒闭的情况,中央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并对国企实施“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把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从而出现了不同于1993年的“国退民进”的新型的“国退民进”格局。在这次“国退民进”的过程中,不少国企职工下岗分流,他们可谓是被迫“到体制外去”的那部分人。
无论“到体制外去”是主动选择还是出于被迫,它都可称得上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推手。正是这些“到体制外”的农民、工人、大学生以及部分干部,以他们的流动性(空间流动、职业流动、社会地位流动等)的增加,深刻改变了中国,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
“到体制内去”:社会分化正向功能的衰减
从“到体制外去”到“到体制内去”的转变,大致可以2003年3月十届人大设立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为起点。因为在国资委成立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免于淘汰,这就导致央企必须不断进行扩张、收购、兼并,从而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进民退”态势。正是在“国进民退”态势的刺激下,社会上开始出现重返“体制内”的大潮。
从“到体制外去”到“到体制内去”的转变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国进民退”的政策导引下,尽管国家层面仍然有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性意见,但非公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已居明显的弱势地位。而“体制内”单位拥有社保、医保等诸多优势,让那些经受了改革风雨、感受了体制力量强大的人们对“体制内”单位趋之若鹜。总之,经历了十多年风光的“到体制外去”,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失去了吸引力。
虽然不能说是国家与资本的合谋而导致了身处“体制外”人们的权益保障的缺失,但是,身处“体制外”人们的保障缺失的事实,必然会造成人们的无助与无奈、孤立与冷漠的社会情绪。在改革开放的行进中,我国不仅具有了风险社会所具有的一般风险,而且还有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严重、国家机关信用下降等独特的重大风险。在此期间,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出现的社会风险的政治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便成了规避风险的港湾。
如果说“到体制外去”所带来的社会分化,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松绑)条件下竞争的表现和结果,是竞争释放出了社会变迁的动力,是“竞争型社会分化”,它对于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具有正向的推动功能,那么,“到体制内去”显然是强化了体制的分量,强化了体制对竞争的介入、干预和影响,进而弱化了竞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说没有社会分化,但这种社会分化是社会阶层固化条件下的分化。一方面是社会分化,另一方面又是阶层固化,两者看似矛盾,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它是体制制造的潜规则盛行之下的“非竞争型社会分化”。它对于社会转型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减弱,有时候甚至会产生负面效果。社会分化的两极化、阶层固化态势凸显,社会的流动性大大降低;社会心态恶化态势明显,社会诚信濒于沦丧的边缘。这种状况不改变,社会就有可能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断裂”。这也就是说,社会分化已难以承担起社会变迁的动力角色了。这也表明: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社会变迁的动力需要转换了。
“组织再造”:社会变迁动力的转换
在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的关键时刻,由于社会分化已难以承担起社会变迁的动力角色,因而亟需实现社会变迁的动力转换。而开始这种动力转换的时间节点大致可以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
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当然,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进行社会整合。因为只有通过社会整合来调节社会分化产生的问题,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而此时的社会整合,自然可以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动力。那么,十八大以来,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社会整合手段是什么呢?答案是:组织再造。
所谓“组织再造”,是指针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成员的“去组织化”现象,而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再组织化改造。
在这里,需要对我国社会成员的“去组织化”现象加以说明。在农村,不少的村民失去了组织的依托,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再加上农村原有的宗族制度受到市场经济、城市化等多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冲击,不再对村民形成有效的约束力,更是加剧了农民的去组织化。在城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先那种较为普遍的单位办社会的现象到21世纪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单位已很难像改革前那样对员工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造成员工的组织化程度弱化;还有一些单位在改革中,或破产或重组,从而顺水推舟般地实现了对员工的管理与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单位人由此而变为了社会人,进而呈现出一种“去组织化”的状态。而在不少的非公经济组织中,它们只是使用工人的劳动力,并不对工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同时,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不少没有设置党的基层组织,即使有也是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
当然,在当今的社会成员中间,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的市民化在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性难题,他们有成为市民的意愿,想在城市落户扎根,而城市却又设置各种门槛要把他们挡在门外。农民工属于城市,但城市不属于农民工。农民工脱离了村庄的组织,但城市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足以使他们稳定下来的组织归属。因此,“无组织”可谓是农民工的典型特征。
应当说,社会成员的“去组织化”现象,曾经是我国社会变迁的动力。但是,如果“去组织化”过度发展,却有可能产生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有鉴于“去组织化”的危害,就必须对社会成员进行再组织化,即“组织再造”。通过“组织再造”,以组织的力量来化解社会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的风险,提升社会流动性(尤其是纵向流动),纾解社会心态恶化,构筑社会诚信。在很大程度上,组织再造的过程就是社会整合的过程。
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上议事日程,而所有这些措施中间,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组织化建设。组织再造的核心目标,就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就在于对那种不良的社会分化进行纠正、纠偏,使社会分化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它不是使社会停滞,而是使社会分化趋于优化。因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再造保证了社会变迁的方向、提供了社会变迁的接续性的动力。
结语
综观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社会变迁,其动力系统大致经历了“打破整齐划一→到体制外去→到体制内去→组织再造”的转换。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换,主要就在于党情、国情、世情等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民众利益和要求发生了变化。当然,在我国社会变迁动力的转换过程中,既有官方主动回应,又有民众实践的推动,更是两者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从总体上看,在我国社会变迁的动力系统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分化,进而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尽管“到体制内去”反映的是阶层的固化、利益的固化等不良的社会分化,但是,在经过这样的社会分化的阵痛之后,在新时代条件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共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对策,即组织再造,并通过组织再造,力图实现社会整合,从而使社会分化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