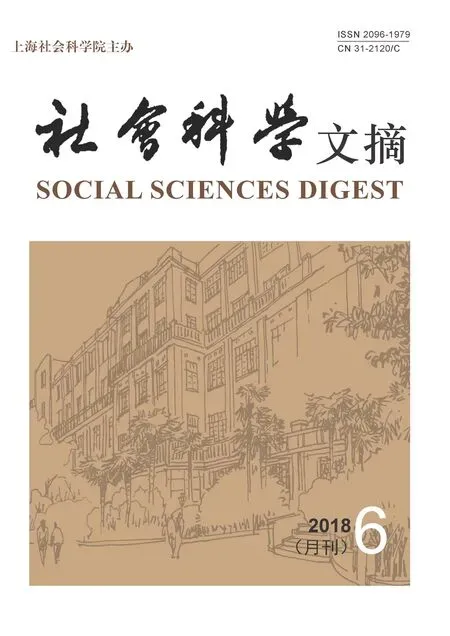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再探讨
2018-11-17胡逢祥
文/胡逢祥
陈寅恪堪称中国现代最具个性的史家,有关他的研究,自1980年代末兴起以来持久不息。但仍有一些问题,如陈氏一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学术为本位,但其学又深含“淑世”精神,如何看待其间的关系?陈氏治学特征究系以“乾嘉朴学”还是“宋人长编考异法”为主,其学术的总体路向为何?如何认识陈氏政治观的立足基点及其与学术之关系?均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陈寅恪的淑世情怀与文史研究
近年来,论及陈寅恪的治学,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其一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及其“为学术而学术”的典范意义。但事实上,陈氏的学术还明显有着继承传统“经世”精神和留心时政的一面,这同样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陈氏出生晚清官宦家庭,受祖父辈忧心时局和忠勤国事的家风熏陶,自小便十分关怀时政。即使长期留学海外期间也是如此。据《吴宓日记》,一战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留学期间,与之日常交谈的主题,除学问外,亦多涉现实社会风气和国家发展前景等。李璜回忆1920年代在欧时,陈氏与朋友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亦每好谈论政治、民生和教育等问题。回国后,他虽专事文史教研而不参与实际政治,却依然十分关心政局变化,认为学术研究固有其独立性,但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他本人的文史研究,尤透发出一种鲜明的淑世精神——希望为改良社会风气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正面作用。从学术实践看,他的这种社会抱负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是出于对近代以来国势衰微而致学术不振的忧思,欲奋身与东西方汉学一较高低,为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独立和发展培植元气。这一点,从其发出“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等呼声中,可清楚地感受到。
二是其文史研究的选题,多贯穿着深切的社会关怀意识。其亲友俞大维即说:“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至于具体论著中以古通今,致力揭示可供现实资鉴的历史教训,更时而可见。如主张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而唐史也颇具这样的特点,可从中获得启发。在论及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关系时,他还指出思想史上儒佛融合的经验,足为今日应对中西文化交汇之资鉴。
当然,理解陈氏上述“淑世”精神的同时,还须看到其不遗余力倡导“学术独立”的一面。他一再提倡:“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样的立场,与前述学术“淑世”意识是否存在冲突?则正是我们应加关注的。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与“直笔求真”是支撑其持久发展的双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会出现偏颇:过执意“经世”者,有时或不免因此丧失学术本位立场,甚至成为某种政治的附庸;专以学术自娱者,则易遁入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这一点,在现代学术史上并不少见。陈寅恪的学术实践表明,他对此始终保持了一份理性。即一方面要求坚守现代民主的理念,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或私欲与各种外在压力的制约,以“独立自由”之人格,行实事求是之研究,以为非如此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古来志士仁人以天下为任的“淑世”精神,“笃信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之旨”,自觉将忧心国事、关切社会的人文精神注入学术事业中,致力从史中寻求史识与教训,以贡献于时代。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应无例外地都从原始史料出发,“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可见其主旨明显倾向于保持两者的兼顾和协调运作。
陈寅恪的上述观念和实践是否得当,自然可作进一步讨论,但至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史学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实事求是,背离了这点,必然走向虚幻和误导社会,哪里还谈得上发挥应有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史家的经世意识若非夹入觅取功名利禄等私心,在不少场合实可增强治史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内化为史学发展的一种动力。如司马迁、司马光和顾炎武等,都是典型的经世学者,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史学也一直被公认为是古代最具求真精神和最为严谨的。故并无足够的理由表明讲求“致用”就一定会违背“求真”的戒律。只要把握得当,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应当可以和现代史学的“科学性”接榫相容,并在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
当然,肯定这一点,并非意味着每位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或史著撰写都须注重“经世”功能。作为个人,只要遵守学术规范,其研究无论是追求“纯学术”,还是志在“经世”,都应受到尊重,因为这对史学的整体发展,都是一种推动。只是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术,从整体上要求,发挥其健全的学术和社会综合功能,依然是人们所期望的。
从追摹“欧洲东方学”到倡导“新宋学”
关于陈寅恪的治学路向与特征,目前学术界颇有争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汪荣祖和许冠三两家说。对陈氏的治学风格,前者比较强调其继承乾嘉朴学的一面,指出“他虽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但已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后者却不以为然,以为此“‘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之说,尤为无根”,其所继承发展的当系“宋人的长编考异法”,陈门弟子王永兴也对此表示了呼应。笔者以为,要认清这一问题,不妨先对陈寅恪的学术渊源略作梳理。
首先是家学渊源,其中影响深远的至少有三端:一是乾嘉朴学。这应是清中叶以后一般官宦子弟接受正统经史教育的常态。二是宋学,亦即“理学”。陈氏13岁之前一直就读于家塾,此家塾为其祖陈宝箴创办。因陈宝箴主“讲宋学”,这种观念必然会注入所办的家塾教育中,成为形塑陈寅恪学术人格的重要因素。三是诗学。其父陈三立为晚清著名“同光体”诗人,诗宗宋代江西派黄庭坚等,遣词造句,主“避俗避熟”,颇喜用典。陈寅恪一生爱好作诗,且于风格上也有所承继,于此实关系匪浅。
其次是留学训练。陈寅恪自13岁起,赴东西各国留学长达16年之久。1914年之前大致以学习日、德、法、英诸国通行语言为主,并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修习政治经济方面课程一年。1918年底起以历史学及东方古文字为主攻方向,除受到欧洲东方学的深刻影响外,于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有相当接触。
可见,“乾嘉朴学”或“宋人长编考异法”固然是陈寅恪学术的重要渊源,但都难以概括其总体治学特征。而从动态的角度加以观察,将其学术路向概括为从追摹“欧洲东方学”到力倡“新宋学”,或许更能接近事实的真相。
1923年他在《学衡》发表的《与妹书》,较早公开表达了其欲从藏、蒙、满、回等文献比勘入手,研治唐史和西夏史的学术志愿。这一治学方针的确定,当与一战回国居住期间受到与其父陈三立交往甚密的学者沈曾植等影响有关。其后来发表的《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对此有清晰的表露:“曩以家世因缘,获观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可见,此举同时也含有鲜明的经世意识。
东方学是19世纪兴起于欧洲的一门研治亚非地区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综合性学问,与中国有关的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蒙古学等都被囊括在内。其研究不但注重各类原始文献的广泛搜集整理,且与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从追摹“欧洲东方学”的治学范式出发,陈寅恪在清华任教伊始,就作了“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的讲演,负责指导进行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比较、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比较、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等研究。并在最初几年通过汉藏佛典文献的比勘考证,接连发表了20余篇涉及佛教史、敦煌学和蒙古史的研究论文,其中明显透出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风格,往往以较小的题目,比勘多种语言资料,作精深绵密之考证。从方法论看,大体不出1923年提出的“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的路径。
然自1930年代初起,其治学风格渐起变化。首先,研究主题逐渐由原先集中于佛教文献比勘考史,转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其次,论文的写作,也不再满足于史料发掘和由此直接带来的“发覆”,而是从“求史识”的目标出发,明显增大了诠释和阐发新见解的比重。此种转向,既是依据实际条件对原先计划作出的调整,即所谓“年来自审所知,实限於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於其间”,更与其学术理念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尤体现在其后来提倡的“新宋学”主张中。
陈氏所说的“宋学”,非指一般所谓“汉宋之争”的宋学(理学),乃“广义之宋学(包括文学、史学、理学、经学、思想等等)与今日之关系”。而“新宋学”亦非旧宋学的简单恢复,应是包含了新时代内容和境界的文化学术,正如融合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宋代新儒学已非复两汉儒学旧貌一样。
“新宋学”的提出,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思考,至少表达了他对当时主流学术视考据为极则感到不惬。在他看来,宋学的讲求学识兼具考证与综合分析并举,显然要胜于偏重考据的清学。而从社会大文化的角度看,倡导“新宋学”同时也寄托着其对中华文化再次复兴的热切期盼。在他心目中,宋代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发展高峰,与其前中土经历的民族融合和华夷文化交汇成功有极大的关联,新儒学的形成尤为其中的典范,其历史性贡献在于将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完全消融于本土文化体系。当今日中国再次站在中外文化大碰撞的路口之际,若能以唐人兼容并包的宽大胸襟和宋儒文化综合的智慧处之,建成融会中外的“新宋学”,则中华文化重新崛起于世界之日定将不远。
在此意义上,陈寅恪融会中西的治史理念与方法,亦可视为其努力构建现代“新宋学”的实践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厥为以下几端:(1)宽博的史料观与“诗史互证”;(2)历史主义的诠释意境——“了解之同情”;(3)社会科学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兼取。从中可见,陈寅恪倡导的“新宋学”及其史学,是一种中西合璧、传统和现代意识交融的学术形态。此种学术形态,与其反对简单套用印欧语文法,主张从本国语文特性出发建立自身的文法学一样,目的都在顺应时代潮流,推进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政治意识与学术
陈寅恪虽说过“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时政或学术研究中毫无政治寄托,事实上,目前陈寅恪研究中出现的争议,有些正是因此而起的。兹就其中与之关系最直接的所谓“遗少”情结与1949年去留大陆问题,略抒管见,并对其政治倾向和心曲,及与学术之关系试作研判。
陈氏的某些言行,确不免给人留下前清“遗少”的印象。但须看到,其观念与通常所谓的“遗民”明显不同。首先,从他1922年冬与游历德国柏林的李璜等每周聚谈中,“于畅饮淡红酒而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情况看,足证其政治上乐见现代民主国家之成功,而非如一般遗老之惓惓于前清王朝及其帝制。其次,在文化上,不少人因其始终十分强调尊重和继承传统,而将之定义为文化“遗老”。但现代史上与陈氏同持此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尚有章太炎、柳诒徵、蒙文通、钱穆,以及现代新儒家等,何以这些人均未被冠以“文化遗老”,而独独陈寅恪就非得与“遗老遗少”扯上关系?应当看到,陈氏所处为古今中西冲突交汇的社会大变局时代,他本人既深受官宦家族深厚的传统义理教育,又经国外长期留学而受到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训练,身上杂射出传统与现代观念的斑驳色彩并非不可理解。其诗文中流露的某些恋旧感情,实非眷恋于前清政权(因他本未仕清,即使按照传统伦理,亦毋须为亡清“守节”),更多的当出自对祖、父辈清季遭际和功业未遂的同情与孝思,当然根本上,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依恋。
至于1949年陈寅恪“去留大陆”的真实心迹,经学术界多年讨论和材料的逐步充实,基本史实已较清晰。有证据表明,在南下广州后,他一度萌生过移居香港或台湾之意。但从他致马季明、陈君葆函看,此乃“万不得已”之计,非至绝望则“决不轻动也”。所谓“万不得已”,当指陷于无法维系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困境而言。后因各方信息表明,形势并非如此悲观(其时自然不可能预知后来会有对他精神压力很大的各种运动和“文革”发生),而台湾方面的境况反甚显窘迫。这些,应是他决意留在大陆的现实原因。
不少人试图把陈寅恪的“去留”直接作为判别其在国共政权间进行政治选边的依据。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事实上,陈寅恪对国共政权都有所不满,即便离开大陆到台湾,也不见得表明他愿意追随国民党政权。应当看到,在决定人生行止的大关节上,陈氏心中实另有一种更深的系念,那就是对自己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挚爱。这种系念,不但承袭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理念,也标示出鲜明的现代政治意识。
“民族国家”是近代兴起的政治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族类观念虽早已存在,但并未与“国家”形成自觉的联系,“国家”一般被视为某个集团或家族建立的政权,故在旧时代,一朝之亡,即为一国之破亡,“忠君报国”亦被合为一种不可分割的德性看待。但近代“民族国家”则是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合而为一的产物。理论上,它代表了境内所有民族或政治集团、阶层的最高共同利益,也因此而得到所有成员的认同。在这种语境下,国家已不再是某一政权的对等词,换言之,政权可以兴衰或改易,而民族国家却是国人始终不可背叛的安身立命之地。正是这种系念,将之与国家命运拴在了一起,成为其政治意识的根本立足点。这不但足以注释抗战中他在香港身陷极度困厄而仍能坚拒敌伪威胁利诱的行为,事实上也是其1949年宁留故土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种政治意识,正是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特重民族文化的兴衰传承和中国古代民族冲突融合之迹的考察,并将之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独立自强的思索紧连在一起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