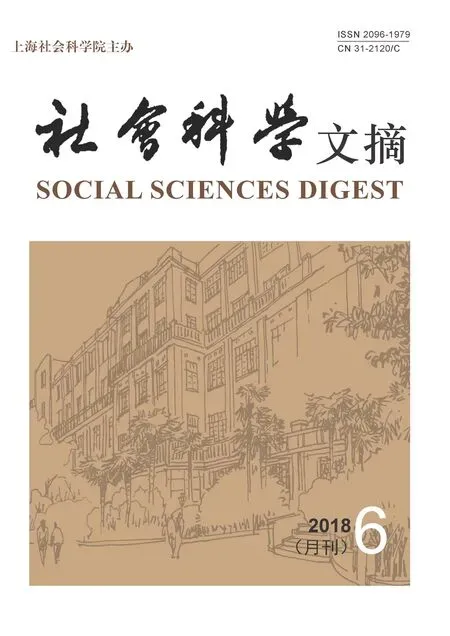古代治水、开河与通漕的历史逻辑
2018-11-17吴士勇
文/吴士勇
近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不断推进,运河与漕运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亦层出不穷。然而,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回答治水、开河与通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却极为稀见。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孕育于传说中的治水时代,当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确立后,开始开凿运河,以漕运的方式维护帝国中央的长治久安。倘若如此,应是先有治水及治水社会,然后才诞生中央集权体制;作为漕运载体的运河也必然开凿疏浚在前,而作为运河主要功能的漕运则运作于后。如果治水、开河与通漕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治水为因,开河为果;开河为因,通漕为果,而不是相反。这种未经详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论证的论调,其实经不起审慎地推敲。
治水与开河:从中央集权体制到水利社会
国内学者从研究治水到注意发掘水利社会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不无遗憾的是,水利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主要成果或主流话语仍限于少数水利史专家,水利史研究依然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将我国古代的治水及水利工程研究拓展到广袤无垠的“水利社会”学术视野,有很多学术问题需要解决。依笔者看来,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治水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如何看待政治权力在治水及水利工程的角色扮演,成为认识治水与政治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
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追溯到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1859年,马克思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争议。其中的“专制政府承担农业灌溉、修建公共水利工程的任务”一直被学界认为是理解欧洲以东的东方社会形态发展的关键理论。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在论证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持有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是在话语系统中依然保持着西方与东方之间权力符号表现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显现的矛盾历史地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体系的逻辑构造力量”。事实上,在我们的学术话语系统还没有完全构造成形之时,自觉或不自觉的引用西方学术话语是不可避免的事。具体到中央集权政府承担治水及水利工程任务之理论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将之视为我国古代社会理论的圭臬之一。
马克思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解释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德国学者魏特夫则将其进一步加以发展。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形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治水活动。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方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严明的纪律、从属关系、强有力的领导以及遍布全国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君主专制为主导的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与马克斯·韦伯的先有新教伦理后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断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这种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逻辑,正好与马克思的论述相反,也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事实上,先民们的治水举措只是水患面前的自发行为,只有当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形成后,才能对大型水利工程有效地规划、运作和管理,而不是相反。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规模地开凿运河是在中央集权政体确立以后才能付诸实施。在帝国体制下,官僚阶层的经济职能取决于中央集权政权的政治目的,而远非魏特夫所言的对人民大众的义务感。
大规模地开凿运河远非个体小农所能承担,因而需要集体的力量,也就是要把小农组织起来共同参与。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社会这是中央集权政府的职能。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以宗族为主要纽带的乡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政府关注较少的自治群体,这样,小范围的水利工程得以完成并持续。傅衣凌先生就曾指出:“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很大一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是在乡族社会中进行的,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干预。”但对整个帝国来说,开凿运河光靠分割的村落自然是难以完成的,由此在逻辑上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动员、管理和监控网络。就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论,帝国的产生与治水的需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能还有争论。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自华夏大地上出现农业国家以来,这个国家的维持就再也离不开对治水的密切关注了,进而也就离不开复杂而完备的官僚系统了。
运河与漕运的因果律
大运河的开凿是在挑战中国大河东西走向的自然规律,历代王朝为了维系大运河的正常运转,耗费了惊人的人力物力,这到底所为者何?简单回答,是为了漕运。这种简单而直线式的因果关系似乎是漕运与运河之间的唯一纽带。仔细思索一下就可发现,无论从逻辑推理还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二者的关系均远非如此。
许慎《说文解字》云:“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均认为漕运的本义为水运,尤指谷物水运。人类开始舟行水上,运输物资,便有了漕运。明代学者丘濬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自古漕运陆、河、海三种皆有。清人段玉裁作注时,认为“人之今乘”后脱一“车”字,“盖车亦得称漕”。近人张舜徽在《说文解字约注》将“漕”字按语中引《汉书·赵充国传》及注:“臣前部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颜注云:‘漕下,出水运木而下也。’”张氏认为,漕之为用,不专于转谷也。何乔远认为:“漕之道有三,曰陆、曰海、曰河。陆之运费,海之运险,惟河为宜。”
由是观之,漕运可陆、可河、可海,其运输对象亦不限于粮食一种,只不过所费人力、财力有多寡。河运视陆运要省力,视海运要安全,除元代外的历代王朝漕运均首选河运。总之,自然水道作为漕运载体,出现较早,且渐被广为接受,而运河显然是作为自然水道的补充而呈现于世的。如此看来,运河并非漕运的必要条件。
漕运的历史动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漕运的制度化始于秦。那么,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导致了漕运制度化?鲍邦彦、彭云鹤认为漕运制度化的前提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及小农经济形态下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分离的社会形态。不过,这样的概述缺乏对漕运制度演变的分析,对漕运的具体特征也没有具象的界定。李治亭认为,漕运由国家经营,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通过水上运输,把征收的税粮及上供物资,或输往京师,或实储,或运抵边疆重镇以足需要,并藉此维护对全国的统治。此论比起星斌夫之说“漕运就是把税粮为主的官有物资,通过水路由地方送往京师,有时则从京师运送到地方的一种制度”要详尽得多,将漕运的基本特征胪列殆尽。此外,吴琦认为,中国漕运是封建社会中央政权通过水道强制性运转官粮物资的一种形式,主要满足京城皇室、官兵及百姓的用粮需要。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它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土壤,以优良的水道运输系统为运输载体。以上学界诸说各富特色,但大都忽略了漕运的内在历史演进。倪玉平认为,传统社会早期的漕运泛指官方物资的水运,它的内容多样,诸如粮食、木材、金属等物质的运输,均可视为漕运。到了宋元以后,随着漕运制度的发展,漕运便专指漕粮运输。此为确论。
中央集权王朝对粮食的政治渴求,使得漕运成为帝国母体须臾不可废止的附属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强大的集权统治下分散而软弱,只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赋税。统治者往往扶植小农生产,巩固其赋税之源,从而维系王朝的长治久安。很明显,帝国中央集权体制与小农自然经济的结合,才是漕运制度出现并发展的最根本原因。至于运河开凿与疏浚之类的大型水利工程,亦完全是历代王朝利用已有的自然水道而实施的政治行为,运河只能是漕运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甚至不能算是漕运的充分条件。
质言之,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是多维的,运河与漕运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远非唯一直线式。运河既非漕运制度化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政治:连接治水、开河与通漕的纽带
既然如此,那么连接治水、开河与通漕的媒介又是什么?答案是政治。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政治诉求多通过运河的漕运功能彰显。表现如下:
第一,帝国中央集权统治是漕运制度化的母体,漕运是超经济的政治行为,因而自漕运制度化始,中央王朝就拒绝了以商品流通的方式调节市场粮食供应的可能性。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俊亚认为“即使政治权力起源于某些经济权力,但政治权力始终对经济权力起决定性作用”。政治权力能够决定社会财富的流向,并且这种流动还可以被纳入统治者预先设定的、可控制的通道中。既然如此,政府就失去了发展商品经济、以市场原则进行物资流动的动力。这种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帝国集权体制下,国家所需物资只能通过漕运,而不是通过商品的自由流通来解决的问题。
第二,政治与运河联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原因很多,关键在于历代政治中心与基本经济区不断转移。自秦以来,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始终在变化中:秦至北宋的政治中心变动轨迹大致沿着长安——洛阳——开封这一纬线作由西向东运动,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东西关系。南宋至清末的政治中心变动轨迹大致是由杭州——南京——北京这一经线作由南向北运动,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与之不同的是,古代基本经济区不断南徙,走上了与政治中心不同的发展轨迹。这样的背景下,运河自诞生之日起,其选线就与政治中心和基本经济区的连线大致重合。秦汉至南北朝的政治中心与基本经济区都在中原,运河大致是东西走向,中原之外的运道也大都是指向中原。北宋亡国,南宋僻居杭州,汴河繁荣不在,五百多年国命所系的大河,陷入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颓境中。元代建都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离开了东西横向的轴线,不过此际的基本经济区已远在江南,原有运河或淤或塞,不能满足漕运需求,这样,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应运而生。历史上运河经历由东西走向向南北走向的巨大转变,主要原因就是国都与基本经济区连线的变迁,国都变了,运河随之变;基本经济区南迁,运河随之南迁。谭其骧先生认为,唐宋以前的运河以中原为主,呈多枝形发展,将众多地区联系起来,对于平衡调剂各地经济文化有重大作用。元明清运河的南北向线形布局,将政治军事中心的北京与基本经济区的江南连接起来,在形成东部交通大动脉的同时,将广大的中部和西部摈之于主要交通线之外,这既不利于中西部地区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漕运:治水与运河的政治化
运河的政治化,表明运河的开凿、疏浚、运行、维护等实践行为均为集权政体政治运作的结果,并且首先服务于漕运这一政治主题。由于漕运的需要,治水及水利工程趋于附属地位,王朝大政向运河倾斜及运河的政治化几乎同时进行,或者说,三者就是孪生的兄弟,彼此的基因相差无几。治水及运河的政治化首先表现为历代王朝设职官对水利工程、运河及漕运进行有效的管理。
随着国家对漕运需求的不断增长,政治对运河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表现为:治水、运河与漕运职官逐步走向专职化、制度化,至明清已趋于完备与成熟;运河与漕运最高长官从地方行政系列逐渐升格为中央官员,至清代时已达臻顶峰。
古代运河的政治化还表现为:为了维护漕运的畅通,中央政府动用一切政治资源,不惜浪费人力、物力,牺牲局部利益,并由此形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利益集团。这一点在明清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家为了保漕,往往不计经济成本。如此的财政支出既让国家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又使得最后被转嫁负担的升斗小民日趋贫困下去。
为了漕河的整体畅通,统治者还不断牺牲苏北、皖北、鲁南等地的局部利益。1128年,宋人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挡金兵南下的铁骑,从此黄河夺淮,改变了淮河流域的水系。明后期及有清一代,罔顾淮河中游平原地带不宜修建水柜这一事实,不断加筑高家堰,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泊洪泽湖。繁华的泗州城及周边乡镇,终成烟波万顷的水乡泽国。又如微山湖,地势本低于运河河床,清代强行将之纳入为蓄水济运的大水柜,致使微山湖淹没的农田与村舍越来越多,乾隆年间,微山湖的面积竟达2055平方公里。对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而言,这条政治的运河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唐时还是富足天下的鱼米之乡,明清以后竟成了水旱频仍的穷乡僻壤。即便被称为点缀在运河沿线的明珠——运河城市,也是建筑在沙滩上的虚假大厦。它们依靠漕运政治的表面商业繁荣,并无城乡实体经济的强力支撑,其积聚的商业资本多为政治的附庸,一旦漕运大政改变,繁华的浮萍随风而逝,就只能永远地停留在后人的追忆中。
运河及漕运的职官制度至明清两代日益完善,这种制度下的官僚群体和乞食运河而生的人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利益群体。运河政治化的最大受益群体是漕运与河工大臣,他们获益方式多样,最主要的便是不断制造水灾,兴办治河工程,进而中饱私囊,成为引发社会矛盾之蠹虫。运河政治化的利益群体是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产物,其政治、经济利益的习惯性膨胀,损害了商业阶层、普通百姓甚至王朝的利益,成为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绊脚石。
今天大运河的北段早已淤塞,甚至变为良田,但中国政区地图上的运河依然以连贯的蓝色线条表明大运河贯通南北。这些足以说明,大运河已经超出了历史遗迹与现实航运的社会存在,她同长江、黄河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希望南北畅通、天下一家的心灵图腾。大运河的文化符号是历代王朝对其施加的政治影响的结果,民众从心理上弱化了这条违背自然规律的长河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强化了人们对祖先建造这一宏大工程的自豪感,以及基于祖先崇拜孕育而生的国家与民族的共同认同感。此种结果,恐怕也不是当初设计与开凿大运河的统治者所能料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