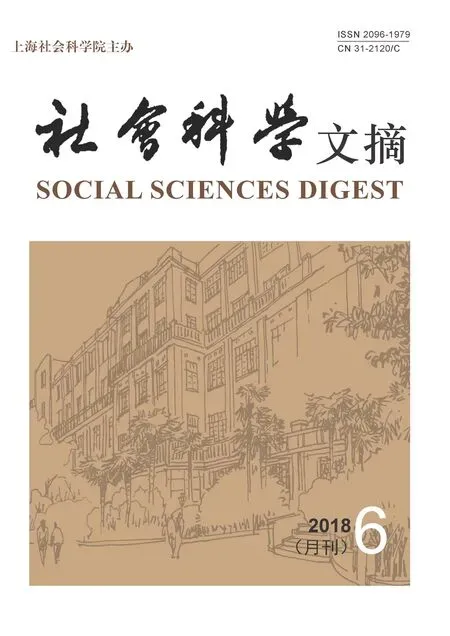中国的正义体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018-11-17黄宗智
文/黄宗智
笔者采用的是总体性的正义体系视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与“法”,正式和非正式正义体系,以及来自两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体系(“第三领域”)。本文所论述的和引用的实例跨越古今、中西,并兼顾实践和理论。前后一贯的是,由实践历史出发来突出其所展示的理论含义,特别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二元合一(互动、互补)的思维与逻辑。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
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以及新型中华法系
最近几年,笔者在对法学和法律的探索上更明确地使用“正义体系”的概念来认识其整体的框架——包括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正义,强调唯有从如此的整体视野,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正义体系只可能是一个同时来自三大主要传统的体系,即古代的“中华法系”(尤其是其非正式民间调解和正式法庭断案以及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近现代和改革时期从西方移植的法律,以及从中国革命传统所承继的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笔者从这个角度分别对不同正义领域,如调解、婚姻法、侵权赔偿法、产权法、继承与赡养法、取证法、刑事调解以及党国体制等所展示的三大传统进行了梳理和论证。
笔者聚焦于民事与刑事间的关联,说明即便是在今天,中国正义体系仍然倾向长期以来不截然划分两者的传统。同时,兼用非正式正义(民间调解)和正式正义,以及由两者的互动而在革命根据地所广泛形成的半正式正义,如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这里,笔者有意识地与新近的、影响极大的“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直接对话。WJP设定了八个主要要素来衡量全球主要国家的正义体系,并且比较重视其实际运作。但是,由于西方大多缺乏像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和在其中生成的调解体系,一直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国的非正式调解制度。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试图建立的“非正式纠纷解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制度,无论在主导思想和运作机制方面其实都和中国的调解制度十分不同,而在实际效用方面,更和中国相去很远。由于WJP倾向于把中国的非正式正义等同于西方自身的ADR,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调解体系。何况,其调查一直都限于每个国家的三大城市,完全无顾农村。虽然WJP如今已经认识到其在这些方面的欠缺,已经决定今后将把农村纳入其调查范围,并把“非正式正义”(informal justice)作为第九个估量要素,但尚未做到把其真正纳入对全球正义体系的评估数据中,亟须进一步改正。只有正确纳入农村的非正式正义指标,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所代表的中华法系,包括曾经大规模引进中华法系的其他东亚国家(日、韩等)的正义体系。
关于中国正义体系中“政”与“法”之间的关联。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完全纳入从西方引进的三权分立制度,其正义体系中的“政”与“法”一直紧密交织、缠结。此点可见于中国党国体制中,根据“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所占的领导国家的“超级政党”位置和西方的政党一般被视作处于国家和法律之下的体制十分不同。文章追溯此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党章和国家宪法文本中的体现。同时,“政”与“法”的交织更可见于广泛的“行政施法”实际之中,如公安部门所大规模执行的“公安调解”司法功能,以及其所设置和管理的感化教养等机构(包括未成年人管教),也可以见于基层法律事务所的调解和司法功能等。“行政施法”更可以见于党组织本身的“双规” 制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下设置作为劳动纠纷诉讼前置条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制度,以及国家直接通过《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起实施)而介入工伤事件的裁定等诸多实例。此外,还有由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发布的半正式、半法律的行政“条例”“规定”“补充规定”“通知”“意见”等。如此行政与法律交织的体制固然带有韦伯所批判的行政权力介入司法的问题,但在转型中的中国,应该可以说也不失为一种能够更灵活地在法律之外采取多渠道的行政和半法律措施来处理社会问题的体制。虽然,未来肯定需要进一步规范。
此外,笔者特别聚焦于2006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失败实例,其基本出发点是试图模仿高度企业化的美国农业,完全无视中国农村社区以及其仍然主要是小农经济(而不是企业化农业)的基本实际。它是一个意图凭立法手段来进行行政管理的实例。这是一个由错误的立法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实例,导致了大量的“伪”“空”和“虚”合作社的兴起,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权益和农村的重建都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如此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训,既是主导(模仿美国关乎农业的)立法思想上的错误,也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和过分依赖行政权力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高度形式主义化法律如今所显示的诸多弱点。举其要者,首先是律师和法庭费用高得离谱,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民所能肩负的程度——这是韦伯早已经观察到的问题。其导因归根到底乃是(韦伯所倡议的)法律体制的高度封闭化和专业化。再则是过度形式化而无顾实质的问题。譬如,如今大跨国公司广泛雇用众多专业律师和会计师来为其钻形式化法规中的漏洞和空隙,惯常并公开地从事实质上违法但形式上合法的行为。再则是过度法条主义化的问题。譬如,美国法律近年来广泛过度形式化地使用“三振出局”的条文,不合理地严重惩罚下层社会的轻罪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和贫穷群体。那样的现象与跨国公司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直接影响到法律体系整体的威信和效率。固然,中国的实质主义倾向也有众多的弱点,但可以适当采用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来遏制。这不是一个形式与实质非此即彼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在两者之中“取长补短”的问题。
相应当前的“民法典”编纂,欲探讨更为系统的突出融合中西的理论与实例,可以聚焦于三个主要领域:
一是结合实证性调节(包括民间、行政与法院调解)与形式化法院制度的具体方案,建议从具体情况出发,在无明确过错的争执中采用实质性调节,有明确对错的纠纷则采用形式化的法院裁判。
二是在道德理念层面上,倡议结合中国的“家庭主义”道德理念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法理,考虑到现今社会的实际需要与具体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实际情况下,适用或结合不同法理的方案。
最后是“政”与“法”交织的党国体制,以及如何长期结合的可能方案,倡议把党章确立为中国的非正式“实质宪法”,借此以进一步明确共产党自我设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历史使命。同时,以引进的形式主义宪法为国家机构的正式“形式宪法”。两者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制度的体系,取长补短。这其中的一个要点应该是,在革命胜利已经70年之后的今天,可以把党组织进一步透明化、民主化,更完全地脱离其列宁主义式的地下革命历史背景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再符合历史需要的制度和操作方式。如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需要设想、创建可以长期持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万世之法”的正义体系。
新型的中华法系
首先把法律和正义理解为活生生的使用和转变中的体系;从历史、现实及其前瞻的视角来设想中国应建立的正义体系,试图根据已经具有一定成功经验的具体实例来初步勾勒一个未来的图景;同时,也检视一些反面的实例,来进一步阐明正面实例的含义以及其对立法方向的启示。
作者的视野和如今分别占据法学两大主流的“移植主义”和“本土主义”都十分不同,也与简单的、描述性的“多元主义”不同。所突出的是一个融合和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路;说明长期以来实用道德主义在中国古今正义体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阐释其与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主流的不同,由此来勾勒一个“实质理性”的正义体系传统。而后,借助西方挑战主流的理论,如美国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传统,以及欧洲的“历史法学”“法社会学”“程序主义”法学等非主流法学传统,来对形式主义法律进行优劣的梳理,再由此探讨中国的实质主义法律传统应该如何与西方偏重形式主义的法律共存、拉锯和融合。
笔者不仅从立法的角度,也从学术研究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对比“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大法律思维方式,并建议同时借用两者,由其相互作用、融合以及创新来超越单一方的局限和偏颇,借此来形成未来的新型中华法学。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形式和实质、抽象和具体、普适和特殊都是真实世界所必然具有的双维,不可简单偏重任何单一方。兼顾双方,追求其最优配合乃至超越两者,既是学术认知也是正义体系制定的明智选择。未来的道路需要从两者的实际并存出发,不仅要追求其逐步磨合,更要探索其融合与超越的道路。那样,才可能真正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束缚,建立中国式的、真正现代的、可长期持续的新型中华法系。
一个新型的“万世之法”
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使我们联想到秦汉一统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继受春秋战国百家中任何一国或一家的理论,而是在新时代中,如何建立新的、长期可持续的“万世之法”的问题,尤其不是在法家或儒家的二元对立之中简单选一的问题,而是要探寻超越两者的综合;不是继受任何单一元,而是如何综合多元的各元而超越之,如何开启综合与整合的、长远的正义体系。
回顾汉代前期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具有特别启发的思想是当时的儒家思想,特别是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思想中的洞见。他在严峻的法家的治理体系和法律之上,纳入、贯穿儒家的道德理念,特别是“仁政”与“德治”,借以补法家之不足,要求在严厉的制度之中,添加和贯穿仁慈、温和的道德理念。其卓越之处在于不简单依赖法、儒任何单一方,而是凭借两者的并用与结合来创建一个更宽阔、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正义体系。
如此的思路和其从阴阳学纳入的宇宙观是一致的,认识到阴与阳的有机结合,好比法家与儒家的结合,要比任何单一方更全面、更可持续,尽可能使偏重刑罚的(正式正义的)法家法律体系为辅,儒家的德治、仁政为主。同时,借助儒家的和谐人际关系理念,开启家族和村社中的(非正式)民间调解机制之逐步形成,其后成为非正式正义(民间调解)与正式正义(法庭判决)结合的正义体系,比其任何单一方具有更为长期的可持续性。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基本点,而不仅是瞿同祖先生所强调的把法家法律等级化(即在其适用中加上儒家的尊卑之分),才是“法律的儒家化”的至为重要的内容。其实,瞿同祖在其论证法律的儒家化的过程中,虽然特别突出了源自儒家的尊卑等级之分,但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董仲舒的“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的思路”,“阳儒阴法”的构想。当然,瞿之特别强调“礼”和“三纲五常”,以及其中的等级尊卑划分,把其当作儒家的核心制度,是没有错的,但在笔者看来,儒家的思想中至为关键的,不是其等级制度,而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仁”的崇高道德理念。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董仲舒承继的是儒家一贯的“仁政”理念,譬如,声称“天,仁也”,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设想。特别是对“德”与“利”的鉴别,即《论语》之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此来反思剧变时代中的社会现实。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这样的理念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利”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潮流“新制度经济学”提倡的是,凭借人人自我逐利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因此而特别强调稳定的私有产权,认为那样才有可能激励人们的创业而推动经济发展,并美其言曰,如此才能造福全社会。在那样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如今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逐利“小人”的天下,几乎人人都在忙着盘算怎样去赚更多钱。儒家的“义”与“利”划分则自始便已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评,可以说一言点到其中的致命问题。今天读来,特别适切。
固然,董仲舒非常有意识地要为汉代皇朝建立一统天下的统治意识形态。西方19世纪的汉学大家理雅各,在其影响深远的大作中把其称作“帝国儒家主义”。其中,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将皇帝置于“天人之际”,为的既是巩固皇帝的威权,也是借“天”来限制皇帝的权。他特别强调“灾异”,以为其表达了“天”对处于天人之际的皇帝的“谴告”。那样的学说,虽然巩固了历代的帝国政治体制,但是并不符合当今的需要。它有意识地把儒家学说构成一家独尊的统治意识形态,乃至于将其宗教化,当然也不符现实需要。
这里还要说明,在儒学之中,董仲舒的帝国儒家主义思想和经学中的今文学派有一定的关联。在今文学(亦可称公羊学)的“家法”中,一贯把孔子建构为“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素王”;读《春秋》以《公羊传》(而不是《左传》)为主导,突出其所包含的“微言大义”,特别是对统治者的“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宇宙观则取自《易经》。如此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应时而变的历史感与“改革”倾向,故其“家法”包括把孔子认作“圣之时者也”。到了近现代,今文经学派的这些思路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得到至为系统的表达。笔者青年时曾在台湾师从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鎏(“俗姓”刘,康有为的第三代“天游辈”弟子,后来在台湾的经学界中影响颇大),对刘毓鎏老师讲授的这些(公羊)“家法”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回顾,其核心在其崇高的、带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念“仁”与“德”——也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法系的核心。
笔者正是出于对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如此的理解,来设想中国正义体系今后的走向。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设想,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设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中至能适应现代需要的传统,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理性正义传统进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另一方面同样借助西方一些至具洞察力的非主流传统,如法律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质主义来对其主流形式理性法律传统进行去劣存优的梳理。在两者的并存和拉锯的大框架之下,来设想一个新型的中国正义体系。具体的研究和所倡导的立法进路则是,从实践历史中区别优良的融合和恶劣的失误,梳理其中所包含的法理,借此来探寻综合两者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一个要求综合中西的设想,也是一个要求适用于中国变迁中的实际的设想。笔者深信,来自那样的探索而形成的正义体系,才可能成为一个可供“万世”之用的新型中华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