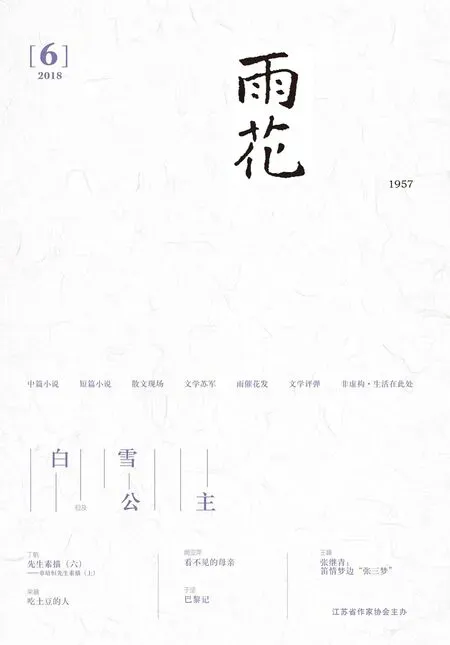谈中国文学走出去
——以《中华人文》编译为例
2018-11-15杨昊成
杨昊成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口号似乎越喊越响。多少国人期盼着有朝一日,世界的眼光能再次如汉唐时期那样,聚焦到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或者,今日的中国能像大洋彼岸的美利坚那样,一举一动,一草一木,均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成为各国人民心中的“山巅之城”,光耀万丈。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支撑下的雄强自信,必然要寻找出路,以自己的软实力,逐渐影响他民族的文化,从而诱导其他国家和民族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进而从心理上占领文化的制高点,最终实现全球领袖的实际梦想。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等,都是各自国家从事文化交流的重镇,但潜意识中是否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梦想或“野心”呢?
中国的情形多少与前者有所不同。虽说这些年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但至少从甲午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处在被人鄙视甚至挨揍的不堪境地。后来又紧锁国门,内斗而至于不亦乐乎。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想到自己的种种实际,才意识到必须快马加鞭,猛追时代的潮流。终于,我们以令世人瞠目的速度,泥沙俱下地进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也终于想到要让外面的世界来了解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我们或者还没有原来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野心。一些“高瞻远瞩”的外国有心人士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未免多虑了。
文学是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生活的全方位展示,文字的精巧安排,也是作家个性风格的闪耀。而众多作家千姿百态的集体亮相,可以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特性的重要窗口。文学是文化的高级形态,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文化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文学走出去。
那么,中国文学走出去了吗?以我主编《中华人文》几年来的经验,答案是否定的。这其中有诸多教训值得每一位对此抱有期望或幻想的人深思。
《中华人文》是2013年年底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一份全英文半年刊,英文名Chinese Arts and Letters。期刊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篇幅是翻译,其余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是纯英文写作。所翻译的内容基本是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主打 作 家 ”(Featured Author), 其中包括他/她的三个左右的短篇,一篇评论(Critique)和一篇访谈(Interview);两位左右的其他作家的短篇(Short Stories);一位散文家的两篇左右的散文(Prose);一位诗人的十首左右的诗作(Poetry)等内容。纯英文写作部分以前就叫“文章”(Articles),从第九期开始重新命名为“文化与传承”(Culture and Heritage),没有题材、体裁、时代、内容、风格等方面的限制,只要与中华文化有关的文章均可入选。但对英文文字的要求很高,一般选择英文纯熟,对中华文化有着相当了解的国内外专门家捉笔。此外每期还介绍一位重量级的现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Art),介绍文章可以直接书写,也可以是翻译。综合看来,这是一份始由江苏,辐射全国,兼顾海外,融文学性、知识性、多元性、时代性、趣味性于一炉,侧重当代,兼及古典,图文并茂,雅俗共容的国内一流的优秀英文刊物。最值得推荐的是,《中华人文》所有的译者都是母语为英语而又专门从事汉译英的优秀翻译家或汉学家,出自他们之手的译作,文字纯正,味道正宗,在英语世界有着很高的可接受性。这在一般由中国人主办的刊物中是很难看得到的。
尽管有这么多优势和特点,但办刊四年来,我们还是遇到了诸多问题。当然主要是选题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来翻译,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中华人文》创刊号选择了江苏乃至国内外一流的作家和学者的作品,以期一炮打响。事实上我们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理想。毕飞宇、苏童、范小青等人的小说,李敬泽、施战军、王彬彬等人的评论,庞培的散文,张隆溪、Martin Puchner(哈佛英文系教授)的专文,复旦外文学院教授沈黎介绍徐悲鸿的艺术评论等,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都是无懈可击的、扎实的、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可以代表中华优秀人文成果的力作。可到了第二期问题就来了。当初负责为我们提供翻译稿源的评论家提供给我们的“主打作家”是专写长篇的一位作家,没有短篇。其他两位小说作家及诗人的作品也实难恭维。这让我们犯难了。但为了尊重评论家的选择,我们还是勉为其难,从他提供的“主打作家”的一部长篇中,选择一个章节约三万多字的分量,拿给我们的译者兼副主编之一Josh Stenberg翻译。另几位作家的作品,我们的翻译家拿到作品后竟拒绝翻译,使我们非常尴尬。后来我们紧急请范小青出面推荐替代作品——叶弥的《亲人》和鲁敏的《谢伯茂之死》,才安全渡过了难关。
这件事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用强推的办法是很难奏效的。这就要谈到目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三大主体:各级政府官员,不谙外文或外国文化的专业工作者,以及从事汉译英编译工作的专业人士如翻译家、汉学家、比较文学研究专家、编辑等。政府官员高瞻远瞩,视野开阔,能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或建议。但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官员们往往容易从意识形态出发,一厢情愿地把他们认为重要的文化成果推介给西方读者。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创办于1951年的英文刊物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虽然先后有诸多英文纯熟、为人正派的知识分子担任主要编辑,但在其长达五十年的生命中(《中国文学》于2001年终刊),内容从阶级斗争到歌功颂德,从战斗檄文到庸俗文艺,始终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严重规范,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印记,很难越出所规定的藩篱,虽说是半个世纪内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但在西方读者眼中不过是一部红色中国的宣传册,根本引不起人家阅读的兴趣。
不谙外文和外国文化的专业工作者,囿于其自身的视野,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很难作出健全而理性的判断,往往从仅适合于自己文化或文化口味的视角选择材料,供人翻译,忽视了可译性、可接受性、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等重要因素。《中华人文》曾接到过专写地方戏曲的文章,其中有大量的专业术语、充满历史蕴含的人名地名等。虽说文章本身写得灵动而富有生气,但这样的文章显然缺乏可译性,如果加注,则满页都将是注释,令人难以卒读。我由此联想到2014年4月底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镜中之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一个发言,“How Can Chinese Literature Reach a World Audience?”(《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葛浩文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绝大多数作家和评论家不懂外文的问题,我以为切中要害。葛浩文说:“如果中国作家只满足于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那倒也罢了——事实上有些作品也只适合于‘内销’,问题是你不是想走出去吗?不是要走向世界吗?走出去就得遵守既定的规则,至少得懂得别人是怎么玩的,然后才谈得上参与。”葛浩文一生接触过的作家、文人、评论家不计其数,所以在这方面他感慨良多。他说,中国作家、评论家缺的不是才气,而是国际视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外的作家和评论家,这些人大都精通两三国语言,尤其是国际通用语英语和法语,随时随地可以无障碍地与人交流。而我们的作家呢?四年前苏童曾跟我说,他和其他中国作家到国外进行“友好访问”,至多只是“观光”,根本谈不上交流。有时也有翻译在,但依靠翻译的交流怎么能够深入?而中国作家是多么渴望与他人深入地交流啊!可惜葛浩文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被许多爱国人士斥为“文化霸权主义”。我不管,他那篇发言除几处文字略有改动外,完完整整地被刊登在了第二期的《中华人文》上。
相比较而言,从事汉译英编译工作的专业人士如翻译家、汉学家、比较文学专家、编辑等要懂行得多。但这其中也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虽说改革开放多年,国人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有了较以前大幅度的提升,但真正了解一国一民族的文化及文化心理,谈何容易!不是你满口“kind of”,耸肩摊手,就是掌握了别国的文化,那是“假洋鬼子”。同样,教别人打几手太极拳、写几笔毛笔字、剪剪纸、唱几段京戏,就像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所从事的主要营生一样,也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中华人文》从创办之日起就明确规定不用母语为中文的译者,正是基于对不纯正英文使用者的警惕。有些很负盛名的国内译者或翻译家,其实在国外的境遇是很冷淡的。例如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他是牛津毕业生,又娶了同为牛津毕业生的英国太太Gladys M. Tayler,两人合作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一生出版了包括《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等在内的一百多部作品,被誉为当代中国汉译英第一大家。可就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其翻译作品在国外遭到冷遇。前些年曾有上海学者做过非常详实的统计,其中说到杨先生翻译的《红楼梦》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出借的情况。与当代伟大的英国翻译家、汉学家David Hawkes(大卫·霍克斯)的译本《石头记》相比,杨先生的《红楼梦》译本几乎无人问津。我起初对此还抱有怀疑,但到自己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经典翻译”课时,其中谈到《红楼梦》的翻译,自然就用到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译本。两相比较之下,高下立判。甚至学生们在我逐字逐句的精讲之下,也能体味出霍克斯译本之无与伦比。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杨先生的意思,事实上,杨宪益的《红楼梦》译本也已成为汉译英的经典,处处都能找出精妙绝伦的佳译、妙译。杨先生与霍克斯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同道,互相敬重。但总体来说,霍克斯的译笔要更加地道、纯正一些,更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事汉译英,目标语为英语,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天然地占了优势。我回想起大约十三年前,因为教授《水浒传》的翻译,曾打电话给它的译者Sidney Shapiro(沙博理)。沙老用地道的北京腔对我说:“对我来说,翻译像《水浒传》这样的作品比将英文材料译成中文要容易得多。虽然早在1963年我就入了中国籍,但中文毕竟不是我的母语。”
另一个例子更加让我记忆深刻。2006-2007年,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赴美前,由我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集《历代名人咏江苏》刚刚由扬州的广陵书社出版。我虽有过近两百万字的翻译实践,但汉诗英译还是第一次。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心中到底没有数。有过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汉诗英译,而且还是古典诗词的英译,那是一般人不敢碰的。我带了一部《历代名人咏江苏》到了哈佛,想找机会请教一下有关专家,请他们提提意见,以便重印时作些修订。我先后找过包括我的合作导师英文系教授John Stauffer、英文系特聘诗歌教席Peter Richards等五位专家看过。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哈佛一级教授Stephen Owen,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中国古典诗词学者,中文名宇文所安。后来《历代名人咏江苏》被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我记得拜访宇文所安教授时,问及他是否读过国内名气非常大的一位从事汉诗英译的北大老教授的译作。宇文说当然读过。我问他怎么样。宇文连说了两遍“Rotten stuff!”译成中文就是“烂货!”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至今言犹在耳。我当然要请他说出理由,因为那时我和国内众多从事翻译的人一样,对那位老教授是相当敬重甚至崇拜的。宇文说了一大堆,但中心意思只有一个:那种诗歌的表达方式不是英文的表达方式,因此读起来觉得别扭,有的甚至不知所云。
有鉴于此,我在《中华人文》创办之初就明确规定,本刊所有译者一律必须是母语为英语者,或者长期生活在国外,其英文水平相当于母语的专业工作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中华人文》之所以获得西方读者和圈内有关人士的交口赞誉,正是由于这些译者地道、纯正的英文和他们对汉语的准确把握。当然,译者中也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我们曾碰到过一位英国译者,还是剑桥毕业生,请他翻译了范小青的两个短篇。译稿最终到了我手上,怎么看都有问题,甚至还有语法问题。让他按我们的意见修改,他坚决不改,强说英语是他的母语,怎么会有问题。后来我们决定退稿,让另一位老牌翻译家Denis Mair(梅丹理)救急。这时他急了,对我说出了实情:原来他是剑桥数学系毕业生,在复旦读研究生,初次从事翻译,顺便挣一点生活费。当然,为了安抚他,我们最后还是用了他两篇译稿中较好的一篇,稿费照付。
还有一些译者,能力非常强,翻译经验也很丰富。但不知何故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把我们现在常说的“拼爹”,译成“fight with his father”(与父亲打架)。审稿时看到这样的“神译”,我不禁莞尔。再比如朱辉的《郎情妾意》,这是一篇优秀的短篇,我个人非常喜欢。译者Eric Abrahamsen是著名的美国翻译家,现任《路灯》(Pathlight)杂志编辑总监。整个小说译得相对精彩。但小说题目译成“True Romance”(真正的罗曼史),黯然失色,全然没有原文的幽默带嘲讽。后来我建议译成“The Perfect Match”,回译成中文就是——绝配。我以为还是颇能传达原文的精髓的。类似的例子很多。审校这样的稿子,对于我们做编辑的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提升自己中英文水平的绝佳机会。
作为一份诞生不久的刊物,《中华人文》自然期望和所有刊物一样,能够前程锦绣,产生愈来愈广泛的影响。然而,正如我在创刊号Editor’s Note(编者的话)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知道,口号可以响亮,话语尽可宏大,志向不妨高远,但说到底,即便没有你这份刊物,世界照样存在,地球依然运转。所以,我们在尽心竭力办好刊物的同时,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因为理想与现实、期望与效果之间永远都存在着距离。就《中华人文》而言,必须对以下四方面的因素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首先,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审美享受从来都是小众的奢侈行为,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文学虽然并未如悲观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亡,但其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时代,不是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王尔德、萧伯纳、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的时代;不是民国、五四时代,甚至也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中国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人们获取知识、信息、娱乐的渠道和方式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大众为什么非要来阅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呢?
其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愿望本身可以理解,出发点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虽然我们如今言必称“一体化”“地球村”,而实际上民族、国家、地区之间隐形的疆界始终都还是存在的。每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无疑更愿意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更愿意关注他们自身的命运和发展。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凭什么非要来了解或接受一个与其切身利益并无现实关联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中华人文》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中华读书报》记者对苏童的采访,记者最后也提到了“走出去”的问题。苏童的回答很是理性,他说,“当代德国作家又有多少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呢?除了君特·格拉斯等极少数作家以外,也不多。所以看这个事情要心平气和,中国作家不存在急待解决的问题。”我在跟毕飞宇的一次通话中也听到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比方印度、巴西或其他什么国家的读者,他们凭什么要来阅读你的作品?”我相信,头脑清醒的作家艺术家们都会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像搞运动那样,动辄轰轰烈烈,奢望五湖四海都来争相阅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人文》创刊号2014年4月8日在伦敦南岸艺术中心搞了一个首发式,借助2014年伦敦书展这一重要的国际文化平台向西方世界宣告了她的诞生。这无疑是有关部门采取的聪明之举,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盲目地乐观,以为世人的目光从此就会真正来关注这份刊物的发展动向。一份刊物,即便对象是小众,归根结底还得凭借质量和实力才能保住其生命,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再次,作为一份人文读物,《中华人文》和国内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不同,不能为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众多需要为晋升职称而发表论文的人员提供被有关方面认可的学术平台。《中华人文》也不是通俗读物,绝不会为了经济或市场效益而降低格调,更不会迎合低级趣味,沦为庸众猎奇或猎艳的渠道。又因为《中华人文》是一份全英文刊物,读者必须具备中等程度以上的英文阅读能力才能走进她或对她产生兴趣。所有这些也都决定了本刊要想在广大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之不现实之处。
最后依然是媒介这个古老的问题。对于文化交流,翻译是必需的,但又永远是无奈的,遗憾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翻译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人文学科成果的翻译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诗歌,许多人以为根本就不可译。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就说,“所谓诗歌,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中华人文》每一期的主要内容是汉译英,尽管我们启用的译者基本都是精通中英两种文字的西方职业翻译家或汉学家,有的译作堪称一流,然而无论如何,与原作相比,总还有缺失和距离。文学艺术中最精微的成分也最容易在翻译过程中丢失,而一旦丢失,对译文的欣赏和审美度就要大打折扣。更何况还有许多东西其实是不可译的,因为他们在目标语中根本就没有对应物。所以,从本质上说,文学翻译充其量只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为,可歌可泣,但有着诸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