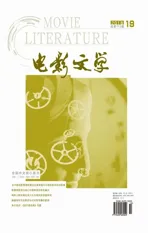在矛盾和不确定中探寻欲望与命运的本源
——论《春去春又来》的模糊美
2018-11-15杨建生
杨建生
(常州工学院 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韩国著名导演金基德执导的《春去春又来》给观众留下了太多的思考空间,令人回味无穷。当我们企图去清晰地梳理影片的思路和特征,并从理论上做出某些总结和表述时,我们发现这个过程是极为艰难的。每次我们试图做这种努力时,总会有一种“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本人就曾经感觉到“影片思路上的某些紊乱与模糊”。也曾阅读过一些关于金基德电影评论和研究的文字,它们对于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意象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观点甚为丰富。对这些观点做整体性综合思考时,我突然发现,正是由于金基德电影具有一种“模糊美”的特征,才留下了如此多的“空白点”来让我们反复把玩、思考、填充,也许这正是金基德电影艺术上的一个美学特征吧。
以柏拉图、黑格尔和尼采为代表的传统观点把语言的模糊性看作是语言的缺陷,希望限制它,消除它,对事物往往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接受美学的产生极大地颠覆了这种观点。艺术作品的“召唤结构”“启示结构”“未定点”“意义空白”等概念的提出,极大地迎合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影响深远。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创作中,虽然无意于去迎奉这种理论,却总是暗合这种理论,这是一种必然,也是艺术创作的规律,因为模糊美是艺术存在的必然,只不过在有的艺术品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有的体现得比较隐晦。我们在分析《春去春又来》的美学特质时就发现,这是一部“模糊美”特征体现得尤其强烈的影片,模糊性为作品增添了更为丰富、多样化的审美想象空间,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什么是“模糊美”?王明居在他的《模糊美学》中阐明了模糊美的内涵,它具有相对性、互渗性、包孕性和亦此亦彼性等。胡和平在《模糊诗学》中也论述了其基本理论范畴,包括象征、隐喻、反讽、悖论、空白、未定性等。在《春去春又来》中,作品的语言、意象、情节、结构等都带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具有极强的概念外延性,由生活现象到艺术世界,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充满着空白与不定,留下了巨大的弹性空间,既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又能够最大地调动读者再创造的想象力,具有独特的审美潜能。这些美学因素可以极大地唤起审美主体审美意识中的联想、体验和感悟。这些不确定性为接受者提供一种理解的张力,使不同的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创造性思维来赋予作品不同的理解,这种模糊性既调动了审美主体,也扩大了审美客体,从而扩大了艺术审美空间。
在影片当中,庵门能自动开合;水中孤寺可以漂移;小船可以在老僧的意念控制下往来于水间;老僧随手扔出去的一粒石子能轻易砸中水中的易拉罐,而持枪的警察却屡击不中;灵蛇也违背冬眠的习性,成了衣钵的守护者。这些细节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突出了一种非真实性,干扰了我们对于惯常的真实性寻求,作为影片,这种虚构无可厚非,“电影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必须要以创造的主体性去超越现实的客观性”,任何艺术创造的本质也都在于对现实的超越与重构,与神话一样,电影对人类世界的描述方式也是超现实的。所以我们不必用现实的逻辑来衡量这些细节是否合理,这些只是一种理念的传达——甚至传达的理念也具有不确定性,呈现出一种模糊美。不可否认,这些细节有一种把我们引向禅意的“企图”,时时刻刻向我们传达禅的“意念”,但是,这种意念是很难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述和传达的,或许,这正是细节模糊美的魅力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些细节的神秘,读者从其中也同样能感觉一种“不确定”,即人生的不确定,生命的不确定。在人的一辈子中,有很多东西是超出我们预期之外的,是难以控制和把握的,它的存在不能用偶然或者必然来界定,在生命当中隐隐约约地存在,这种存在就是生命的模糊美。有人把这种不确定称为人生的虚无和虚幻,实际上,从美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生命的模糊美,人生就是一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体,二者相互包孕和渗透。
故事没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影片中的人物也没有来历,没有姓名,没有关系介绍,身份信息等都不详。实际上,他们是一种“普适性”人物,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并没有作为个人存在所展现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只是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人物”或者符号而存在,这也是出于一种艺术传达的需要,好处之一就在于这类人物易于辨认,接受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认知、识记和理解。这一点在“冬”的片段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雪夜托孤的女人在系围巾时,向我们展现的只是她的背影,中年和尚把女人从冰湖里捞出来,解开围巾的一刹那,导演也转换了镜头,刻意隐藏了女人的面孔,始终没有交代女人的身份。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蒙面?她与中年和尚曾经有过什么瓜葛吗?所有这些问题,导演刻意回避着,观众越是不知道就越想去探求,观众越是想去弄明白吧,导演却偏偏不让你弄明白,就这样让你欲罢不能,被一再强化的是那种不必知和不可知的模糊性。导演似乎也并不着意从“典型人物”身上来体现“典型性格”,而是把重心放在探索这些人物符号存在的价值上,要去探寻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生命本源意义。在这些不确定的人物本身向我们展示一种神秘和模糊时,导演所传达的理念更具有丰富性、多层次性、神秘性。这就跟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特别喜欢选择人的裸体形象来描绘和刻画是一个道理。一方面,人体本身毫无疑问是地球上最美的,是自然美的最高级形态,也是最高雅的感性艺术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裸体人的身份、职业都是不确定的,这就更具有最广泛的包孕性、代表性,可以指代需要指代的任何人群或个体,其概括性、寓意性就更丰富,阐释空间也就更大,艺术传达的效力则更强,该艺术产品的文化消费价值自然就更高了。在《春去春又来》中,不但人物关系、来历模糊,人物的活动范围同样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体。一扇庵门把人物的活动范围划分成两个世界,即佛界和俗界。中年和尚走出寺庙后,随欲望的驱使去追寻他俗世中喜欢的女人,后又犯下了杀妻之罪,这中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过程,夫妻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情感生活的纷纭诡谲,影片并没有做详细的交代,只是在师父面前发泄愤怒和抱怨时透露出一鳞半爪,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作者在影片中着力探求人性的本源,和尚在往返于佛界与俗界之间,最终是回归了佛界,整部影片充满了禅意。但是,影片中“弥足珍贵”的对白和一些细节却又超出了“禅”之外。小僧虽然生活在佛门之中,但是并没有得到佛理的熏陶,身在佛门,佛在心外,并没有领悟佛法真谛,在游玩当中对小动物实施虐待,长大之后又犯了杀妻之罪,青年杀妻不过是童年虐待动物的一种延续。开始,小僧还处于欲望的最底层,出于简单的童趣而虐待动物,当年岁渐长,欲望开始膨胀,最终淹没了人本身。老和尚的教导并没有使小和尚由“恶”导向“善”。小僧在夏日的湖水里面进行了多次佛性与欲望的较量,但最终抛开了佛门禁忌投入到情爱的河水中。当年轻和尚和治病少女在上船时产生身体接触的那一刹那,他内心的欲望已经开始潜滋暗长,就像湖水的涟漪一样,开始不断向外荡漾开去,膨胀起来,最终把心中的佛性涤荡得一干二净。对于这种恋情,老和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只有爱情才是治疗你这种病的最好良药。”佛门作为清修之地和“禁欲”之地的大众化观点基本上就被老和尚的这句话给彻底消解了。年轻和尚和少女之间由恋情进一步发展到“交媾”,寺庙的威严形象也被彻底颠覆了。而且,这种交媾是一种“拼命”式的,二人缺少必要的、充分的情感酝酿、交流,有的只是内心欲望的释放和外泄。片中人物的举动和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变了人们的惯性思维,干扰了欣赏者对于故事的常态的真实性寻求,眼前的寺庙由“禁欲之地”变成了“世俗之地”,这是一种“陌生化”的故事叙述技术,能够造成一种所谓的“间离效果”, 正因为其模糊性,反而令人产生强烈的破译冲动,从而大大拓展了作品艺术欣赏的时空纬度,使作品获得更大的审美效应,进而把欣赏者的思维导向一个更高的境地——去思索人性的本源问题。
换个角度,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讲,正如寺庙里有门没有墙一样,庙本身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而存在,导演所要侧重传达的并非描写发生在寺庙里的事情,寺庙作为“禅意”和“出世”的符号,是与世俗相对立而存在的。整部影片虽然充满了浓浓的“禅意”,但是,导演的终极目的不是向我们宣传佛教,介绍佛教,而是把佛教作为一个载体来探讨人的命运归宿问题。影片中的寺庙只是作为物质性的存在,作为渲染“禅意”的工具而存在,实际上并没有作为承载佛教精神的场所而存在。因为生活在寺庙里的生活和世俗的生活并没有两样,同样是充满了俗欲。影片告诉我们一个真谛,佛只有真正进入心中,人才能得以超脱,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佛理和与世隔绝的环境并不能抑制人的欲望的膨胀。日本神学大师铃木大拙说:“禅存在于个人的一切经验之中。没有个人的经验的背景,思想便难以传达。”禅尚未被年轻的小和尚所经验,师父的教诲就阻止不了小和尚的欲望,他最终还是归入了尘世,只有经过个人内在的经验、洗礼,重返佛门时,中年和尚才不再是以“我”观佛与世,而是以“佛”观世与我。夕阳中,僧人以石磨为基座,将佛像置于山顶,冰封的湖面不过山地石臼大小的一汪,这是超越欲望之上来看欲望,显示了对欲望的彻底超脱。
老和尚的死也很值得深思。他选择了“自焚”,而且是五官“紧闭”。老和尚是看透尘世而觉无所留恋了?还是对人的本能欲望无法抑制感到无奈,而对内心“佛”的轰然倒坍所做出的消极回应?抑或是他已经预见到了中年和尚有回来的那一天,自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他的死显得扑朔迷离,朦胧模糊,难以确定。可以肯定的是,老和尚选择闭五官而死,传达了他对“欲望”的反对与否定这一信号,但是,他为什么又肯定情爱的合理性?在这些肯定与否定之间,影片所传达的理念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显得特别丰富。正是由于这些不定性的模糊区域,才为接受者制造了障碍,提供了再创造的艺术空间。这些不定性会在接受者与作品的双向交流作用下,有效生成别有意味的审美世界。康德也说过:“模糊观念比清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美应当是不可言传的东西。”因为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人的天性,对于模糊美的不断追求和探索既能满足人的天性需求,又能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内涵,在艺术审美的主客体双方相互吸引、相互作用中,艺术魅力便应运而生。恩格斯也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在影片中,诸多充满隐喻和象征的意象都没有陷于简单抽象的“非此即彼”,而是具有一种不确定性,都是明晰与模糊的统一,静态与动态的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和尚的一生经历了童年杀生—少年色戒—中年作孽—老年超脱四个阶段。在充满“禅意”的寺庙,小和尚的欲望并没有因为这些意念的熏陶而得以抑制,反而得到了更为强烈的爆发,佛界的教化静心功能遇到尘世的“欲望”时,显得无能为力,不堪一击,很快败下阵来。小和尚生理与情感的浪潮冲垮了佛门的堤坝,离开清修的庙宇而踏入尘网。但是,中年和尚在犯下杀妻之罪以及后来刑满释放后,都选择了回归寺庙,如果说前一次的回归是一种逃避,那么后一次回归则是真正的“出世”。中年和尚在面对尘世而无以解脱时,选择了寻求佛教,得到了生命的升华和超脱。这一次,在和尘世的较量中,佛教占据了上风,彻底征服了尘世。金基德在影片中一如既往地在思考人在满足和追求欲望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在探索如何摆脱欲望的道路上,影片仍然显得矛盾和迷惘,虽然最后仿佛也给出了答案,即皈依佛教,但是这种答案显得极为软弱和牵强。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导演内心所呈现出的矛盾,也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矛盾,即人类如何摆脱自身的欲望?或许,人类在不断探索,但永远没有答案。金基德的矛盾也是整个人类的矛盾,没有确定,充满了模糊和不确定性。实际上,金基德所涉及的命题,人的欲望以及命运等命题,都具有一种本源的意义,不可能得出确定和明晰的答案,导演用模糊性的表达方式能更深刻地探讨人性本源的命题,接受者也能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理解此类命题。
中年和尚回到寺庙以后,为了洗脸而凿了一个冰窟窿,托孤的女人在深夜离开寺庙时,神情慌张,掉进了这个冰窟窿。如果说青年和尚犯下的杀妻之罪是故意为之,那么这次的“杀人之罪”则是一种无过,正是这种无过体现了人生的无常、虚无和不确定,有时候,“为”或者“不为”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中年和尚在命运之神的诅咒下饱受内心的煎熬,陷入了宿命的怪圈。纵观整部影片,导演在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人饰演和尚,但在结尾中却用同一个孩子饰演童僧,前面的不同暗示了人人都有成为僧人的可能,最后的相同却让人明确感受到了轮回的宿命,老僧是否也经历了人生的春夏秋冬?影片的环状结构昭示了命运的轮回,人只是命运的一个棋子,开放式的结尾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实际上,金基德的影像世界也是个符号化的世界,这些视觉符号充满了复杂而丰富的意义,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抽象性,充满了哲思和隐喻,显得凝练而意味深长。他运用了更为广义的影视语言,画面构图、特定场景的设置、道具、色彩、光效、音乐等,更加充满了隐喻性和延展性,突出了一种模糊美。有成就的艺术家总是善于以模糊手法创造出具有更广泛包容性的艺术形象,唯其模糊才更有魅力。综观《春去春又来》全片,金基德用西方的思维提出了一个命题——原罪,又用东方的思维做出了回答——皈依佛教,实现了中西杂糅,亦此亦彼,相互渗透,真可谓此处模糊胜清晰。
欲望和命运本源问题的探寻是艺术创造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春去春又来》整部影片充满了大大小小矛盾和不确定的关于人类生命的隐喻和象征,其模糊性、未定性和无限性能始终吸引观众去做无尽思考和解读,显示了特有的艺术张力。“生命美学”代表人物潘知常先生说过:“在我看来,审美活动就是以‘超越性’和‘境界性’来满足人类的‘未特定性’和‘无限性’的特定需要的一种生命活动。”是的,金基德的《春去春又来》正是这样一部带领我们享受文化消费盛宴和探索生命之美旅行的经典影片,余味不尽,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