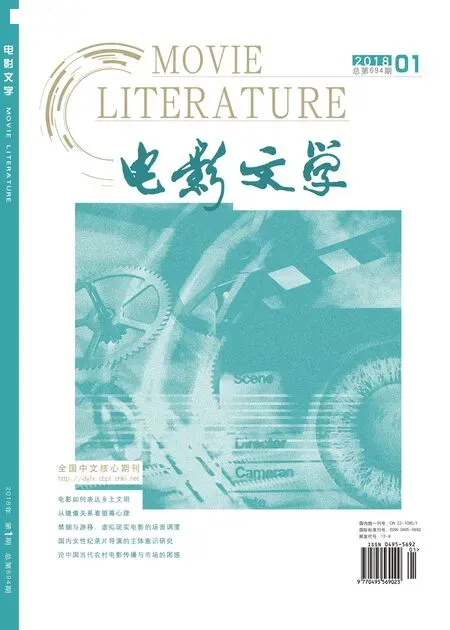故 乡
2018-11-14
1.北京前门
白雪皑皑,莽莽苍天。
银雪覆盖,冰凌倒挂,整个城市,房屋街道,轮廓清晰。
街上行人,寥寥无几。
一个人力车夫,深一脚,浅一脚,步履艰难地挣扎在雪窝中,行走在薄冰上。车子慢慢地在伸向银幕尽头的雪地上,留下一对对、一道道明显的脚印和车辙……
2.火车上
一辆蒸汽机车,“呜——”一声长鸣,划破冰冷寂寥的天空,迎面飞驰而来。
车厢里,迅哥透过车窗冰花,望着空旷的原野。
光秃秃的山地,绵延起伏的丘陵,潺潺的小溪大川一晃而过。
3.河道上
水天相连,茫茫一片,夕阳衔山,孤鹜独飞。
水天一线间,一只篷船,迎面缓缓而来。
呼啸的凛冽寒风,呜呜作响。
迅哥身着长衫,系黑色大围巾,被朔风一吹,飘然而动,伫立船头,凝视远望。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
衣衫褴褛的纤夫,吃力地拖着一条满载货物的船只,逆流而上。悲凉沉重的号子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消失在远方。
迅哥搓了搓冻得麻木的双手,凑到嘴边用热气哈着。
迅哥深沉的画外音:“1919年冬天,我冒了严寒,从北京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20余年的故乡绍兴。”
推出片名:故乡。
篷船拐弯抹角,穿过河沟港汊,来到绍兴“覆盆桥”岸边。
迅哥跨上河岸,走过拱形桥,抬头望着,南城东昌坊口,聚居而居的大家族,新台门周家。
周家,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黑漆大门的油漆已斑驳脱落,门匾上的字迹“周宅”依稀可见。
迅哥画外音:“我这次回故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因为我是专为了别它而来的……
4.周宅宅前
迎着迅哥出来了周母和宏儿。
迅哥重重地喊了一声:“妈妈……”
周母上下端详迅哥。
迅哥的外貌特写:深邃的双眼,几缕淡淡的皱纹,面颊两颧骨微微凸起,略显有些消瘦,短短的下颚,颤动着。
周母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但非常高兴地递过古铜色的手炉,将迅哥迎进门里。
5.周宅
五进大宅院,一派破败景象,颓垣断壁,房屋年久失修,东西横七竖八地堆放着,抛在那里,到处是尘土蜘蛛网。
正厅堂正中的金字匾额,两旁柱子上的对联,陈旧不堪。
进了屋里,周母边说边忙着给迅哥端水洗脸。
迅哥在擦脸时才注意到,远远站在对面一直看着自己的宏儿。
周母拉着宏儿说:“宏儿,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你大伯。”
迅哥招呼宏儿,宏儿喊着伯伯靠近迅哥,站在迅哥身前膝边。
大家坐下,歇息,喝茶,扯家常。
迅哥边抚摸着宏儿边问:“叔叔、伯伯都搬了吗?”
周母:“都搬了。这老屋公同卖给朱文公家以后,说定今年交屋,这才叫你正月以前来。”
迅哥:“北京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
周母:“行李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卖了,到北京再去增添,只是收不起钱来。”
迅哥:“不急。”
周母:“早晚得走,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
迅哥:“是的。”
周母:“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告诉了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迅哥喃喃自语而又兴奋地说:“闰土……”
此刻,外面传来吵吵嚷嚷声。
周母站起来,拉着宏儿一同走出屋外。
迅哥坐在屋里一动不动,看着母亲和宏儿走出屋外,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迅哥的内心独白:“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那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父亲周伯宜还健在,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恰逢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
6.周宅正厅堂(回忆)
金碧辉煌,正中的金字匾额,两旁柱子上的对联,“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闪闪发光,习习生辉,耀眼夺目。
神像前摆有古铜色大香炉一尊,高高的烛台两个,青花瓷花瓶一对,高而大,重且值钱。
十来岁的迅哥儿,随着父亲周伯宜观赏祭器。
迅哥儿新奇地指着香炉、烛台问:“爸爸,这是什么?”
周伯宜:“这是供祖的香炉和烛台……记住,祭祀,小孩子不要多嘴。”说着,掠着胡须,迈着方步,审视着祭祀的摆设。
庄严肃穆的祖像牌位居中,供桌上丰盛繁多的供品,还有十分考究的祭品。
周伯宜环视中,凝神注视着香炉、烛台和花瓶,稍事停留片刻,对跟在身后的章运水说:“阿庆,这祭器,特别是这香炉、烛台和花瓶,价值千金,要严加看管才是。”
阿庆:“是,老爷。只是这人手少,拜祭的人又多,实在照顾不过来。”
周伯宜“嗯”了一声,点头称是。
阿庆:“老爷要不嫌弃,叫我儿子闰土来看管祭器,只是那孩子年龄小,干不了重活……”指着迅哥儿说,“比小少爷还小一岁呢。”
周伯宜看了看阿庆,满心欢喜地说:“那好,那好。好在也就是一个月。”(回忆完)
7.周宅
陷入深思的迅哥嗫嚅着:“当年的闰土……”
8.周宅正厅堂(回忆)
小闰土滴溜溜的双眼,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宛如一个小英雄哪吒。他在阿庆的指引下,给周伯宜行过磕头大礼,跟在阿庆身边,出现在香炉、烛台、花瓶面前,煞是惹人喜爱。
周伯宜抚摸着小闰土,高兴地比划着,交代了好好看管祭器的任务,便走开了。阿庆也跟了出去。
正厅里,只剩下迅哥儿和小闰土两人,迅哥儿望着小闰土,小闰土望着迅哥儿,两人共同看看香炉、烛台,最后两人的视线盯在高大花瓶上的插花上,那是两米高,又大又美的牡丹绢花。盛开的牡丹绢花,红彤彤映红了两位少年英俊的小脸。
迅哥儿喊着:“闰土!”一下扑向闰土。
闰土腼腆而又大方地喊着:“迅哥儿!”朝迅哥儿迎过去。
两个小伙伴紧紧地抱在一起。
迅哥儿:“你在哪里住?”
闰土:“在海边。”
迅哥儿:“你为什么叫闰土?”
闰土响亮地说:“我爹说,我是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我们家要有田地,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闰土。”
迅哥儿兴高采烈地说:“好听的名字。”他好奇地抚摸着闰土脖子上的银项圈,看看自己颈上却没有。
闰土会意地说:“我刚生下来时,爸爸怕我死去,在身佛前许下愿心,用圈子把我套住。”
此时,闰土见有人走来,就老实羞怯地站在花瓶旁边不说话。
迅哥儿见此情景,也心领神会地站在另一只花瓶旁边不言语了。
两束盛开的牡丹绢花,越发显得娇艳。
娇艳的绢花牡丹,化作洁白晶莹的雪花。
9.院子里
落英缤纷,鹅毛大雪,纷纷飘落下来。房屋上雪越聚越多,愈发显得院子里高墙上的四周天空,寂寥空旷。
迅哥儿和闰土,两个小脸不约而同地贴在窗上。
迅哥儿画外音:“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这都是我以往的小朋友所不知道的。记得,有一次雪下得也很大,我怨声怨气,不高兴地说,不下雪没好玩的,下雪了更没好玩的了。闰土听了,若有所思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一下。”
10.院子里
闰土扯着迅哥儿往院子里跑,迅哥莫名其妙地跟着闰土,他们穿过院子,来到后面的百草园。
闰土顺手抄起一把扫箒递给迅哥,指着百草园中心的一块厚厚的积雪地,命令似地说:“快!把雪扫开一个圆圈。”
迅哥儿顺从地扫着地上厚厚的积雪。
闰土又找来竹筛、绳子和鸟笼。
迅哥儿问:“干什么?”
闰土:“捕鸟!”
迅哥儿高兴极了,用力扫着积雪。
只见闰土在迅哥儿扫过的空地上修整了一下,把四周的雪围得高高的,空地上又轻轻地挖了一个小洞,撒下秕谷,用短棒把大竹筛支起,在短棒上绑了一根绳子,远远地扯到石井栏旁边的一棵皂角树后。
一切收拾停当,两个小家伙蹲在树后瞅着大竹筛。
霎时,鸟儿吱吱吱、喳喳喳,由远处飞来,落在雪地上,飞在竹筛顶上,靠近竹筛边上,瞧着秕谷乱叫。
这时,迅哥儿急不可耐,揪住绳子要扯,闰土不让扯,迅哥儿还要扯,闰土还是不让扯。争执中,他们不经意将绳子拉动,支棒倒了,竹筛扣在地上。两人飞速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掀起竹筛,一只鸟儿也没有,秕谷却少了不少。
闰土又撒一些秕谷在竹筛中心,两人才又回到皂角树后。他们的四只小手冻得红红的,不约而同地用口呵着,暖和着。
鸟鸣声,鸟儿越聚越多,还是从雪地到竹筛边,到竹筛里,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闰土示意,两人将绳子一拉,支棒“啪”地一蹦老远,竹筛结结实实落下,鸟儿在竹筛里吱吱喳喳乱叫乱飞。
两人欢呼跳跃地跑过去,只见闰土敏捷地将竹筛慢慢移动,半露出挖的那个小洞。突然,一只小张飞鸟,钻出头来,闰土轻轻抓住放进鸟笼。
迅哥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鸟?”
闰土:“这叫张飞鸟,性子急,养不活。这是稻鸡,这是角鸡,这是鹁鸪,这是麻雀,一只,又一只……”
迅哥儿看着鸟笼子里活蹦乱跳的各种小鸟,高兴极了,拉着闰土就往前院跑。
11.屋内
闰土拎着鸟笼子,两人飞也似地来到周母面前。
两个小家伙,头上、眼眉上、身上全是雪,简直就是两个“小雪人”。
周母疼爱地赶快给两人扫除身上的雪,拍打着说:“大冷的天,干什么去了?”
迅哥儿说:“捕鸟!捕鸟!可好玩了!妈妈,你看。”把鸟笼子拎起来给周母看。
笼子里的鸟活蹦乱跳,两个小伙伴眉开眼笑。(回忆完)
12.周宅正厅堂
小迅哥儿化作迅哥,他坐在正厅里一动不动,依然陷入深深地回忆中。
迅哥画外音:“那一年,闰土深情地对我说……”
13.院子里(回忆)
“到夏天,你到我家的海边去,我和你到海边去捡贝壳。红的、绿的、斑驳陆离的、五光十色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都有,什么‘鬼见怕’、‘观音手’……最有趣的是一到晚上,我们和我爹去看管西瓜……”闰土一往深情,津津乐道地描绘着。
迅哥儿入神地听着,问道:“管贼吗?”
闰土:“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光下,你听,啦啦地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迅哥儿听得入神入画。
随着闰土的描述,一幅幅神奇的画面出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而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14.周宅正厅堂
闰土的父亲阿庆对周母、周伯宜说:“老爷,祭祀完了,明天我准备带闰土回去。”
年幼无知的迅哥儿对阿庆说:“阿庆叔,你要带闰土到哪里去?”
阿庆:“回家到海边去。”
迅哥儿对周母说:“妈妈,我也跟阿庆叔去海边。”
周伯宜:“迅儿,不要多嘴,到阿庆叔那儿去,以后再说。”
迅哥儿:“不让我去,就把闰土留在这里吧。我不让闰土走!我不让闰土走!”说着哭闹起来。
这时,周母才发现闰土不知去向。
周伯宜:“闰土去了哪里?”
阿庆:“早跑到厨房里哭去了。”
迅哥儿执意地在周母面前撒娇,哭着不让闰土回去。
15.厨房
闰土躲在这里哭着不肯出门,阿庆一个劲地拉闰土。
闰土哭得是那么单纯,幼稚,可笑,一个劲地说:“我不回去,我要在这里看祭器。”
阿庆:“好孩子,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再带你来好吗?”
周母:“要不,阿庆,你就把闰土留在这里,叫他哥儿俩多玩几天吧。你自己回去好了。”
阿庆:“那怎么行,又要给老爷、太太添麻烦了。到收租晒谷的时候,我再带他来玩么!”边说边拉着闰土走出门。
16.周宅门外
迅哥儿眼望着闰土随着他父亲阿庆出了门,走过石桥,上了船,远去了。
闰土回头看着迅哥儿,迅哥儿目不转睛地望着闰土,俩人恋恋不舍,依依惜别。
迅哥画外音:“后来,闰土还托他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回忆完)
17.周宅正厅堂
迅哥忙碌着打点行李。
周母从院子里边说边来到屋里:“迅儿,闰土来了。”
迅哥闻声,手里还拿着捆行李的绳子,站起来看时,不由地“啊”了一声,慌忙迎上前去。
闰土身材增加一倍,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戴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而是又粗又笨,开裂得像是松树皮了。
迅哥十分兴奋,但又不知怎么说才好,只是嗫嚅着说:“啊!闰土老弟……你来了。”
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闰土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分明地叫道:“老爷。”
迅哥打了一个寒噤,被捆行李的绳子绊了一脚,绳子牵动了打得半好不好的行李,那隔了一层又一层的行李外壳,抖动着,抖动着。
闰土回过头去,对身后一个小孩说:“水生,给老爷磕头。”说着,便拖出躲在身后的孩子来。
迅哥看着孩子,不由得一愣,这正是一个30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项圈罢了。
闰土喃喃地说:“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总是躲躲闪闪的……老爷别怪他!”
周母:“阿土!你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了。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吗?还是照旧,叫迅哥儿!”
“哎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
那孩子却是害羞,紧紧地只是贴在闰土背后。
周母:“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是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出去走走吧。”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拉水生,水生轻轻松松、爽爽快快地和宏儿一块出去了。
18.院子里
宏儿和水生手拉手,肩并肩,活蹦乱跳地穿过深邃的院子,来到百草园,爬着皂角树,戏游在井台石栏上。
宏儿:“咱们来捕鸟好吗?”
水生:“这不行!须大雪下了才好。在我们家沙地上,下了雪,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筛,撒下秕谷看麻雀来吃时,远远地将缚在棒子上的绳子一拉,那麻雀就罩在竹筛子下面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两人说笑着,戏游在当年迅哥儿和闰土雪天捕鸟的旧地方。
19.周宅正厅堂
周母:“来,阿土,不用客气,这里坐。”指着迅哥对面的一把椅子。
闰土迟疑了一下,终于就了座,将长烟管放在桌旁,递过一个纸包来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迅哥不好意思地说:“闰土老弟,别这样……家境日子过得还好吗?”
闰土吸着长烟管只是摇头:“难啊!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不够吃的……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一定的规矩,一会儿是这捐,一会儿是那税,没有个头……收成又不好。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好几回钱,总是折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唉!苛捐杂税,兵荒马乱……难啊!”
现如今的闰土,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木偶、石像一般。
随着闰土的话语,顺着闰土的长烟管,缕缕青烟,袅袅飘渺,依次出现如下画面:
含苞欲放的春天,一望无边的海滩沙地。
闰土、水生一家含辛茹苦,辛勤地劳作,播种收割。
大锅里有几片菜叶,被一个大勺搅动着,十几只小手,捧着空碗,眼睁睁地张着嘴。
炎热酷暑的夏天,沼泽泥泞的稻田,闰土、水生一家苦苦地劳作。
一声枪响,闰土被匪兵驱赶着。
闰土在匪兵的看押下挖战壕,筑堤坝,修作战工事……
丢在家里的孩子们鬼哭狼嚎。
昏黄暗淡的秋天,风吹树叶哗哗响。
闰土、水生,压弯了腰,将一口袋一口袋稻谷,朝地主的斗里倒了又倒。
地主的算盘啪啪作响,闰土一家人的眼泪,泪汪汪……
冰天雪地的冬天,冰凌倒挂满屋檐。
闰土、水生一家饥寒交迫地畏缩在一起。
闰土心灵手巧地,编织着各式各样的竹器,有竹篮、竹筐、竹篓,美观大方,结实耐用。闰土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被竹签扎破,鲜血直流。
闰土牵儿带女,肩挑背扛各种竹器沿街叫卖,所得钞票、铜钱寥寥无几。
坐在迅哥对面的闰土,吸着烟,诉述着,哭说着,两眼滞呆,呆若木偶,额头上的皱纹,一道比一道深,如果不是眼睛的转动,仿佛一尊泥塑、石像一般。
沉默了片刻,闰土便又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
周母拭了拭欲滴的眼泪,打破死一般的沉寂,说:“二三十年了,你们俩难得见一面,没几天我们就要走了,东西随你挑拣。”
“谢谢老太太。”闰土望了望迅哥,慢慢走出来,试着挑拣家具什物。
迅哥目送着动作迟缓的闰土,眼睛直盯盯地望着闰土放在桌子上的纸包。他打开纸包,干青豆化作颜色鲜艳的牡丹绢花,变成五光十色的贝壳……眼前呈现的是一个手捏一柄钢叉,英俊无比的少年闰土。
迅哥长吁短叹,惊异地大喝一声:“唉!”
20.周宅正厅堂
一声刺耳怪声怪调的大叫突然响起:“哈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
迅哥大大地吃了一惊,吓了一跳,赶忙抬起头。
一个凸颧骨,薄嘴唇,50上下的女人站在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迅哥愕然了。
“不认识了吗?我还抱过你呢!”那“圆规”抢白地说。
迅哥愈加愕然了。
周母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忘却了。你该记得吧,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还没等迅哥开口,杨二嫂冷笑着说:“这真是贵人眼高!”
“哪有这事……我……”迅哥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这些笨重的东西,又沉又笨,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迅哥说。
“哎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还说不阔?咳,什么都瞒不过我。”杨二嫂一个劲地说个没完。
迅哥呐呐地说:“放了道台……三房姨太太……八抬大轿……什么时候?”
“哎呀哎呀,真是愈有钱,便愈一毛不拔,愈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回转身,一面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说着慢慢地往外走,顺便将周母的一副棉手套塞在裤腰里,露出几个手指头出来了。走到院里,还弯腰朝旁边的一叠碗碟上,扬了厚厚的一层稻草灰,便无影无踪了。瞬间,又旋回来,扒开稻草灰,拿出碗碟,边扒边说,“你看闰土,把碗碟藏在灰底下,真是……”拿着几个碗碟就跑,她藏在屁股上的棉手套更明显地露出来,几个指头套不停地拍打着杨二嫂这个当年享有盛名的豆腐西施的大腚。
周母摇了摇头,叹息道:“这个杨二嫂,这些日子,三天两头地来回跑,不是拿这就是拿那,亏伊是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呢,竟跑得这样快。”
迅哥下意识地“嗯”了一下,陷入沉思。
迅哥画外音:“杨二嫂,豆腐西施,想当年,我是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擦着白粉,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随即出现如下画面:
21.豆腐作坊
“梆梆梆”,豆腐梆子响个不停。
周宅斜对门的豆腐西施作坊顾客盈门。
杨二嫂干净利落,或拐磨豆浆,或大锅煮豆浆,或点卤加石膏,或挤压豆浆成豆腐,样样会做,个个精通,尤其是那切白豆腐,称白豆腐,拿白豆腐,将白豆腐递给顾客的姿势,飘飘欲仙,妩媚动人,连同那细腻柔白的皮肤、大腚,着实招惹了不少是非。
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不时地对杨二嫂做着某种轻薄的举动和戏辱,拍打,抚摸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大屁股等。
22.周宅正厅堂
闰土虔诚地用手捧着一副香炉和烛台走来。
迅哥:“闰土老弟,这香炉和烛台……”
闰土:“我要!我要!我要等祭祖供神的时候用。我还挑了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杆抬称……还有那草木灰,做肥料用的,等你启程的时候,我用船来载去。”
迅哥:“老弟,随你的便就是了。”
闰土:“谢谢老爷!水生,过来给老爷磕头。”
水生像熟悉过来似的,从宏儿身边走过来,就要跪在地下磕头。
迅哥忙上前扶起水生,对闰土说:“怎么能这样!不能这样!我希望我们还是哥弟相称的好。”
23.绍兴河埠头
迅哥、周母、宏儿由新台门周宅走出。
迅哥回头望了又望,那黑黑的高台大门,那瓦楞上当风抖动着的断茎枯草。
迅哥走下河埠头台阶,跨上行船,站在船头。
迅哥画外音:“我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闰土和水生,站在另一只满载稻草灰的船头,向迅哥即将远去的小船挥手。
迅哥、周母、宏儿也站在船头,向即将远去的闰土和水生的小船挥手。
两只小船,渐渐远行,越距越远,越走越远,向相反的方向划去,逐渐消逝在水天相连的各自一方。
24.船上
迅哥的船在前行,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妆成了深黛颜色,涟涟退向船的后梢远去。
周母走进船舱。
宏儿和迅哥靠着船窗,望着外面模糊的风景。
宏儿:“大伯,我们向哪儿去?”
迅哥:“上北京。”
宏儿:“光坐船吗?”
迅哥:“先坐船,再坐火车。”
宏儿:“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迅哥:“回来?你怎么还没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哩……”宏儿瞪着两个大眼睛,痴痴地想了又想。
故乡绍兴的山山水水,早已远离得无影无踪。
寂静的夜幕渐渐降临,只有船底下流水哗哗作响。
迅哥心情沉重地披上长长的大黑围巾,独自走出船舱,伫立船头,迎着凛冽的朔风,远望着点点闪闪的渔火。
迅哥画外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代还是相见如故,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们,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是我们未经生活过的。”
出现如下画面:
安然熟睡的宏儿,甜蜜的笑脸,微笑的梦呓:“水生……水生……”
水生与他的力气极不相称地拼命地摇着橹,闰土痴呆像木偶似地机械地摇着橹……
月光如水,倾泄在满满的草木灰、抬称、香炉、烛台上。
朦胧中,展现在银幕上的是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石像般的闰土又化作当年手执钢叉的英俊少年,随着水纹的波动,少年英俊闰土的影子逐渐模糊,消失得无影无踪。
25.船上
迅哥矗立船头,航船在黑暗中激流勇进。
迅哥画外音:“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航船冲破弥满水草的河面,掀起层层波浪。
轰鸣高歌的火车奔驰而来。
银装素裹的北京,庄严雄伟的前门屹然耸立。
(剧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