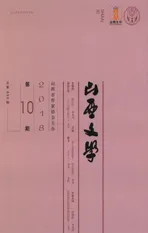波德莱尔的诗和他的形象
2018-11-13聂尔
聂 尔
有人曾不无夸张地说,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在其人生的某一阶段爱过波德莱尔;其中大多数的人,更是通过波德莱尔才走出了自己的童年。我的情况与此有若即若离地吻合。我是二十多岁才读到波德莱尔的。我把自己对波德莱尔的迷恋视为一种青春期病症,而病根儿正在于对行将隐没的童年乐园的返视,抑或是对未曾有过的童年的一种诗歌的补偿;也许在弗洛伊德主义者看来,还不无宽泛意义上的“恋母情结”。
波德莱尔给予了世界以性感。那远非我们的世界,但却可以对我们的世界进行象征,暗示和颠覆,因为我们的世界也同样有黄昏,女人,花朵,街道。在那里,色,香,味,触等各种感觉不再是飘忽不定的,而是经由波德莱尔式的奇妙手段得到了固定和延伸,成为了世界的性质和它的建筑材料;女人成为世界的神秘的中心——正如童年的我早已隐隐约约认识到的那样,女人不止是一种生物,她乃是一种创世的源起,如果我不能接近和进入她,我就永远不知这世界因何而起,永远是中心之外的一个过客,不能目睹和触及世界中心的壮丽辉煌,以及它那不可言说的质感和包容性,我就是悬挂在世界边缘的一个可怜的缺着一半灵魂的半生物。是波德莱尔,用一本书将“一朵奇花”似的世界中心推到我的面前,就像用一小块印度大麻就展示出了原本凝滞不动的物质世界生动的、华丽的、精神的节奏,并将我带入了其中。波德莱尔就这样将20多岁时的我带出了童年。那是一个幼稚的,躁动的,尚未确立感知方法的,在世界的门外玩泥巴的小巨人。他不知该将眼睛望向何处,手伸向何处,鼻子嗅往何处。此时,他终于凝定为一体,可以动用他的感知,为世界唤来春天了。
这就是波德莱尔之于我的意义。
我读的是钱春绮先生翻译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我通过《恶之花》而形成的对钱春绮先生的信任,亦兼及他翻译的歌德、尼采等。当我重新打开《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时,我发现这种重逢显然已经失去了初出“童年”时的新奇,憧憬,激动和浪漫之情,而多了几分审视,挑剔,求证,甚至沮丧的心情(对于此生终于不能学会法语,因而无法仔细求证的沮丧)。但我同时又发现,尽管难免挑剔,但我对译本可能的瑕疵却仿佛也同样地充满了爱意,就好像这个译本也有属于我的一份。这种感觉当然荒唐,荒谬,只宜于自己消除了事,而不必公布出来,但又觉得这是阅读的一个教训,亦不妨一说,以引起注意。
我后来又读到波氏的散文《人造天堂》《我心赤裸》和评论集《1846年的沙龙》。伴随我时间最早并且也是最久的一个版本,是一个64开袖珍版的《恶之花选》。这个“口袋书”是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者当然也是钱春绮先生。这个小书做得非常讲究,封面为塑封铜版纸,封面画是一幅叫做《镜前的妓女》的油画,画家为(法国)鲁奥,画风相当大胆——以80年代的标准看更是超乎大胆了。封面勒口简介中引用了兰波的名言:“波德莱尔是最初的洞察者,诗人中的王者,真正的神(上帝)”,——这段话在当时肯定震撼过我。
但我总是越过封面直接打开中间的某一首诗,比如《阳台》: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你赢得我的全部喜悦!全部敬意!
请你回想那些抚爱的优美温存,
那炉边的快慰,那些黄昏的魅力,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我是吟诵还是默诵这首诗——或袖珍本中的任何其他一首诗,当视时机而定。如果有我认为合适的伙伴在场,我是会念出声来的,但我的朗诵总是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总是被我的伙伴(们)无情地打断了。如果我想再朗诵另一首,比如《异国的清香》:
当我闭上双眼,在暖秋的晚上,
闻着你那温暖的乳房的香气,
我就看到有幸福的海岸浮起,
那儿闪耀着单调的太阳光芒;
结局仍是一样的,就是我的朗诵仍然会被打断,阻止,甚至被嘲笑。
所以,大部分时候我只有一个人独享我的波德莱尔。
我最喜爱的还有一首叫做《遨游》的,其开首是:
好孩子,小妹,
想想多甘美,
到那里跟你住在一起!
在那个像你
一样的国土里,
悠然相爱,相爱到老死!
阴沉的天上,
湿润的太阳,
对我的心有无限魅力,
多神秘,像你
不忠的眸子
透过泪水闪射出光辉。
那儿,只有美和秩序,
只有豪华、宁静、乐趣。
《阳台》中歌咏的女性为让娜·迪瓦尔。她是与波德莱尔相爱、同居时间最久的一位女性,她被认为是一个妓女,波德莱尔与她的爱情最终转化为夹杂着爱情回忆的慈悲之爱。上面所引第二首《异国的清香》,也是为让娜·迪瓦尔而作,但其中有对诗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旅行的回忆——这次旅行中所见到的热带风光成为波德莱尔诗中永恒的异国形象。“在暖秋的晚上”,“闻着你那温暖的乳房的香气”——诗人来到既是回忆又是幻想(亦即既是过去又是未来)的热带海岸;“你的香气领我到迷人的地方”——情人身上散发着的“香气”,成为此刻的、存在的、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导航。有意味的是,并非因为她的美丽,善良,贫穷,或者智慧,而是因为那股“香气”,诗人就得以遍游存在的家园。波德莱尔善用各种香气,香味,芳香,清香,发香,芬芳,来浸染、渲染他的不如意的悲惨的现实之“美”,“恶之花”。他甚至可以驾驭这气味,超越于现实之上,达到他本身的精神性。正如他在《头发》一诗中的供述:
像别人的精神飘在乐曲之上,
爱人啊,我的精神在你的发香上荡漾。
“别人的精神飘在乐曲之上”,是因为乐曲是抽象的,观念的,无形的,传统美的;“我的精神在你的发香上荡漾”,是因为发香是具体的,当下的,有形(味)的,驻留的,弥漫的,飘忽的。这是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区别之一,尽管波德莱尔并未明确反对过浪漫主义。
“芳香”在波德莱尔诗中的地位之高,还因为它具有感应(通感,联觉)的功能,而感应正是诗人将世界诗意地统一起来的最重要的美学手段。它是在浪漫主义之后,波德莱尔作为诗人,对观念的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并且他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他作有《感应》一诗,以表明他的美学思想,其中有对“芳香”的明确的赞颂:
有些芳香新鲜得像儿童肌肤一样,
柔和得像双簧管,绿油油像牧场,
仅此两行诗,就囊括了嗅觉,触觉,听觉和视觉的联通与互动。
在这里,波德莱尔越过了浪漫主义的界限,来到他所开拓出的新的领地,象征主义。
如果说浪漫主义是强烈,混沌,自然,高昂而又阔大的,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则是明确的,精细的,忧郁的,现代的,是城市的现代的自由人对于不断堕落的生活的一种目标确切的反对,一种诗意盎然的反对。他宣称他的理想是:
他能凌驾生活之上,不难听清
百花以及沉默的万物的语言!
——《高翔》
但是,这一与自然相关,以感应为通道的理想并未能够得到实现,反而只留下了忧郁;于是他到城市里去寻找,他发现城市是虚幻的;然后他到酒中寻找……;到同性恋等“恶”中去寻找……;到叛逆中去寻找……;最后来到死亡之地,他发现,只有死亡能治愈厌倦,无聊,时间的折磨等现代人的重大疾病。于是,波德莱尔唱道:
啊,死亡,啊,老船长,时间到了!快起锚!
我们已倦于此邦,啊,死亡!开船航行!
——《旅行》
只有死亡还是未知之国,在那里,还有“猎获新奇”的可能。
到此,《恶之花》全部的旅程告以完成。
这个“颓废者”,以诗意考察了一遍世界,最终宣布这个世界令人失望。不过,幸好还有死亡。深沉的死亡,是一道来自深渊的光,它已经在映照出“活的世界”的死之光影,已经催生出了一些“恶之花”,但它仍然有待于更加漫长,深入,具体的考察。
这就是《恶之花》。“恶之花”是失望,忧郁,探索和死亡之花。
波德莱尔本身是一个寓言和启示。他开启了他的直接的精神继承者兰波、马拉美的道路。得神启的青春的兰波,从开始就“凌驾生活之上”,听清了“百花以及沉默的万物的语言”,并且以“绝对现代”的步伐毫不迟疑地奔赴死亡,他大约是真的看见了死亡之地的“新奇”,急不可耐地前往猎获。马拉美则是营造出了更加精美的,人和自然丝丝入扣地相互感应的“神殿”。
但是,波德莱尔的形象却绝不只是一个诗人,正如兰波也不只是一个诗人一样。首先,波德莱尔显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更不可能是他的时代里、审讯他的法官们所指控的那种现实主义者——那时的现实主义者似乎指的是一种无神论的无所不为者;其次,波德莱尔是一个浪漫主义(就浪漫主义的原初意义而言)和社会主义者(最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正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社会性发展;他是一个无法治愈的造反者,一个与资产阶级的生活和道德势不两立的人。与他的同时代人福楼拜相同的是,他们都无法容忍资产阶级生活,甚至无法容忍任何一种有职业的生活,二者不同的是,波德莱尔更加躁进,更不安宁;如本雅明所指出,波德莱尔还是一个闲逛者,浪荡子,孤独者,但他的孤独必是人群里的孤独,城市里的孤独,必以妓女、乞丐、接近死亡者为自身灵魂的镜子和伴侣;他是一个印度大麻的吸食者,他所写的《人造天堂》是关于毒品对人类精神所发生影响的迄今为止最为精妙、细腻,最富想象力的散文作品;他还是一个梅毒患者,这一点亦与福楼拜相同,有人猜测正是因此,使得他们都绝对地成为了资产阶级家庭伦理的局外人——这一传统延伸至萨特,而萨特为他们二人都写了传记,并非偶然;最后,他还是一个美术鉴赏家、评论家,一个现代性的理论家,他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影响至今,绵延不绝。
波德莱尔是不朽的诗人,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七彩棱镜。他的诗歌和他的形象相互映射,能生产出更加丰富的含义,成为屹立更久的一则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