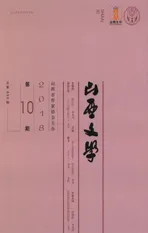【小对话】
2018-11-13
山西文学 2018年10期
唐晋:
为什么会有这一组诗?石头:
从《肉》之后的《随便诗》《无所诗》,再到2015年的《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应该让每一个汉字都要与内心“贴紧”,不能有“贴紧”之外的多余的汉字。这种“贴紧”关系的建立,不是单单依靠写作,而是重新生活,是重活,不单单是知,而是行,不单单是说,而是做。云南大山本身就是一个廓大且爽朗的意象,2016年有个机缘与几个朋友相会于山野,便写下了这首《云南朝山记》。唐晋:
《云南朝山记》一如你的当下的诗风,并且,在继续减降修辞意义的同时,更加突出强调文字的记录功能。这个并非由这首诗的题材决定,在所谓时间、地点、人物的具象罗列下,其实表现的仍然是个人“心念”、状态的记录。你对“当下”的注意力以及过后对这一“当下”记忆的反溯能力使得全诗成为一个比较浑然的“场”的集合,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你内心较为长久的一种稳定、平和。可以说,每一次出行,或者说每一首出行所得诗作的出现,都成为你对自身状态的及时捕捉。石头:
唐晋兄的解读非常到位,谢谢!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之后,我的重要作品都不在小意象、小修辞上着力,而是以一个“场”来呈现诗歌的基调,也可以说是以“气”来完成作品的构造。如何让写作成为自己的写作,而不是别人的写作,这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的“焦虑”,也是构建一个独特文本的出发点。如果不能打破现有的诗歌“规矩”,就无法深入无人之境。从目前我的写作方向来说,古代的山水诗、禅诗,当下那些从禅文化出发的书写,从禅意生发禅意的文字,大都因其不“近心”无法给我带来大喜悦。经常有人对我疑问,你焚烧自己的诗集,你行脚,你吃苦,是不是为了写作而做个样子,甚至作秀,我笑一笑。在最近的一个纪录短片里我回答说,我不管别人,对于我来说,如果不去走,不去行,不去吃苦,我觉得自己还无法贴近那些“未知之物”。唐晋:
朝山,这个“朝”说出了你的恭敬之心。我们知道你经常去朝台,在一种习惯里,朝台可能放大了人一生的“行进”过程,它使得行者更容易关注到自身,关注到自身与外界的关系。或许正是对这一“疏远”的享受和追求,人会发现自己的成长,正如里尔克描述过的。因此,“疏远”自然也成为你诗作的基本建构,除了我们已知的你对修辞的剔除之外,你还要在诗作中消除“诗意”,消除与阅读之间应具有的那种“温度联系”。就是说,你的诗作不负责“向外”,而更多地形成一种自适。石头:
每个人与外在事物之间都有一个“我见”,而大多数人会非常固执地、诚恳地认为这个“我见”是真实的。却不知道,在我们与外在事物之间还存在一个东西,就是“无明”,而后才是“我见”,也就是说“我见”是由“无明”决定的。我们大多数人习惯了向外张望,而忽略了对自身的关照,这便是问题所在。在自己没有弄明白自己之前,对外部的“我见”都是可疑的。自觉的人生就是做个清洁工,不断清扫自己的“无明”,我愿用一辈子打扫自己内心的垃圾。朝台也好,行脚也好,都是在清扫。我的写作也可以说是一个清洁工的写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唐晋兄提到的“疏远”,其实就是显发“本来面目”,这才是人的“正常”,人活着就应该这样。但我们现在往往把不正常当作正常,正常的事情却以为不正常,价值判断完全扭曲,问题的根源还是“无明”。不论是剔除修辞,还是消除诗意,主要是把诗直接写出来。这种“直指”的写作,与当下很多人“作为诗人的写作”是不一样的,我也一直警惕自己写那种“诗人之诗”。写对我来说是要还原为本能,我只写一种非写出来的诗,但写出即诗。唐晋:
记得在首届诗当代论坛上,我曾半开玩笑地说,石头从五台山下来去了崂山,是不是要学“穿墙术”,以解决目前创作中的困境,等等。当时我和你的观点冲突主要在于“修辞”。从我的角度,修辞是诗的基本属性,伴随着行吟诗人给听者以丰沛鲜活的想象,一定程度上消除着时间和空间距离。对我而言,很难想象一首诗脱离了修辞之后的样子究竟会有多么的理想。我承认你在剔除修辞方面的确获得了相对比较好的效果,但它几乎只适合一首,否则很难看到多首诗产生并表现出来的那种丰富性。也就是说,我认为你的剔除修辞在具体的文本上只具有某种“唯一性”,比如,如果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相比,《云南朝山记》基本上变化不大。石头:
呵呵,唐晋兄提到的“修辞”问题,可以用另一个词来置换,那就是“技巧”或者“技艺”。对那些过度修辞的诗歌,我内心一直拒绝。修辞是显化的、暴露的,而技艺不是。“技艺”是在“修辞”之后的打破和提升,是化“修辞”于无形。如果敞开来讲,这个问题比较大。我的写作是在写作过程中解决技巧问题,也可以说是让写作自身解决写作的技巧问题,让技巧自然地来,自然地呈现,就像呼吸一样。我曾提出一个“诗歌的临界点”概念,在这个临界点,不增加一点,也不减少一点,写出即是。其实,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之后,我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一种“气息结构”。诚如兄所言,这首诗因为在写作时间上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较近,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变化不大,但这只是表面的。因为很多技巧已经平常化,也一体化,并没有“暴露”出来。写作是有秘密的,这里我也没有必要老王卖瓜了。唐晋: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你最近几年的作品身上渐渐具备了一种“文献”的品质,它无疑是一种原生态的气息,但又有着无处不在的经验积累,甚至还包括写作者个人的体悟。如果想在这样的路子上走得很远,我觉得还需要减弱体现“行”的那部分,继而增强“要义”的容量。石头:
我的写作就是我的修行,不是表达,不是表现,也不是炫耀,而是“磨”。修行到哪里,便写到哪里。记得平兴寺延道法师说过一句,“走路不问路,走山不看山”,这句话可能能够表达我的写作。用写作来克服写作,用写作来消除写作,这大概就是我的轨迹。唐晋:
云南也是你的常驻之所,六大茶山那些大大小小的寨子几乎都被你踏遍。据我所知,你也有另外一些更宏大的创作构想与茶山有关。诗禅茶都是修行。朝台是一种方式,朝茶山是一种方式,所求不尽相同。但在有和无之间,你如何恒定自己的内心?石头:
我们常常把写作当作“另外一件事情”,甚至神圣化、道德化,好像写诗就高人一等,这很搞笑,这些都是名利之心在作怪。其实,写诗是平平常常的,喝茶是平平常常的,参禅也是平平常常的,都是一回事情。放下名利之后,对于我,五十岁即是新生,这样算来今年我刚刚一岁多。五十岁已经归零,现在不论什么事情,常常会有一种新鲜之美。五台山也好,太姥山也好,鸡足山也好,鹅屋大山也好,古六大茶山也好,在它们面前,我只有一颗恭敬之心,没有多余之心。唐晋:
记得你曾经提出诗思考十条:“1.‘我如何在’,这一直是诗歌中的核心问题;2.不论是冷抒情,还是热抒情,以及事实的诗意,等等说法,最后都要回到这个问题上;3.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几人称,最终还是这个问题;4.首要的是‘我’有多大,‘我’有还是没有;5.接下来是‘如何在’,这必然指向语言;6.对诗歌异质的追求,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7.没有独异性的诗歌写作,都是无效写作;8.写着写着,就什么也没有了;9.写出一种什么也没有的诗;10.一种有却没有的诗。”你的诗作实践基本上遵循着你的思考前行。对于后面三条,我觉得更接近佛学概念。写作,特别是诗的写作,几乎是一生力量的集聚与耗散。佛讲圆融,诗人可能更渴望一种大成现实,这其实是两个方向,或者说是两种人生。圆融意味着去执,这一点,诗就是执和我执。石头:
佛法也好,诗法也好,没有二法,这要看在什么层面去讨论。在低层面上,它们好像是分开的,但到最高层面却是无二的。前面我讲过,我的写作就是我的修行,修行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你说的圆融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真正达到了无我。达到了无我,什么我执、法执便自行脱落,这很难。我一直敬重王维,王维诗歌的高度不是写出来的高度,而是修行的高度,其诗歌背后这个巨大的支撑却被多数人忽略。很多人写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套,耍聪明,耍滑头,这样的写作可能貌似很美,却是我拒绝的。古人的那种苍莽之气,在我们这里已经衰微了,但我不甘心。任何形式的取巧,都过不了内心这一关,我愿意像古人那样重活、重写。唐晋:
……有时候想,这个石头在云南待那么久了,还不回来?有时候想,这个石头还不去云南?呵呵……石头:
云南地处边远,存活着蛮荒气息,那里还有很多古人出没,我去云南就是去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