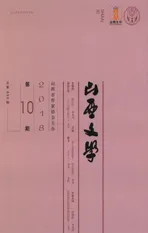悦芳:白昼被取走之后
2018-11-13王朝军
王朝军
热烘烘的夜飞翔着泪珠
毫无人性的器皿使空气变冷
死亡盖着我……
白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现在被取走
我一直认为,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的人格相互联系,相互印证,乃至相互确认。在这几年对悦芳的诗的持续关注中,我也同样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我再次坐下来想为悦芳的诗写点什么的时候,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翟永明1984年在《女人》组诗中被命名为《生命》的那一首诗的句子。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冥冥之中的召唤,让悦芳这个经历过“白昼”曾施予其苦难和痛彻的诗人,在“夜”的暗处找到了有别于“白昼”的世界,找到了一种独属于她的诗歌母题。
这个母题可能在她初起的诗歌写作中,并没有被明确地定义,但伴随着她诗艺的成熟和对诗歌创作及理解的深入,这个母题越来越清晰和表征化。尽管在她的诗歌中仍然可以看到某种反复和沉浮,但我越来越感觉到,那种命定的安排让她走上了“无所适从”的适从,“无所依托”的依托。看起来悖反的两种状态,恰如“白夜”一样,在分裂和抵牾中走向了统一,从而生出了新的意义。我将其称之为“边缘意识”。时刻为边缘而恐惧,又为能在边缘处舞蹈而感到确幸和获得少许的满足感。
所以,悦芳的诗便在这种“边缘意识”的统摄下,走出了同质化写作的陷阱,变得有棱角和皱褶起来。
孤独抒情者的灵魂“出轨”
孤独,是悦芳的诗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在阅读悦芳众多诗作后的普遍感受。诗人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化写作,孤独情感的流露再自然不过,所谓黯然神伤,很多时候无来由,也无须过多地酝酿和铺垫,往往就是那么一瞬间便会莅临。因而,像“疼痛”“怜悯”“命运”“寂寞”等类似的词语在悦芳的诗中很常见,有时候在一首诗中会反复出现。比如《断章》:
不谈论爱情的夜晚
注定是孤独的
我甘愿承受
这安静下来的孤独
很多谎言挤进来
又被关在门外
拥挤的世界
今晚变得寂寥
“注定是孤独的”“这安静下来的孤独”“今晚变得寂寥”。如此高频率的书写孤独,甚至是渲染,在新诗发展至今天的时代语境下,已不能说是一种成熟的诗歌形态。诗人在意图以“孤独”语词强调孤独本身时,也弱化了诗歌的表达力度。但在这种看似落后于时代的笨拙形态中,却让我看到了诗人向内心挖掘和延伸所做出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是与极力逃脱既有经验世界的桎梏和急于重塑主观世界分不开的。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重新安排内心的秩序”。所以才有了让
我们为之怦然心动的另一句诗:
用冷色调的唇,吃掉
整个季节的忧伤
(《我囚禁在我的身体里》)
尽管这里也有“忧伤”,但已不是简单的述说或者重复,它被赋予了身为女性的独特的隐秘体验,这是一种自发的乃至自觉的心灵沉潜,是绝大的忧伤之后的绝大爆发。具象化的语词背后涵纳的是诗人与整个经验世界“决裂”的野心,是灵魂风暴席卷而来的“出轨”冲动,但也是“出轨”后重新整合与确认生命世界的无语凝噎。
温润意象的情境再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象是诗歌的生命。没有意象,便没有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最基本要素。即便是被人们所熟知的北岛的那首著名的《生活》,虽仅有一字,但那个“网”字及其留下的无边的空白,也还是以“网”作为意象的中心。
悦芳诗歌自有其意象建构,且她笔下的意象,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温润。这关系到悦芳抒情诗的色调,也关系到悦芳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虽然她在诗中时刻以“白昼被取走之后”的独行者自居,表现出一种裂帛式的决绝态度,但在内心深处,她依旧给世界厘定了温润的底色。这并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善良和温柔的本性决定的,甚至我以为,这和她的母性本能息息相关。因此,在她的诗歌中,意象的选择并非最有力的支撑,而是吸附意象的情感。这也是我为什么把悦芳的诗归属于抒情诗范畴的原因所在。
“杨柳”“体温”“浅草”“睫毛”“拥抱”“曳动”……这些词所焕发出来的无不是光泽和美丽,它们本身的质性与诗人的主观情感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让她的诗产生了相应的张力和弹性,由此,在“边缘意识”的驱动下,展拓了诗意。
悦芳对诗意的展拓是小桥流水式的,是徐徐缓流的,前后很少见兀然的转折,像一种“精神绕指柔”,多了一层《诗经》式的回环往复,多了一点古典式的婉约。这让我们在阅读其诗歌时,无须太过注意诗歌结构的营造,而是循着诗人情感的流淌渐入佳境。
或许正因为此,悦芳特别注意将瞬时的细腻感受予以情境化和具象化。比如《旧日》组诗中的一首:
我从树林走过
常常听见自己的咳嗽声
每一种咳嗽,都有树叶飘落
药片一样,嵌入时间的
裂痕之中
咳嗽声作为常见的意象,被诗人主观情感化,从而在具象的意义上得到了情境的延伸,“每一种咳嗽,都有树叶飘落”;又在想象的空间中添加了新的意涵,“药片一样”;最终在情感的向度上形成了突变,“嵌入时间的/裂痕之中”。
诗意的层层递进,最终让悦芳的诗常常在结尾处闪现出光华,于不经意间通达庸常所忽视的发现。比如《镜中的花朵》那最末两句:“一些静止的皱褶/赤裸,真实,充满欲望”。皱褶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皱褶本身,也看到了诗人的心境,看到了一个裸露的毫不掩饰重重欲望的真实生命。
“白昼被取走之后”的夜之光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斯有一种“一次性诗人”理论,大意是说那种将生命人格与诗歌完全、彻底地合而为一的诗人,例如荷尔德林、海子等等。其实,我认为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有这种涅槃冲动,是否以肉体的毁灭为代价暂且不论,但总要有经历一种灵魂的死而复生的洗礼吧。我想,悦芳应是有的,但在这场洗礼的过程中,她可能尚有更为彻底的空间。我这里说的诗境。就是说悦芳的诗境或许可以再阔大一些,无论是意象意绪或语言,都可以找到更具有陌生化和独特性的所在。
须知,个人化的表达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个人经验或情感的表达。同理,诗境的扩大也并不意味着单纯地走向外部时空,或人们所担心的“丢弃灵魂”,而是为了更尖锐地、直接地、从容地回到内心,回到个人。
唯此,这场灵魂的博弈才会在“白昼被取走之后”,获得夜的光和永恒。才会像悦芳在《末日之诗》中所言:
在炫目的光晕里
互为灰烬
在无限的蔚蓝里,成为
蔚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