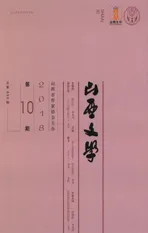猥精(外二篇)
2018-11-13何亦聪
何亦聪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的家乡曾兴起过一阵吃刺猬的风气,其烹制方法以油炸、炙烤为主,一时间周围各区县的食客蜂拥而至,街边的饭馆子门口,都可见到剥下来的刺猬皮。当时人们也没有什么动物保护的意识,吃刺猬无非图个新奇罢了,据一位吃过几次的食客讲,猬肉甚肥,因为其本身有股子腥气,所以烹制之时不厌厚味,以油炸加椒盐辣子为上品,以清汤炖煮为下品。这阵风气大约持续了有半年之久,便迅速消歇下来,猬肉一物,就此无人问津。据我想,可能还是口感欠佳的缘故,然而有好事者散布一些无稽之谈,如说某豪客驱车到一个饭馆子吃炸猬肉,返途中车胎竟全部爆掉;又如说某少年吃了猬肉之后颔下竟生出骨刺来。北方民间本有“四大仙”的说法,指的是四种有灵性的动物:狐狸、蛇、刺猬、黄鼠狼。
古人小说中多记狐仙、狐精之事,关于刺猬的故事却甚少见,大概是因为这种动物多少显得不大“风流”,难以寄托“艳事”。闲斋氏《夜谭随录》中曾记有发生在昌邑的一件怪事:当地正值割麦的前夕,为防偷窃,农民都在田间搭上芦棚,让自家子弟夜宿其中,乃至有“连棚十余”的盛况。有一位姓余的少年,大约是家里田地较偏僻,又或者是心性孤独,“独卧一棚”,不与其他人交接,后来住了没多久,便渐渐消瘦,显出病态,父兄垂问,也只支支吾吾,不以实告。众人讶异,遂暗中观察。薄暮时分,便见一丑女人进了这少年的芦棚,乡人荷锄追赶,只见此女“面色如瓦兽,巨目大口,蹀躞而行”,追了足有二里地,于乱草中发现一个黝黑巨大的洞穴,众人不敢进,只在洞口烧烟熏烤,熏得此女出洞,“勉行数十步,即不复动”,凑近观察,“则一猬死田间耳”,其怪遂绝。事后乡人皆释然,独有这位余姓少年哭泣不已,“以为磔其丽人也”。
狐狸成精后便可化作美女,刺猬成精后却只能是丑女人,何其不公平尔!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若将故事中的猬精换作狐精,或许故事本身就会变成一场爱情悲剧吧,惟因主角容貌丑陋之故,便传为笑谈,可见人类的“颜控”本性,是自古而然的。然则那位孤独的乡间少年的心事,终究只能丢弃在田野风中了。昔日宋高宗乐闻鬼神之事,郭彖撰《睽车志》一书以逢迎,其中也有记猬精的一则故事,该猬却作老叟状:姚安礼暮宿驿馆,因暑热难眠,于深夜独自起来散步,忽闻庭院中传来簌簌声音,透过屏风的缝隙窥视,只见一个尺许长的老叟,身着白衣,顶冠策杖,缓缓而行,“仰自视月,以手加额”。姚拔剑追逐,这老叟却凭空消失了,他便插剑于其消失的地方,次日令仆人在插剑处挖掘,“得一白猬甚大,旁有故铁托火箸各一,盖其冠杖也,乃杀之。”古人多视精怪为异类,不问情由便要“杀之”,未免有些寡趣,在这方面,还是蒲松龄的态度更可爱些。
天津旧时关于猬精的传闻最多,光绪年间有一位名叫李庆辰的天津文人,写有《醉茶志怪》一书,此书虽不能脱纪昀一路因果劝惩的老套,更兼作者好发议论,动辄纵论是非祸福,很煞风景,但记猬精故事却最详,其中有云:“予乡有供五仙像者,其神为胡、黄、白、柳、灰。胡,狐也;黄,黄鼠也;白,猬也;柳,蛇也;灰,鼠也。”又云:“乡愚陋习,呼蛇为柳,猬为白,相沿已久。”另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天津有所谓姑娘子者,女巫也。乡间妇女有病,辄使治之。巫至,炷香于炉,口不知何语,遂称神降其身,是谓顶神。所顶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猬也”。鲁西一带过去也有“白老太太”的传说,由此可知其真实身份即是猬精。又如“猬火”一则,写李氏家祠夜间的异象:“一老猬立墀下,高于三岁童子,口中喃喃作人语,其双目放光类炬然。”更为奇特的是“白郎”的故事:天津有户人家,某日在腌咸菜的大瓮旁发现了一只硕大的白色刺猬,男主人想要将刺猬杀掉,被其妇劝止了。入夜后,此妇一人躺在床上睡觉,似梦非梦间,见一美少年入内,穿着褐色的袍服,周身都垂着穗子,仿佛蓑衣。这少年自称白郎,对妇人表示感恩之意,后来语涉调谑,妇人为术所制,不能动弹,只得由他放肆。如此一来二去,妇人怀了孩子,然而腹中如有万千钢针攒刺,剧痛难忍,后来家人虽延请法师驱邪,仍不能救,终于“气绝于室”。此事说来甚惨,作者的评论是“妇人之仁,往往害事”,实在不大高明。李庆辰还曾评点过《红楼梦》,见解也往往褊狭肤浅,如说:“袭人是假正经,宝钗是假道学,二人可称知己”,其胸襟见识,由此可知。
华北乡间有些地方视刺猬为财神,农家院落中种满瓜果菜蔬,如有刺猬出现,则以为福兆,往往任其行动,禁止孩子们捕捉或打杀。陈恒庆记北京旧俗,说李铁拐斜街有一家名万源堂的饭庄,生意极好,财源广进,甚至得到了为皇室供应饭食的专差。其所以如此,是因饭庄老板在后房中蓄养了几十头刺猬,后来老板病故,子弟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刺猬们遂于一夜间自行迁徙他处,不知所踪,万源堂的家业便就此败落了。查北京在同光年间似确有一家“万源堂”,这桩怪事或是其后人在家败之后为免讥嘲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亦未可知。说到底,在中国,一切精灵鬼怪、奇闻异趣的背后,都是人情世故,即便在故事中,也很难找到那种纯粹的、对于世间万物的好奇,而这一点,或许才是最令人气沮的吧。
萧萧白杨
幼年长居鲁西、豫北一带,当地最多白杨树。乡间自不必说,即在城市里,街道旁也往往种着两排白杨——现在自然不同,稍繁华些的街道,都种上了法桐之类较昂贵的树木。白杨木虽质地松软,容易变形,但到底木材易得,且便宜轻巧,所以乡人多视白杨为恩树。有些学校不能备统一的课桌、板凳,贫寒人家的子弟便取杨木为材料自行打造桌凳,纵然质量不怎么坚实,倒也能勉强用上三五年。梁山、东平诸县的顽劣少年,大都崇拜水浒人物,生性好武,旧日里百物不齐,玩具之类更是罕见,乡民也是用杨木为材制成玩具刀枪,或为长矛,或为偃月刀,或为方天画戟,供孩子们玩耍。后来我到苏州求学,当地植物繁茂、树木葱郁,却绝少白杨树的踪影,心中颇感讶异。读苏州人刘昌所撰的《县笥琐探摘抄》,其中有云:“予初不识白杨,及来河南巡行郡邑,尝出北邙,经平畴入山谷,见丘冢间多大树,问从者,曰白杨也。乃悟古人哀捝用此不为无谓,东南丘垅多植松柏,故人歹不识白杨。”刘昌是明正统年间进士,曾在南京做工部主事,后调河南任提学副使,大约在去河南赴任之前,从未到过北方,致有如此感慨,由此亦可见南方本就少有白杨。
近人多有礼赞白杨者,但我不喜以物寄托人事,因此并不想写一篇新的礼赞。由于杨絮扰人,白杨在许多地方被视为害树,不过杨树株分雌雄,雌树生杨絮,雄树生一种外形极似毛毛虫的东西,鲁西人称之为“杨巴狗”。“杨巴狗”虽形貌丑陋,但不致影响人的生活,所以城市里栽种白杨,以雄树为上。据说华北某市当年栽白杨为行道树,一时疏忽,竟误雌为雄,忽忽数载之后,每到阳春时节,便见杨絮漫天,街边墙角,竟能积絮盈尺,闹了不小的笑话。白杨在旧时常作墓树,寓意不祥,且更是鬼狐志怪小说中的常客。黄公度所谓的“白杨衰草露沾衣”,到底也不是什么好景致。据说王荆公离世前一年,曾有一个蓬头青衣的仆人手持一块白杨木做的笏板以献,外面裹着青布,当时荆公甚感烦恶,将笏板扔到了地上。笏板是大臣上朝所执之物,向来用玉、象牙或竹片制作,断无用白杨木之理,故此事听来十分怪异,仿佛一种死亡的预兆。北方村谚有“院中不栽鬼拍手”之谓,鬼拍手即是白杨树,吾乡人既习见此树,倒也并不在意其寓意如何。鲁西乡民院落大者,往往会栽种上一两棵白杨树,可以遮荫纳凉,只是白杨的树枝有股异味,取为烧烤用的炭火之材却是大不相宜。
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又云:“青山衔落日,白杨吐悲风。”。其实杨风萧萧如雨,倒是最有情趣的。谢在杭《五杂俎》中记有这样一件事:“予一日宿邹县驿馆中,甫就枕即闻雨声,竟夕不绝,侍儿曰,雨矣。予讶之曰,岂有竟夜雨而无檐溜者?质明视之,乃青杨树也。南方绝无此树。”青杨即是白杨,谢氏是福州人,没有见过白杨树很正常,而邹县距我家乡不过百余里,植被、口音都极相近,因此,对于谢在杭这段经历,着实感到亲切。我少年时住处附近多栽杨树,夏秋时节深夜读书,常听得外面淅淅沥沥,以为雨下,推窗看时,却只见月色下一排高大树影摇摆于风中。某夜读《聊斋志异》至“连锁”一篇,其首云:“杨于畏移居泗水之滨,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虽知随后必有鬼狐之事,但竟为此种情境所浸染,不胜心向往之,颇欲于将来财力充足时筑书室于旷野白杨林畔,如今时过境迁,世路苍茫,当年筑室的梦想仅留存了一个影子,只是既已移居到城市里的高楼中,再要听那萧萧如雨的杨风,怕是不易了。
世味
初次见到“世味”这个词,自然是在陆游那首著名的《临安春雨初霁》中,“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当时不过十岁,只是不解:“世味”究竟是种什么味?何以径用一个“薄”字来形容?脑中浮现的却是一碗白开水,世间滋味,若论淡薄,大约无过于白开水了。后来读诗渐多,乃知古人亦有“世味薄于水”之句,幼时的想象,倒也不算离谱。
宋人写诗喜言“世味”,只是一旦形诸笔下,便常带几分黯淡,薄于水或淡如水自不必说,其他如春酒淡、和蜡嚼、回橄榄、蔗滓残等形容,读之也不免令人意兴阑珊。更有用辞蛮狠的,如戴剡源,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乡心几夜马生角,世味一时龟脱筒。”所谓“马生角”,用的是燕太子丹的典故,当初太子丹被秦王囚禁,请求放还,秦王有言:“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这里用此典,意思是思乡心切却归去无望;至于“龟脱筒”,即如一只乌龟生生被剥去甲壳,世味如此,其痛可知。剡源是宋末进士,宋亡之后,本有遗民志向,辗转求生二十多年之后,终于仕元,做了信州路的儒学教授。这只是一个九品微末小吏,所以全祖望讥讽他“执德不固”,“以薄禄竟受教授之官”,话里话外,都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意思。
究竟戴剡源为什么要暮年出仕?这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若说是为了求功名,九品的官职压根算不上什么功名,更何况他是进士出身;若说是为了 “隐于教业”,则之前二十多年的挣扎、纠结,如此一朝了却,又未免太轻飘飘了。在读《剡源集》的时候,我常想,人生恐怕很难用牌局来形容,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可能。对于遗民而言,鼎革巨变,天翻地覆,固然是惨烈的经历,但更痛苦的却是,在鼎革翻覆之后,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并且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所有重回旧时光的愿望都如“马生角”一般,绝不会变为现实。或许这种仿佛“钝刀割肉”的痛感,才是“世味”的真髓吧。
剡源诗里真正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那些关于遗民生计的句子,在粗粝的现实生活面前,这些句子已全无艺术的光滑润泽之感。比如他入山采藤,以所采之藤换粮充饥,如同小商贩般精于算计:“须臾叩门来海贾,大藤换粮论斛数。小藤输市亦值钱,籴得官粳甜胜乳。”又如他诗歌中屡屡出现一个“饱”字,“为农倘可饱,何用出柴关”,“客来问计何所出,一饱自悬饘粥外”,“脱身得一饱,激烈陈歌诗”,“诗文虽满家,不饱妻子腹”,“明朝满意作晨炊,饱饭入山须晚归”……这般絮絮于饥饱,其时时为果腹而烦忧的窘态亦不难揣想。那么,为什么这位堂堂进士会“以薄禄竟受教授之官”呢?答案似乎也隐隐约约与此有关——你眼中的“薄禄”,在别人看来未必就“薄”。世间道理,常常抗不过“穷怕了”三个字。
魏晋六朝诗人似乎没有用“世味”这个词的,哪怕到了唐朝,也十分稀见,可以举出的,只有韩愈的一句“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连”,以及诗僧贯休的“迂谈无世味,夜深山木僵”。与宋人不同,唐代的诗人大都有两个世界,一个在此岸,一个在彼岸;一个在儒学,一个在僧道;一个在都市,一个在山林——这就是他们的幸福之处,于他们而言,生活不是无可闪避的,人生总是有另一种备用选择的,过得不开心,大不了到山里去,到寺庙、道观里去。“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也是一种活法。怕就怕世味如霾,逃无可逃,呼吸之间,烟尘满鼻,最后终于变得麻木,也就只能“心谙世味冷于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