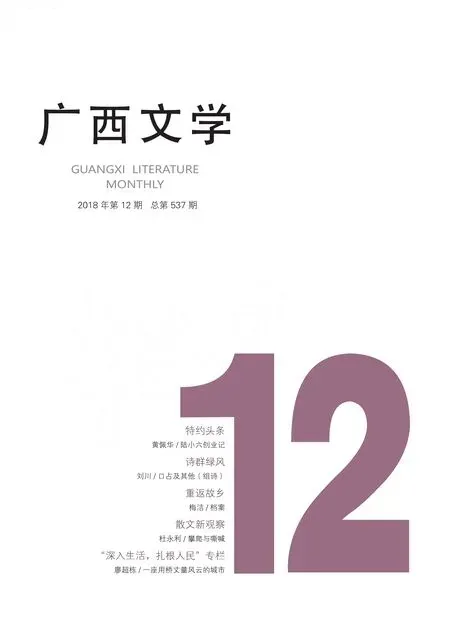远 方
2018-11-12红日
红 日
革命老区东兰县有一种精神叫牺牲,还有一种精神叫奉献。
——题记
河水涨起来了,果然涨起来了。这些日子以来,有一只大喇叭不断地吆喝河水要涨了,河水要涨了。这回真的涨了,看来大喇叭和天象早就有了沟通。浑浊的河水像晒谷坪上的捆席,缓缓地向前铺展。捆席属于小家子气,是小农经济的格局。河水财大气粗,是铺天盖地而来,压倒一切地来。不到一支烟工夫,河堤上凸立的那棵大榕树,眼看就要被河水吞噬了。那是一棵神树,库底清理时没人敢动斧头。水不是从上游而是从下游涨起来的,是被下游电站大坝拦回来的水,官话叫回水。回水改变了河流的身份,河流摇身一变成了湖。河流向来喧闹,湖是沉默的,哑巴一样。
十余辆大货车和十余辆大巴车从村口一溜排开,大货车装满了各家各户的家当以及牲畜,十余部大巴车正在等人。大喇叭像车站的播音员不停地催促:大伙抓紧时间上车了,车队马上就要出发了。这一天是公元1992年2月18日,农历壬申年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发车的地点是东兰县大同乡河龙村,目的地或者终点站是三百公里外的宾阳县黎塘镇,具体一点是广西第二劳教所监区所在地。当然,即将出发的这二百多号人不是犯人,他们是岩滩水电站库区的移民。他们当然不是去服刑,而是迁徙到易地安置点去重建家园,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六十三年前,东兰的几千农家弟子也是这样走上百色起义的战场。
离乡的脚步是沉重而缓慢的,何况是背井离乡。人们每抬起一步,需要连根拔起,因为每一个人的脚板长满了根须。根须深深地扎在故乡的每一座山、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条溪流。当年,为了翻身求解放、当家做主人,几千弟子毅然走上战场,舍生取义。今天,国家建设需要他们搬迁、移民,需要他们抛弃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他们需要顾全大局,需要舍小家为大家。这是大道理,大道理谁都懂,还是讲点具体的,具体的情形是:岩滩水电站下闸蓄水后,河龙村的群众有的需要迁移到山顶、坡顶上去,术语叫后靠,群众戏称“赶猴子上山”(1992年正是农历猴年);有的群众需要迁往陌生他乡,在另一片一无所知的土地上重建家园。这二百多号人属于后者。
有谁心甘情愿放弃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纵然故乡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有谁愿意带着迷惘踏上陌生的旅途?纵然远方无比令人神往,答案是,没有!一个也没有。
牲畜也不愿意,它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或许比人类还要深沉。开始任人怎么拉扯,牲畜们始终岿然不动。后来被强行拉到大货车上后,它们就齐声地集体呼唤,从昨夜一直呼唤到现在,似乎还要沿途呼唤下去。牲畜中公牛应该是比较坚强的,它们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却是“妈呀”“妈呀”。牲畜们是在倾诉或者追忆似水年华。
车子缓缓地启动,所有的目光投到窗外,即将成为故乡的家园面目全非,搬迁户的房子全打下来了,满目一片断壁残垣。那一刻,车上的人儿泪如倾盆雨,将故乡浸泡,整条河流或者整面湖水被泪水淋湿了。
这一天自然是吉日,吉日还需要良辰。良辰也是选好了的,但良辰延误了车队出发的时间,聪明的领队在时间节点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以致整个搬迁队伍按照良辰出发连续颠簸十多个钟头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抵达安置点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多钟。良辰往往是现在时,而不是将来时;良辰有时候只是一厢情愿,刚性的现实常常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
偌大的一个场院只见到隐隐约约的灯光,根本看不清安置点四周的情况。这天不是正月十五吗?可天上的月亮一点面子也不给,保持中立或者回避一边去了。当然,这个时间节点也有好的一面,美国卫星拍不到,不然以为我们的军队在集结。
天黑只是麻烦之一,整个车队停到安置点的时候,更大的麻烦发生了。广袤的平原地区天气说变就变,白天还阳光明媚,到了夜晚,骤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移民们没来得及下车,一个个惊雷就在车棚顶轰然炸响,伴随着张牙舞爪的闪光,啪的一声,又啪的一声。河龙村人从未听过如此尖厉的春雷、霹雳惊雷。这不是说河龙村人没听过春雷或者说河龙村的天空没响过春雷,以前河龙村的春雷只是提示性的鸣响,近似于钟声,提醒村人春播的季节到了,该耕耘了,该播种了。眼下的惊雷炸得耳膜剧痛,心里发骇。炸与响,是两种不同的分贝,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时间,大伙抱成一团,哭声水一般荡漾开来。突然,安置点停电了,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
领队走下车来,命令乡干部打着手电筒,带领各自负责照顾的移民户去找自家的房间。然而,哪里还弄得清楚哪个房间是哪户移民的——狂风暴雨早已把门上粘贴的纸片冲刷得无影无踪。房门钥匙也搞乱了,一把钥匙开不了一把锁。情势紧急,领队当机立断,命令干部破门而入,然后将移民从大巴车上引导下来,住进房间里去。大雨下个不停,床上用品一样也没能搬下车来。二百多号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身披淋湿的衣服,在电闪雷鸣的寒冷春夜挨到天明,度过移民生涯中惊魂落魄的初夜。
次日一早,太阳出来了。
温暖的阳光洒在凤凰岭上,照在高墙内的平房上,透过树叶、窗户照进移民们昨夜来不及审视的房屋内。昨夜的大雨把打前站的人苦心粉刷的墙壁“出卖”了,那些警示标语漏出来了,在阳光下闪着森严的光泽。院墙上还来不及撤下的铁丝网,还有高墙那边传来队伍集合报数的声音,一下子把惊魂未定的移民们再一次抛进旋涡。人们陆陆续续从房间里出来,惊奇地探视自己的新家。突然,有人喊道:你们快看呀,墙上有铁丝网,那边还有警察,还有犯人,这哪里是移民点?他们把我们关进劳改场来了。
没错!这里原来确实是个劳改场,但现在它确实是个移民安置点。
这个即将搬迁完毕的广西第二劳教所监区所在地,已由东兰县移民局出资七千多万元购买下来。这里所有的土地,将用来安置东兰县大同、长乐、三石等三个乡镇一千多个移民。打前站的人当初来到这里,劳教所还没有完全撤离,当然现在也还没有全部撤离。高墙、铁门、铁窗、铁丝网都还在,部分狱警和劳教人员也还在,院墙上的警示标语赫然醒目,这是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打前站的人临时对安置点的平房进行了粉刷,用石灰水将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标语覆盖起来。这些用高质量油漆喷涂上去的警示标语,哪是渗水了的石灰所能掩盖的?沐浴雨水之后,标语又英姿勃发了。
我要回家!我要回东兰!
一个妇女喊道。
妇女喊出了移民们共同的心声,于是二百多号人纷纷拥上了大巴车,叫司机把车子开回东兰。
司机都是东兰籍的,见移民拥上车子,也就纷纷启动了马达。昨夜大雨,家当没卸,只要车子一走,移民们又返回到河龙了。可是河龙已不是他们的河龙,是岩滩公司的河龙了。最关键的是河龙已经不存在了,河龙已经在水底下了,或者说河龙只是一面湖水。
大喇叭响起来:乡亲们!这里是劳教所没有错,但这个劳教所不久就全部搬走了,东兰移民局已经把这里的土地全部买下来了,从此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园了。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来不及清理房间,只好把空出来的宿舍打扫临时给大家暂时居住,等安顿好了,我们就选房基起楼房。大伙要冷静,不要冲动,说走就走,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东兰那边已经没有家了,河水已经涨起来了,你们回去,也没有地方住了。你们看看这一大片平坦的地方,土地广袤肥沃,自然资源丰富,比老家东兰还好,比我们大同还好,比我们河龙还好!你们要相信政府,政府是不会欺骗群众的,政府什么时候欺骗过群众!大伙先安顿好,再过几天,我们就分田分地,种桑养蚕,种甘蔗赚大钱,大伙的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移民的生活很快就会富起来。
大喇叭就是领队。
听领队这么一广播,大伙的情绪稍微稳定。人们陆续从车上下来,发动机也熄了火。移民们是答应留下了,但谁也不愿住进那些“牢房”。他们的家当从车上卸下来了,卸到了树下,却个个哭丧着脸,呆坐在各自的家当上,闷声抽烟或者默不作声。
双方僵持着。
有干部急了,问领队:咋办?
领队胸有成竹地说:天公会帮我们的忙。
远方的天际已生成一片乌云,并逐渐生动起来,仿佛一张哭丧的脸随时声泪俱下。
领队望着那片云团说:雨从那边过来了。
所有目光投向天空,随着那片云团移动。突然,一个移民鬼拉神拽地站了起来,把自家祖宗的牌位恭恭敬敬地捧在胸前。接着第二个、第三个,陆陆续续地站了起来,四十余户移民全部站了起来。表面上看,移民在跟乡干部僵持,其实是跟雨僵持,或者说跟自然界僵持。活人可以淋雨,祖宗的牌位是绝对不能淋雨的。雨一来,移民就妥协了,僵持也就结束了。雨是乡干部和移民们共同的台阶。这时,高墙那边传来声音: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1、2、3、4、5……
领队于是发出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目标宿舍——跑步走!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也必须这样开始。树挪死,人挪活。当今树挪了不仅不会死,而且活得比原来还要鲜活茂盛。人自然比树还要出彩,不然就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语了。每天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高墙那边的人集合队伍报数的时候,大院内的河龙村人也在集合队伍报数,他们每天集体出去种甘蔗,甘蔗是他们在安置点的重要产业。他们在老家是单干,现在是大集体一起干。——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放出万丈光芒……河龙村人每天集合报数后,就唱着这首歌走向甘蔗地,走向希望的田野,走向新的生活。渐渐的河龙村人达成一个共识:故乡无处不在,就像天上的太阳,只要天晴,抬头就能看到。他们已经适应了高墙那边的存在,那是一种遥相呼应的存在,仿若老家的邻居。他们已经看惯了高墙以及高墙上的铁丝网,就像看惯了邻居菜园的围栏以及围栏上带刺的荆条。
有一天,高墙那边集合报数声消失了——劳教所最后的人马全部撤走了。第二劳教所监区终于完整地回到了移民的手中,或者说这个地方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安置点。望着突然寂静下来的高墙深院,河龙村人再集合报数的时候有些怅然若失——他们的邻居迁走了。
一切都在朝着井然的秩序和规范的程序行进,分配土地、种植作物、规划宅基地、小孩入校……河龙村人挽起的袖子卷起的裤脚只有到夜里才能放下来。毋庸置疑,河龙村人开始忙碌了,真正地忙碌了,投入地忙碌了。他们在不久的未来将要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黎塘人。这种忙碌首先是一种认同或者一种接受,认同脚下这片土地,接受这片新的家园。然后是一种欢喜的景象,欢喜的花朵不仅盛开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脸上,还绽放在移民群众的心里。这叫双赢。
随着各家各户逐渐分工不一,也随着高墙那边人马的彻底撤离,安置点每天集合报数的仪式也就取消了。其实劳教所还没全部撤走的时候也不是天天都集合报数的,有一天早上下着瓢泼大雨,挤在屋檐下等待出工的河龙村人,听到高墙那边依然传来集合报数的声音,一个移民好奇地冒着大雨跑到大门前窥视,回来报告说,场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是在放录音。没想到取消每天集合报数仪式之后,移民安置点发生了一件事情:
阿剑失踪了!
这是河龙村人移民搬迁到黎塘后,发生的第一件意外的事情。阿剑一家是河龙村安置到黎塘的四十余个移民户之一,他们原先被安置到北海的一个农场,后来调整时又被安排到黎塘来。河龙村人经过仔细的回忆,坚定地确认移民搬迁那天阿剑是上了车的,上的是三号大巴车,是和户主在一起的。第一天集合报数的时候,阿剑也是在场的。第一次去丈量甘蔗地的时候,阿剑也是在现场的。确凿的证据表明,阿剑是在安置点失踪的。然而,阿剑具体在哪一天不见了,户主也说不清楚。忙得焦头烂额的户主,只想起起码有五天不见阿剑了。领队安慰了户主一番之后说: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仪式是不能忽略的。领队此话与他的行为或者观点前后矛盾,当初“引进”集合报数这个仪式的是他,他认为移民刚进到安置点应该统一行动,统一步骤。领队还引用了一句伟人的话: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后来取消集合报数这个仪式也是领队他本人,他认为既然劳教所已经全部撤离了,就没有必要继续效仿人家这个仪式,不然人家误以为我们是留守犯人。领队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集合报数那是世界上通用的操典,不分敌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
整个安置点的移民全部出动,分头寻找阿剑。连续找了三天三夜,人们在安置点的各个角落没有发现阿剑。河龙村人怀疑,阿剑是不是被黎塘人搞掉了。
阿剑的失踪很快就反馈到当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全来了。这事关移民安置点的治安问题,治安不好,移民们何以安居乐业?安置点周边的群众也加入到寻找阿剑的行列,黎塘人搞掉了阿剑的风言风语传到了他们的耳朵,他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没有搞掉阿剑,他们的法律意识比任何人都强,因为劳改场就在家门口,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每天都在接受警示教育。派出所的人在安置点周边前后忙碌了一个星期,阿剑依然没有找到,不过警察下结论说:阿剑肯定还活着,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活着。
阿剑是河龙村移民户覃老汉家的一只黄狗,也是河龙村唯一随迁到黎塘移民安置点的一只狗。阿剑聪明乖巧,通晓人性,那天搬迁在车上,见到主人一直在哭泣,就在旁边不停地摇着尾巴,不时用舌头去舔主人沾满泪水的手,偶尔也呜呜两声,却一直乖乖地待在主人身边,两眼哀怨地望着主人,显得也很忧伤的样子,一车凄凄惨惨的人因为阿剑的存在心里好受了一些。到了安置点后,每天集合报数时,阿剑也不落下地汪汪两声,引发大伙一阵阵笑声,牵出移民们一天的好心情。
转眼间清明节到了。
清明节一到,河龙村的人就开始筹备回老家祭祖。从河龙搬迁到黎塘时,绝大部分移民户把祖先的牌位也搬来了。牌位搬来了不等于祖先也跟来了或者说实质性地跟来了,就像交流干部,人是交流去了,可是户口并没有随迁,实际上还是原地的人。既然根在老家,祖先的坟墓都在老家,清明节自然要回去祭拜了。
眼前哪里是家乡啊,分明是水乡,梦里水乡。昔日家园被一面湖水代替了,所有的记忆或所有的回忆以及所有的话语,一下子泅进了这面平静的湖水。湖水也是无语的,它向远方归来的亲人默认了当前的事实。
一只大黄狗从坡岭上冲下来,蹿到覃老汉跟前,摇着尾巴,嘴里唧唧吱吱地哼着,蹭着他的腿,咬着他的裤脚,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覃老汉定神一看,这不是失踪多日的阿剑吗?原来阿剑还活着,阿剑并没有被黎塘人搞掉,阿剑生龙活虎地回到了老家。覃老汉百感交集,他一把抱起黄狗,不停地抚摸它,呼叫它的名字,阿剑!阿剑!老泪溢满了眼眶。
根据老家后靠乡亲的讲述,覃老汉他们搬迁到黎塘的第七天,阿剑独自徒步回到了村里。乡亲们见到阿剑无家可归,就将它收留了。让河龙村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阿剑去黎塘的时候是坐大巴车去的,回来的时候是如何走了那么远的路回来?阿剑从未出过远门,别说东兰县城,就连大同乡政府它都没去过,照说它是不晓得从黎塘回来的路的,况且是徒步。然而,阿剑竟然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三百公里的路途有数不清的大路小路、沙石路水泥路柏油路,它是如何辨别回家的路呢?有人就说,瑶族的祖先是龙犬,叫盘瓠。阿剑是盘瓠后裔有神助,所以能独行三百公里回到故乡。——这自然是神话或者传说。至于阿剑如何从黎塘徒步回到河龙,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清明节后,阿剑又随覃老汉回到黎塘。与上次不同的是,这回阿剑是坐在主人的摩托车后座返回的。覃老汉想,要是哪天阿剑又不见了,它一定是悄悄地回到了河龙,那是它的远方。当然,也是他覃老汉的远方……河龙村人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