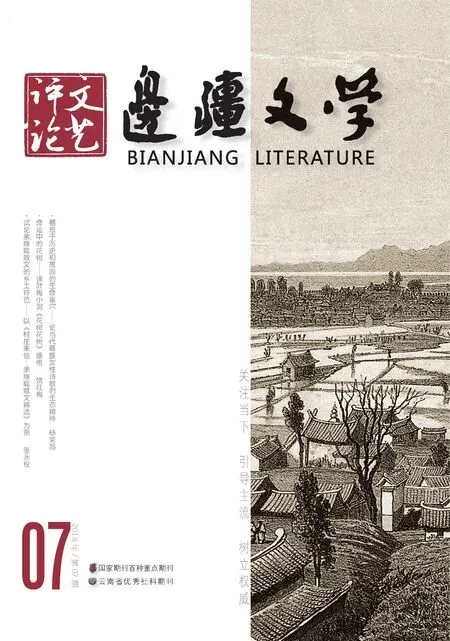《人面桃花》的症候式阅读
2018-11-12钟茹霞
钟茹霞
《人面桃花》以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一代女革命家陆秀米的精神成长史。小说问世十余年,关于《人面桃花》的乌托邦主题,学界通常把关注点放在乌托邦革命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偶然性因素方面,把陆秀米革命意识的萌发归因于性意识、欲望的驱动。“假如没有那个与张季元发生私密接触的难以启齿的‘春梦’,她不会对这个奇怪而且有些轻佻的人物产生好感,也就不会对他所从事的秘密勾当产生任何兴趣!而正是这个没来由的恼人的春梦,使秀米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偏转,一头扎向了中国近代史的惊涛骇浪!” 本文从文本细读出发,重新审视小说中一系列的反常、悖逆、别扭与困惑,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试图探讨小说《人面桃花》的乌托邦革命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必然性,通过挖掘秀米潜意识里的恋父情结来窥视作家潜意识里的乌托邦执念,揭示乌托邦革命理想的希望所在,以及结合“乌托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对当下社会现象及人们的精神面貌得出一些个人的思考与感悟。
一、“父亲出走”的悬念
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深受西方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影响,格非也不例外,创作受到西方文学作家包括博尔赫斯、卡夫卡、易卜生等的影响,当然还有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从 80 年代开始,我有很多小说都和精神疾病有关,首要原因是我担心自己随时会崩溃掉!这是实话!我确实看过大量的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方面的书籍,对精神疾病的病理相对了解!我对治疗强迫症颇有些心得!”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格非小说,显然很有必要。
小说第一章《六指》第一节第一句话:“父亲从楼上下来了。” 格非把“父亲从楼上下来”和“父亲离家出走”放在小说开篇,大肆渲染,显然,这与后面鲜有提及父亲形象,父亲形象几乎被隐去相矛盾,父亲离家出走之谜也被悬置。如此重要的放在开头的人物及其行为表现,为何在后面的叙述中消失不见?黄维群在他的论文《神神乎乎的悬念和突变——格非的〈人面桃花〉解读》中认为:“《人面桃花》一上来,他就制造了一个父亲出走的悬念。初看,这悬念扑朔迷离很有味道,但看下去,这味道则不那么有味道......事实上,我们在《人面桃花》中确也看到,作者没能力也不可能有能力对自己的这个悬念照看到底。那是个只有开头没有继续也没结尾的不了了之的悬念。” 乍眼望去,格非似有笔力不及,高开低收。按照叙事学理论,小说的开篇对于整部小说感情基调的界定以及整体结构,起到奠基石的作用,以文学形式实验成名的先锋作家格非不可能不知。
同理,小说开篇的重要性也是如此。《人面桃花》的开头“父亲下楼来了”与“父亲离家出走”,作者注定要在此苦心孤诣,大做文章。“秀米手里捏着一条衬裤,本想偷偷拿到后院来晒,一时撞见父亲,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下楼来,适逢秀米月经初潮。秀米生理成熟,父亲竟然是第一个得知,这与常识不符,作者用意何在?显然,这恰好可以看作身体发育成熟的秀米,以父亲的出走为起点,开始继承父亲志向,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理成长历程。有论者指出:“秀米对父亲的感情属于崇拜性恋父情结,秀米父亲发疯前曾经在朝廷做官,难免使年幼的秀米对父亲心生崇拜。” 对此,本文的观点立场是赞同意见,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秀米对父亲陆侃是崇拜性恋父的表现,但是笔者认为她对张季元则属于恋父的“移情”,在秀米的潜意识里,张季元已然作为父亲的“替代”。小说中多次提及秀米对表哥张季元的态度转变,由厌恶转为不自觉接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张季元身上有一股烟草味,是秀米自幼熟悉的父亲身上的专属味道。
有论者认为秀米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崇拜性恋父情结使得作为女儿的秀米模仿父亲陆侃的言行而走上革命道路。对此,本文持不同看法:秀米继承父亲理想,历尽坎坷终成一位优秀的革命党人,并不是由于崇拜父亲而模仿其言行,踏着父亲脚印的亦步亦趋,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作为父亲不受宠的女儿,希望得到父亲认可与赞赏,博取父亲宠爱的无意识心理所致。虽然秀米心里崇拜父亲,爱着父亲,但父亲却并不宠爱她。“秀米父亲疯病痊愈后,下楼遇见刚好初潮的秀米,秀米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 这说明父亲发疯前,也就是秀米幼年时期,秀米与父亲的关系都不亲密,更谈不上父亲对秀米有多么宠爱。父亲不宠爱秀米,她为何还要替父亲在母亲面前辩护,为何她爱上的是一个有父亲身上烟草味的男人,又是为何冥冥之中继承父亲志向,成为了一名成熟的革命党人?弗洛伊德认为,恋父情结有时并非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而父亲对于女性个体成长的影响会更复杂一些。因此父亲对女儿的态度关涉到女性一生对自己的彻底评价, 父亲的行为方式也左右着女性对异性的最初认识。秀米作为一个不受宠的女儿形象,只有在别的地方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与价值,最终目的是赢得父亲赞许,博得父亲青睐。
二、“代替父亲”的设置
父亲离家出走第二天,张季元来到家中,住进父亲的阁楼。一开始,秀米不喜欢这个外乡人,乃至厌恶他,秀米对张季元的态度其实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如小说第一章秀米洗头这一情节,张季元说想帮秀米洗头,秀米连说不用,但是心却跳得厉害,还特别留意观察到张季元就在他身边不远处站着。此时秀米的心理活动却又是:“该死!他竟然在看我洗头!真是可恶!” 接着,秀米心想:“他干嘛要站在这里呢?”可以看出,秀米对张季元的感情非常矛盾:既时刻注意到他,对他感到好奇、动心,又处处表现出讨厌他靠近。正如《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的日常相处细节:某日午饭后,宝玉前去探望黛玉,远远听见黛玉念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进屋后,顺手拿这话逗她,黛玉马上翻脸不认账,嗔骂宝玉不该说这样的话来贬损自己。《红楼梦》中类似的细节,譬如宝玉对紫鹃说:“若与你多情小姐共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以及宝、黛二人关于“渔公渔婆”的玩笑。结果都是黛玉被宝玉惹气或惹哭,然而黛玉对宝玉的爱意一目了然。小说中不存在二人恋爱的描写,单独相处的情节也只有两三处。虽然秀米芳心暗许,张季元也是对她牵肠挂肚,但是二人都没有挑明关系,更无实际恋爱关系与亲密接触,为何秀米得到张季元日记后情绪失控而发疯,乃至于被绑去花家舍前后,终日翻阅日记,与日记相依相伴。对于一个还不太了解、熟悉的男子的日记,为何产生如此强烈、过激的反应?这在读者看来,未免读来感觉过分夸张和别扭。
张季元身上实在有太多与父亲的相似之处,“精神分析学家总是断言,女人在情人身上总要去寻求父亲的形象”。 首先,他出现在父亲离家出走的第二天,父亲的缺席,得到了及时的补位。小说中有关于这个男子的年龄外貌描写,“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嘴上还叼着一根大烟斗,母亲一见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秀米与她初次相见,闻到他身上的烟草味道,不禁想起父亲,自从父亲变疯之后,秀米还是第一次闻到烟草的味道,后来秀米才得知此人叫张季元”。这人除了身上有父亲的烟草味,还与父亲一样患着疯病,秀米不禁私下里想,“又是一个疯子”。 其次,张季元居住的地方是父亲的阁楼。小说中还有此提示:“张季元占据了父亲的阁楼,这使秀米多少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父亲并未离开。” 再次,这名陌生男子与父亲一样,都稀罕那件从叫花子手中买来的瓦釜,而且还喜欢荷花,他对秀米说:“独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其旨高洁,故倍觉爱怜。” 这与父亲又是出奇的相似!听罢张季元的“爱莲说”,秀米的言行是:“张季元见秀米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秀米不仅未想离开,还与他因着荷花对起诗来。秀米这样的表现,实际是在张季元身上又找到父亲的影子,所以才忍不住留下,与之交谈。秀米春梦过后,她觉得自己和张季元之间多了点什么。除了梦里把他当作情人之外,还多出来的就是秀米与他从此是一类人——为革命奋斗的同类人。二人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可以说是宝玉黛玉似的情人知己。
显然,张季元这个人物形象是作为秀米的“代替父亲”而出现。现实中女性的恋父情结最大延伸就是移情于父性的年长男子,只要有一点与父亲相似,就会深深被其吸引,更何况张季元与父亲有着如上所述的诸多的相似点。此外,小说中还多处写到了秀米的梦境。第一次是在孙姑娘出殡时候,秀米做了一个与张季元有关的春梦,梦境是最典型的症候,从梦所展现出来的看似无意义的东西出发,分析出对象的精神状态,揭示文本中掩藏的症候。我个人认为,与其说这是格非小说玄玄乎乎的神秘色彩与命中注定的宿命论思想,不如说是秀米恋父情结的集中表现。因此,通过上述关于秀米言行、梦境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潜意识里深藏的恋父情结。秀米继承乌托邦理想与革命历史使命,除张季元日记影响之外,其余相关的内容事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秀米的梦境来完成。梦是欲望的达成,秀米出现这样的梦境,无疑与秀米内心的所思所想相关,属于潜意识深处的欲望。无论是张季元日记,还是秀米梦境,显然都与父亲以及父亲的桃源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结语
格非在一次访谈中谈及《春尽江南》的创作,他坦言:“《春尽江南》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办法给我们生活在苦难,看不到希望的人提供一些安慰,这是我写完《春尽江南》之后最大的遗憾,因为即便是庞家玉这样的人物,用加缪的话来讲她仍然是有希望的,但这个希望却并非她想要的。” 近段时间,莫言在金砖国家文学论坛上谈及:“我们都有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风貌的野心,可奋斗了几十年,似乎也没有谁写出了能够让大家信服,反映时代风貌的巨著”,“尽管如此,作家们没有泄气,也没有停笔,不断地重复着如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工作。这也许是这个时代的作家们的悲剧,也许是这个时代的作家们的光荣。”《人面桃花》不同于《春尽江南》的毫无希望,虽然革命与乌托邦理想也许终会是一场空,但是人类为之奋斗的过程就是价值意义本身。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