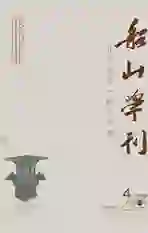朱伯崑的船山易学论
2018-10-29方红姣王方媛
方红姣 王方媛
摘 要: 朱伯崑从易学思想的源流考察船山易学与张载、方以智、程颐、朱熹的关系,认为船山易学主要继承的是宋易义理学派中理学和气学的传统,并指出乾坤并建是船山易学的最大创见,进而肯定船山易学为其气本论的哲学体系奠定了思想根基。朱伯崑对船山易学的阐释,是其易学哲学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船山;船山易学;乾坤并建;天下惟器
朱伯崑(1923—2007)①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王船山思想非常关注。其易学研究可说是从研究王船山易学思想开始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朱伯崑即发表了《王夫之论主观与客观》《王夫之论本体和现象》等文章。在其代表作《易学哲学史》(四卷本)中,他更是倾注大量心力,整个第四卷只有一章,名为《道学的终结和汉易的复兴》,其中关于王船山的专章论述占到五分之三的篇幅。朱伯崑对船山易学的分析,一方面厘清了船山易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体现了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
一、重新定位船山易学的基本倾向
关于船山易学思想的形成,有两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一是将船山易学传统仅仅归于张载,二是在船山易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上,过于强调二者对立的一面。朱伯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甚妥当,并从思想的源流上做了细致分析。
其一,就船山易学与张载的关系而言,朱伯崑认为,将船山易学传统全部归于张载,并不符合易学史发展的真实状况。朱伯崑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区分了张载和张载气本论的后继者,没有将张载及其后继者混为一谈,并且还从易学史发展的角度看到了易学中的象学派对船山思想的影响。
以道器观为例,道器之辨始于韩康伯,朱子以理为体,以象为用,或说以道为本,以器為末,视形而上的理为有形世界的本原,认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而心学派则从程颢开始即不赞同区分形上与形下,主张道器合一,但是以心为本,而不以形器为本。朱伯崑认为,船山道器观与理学派、心学派根本不同。不仅如此,其直接受张载的影响亦很小。在他看来,船山道器观是对元明以来气学派和易学中的象学派道器合一论的继承和发展,并着重说明方以智对船山的影响。他说:“元明以来的气学派和易学中的象学派皆主道器合一说或道不离器说,至方以智则阐发为‘道寓于器,‘即费知隐,‘质测即藏通几,并从物理方面作了论证。方氏的道器观,特别是其质测说,对王夫之颇有影响。”[1]140
元明以来的气学派以及易学中的象学派,在朱伯崑的理解中,主要是指朱震、罗钦顺、方以智等人。罗钦顺是气学派的代表,朱震治易以象学为主。船山论道器关系是从象学的原则出发,以形和象为事物存在的基本特征。器作为道存在的惟一条件,所谓“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 船山从质测说的角度论证即物穷理和道不离器。他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2]633
朱伯崑在《易学哲学史》中,着重以船山的《外传》为例,认为船山的一些重要命题都不是直接受到张载的影响。他说: “如在《外传》中提出的‘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以太极为理气合一之实体,并且批评了圣人与太虚同体说,皆非出于张载,而是阐发明代气学派易学哲学的观点。”[1]10
其二,朱伯崑深度解析了船山易学与程朱理学的内在关系。他从卦爻辞、易学哲学范畴以及易学流派三个方面举证,肯定船山受程氏《易学》的影响很大。朱伯崑说:“关于卦爻辞的解释,主因时而取义;关于易学哲学范畴的解释,主张体用一原,阴阳无始,以天为理,以动为天地之心;关于易学流派,反对邵雍的数学;凡此皆出于程氏易学传统。”[1]11 在朱伯崑看来,船山易学所主张的因时取义、体用一源,以及对邵氏数学的态度都与程氏易学一脉相承。而船山对朱子的批评,主要是因为朱子肯定邵雍先天易学。船山说:“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申之理,而专言象占,谓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几,言精义,言崇德广业者,皆非羲、文之本旨,仅以为卜筮之用,而谓非学者之所宜讲习。其激而为论,乃至拟之于火珠林卦影之陋术,则又与汉人之说同,而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牴牾而不恤。”[3]653 这一段文字体现了船山本人对朱子易学的基本看法。船山肯定朱子学术大体以程氏为宗,然唯独在易学方面,朱子一反义理学派传统,而崇尚汉易偏于取象,“专言象占”。船山的这一观念大概源于朱子对邵雍先天图式的借用。
船山解易路数总体上属于义理学派传统,但就理与象之关系而言,又与程朱重理而轻象明显不同,船山主张即象以见理。正如朱伯崑所说,船山融摄象数学派的观点,不仅表现在取象说上,他还注重将象数范畴作为易学哲学的概念来建构。因此,船山对象学的态度不能笼统言之。简单的割裂船山易学与程朱理学的内在关联,在朱伯崑看来,是有偏失的。
在以上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朱伯崑对王夫之易学的基本倾向作了定位。他说:“关于王夫之易学的基本倾向,主要是继承了宋易义理学派中理学和气学的传统,反对宋易中的象数学派,特别是洛书学和邵雍的数学,进而反对汉易的象数之学。”[1]11
二、提出乾坤并建是船山易学最大的创见
船山在《周易内传发例》中,自称其易学 “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戒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 [3]683朱伯崑将它归纳为三点:一是乾坤并建,错综合一;二是彖爻一致,占学一理;三是占义不占利。朱伯崑认为,此三点为船山易学体系的三大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乾坤并建。朱伯崑称“乾坤并建说最为重要,是船山易学及其哲学的纲领,乃王夫之的创见”[1]16。
所谓乾坤“并建”,即是强调乾坤两卦象相反相成,《周易》卦序始于乾坤两卦,而不是始于乾卦。同时,乾坤两卦的德行也是“并列”的。乾德与坤德同等重要,二者不只是外在形式上的相互依存,在内在的德行上更是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朱伯崑分析了船山乾坤两卦演变为六十二卦的逻辑过程。这个逻辑过程有三类图式。
第一类图式:乾坤两卦变为六子卦,乾坤六子卦进而变为五十六卦。按照这一图式,六子卦是乾坤十二阴阳自身的展开,在展开过程中,因所处之时位不同,因而形式各异。而由八卦到五十六卦,船山则是以经纬交错关系来论述的,八卦是经,其他卦为纬。朱伯崑说:“王氏以乾坤坎离等八卦为经,其他卦为纬。此是说,从乾坤并建开始,到既济未济为终,经纬交错,但皆是十二阴阳或显现屈伸,或升降往来的结果。”[1]88
第二类图式:乾坤变为十二辟卦,此十二辟卦进而变为五十二卦。十二辟卦的排列顺序是依阳变阴合的法则,同时船山效法八卦开展为五十二卦的过程,将十二辟卦分为六组,每组分别形成若干卦。
第三类图式:乾坤并建,展开为八错卦,二十八綜卦,共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何谓错卦,何谓综卦?朱伯崑依据船山在《内传》中对错和综的解释,说:“错卦表示卦象向背屈伸对立,综卦表示爻象升降往来。”又说:“一向一背即错卦,阴阳或升或降即综卦,以此说明卦爻象变化的规律性。”[1]96 因此,《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无非是错综相配。
在朱伯崑看来,王船山提出的三类图式,有以下两个重要的共同点。
其一,就易序问题而言,都是对《序卦》文的“前后相生说”的反对。这种前后相生表现为三种形式,即相因、相成、相反。对这三种形式,朱伯崑都以船山《外传·序卦传》中文字一一反驳,最后得出结论,“王夫之这些议论,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六十四卦的程序,并非像一条链子前后连续的过程,即后卦因前卦而有,而是无渐,无待,无留。”[1]97
其二,三类图式有共同的最核心的观点,即六十二卦是乾坤两卦自身的展开或其显现的不同形式。“六十二卦皆是乾坤两卦阴阳十二位或隐或现的表现形式”,“乾坤两卦所以为六十二卦的基础,因为各以其至健和至顺即纯而不杂之德统率事物的复杂变化。”[1]80 - 81船山是用阴阳向背或幽明,来说明乾坤以及乾坤两卦和六十二卦之间的关系。朱伯崑肯定此是船山乾坤并建说的一大特色。他说:“王氏此论,以向背解释乾坤,认为乾卦中有六阴,坤卦中又有六阳,各有十二阴阳,阴阳来往于向背十二位之中,此是其并建说的一大特色。” [1]79船山以乾坤两卦,每卦六画,或为六阳,或为六阴,这是显现于卦画的,还有未显现于卦画者,亦有六阴或六阳。因此,一卦六画,实际上有十二位。六位为明(显),六位为幽(隐)。这就是幽明或向背之说。朱伯崑认为,船山正是依此说去理解周敦颐太极图的第二图,遂得出其独特的看法:第二图虽为三阴三阳环抱,其实六阴六阳具足,另外三阴三阳没有画出来,只显示三画卦之象。
船山的乾坤并建说,以六十二卦为乾坤两卦自身的展开或其显现的不同形式。用乾坤两卦阴阳爻位隐显的形式,解释六十二卦的差异。这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是重大的理论突破。朱伯崑以邵雍、朱熹为参照,具体分析了其易学史和哲学史意义。
就易学史意义而言,他说:“此说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汉易中的卦气说,特别是邵雍的先天卦序说。” [1]98 邵雍先天卦序重阴阳相分,阴阳之逐渐消长,以乾坤两卦爻位互易解释六十二卦的形成;而不知其变易乃六阴六阳之隐显和升降。船山与邵雍不同,他不以爻位互易而以阴阳爻位隐显的形式解释六十二卦的差异,这也是对宋易中卦变说的否定。
从哲学史上看,朱伯崑认为船山超越于邵雍、朱子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乾坤并建说是对相生说的超越。朱熹、邵雍都认同、阐发《序卦》文的前后相生说。相生说认为前卦和后卦是因果相生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或者相因,或者相反。无论是相因还是相反,后卦都是因前卦而有。邵雍的先天卦次序图,认为先有两仪而后有四象,而后方有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这种加一倍法的理解,在船山看来,实质也是这种相生说的体系。乾坤并建说,以六十二卦为乾坤两卦自身的展开或其显现的不同形式,六十二卦之间不存在因果相生的关系。这是对相生说的突破。
其二,那么乾坤并建说中乾坤两卦与六十二卦以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朱伯崑认为,是一种分合说。这是他所认为的船山超于邵雍和朱熹的第二个方面。朱伯崑说:“王夫之以‘分与‘合的观念解释乾坤两卦同六十二卦以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认为乾坤两卦有合有分,三十六象有合有分,综卦和错卦有合有分,……肯定阴阳作为共性存于个别卦体之中,强调分中有合,异中有同,以阴阳合一说批评了邵雍的阴阳相分说,进而打击了朱熹的阴阳定位说。” [1]106 在朱伯崑看来,以分合观念诠释乾坤两卦和六十二卦以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实质是一种阴阳合一说。这种“阴阳合一说”是对“阴阳相分说”和“阴阳定位说”的超越。
其三,乾坤并建说是对阴阳交错说和卦变说的超越。在船山而言,任何卦爻都有阴阳或隐或显两方面,不存在孤阴或孤阳之象,也即是说,每一卦和每一爻都有两重性。由此,以阴阳十二位向背、隐显和幽明说明乾坤两卦相互涵蕴。同邵雍和朱熹相比,既不采取阴阳交错说,也不采取卦变说,而是以个体自身的向背关系说明阴阳相互依存,进而论证阴阳双重性乃绝对、普遍的法则。此外,朱伯崑认为,船山以向背或幽明关系论证阴阳消长只有变易,没有生灭,这一点也是其超越前贤之处。六十四卦和三十二象,无论爻象上下往来,怎样变易,都是乾坤十二阴阳屈伸、隐显的不同形式,这就批判了汉易以来的阴阳消息说(如京房所说,以消为灭,以息为生),因此这一说法为宋明以来的气不灭论作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哲学上有重要意义。
在朱伯崑看来,以上三点不仅是其哲学史意义的集中体现,也是船山乾坤并建的主导思想。他解释六十四卦卦序的三类图式都是基于上述主导思想而展开的。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朱伯崑指出了乾坤并建说的局限。他认为,有两点值得深入思考:其一,船山的乾坤十二阴阳,以为一半为阴,一半为阳,这种阴阳各半说,有均衡论之嫌。其二,船山所说,阴阳合一或“合异以为同”,此“合”的含义,似有歧义:即“合”到底是对立面的统一,还是对立面的融合?
三、分析船山易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对船山易学经典进行细致梳理之后,朱伯崑围绕以下几个问题阐述了船山易学哲学:天下惟器、盈天地之间惟阴阳、神妙万物不主故常、太极观以及天人关系,进而揭示船山易学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下以天下惟器问题为例,稍作阐释。
船山“天下惟器”命题的提出,乃是基于他对易学中象和数的理解。在朱伯崑看来,船山所说的象和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的形象或规定性;一是指表达物象及其数量的图象和数目。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天地之间所有事物,有象则有数,有数则有象。
故而,“非象无以见易”。船山正是在“非象无以见易”的基础上,对象与道、象与理、道与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别。先有象还是先有道或理?船山以象为道存在的载体,认为道或理不在象外。道作为规律性不能脱离物象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山主象道合一,象理合一。这一观点与他对象数的理解是一致的。
朱伯崑认为,船山将其象理之辨从易学推至哲学领域,遂发展成现象和本质及其规律的关系问题,并且给予了不同于佛、道的新回答。現象是有形的,本质和规律是无形的。前者属形下的领域,后者属形上的领域。依船山象道合一说,作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道或理,即存于形形色色的个体之中,存于现象之中。这与佛道两家的论说截然不同。佛、道两家不能充分正视有形有象的个体的实存性,至象外寻求道(或理),从而割裂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关联。朱伯崑说:“佛道两家的本体论都鄙视有形有象的个体事物,或象外求道,或弃象言理,其结果或视物质世界为虚幻,或以虚无为本体,都走上了出世主义。” [1]130
在朱伯崑看来,船山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说,不仅是对佛、道两家理论的纠偏,同时,就理学内部而言,也是理论上的一次革新。
自宋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程颐提出“有理而后有象”,张载提出“有气而后有象”,开启了宋明的象理之辨。这两种观点争论了数百年。程颐之后有朱熹,而船山则主要承接的是张载的思想路数。不过,船山对程朱和张载都有所批判和改造,船山的象理合一观是对宋代以来象理之辨的总结。从程朱的理论来看,船山通过对程朱“显微无间”说的改造,将程朱的理本论转化为以象为本说,从而为其哲学的气本论奠定了基础。朱伯崑说:“王夫之则改造了程朱的‘显微无间说,以个体的存在为实体,以象和理为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并且以象为理之依据。此种象理统一观,将程朱的理为本说转化为象为本说,从而否定了道或理的实体性,此是王夫之的易学哲学的又一贡献。” [1]131 程颐的“显微无间”,是针对王弼而提出的。关于意、象、言三者的关系,王弼主张“得象而得言”“得意而忘象”的忘象说。王弼引庄子之言,重新诠释《周易》中的意、象、言,把三者关系发展为一个认识论问题,强调言、象在认识中的有限性,对经验知识和经验世界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从而否定在经验层面寻求本体的可能性。程颐反对王弼的忘象说,提出显微无间,象中有理,理在象中,强调理象合一,但是这种理象合一是以理为实体,以象为理之表现形式的合一,是一种理本论。船山的理象合一,则以个体的存在为实体,一切实存的个体都同时具有象和理两个方面,象又是理之存在的依据和载体。由此,船山对理象之辨的论说起到了动摇程朱理本论的作用。
就气本论思想内部而言,船山的理气之辨也超过了张载的理论高度。朱伯崑说:“张载虽然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以及‘幽明所以存乎象的论点,但由于他区别形和象,以气之象为形而上的领域,又导致轻视个体的结论。而船山将象归结为个体存在的特质,如其所说‘物生而后有象,则肯定了个体的实在性,又超过了张载的水平。” [1]131 朱伯崑认为,张载虽 “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幽明所以存乎象”, 是肯定“象”在天地之间的实存性,但由于他以为在“象”之外还有“形”,并且将气之象理解为形而上,对于“形”没有应有的重视。船山则明确将象作为形色个体存在的属性,这一点上弥补了张载区分形和象的不足。可以说,张载的命题,后虽有易学中象学派的阐发,主理寓于象中,但是只有到了船山这里才真正从哲学上作了论证,从而成为气本论的内容之一。
船山象理之辨的观点是其“天下惟器”论的思想基础。所谓“天下惟器而已矣”,此命题强调的是,天地宇宙间,形形色色的个体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器即是指有形有象的个体事物。强调个体的实存性恰恰是象理之辨中船山所反复申明的。道或理不能作为独立实体而存在。朱伯崑对船山的“无其器则无其道”做了阐释。“无其器则无其道”,首先,肯定的是道只能以器为其存在的实体,正如“道器无异体”所说。其次,“道”的含义具有广泛、普遍的特征。他说:“此处所说的道,虽属于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如王位继承之道,射御之道,礼乐之道以及君臣父子之道等,但其理论意义,并不限于人类生活,包括天地之道和万物之道。因为此文中所说的器,指一切有形象的个体事物,所谓‘盈天地之间皆器矣。” [1]135 也就是说,器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一切个体事物,则器之道也是遍及天地之间的,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在内的普遍之道。船山虽只是以人类社会伦理生活为例,但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伦理生活,不仅仅局限于人道的范围。朱伯崑的这一理解是很真切的。他进而总结了船山道器观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两点:
其一,船山“天下惟器”的哲学命题,是传统哲学中道器之争的总结。船山将其“非象无以见易”的易学原则贯穿于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上,坚持一切关于形上学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对物理世界和人类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观点。以往探讨形上学的命题只多流于空中楼阁,船山则避免了这样的“虚而无实,自谓神灵”。正如朱伯崑所指出的那样,船山并不反对建立形上学的体系,他只是特别强调不能脱离形而下谈形而上,不能离开有形有色的个体事物谈形而上问题。船山气本论的本体论体系即是在其道器观的指导下形成和展开的。
其二,船山的道器之辨很好地回答了哲学中的抽象和具体、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规律和实体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船山在哲学理论思维方面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朱伯崑说:“王氏的贡献不仅是肯定规律性的东西,一般东西以及抽象的原则寓于有形有象的个别的物件和事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指出没有个体便没有规律,没有个别便没其一般,没有现象便没有本质。这样,便正确地解决了道器或理事谁依赖谁的问题,从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141
在朱伯崑看来,船山不仅肯定抽象、一般和本质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而且明确指出了抽象和具体、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何者为根本,尤其是关于何者为根本的问题,体现了船山独到的贡献。朱伯崑认为,船山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一方面体现了他高水平的辩证思维;同时也与明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不开。自然科学中的求实精神对于哲学领域亦有它的积极影响。
就易学研究而言,在明清之际批判心学和反思理学的思潮中,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都出现了总结之前易学成果的代表人物。船山可说是义理学学派的代表。朱伯崑认为“王夫之不仅是十七世纪中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宋学中最后一位经学大师。” “就其对《周易》经传的解释说,继承了宋明以来气学和象学的传统,修正程朱的义理之学,批判心学,并同邵雍易学和河洛之学以及两汉以来的象数之学展开大辩论,对以前的易学哲学作了一次总结,终于完成了气本论的体系。” [1]3 无疑,船山哲学体系与易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对《周易》经传的阐释,奠定其气本论哲学体系的基石。
结语
朱伯崑对船山易学的研究,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他的一切论述皆以船山易学经典为基础。通过对船山易学著作的梳理,分析船山易学思想的特色,并且善于从思想源流、历史地位的纵向角度来凸显这种特色和船山易学思想的贡献。其次,朱伯崑对船山易学思想的阐释,为深入理解船山哲学提供了易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新角度。朱伯崑肯定船山哲学都是围绕易学展开,易学是其哲学思想的根基。以乾坤并建说为最大创见的船山易学,体现了气学派易学哲学的共同特点:“以阴阳二气的变化法则解释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象的形成,进而以二气说解释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联系。因而在哲学上都以阴阳二气以及变化解释世界和人生。” [1]115 不同于阴阳相生说和阴阳相分说,船山以六十二卦为乾坤十二阴阳自身的展开,从而导出哲学上的以阴阳二气作为解释世界和人生的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4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
[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
(编校: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