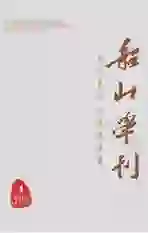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
2017-08-10夏剑钦
摘 要: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有三:一是整理纂注、誊录副本和收藏保管船山著作;二是刊印船山遗书,传承和扩大其学术影响;三是撰写《大行府君行述》,使船山遗书得以入史馆,立传儒林。
关键词:王夫之;王敔;船山著作;湘西草堂; 整理 ;刊行;《大行府君行述》;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自王夫之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以来,以传承、研究、弘扬其人其著作、思想及其伟大人格、精神为主旨的船山学,便逐渐兴起,至今成为“显学”而兴盛不衰。究其兴起、发展以成一门兴盛不衰学科的根由,首先应是船山思想开六经之生面、集古今之大成,在诸多方面达到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思想文化的最高水平,其次则是其传承、研究、弘扬的发展过程,渊源有次,代不乏人。而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第一代学人,则当推王敔、刘献廷、潘宗洛、余廷灿等,而船山之子王敔当然是贡献最大的第一功臣。
王敔(1656—1730),字虎止,衡阳人。王夫之次子。禀承庭训,学问渊博,年三十始应试,为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岁贡生。工诗文,敦尚气节,与邵阳王元复、汉阳王戬齐名,时称“楚中三王”。提学使潘宗洛视学楚南时,延之入幕襄校试卷,乃知其父船山著作等身,“真砥柱一代之伟人”。于是求读船山书,督王敔详述先子始末作《大行府君行述》,而为船山立传以贻史馆。王敔一生大半设馆授徒,曾主讲石鼓书院。筑室湘西草堂之侧以养父,称为蕉畦。父殁后,重修草堂,并于授徒之余整理刊行其父船山的著作。雍正八年(1730)应聘修《衡阳县志》,垂成而病卒于家。著作有《蕉畦字朔》《蕉畦存稿》《怀音草》《笈云草》等。
考察王敔对船山学的贡献,拟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王敔是整理纂注、誊录副本和收藏保管船山著作的第一人
船山一生著作繁富,而他对于自己著作的态度,却在其绝笔诗中表明是“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①,即自己一生作为明朝遗民终身不剃发、不应世,力避“身隐名扬”,宁可无一字留在人间。加之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②,故王敔当时要收集保管好其父的著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据王敔《怀音草自题》,他年少时因学习应科举考试的帖括诗和八股文,而不能悉读父书。然后又以“崎岖烽镝间六七年”之战乱避走山中,又“馆于唐如心之撷翠堂者三载,筑蕉畦以课童子六载”,又“先大人暮年多病,虽晨夕侍药,不敢请益”③等,都影响了王敔对船山著作的研读。加之他在其父隐居著述终年的湘西草堂,“仅固遗书于屋右个,而火灾蚁蚀之害,其震惊怵惕者不一次也”④。这些都说明王敔当时传承、收集、保管船山著作的艰难,及其“以不能传先人之著作为忧”的复杂心情。
但是,王敔畢竟能世其先业,对船山遗著进行了积极的搜集、保管、誊抄等工作,同时还作了精心的整理、编校、补正和注释。这从传世的王敔湘西草堂刻本的各书封面、序、跋、题识及其所署撰著、纂注、校梓等项目来考证,均足以证明王敔是整理、校刊、保存船山著作的第一人。
如现藏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湖南图书馆的湘西草堂本《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约刊于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07—1709),时王敔51至53岁。其第一种《老子衍》一卷,首页第一行镌书名,二行镌“南岳王夫之衍,男敔纂注”,三行镌“同里后学王天泰较梓”。可见《老子洐》一书,是王敔参与了整理和注释工作的。尤其从船山的自序中,可知此书是幸得有王敔收藏的旧本才得以传世的。《老子洐》一书成于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并作序,其序后附记云:“阅十八年壬子,重定于观生居。明年,友人唐端笏须竹携归其家,会不戒于火,遂无副本。更五年戊午,男敔出所藏旧本施乙注者,不忍弃之,复录此编。⑤由此附记,可知该书于壬子年(1672)重订后,被友人唐端笏借去而遭回禄,遂无副本。直至戊午年(1678)船山60岁、王敔23岁时,“敔出所藏旧本施乙注者”,才有幸能按此稿复录付梓。
其二为《庄子解》三十三卷,首页第二行镌“南岳王夫之解,男敔增注”,第三、四行镌“资江后学宁瑛、罗瑄参较”。中华书局本《庄子解》所载王孝鱼先生的《点校说明》中,在说明“从这些迹象推测,至少王敔、宁瑛、罗瑄和蒙之鸿(船山好友蒙正发之子)四人,是当年在湘西草堂亲聆船山讲解《庄子解》的弟子”之后,特别强调说:“王敔对本书的增注,在他增注各书中,成绩最优,用力也最勤。引用古今各家之说很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但绝不见当时最为风行的《南华副墨》及其作者陆长庚的名字。引用最多的是方以智,有十几条。我们知道,方以智是船山的老友,而陆长庚则是以佛理解《庄》的。于此,可见王敔在他父亲的教育下,在学术见解方面也是壁垒森严的。我还怀疑,这个增注,或者是根据当时听讲的笔记而整理扩充起来的。”⑥王孝鱼还谈到,王敔在增注中偶尔还特别指出船山于各篇中单词句义的新解,如《齐物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段末的“莫曰莫若以明”句下,王敔加按语说:“两‘莫若以明与后‘此之谓以明,读《庄》者多混看,《解》中分别观之。”⑦又如《庚桑楚》篇“南荣趎请入就舍”段末,王敔亦加按语:“此段评解,与旧注迥异,玩《解》自明。”⑧这些都可见王敔诠注其父遗书之用功精密周详。
第三种为《楚辞通释》,刻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此书在湖南图书馆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均有王敔在湘西草堂刻印的单种本和五种合刻本,其首页首行均镌《楚辞通释》书名,下有“评点并载”四小字,次行署“南岳王夫之释,男敔补较”,后四行署“后学王扬绪、丁光祺、王扬绩、丁光祹同订”,四名并列,各占一行。可见此书付印前,王敔承担了全书的补校工作。不仅补校,还可从单刻本与五种合刻本的比较中,发现王敔随着清朝文网自康熙末年到雍正年间的逐渐严密,而为钞本和合刊本所做的大量删节与抽去一些文件的工作。
从《船山全书》第十四册杨坚所写的《楚辞通释编校后记》,可知当年杨坚编校《楚辞通释》一书,并没有借阅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的《楚辞通释》湘西草堂单刻本,还误认为省社科院无此藏本,而据湖南图书馆藏单刻本进行编校和采辑附录资料,出现了所录王扬绪、王扬绩《跋》文因书纸朽坏而标白匡缺文148字的遗憾;又据省社科院所藏五种本之《楚辞通释》“缺船山《序列》及其自作《九昭》一篇,目录中亦无《九昭》”,而引发“或出于王敔隐微之用心,于刊刻时有意抽去此两篇,以敷衍清吏之求书也”的推论。然而,刘志盛、刘萍所著《王船山著作丛考》已明确指出,单刻本的《楚辞通释》“湖南图书馆、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各藏一部”⑨。为沉清杨、刘二人说法矛盾的疑案,笔者近日有幸查阅了省社科院藏康熙四十八年的单刻本《楚辞通释》二册,发现其内容依次有巡衡永郴桂道张仕可的《序》,湖广学政潘宗洛署“康熙乙酉八月既望”所作的《船山先生传》,然后是《史记·屈原列传》,王夫之自撰的《序列》和《九昭》,且目录和正文中均有船山《九昭》的九篇之目。其他如参订者丁光祺、储大文、王扬绪、王扬绩等人的《附识》《跋》文等均完好齐全不缺一字。其中尤载有潘宗洛《船山先生传》,是湖南图书馆藏本及其他各处《楚辞通释》藏本均已缺失的,更显省社科院藏本之珍贵。
而省社科院所藏之五种合刊本的《楚辞通释》,开卷除有卷端的释者、补较者、同订者署名页外,便只有目录和正文了;单刻本的张仕可《序》、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史记·屈原列传》、王夫之的《序例》《九昭》以及其他参订者的《附识》《跋》文等均无。显然,这是单刻本印行后抽去了一些副件的重印(下文将进一步论证)。从这里可以看出,初刻《楚辞通释》时,送呈潘宗洛、张仕哥等清朝学、政大员求读的书稿抄件并不一定是不完整的。这从丁光祺《刊楚词南华附识》所说“乙酉秋,豚子元稹应试鄂州,得谒大吏宜兴潘公,值公为先生作传,手把《楚辞》释本不置也”的记载,以及潘宗洛所作《船山先生传》和张仕可《序》的内容,均可说明送呈稿不是被抽去了船山自撰《序例》《九昭》等要件等书搞所能够达到的。尤其是作为湖广学政潘宗洛的同乡幕宾,与王敔友善的江苏宜兴储大文所作的《书王薑斋先生九招后》,更是书稿完整的铁证。“乙酉”是康熙四十四年,张仕可作《序》是康熙四十六年,应当说,康熙四、五十年间,清廷还是以武力统一全国为主,而文网的专制严密只是正在逐步加强。王敔虑患思危,为少暴露船山与屈原一样忠于旧君、忠于故国,“聊以《九昭》以旌三闾之志”(《九昭·序》)的思想,而抽去《楚辞通释·序例》和《九昭》等篇章的举措,也只能是单种本印行后的重印或重刻时进行。在这一方面的良苦用心和周密思考,在下文述《张子正蒙》一书中更为明显。
第四种为《张子正蒙》九卷,卷端题:“南岳王夫之注,男敔较,私淑门人刘美高、王天履、熊成章同订。”王夫之对终生心仪神契的张载《正蒙》一书所作的注释,当然是最能集中反映船山哲学思想的,王敔对此心如明镜。因此,拿什么样的注释本给清廷命官看,用什么样的稿子付梓刊入草堂合订本,王敔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经营的。为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用笔者担任岳麓书社版《张子正蒙注》一书校点工作时对版本的比对研讨所获来加以说明。当时已承蒙《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同仁收集到《正蒙注》一书的本子有两种钞本、六种印本。笔者发现钞本之一的船山十二世孙衡阳王鹏老师家藏本,书分装两册,上册书名“张子正蒙”,下册为“正蒙下”,署“王夫之注,朱宏燝较”,钞本字迹与传世之船山手迹各种完全相同,其为船山手迹似无可疑。钞本末页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成,庚午季夏月重订”小字一行,遂考定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二十七日成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重订,重订时船山72岁。此本书前尚无船山《序论》,书中无王敔所加按语。
用此船山手钞本与其他各本比较,得出此本乃是祖本及其康熙年间四种版本的源流情况是:(一)康熙二十九年,朱氏较本成,是年船山72岁;(二)康熙三十一年腊月,王敔录船山手书朱氏较本毕,是为“蕉畦副本”,船山殁于是年正月;(三)康熙四十六年,衡阳刘氏录蕉畦副本,得所谓“刘氏钞本”;(四)康熙四十六年之后,约王敔六十寿辰之康熙五十五年(1716),王敔复以其所录副本删改忌讳,与《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俟解》合刊为《王船山先生书集》,即湘西草堂五种本。
当时考定祖本及康熙年间四版本源流的依据,除了朱氏较本的小注标注年月日和刘氏钞本封面有“壬申腊月二十八日蕉畦副本,丁亥重九后一日刘□□”小字注之外,另一重要的依据就是以朱较本与刘氏钞本、草堂本对照,后二本的脱文字数,每与朱较本每行17字相合。如《大易篇》“乾之四德,终始万物”一节,船山注文“天德之生杀,本无畛域。以一岁而言,\[春夏秋冬,密运而无截然之限;以大化而言,\]循环往来,无有显著之辙迹”⑩,刘氏钞本、草堂本及其以后各印本均脫方括弧中17字。盖朱氏较本“以一岁而言”一句,恰与“以大化而言”一句前后行并列,因“以”字相同而钞写跳行,最为明显。如此每次跳行17字(或16字)者10余处,加上其他脱文,则藉朱氏较本可发现以后各本脱文有40余处、240余字。
今天虽已见不到王敔于康熙三十一年的蕉畦副本了,但通过比较朱较本、刘氏钞本及草堂本,可以推论出他为此书所作的编校整理和删改等工作。(一)在其父去世之前,已将船山《序论》录入副本,并加了自己的“敔按”小注,可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读和整理。因为刘氏钞本照录蕉畦副本有船山《序论》,且第一本有“敔按”小注,第二本以下才钞写脱落。(二)朱较书和刘氏钞本均只避明讳、家讳,而不避清讳,王敔为避文祸,送呈清廷命官少暴露船山的思想,对蕉畦副本除抽掉《序论》外,还做了一些删改工作。如《乾称篇下》(朱氏较本称《可状篇》)“此人伦所以不察”一节,船山注文云:“王氏之学,一传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发肤\]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蒙古兴\],其流祸一也。”B11此句方括弧中大字皆船山原文,朱氏较本、刘氏钞本同,而草堂本则删去“中国沦没”四字,又改“发肤”为“名义”,改“蒙古兴”为“宋亡”,其为避清朝之讳而删改,十分明显。
第五种《俟解》一卷,刊入《张子正蒙》第五册之后。卷端题:“庚午,男敔较,侄孙勀订梓。”“庚午”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王敔编校整理的时间,但刊印却是康熙四十八年以后。
仅以湘西草堂《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及相关单刻本为例,即可见王敔为整理其父遗著所作的大量工作,而王敔所整理的书稿多次刊刻而镌“湘西草堂藏板”者二十余种,其于船山学的贡献之大自可想见。他的学生曾载阳、曾载述曾在湘西草堂本《夕堂永日绪论、经义》的《附识三则》中说:“自诗文自定稿、四书五经大著作外,凡杂著蕉畦师所辑定者凡二十余种,皆琅玕孚尹之散见者也。蕉畦师岁授生徒,家无长物,传之人者有同心,更以谘之吾党。”B12这就说明,船山遗书的诗文五十、六十、七十自定稿和关于《四书》的《稗疏》《考异》,以及关于《尚书》《周易》《诗经》《春秋》的《引义》《稗疏》《考异》《家说》等之外,还有如《落花诗》《愚鼓歌》《南窗漫记》《夕堂永日绪论》及《经义》等20余种,都是王敔于其父卒后收集、整理、编辑而成的。其后半生的精力和心血大多耗费于此,功莫大焉!
二、 在亲友和门人的帮助下刊印船山遗书,扩大了船山著作的流布和影响
船山先生在世时,盛名虽已为湖南之冠;如河北大兴学者刘献廷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衡阳游知船山后,即在其《广阳杂记》中记船山及其父兄,谓船山“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但船山著作的成批量刊行于世,却是他死后由王敔主持编校、亲友门人共襄出版才出现的事。
据刘志盛、刘萍著《王船山著作丛考》考论,在笔者上述湘西草堂本《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出版之前,还有两种初刻的单种本《楚辞通释》与《庄子解》,且据其“字体不同”,认为“这五种书有重刻、新刻、递修三种情况”。但据最近笔者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查阅比对,则发现该馆所藏单刻本《楚辞通释》与《庄子解》,与五种本之字体、行款并无不同,而明显前后不同的是五种本较之单种本,已抽去不少项目与内容。
如《楚辞通释》,单刻本二册之首册,依次有:
《序》,张仕可题,末署“时今上康熙四十六年季秋月下澣”;
《船山先生传》,末署“康熙乙酉八月既望,提督湖广学政翰林院检讨,宜兴潘宗洛撰”;
《史记·屈原列传》;
《序例》,末署“岁在乙丑秋社日,南岳王夫之释”;
《目录》,末署“私淑门人王後较编”,目录内有“右船山子作”《九昭》九篇的目录:《汨征》《申理》《违郢》《引褱》《扃志》《荡愤》《悼孑》《惩悔》《遗愍》。
除以上五项外,其他如丁光祺《刊楚词南华附识》、储大文《书王薑斋先生九招后》、王扬绪、王扬绩《跋》等俱全。
而五种本之一的《楚辞通释》本,打开即是目录、正文。虽卷端所题“南岳王夫之释,男敔补较,后学王扬绪、丁光祺、王扬绩、丁光祹同订”与单刻本同,但单刻本的张仕可《序》、丁光祺《刊楚词南华附识》和王扬绪、王扬绩的《跋》等均无,更无船山所作《序例》《九昭》和潘宗洛所撰的《船山先生传》。
查1959年1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的《楚辞通释》,虽校点者王孝鱼知道且读过《楚辞通释》刻于康熙四十八年的单刻本,认为是“王敔刻的第一批遗书,现在南岳古典书库内还藏有一部(案:后归藏于湖南图书馆),大概是海内现存的珍本了”,但他没有用单刻本作底本,而是用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兄弟出资刊刻的金陵书局本作底本重刊,当然他更不知道湖南省社科院藏有一部完整无缺的藏本。至于省社科院藏本中的潘氏《船山先生传》,当年杨坚为《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之部》收录此传,却是从金陵书局本转录的,还为其末尾所署的“康熙己酉”系“乙酉”之误,大费了一番笔墨。综上所述可以判断,五种本中的《楚辞通释》并非重刻,而是合为五种本时,抽去了附件,只保留目录和正文的重印,时间当晚于康熙四十八年了。其原因,一是财力物力人力不允许。因为初刻时,是自康熙四十四秋丁光祺之子丁元稹赴武昌应试之后,丁光祺才与其弟丁锡极和船山同里后学王扬绪、王扬绩等四人联合出资校订,由王敔补校,历时四年刊刻完成的。至康熙五十五年王敔六十岁时,虽借助门生姻友之力“续捐资刊先子遗书数种”,但像《楚辞通释》这么费大功夫才能刊刻的书,不可能也无必要重刻,而只可能从简合刊。二是由于清朝文网的逐渐严密,王敔越往后越不得不虑患思危,而尽量减少直接暴露船山思想的《序例》《九昭》等(单刻本《序例》中也已涂墨掩去最为触目两句的六个字)。
五种本中除《楚辞通释》之外的其他四种,也大体情况相同,开卷即目录、正文,惟第一种《老子衍》卷首印有手写体字迹的董思凝《序》。如单刻本《庄子解》中,参与校订者的序、跋、附识等就都被抽去了。
从单刻本《庄子解》的邵阳后学宁瑛《跋》云“今岁杪,虎翁下访蓬室,以先生所注《正蒙》刊本见授,且曰《楚辞通释》方付剞劂,吾友丁吉士力也”,可知清康四十八年刊成《庄子解》《楚辞通释》时,《张子正蒙注》已有刻本行世。
与《书集》五种本的版框行款、卷端题署基本相同,且版式为九行二十字的,还有《夕堂戏墨》七种七卷,前五种《雁字诗》《落花诗》《和梅花诗》《洞庭秋》《前后愚鼓词》卷端均题“夕堂戏墨,男敔较,私淑门人曾荣向订梓”,后二种《仿体诗》题“夕堂戏墨,男敔较,资江后学曾荣旺授梓”,《南窗漫记》题“湘西草堂,男敔较,资江后学曾荣旺订梓”。曾荣旺是王敔的学生,他在此书跋语中说:“《仿体诗》为子船山先生《夕堂戏墨》之第五种,《南窗漫记》则先生辑生平之阅历赠答而手编之者也。……此二帙散见于遗书中,值诸叔侄弟较刊船山杂著,旺窃谓得此,可以识子先生之友于古今者矣。因请稿于蕉畦,合而授之剞劂。”B13所说“诸叔侄弟”,应是指前述曾载阳、曾载述兄弟与曾荣旺、曾荣向兄弟等叔侄辈,曾氏四人都曾协助王敔在湘西草堂校刊过船山杂著。
此外还有《王船山先生诗稿》三卷,即《船山自定稿》,上海图书馆藏本,存船山《五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各一卷,也是清康熙年间王敔的湘西草堂刻本。
以上所述各种,再加上王之春《船山公年谱》书末所载之《春秋世论》《四书稗疏》《四书考异》《思问录》四种,及近人孙殿起在其《贩书偶记》中自述所见之《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两种,又清代禁书目录所列之《夕堂戏墨》《船山鼓棹》《五言近体》《七言近体》等印本,则合计湘西草堂所刊船山著作可知者有27种之多(参考《船山全书》第十六册《杂录之部》)。
在康熙四十、五十年代,王敔编校、刊刻船山著作的过程中,为应清吏求船山书或请朝廷政、学大员作传、作序者,除有潘宗洛、张仕可之外,还有湖广提学道董思凝,于康熙四十八年访船山遗书,获读王敔所投《庄子解》的刻本,“且属为引其端”,于是而作的《庄子解序》,认为船山有得于《南华》之妙,故于内外诸篇,俱能辨其真赝。还有提督湖广学政李周望,是康熙五十八年科考首拔王敔为岁贡生的座师,后雍正间官至礼部尚书的大学者。他读到船山的《张子正蒙注》,并知道船山的其他一些著作,为之作《王船山先生正蒙注序》,“叹其于横渠之学,异世而同源”“尤于《正蒙》一书神会心契,独诣积久,诠释以成编,于清虚一大之旨,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靡不有以显微抉幽,晰其奥窔。则是芟芜辟径、发蒙养正者张子也,扶轮推毂、指津布筏者船山也。横渠之书,微船山而旨隱;船山之学,微横渠之书而不彰。两人旷代相感,一作一述,非如马迁所云颜渊之于夫子,附骥而名益彰者耶?”B14显然,李周望是真正研读《张子正蒙注》且有独特见解的第一人。可惜此序后来已不见于湘西草堂五种本《正蒙注》,而单刻本《正蒙注》更湮没失传,今天能读到的是杨坚转录自嘉庆二十五年《衡阳县志·艺文》所载的《序》。
同样录自嘉庆《衡阳县志》的,还有康熙五十七年任湖广学政的缪沅所撰《王船山先生书集序》。这是缪沅为《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所作的序,也是一篇读船山五种大著而纵论先生志行高洁的学术论文,“因得见先生之全书,大抵其事实,其志洁,其忧深;其事实故其论笃,其志洁故其道光,其忧深故其辞危以厉”B15。像缪沅与李周望这类论船山“其忧深故其辞危以厉”的序文,当然会随着清代进入雍正年间之后的文网渐密而被抽去,好在天不坠斯文,嘉庆《衡阳县志》还为我们保留住了。
从王敔在湘西草堂所刊行的船山著作及其所引来的诸多学者和亲友门人所作的序、跋、识语等,可见康熙四十至六十年间,船山著作的流布和影响之大,亦可见船山学兴起的这一阶段,“种学绩文,能世其先业”的王敔对此贡献之大。
三、作《大行府君行述》,使船山遗书得以入史馆,立传儒林
王敔是第一个给王船山作传记的人,正是因有了他所作的《大行府君行述》,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船山的生平、著作、志节和风貌,故其所撰《行述》是研究船山生平、著述及其思想最重要的材料。船山生前已自撰墓铭,按其遗嘱,“既有铭,可不赘作”《行状》,但他又说了“若汝兄弟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略纪以示后人可耳”的话。既可“略纪以示后人”,船山逝世已14年了,伯兄王攽也已去世,如今(康熙四十三年)自己跟随阅卷、学习的湖广学政潘宗洛老师又“详询先子始末,为立传以贻史馆”,所以王敔“不敢辞命”,便认真作了这篇《行述》。《行述》末尾的这段话,说明了王敔作《行述》的缘由,亦可见潘宗洛对船山的崇敬。
潘宗洛(1657—1716),字书原,江苏宜兴人。康熙三十七年进士,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任提督湖广学政,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任偏沅巡抚,再至湖南。有善政,重人才,识拔多士。康熙五十五年病卒。潘任湖广学政时于康熙四十三年孟夏在衡阳延俊才入幕,襄校试卷,王敔得以延入,也因此使潘宗洛获知船山,“尚有志尽读船山之书”。从他所撰《船山先生传》“余所得见于敔者,《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而已”,可知潘宗洛是真正读过船山这几部重要著作的第一位省外学者,他提出要为船山作传以贻史馆,王敔确实“不敢辞命”。
王敔所撰《大行府君行述》幸有船山八世孙王德兰在《王氏五修族谱》完成后,“于竹花园古箧内觅得老谱敔公所刊原牒”并“照抄无讹”的版本流传面世,而使我们得以见到迥别于同治金陵本《船山遗书》、光绪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及“道、同后续谱”中所载多种删节改易本之外的这一足本。此本《行述》的叙事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先介绍王夫之的各种名号及其家世,然后叙述船山的生平与著述。其生平事迹详于有关船山忠义名节的几件大事,如:为拒张献忠而“匿伯父,自刺身作重创,傅以毒药,舁至贼所”;欲调和堵、何,入南明效力,如何料败如神,在肇庆如何疏奸护国、一片孤忠;拒李定国之聘而作《章灵赋》以见志,后流亡各地隐居著述;又拒绝给吴三桂作劝进表而作《祓禊赋》,以及避兵山中,烽息返船山,对巡抚“受米返帛”,投逸民函致谢等等。其中尤于“亡考慨明统之坠也”之后,对船山的著述、思想及治学态度都作了全面而生动的介绍与评价,是研究船山极为重要的材料。行文至船山临终“年七十三”,成绝笔诗,自题遗像,自志其墓,及其忠义德行等,更使船山的特立卓行、音容笑貌等跃然纸上,真“勿坠先人之文翰家声也者”。
潘宗洛获读王敔这个“述事最详”的《行述》之后,对船山生平志节与著述情况自是若网在纲,了然于胸,对船山及其兄弟一门更为钦佩。如在他另撰的《刊江王氏家谱序》中所云:“船山先生与其兄石崖先生、叔稽先生,以孝友志节并著一时,而船山之著述等身,湘岳之逸也,真砥柱一代之伟人矣。”B16于是,潘氏本王敔之《行述》作《船山先生传》,介绍船山生平事迹,表述语言以史臣口吻,而文字更为简略,仅《行述》4100余字的四分之一强。该传较之《行述》,更为集中地介绍了船山的著述成就。其辞曰:“最后归游石船山,以其地瘠而僻,遂自岳阴迁焉。筑土室,名曰观生居,晨夕著书,萧然自得。作《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外传》《大象解》,《诗广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家说》,《左氏传续博议》,《礼记章句》,并诸经《稗疏》各若干卷。又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倚伏之原。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作《正蒙》释义,《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以阐天人性命之旨,别理学真伪之微。又以文章莫妙于《南华》,词赋莫高于屈宋,故于《庄》《骚》尤流连往复,作《庄子解》《庄子通》《楚辞通释》。又著《搔首问》《俟解》《噩梦》各种,及自定诗集、评选古今诗、《夕堂永日绪论》,注释《老子》《吕览》《淮南》各若干卷。自明统绝祀,先生著书凡四十年而终。”B17可说是对船山著述第一次最集中而全面地列举书目。最后以“赞曰”形式悲叹船山的“终摈不用,隐而著书”曰:“以先生之才,际我朝之兴,改而图仕,何患不达?而乃终老于船山,此所谓前明之遗臣者乎!及三桂之乱,不屑劝进,抑又可谓我朝之贞士也哉!”B18这“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也就成了史官对船山一生的盖棺论定。
从王敔《行述》与潘氏《传》的落款,可知皆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前距船山去世已有14年。《行述》载于家谱,潘《传》入于史馆,于是并为传述船山生平学问志业的最初文献,而为后世所珍。然自此之后,随着清朝文网的逐渐严密,历雍正而至乾隆朝,始有翰林院检讨兼三通馆纂修的余廷灿(1729-1798)据潘宗洛《船山先生传》而作的《王船山先生传》。余《传》记船山的生平事迹,实际上是节抄潘氏《传》,而于某些细节略有不同。其特点是大段引用船山《张子正蒙注自序》,推重船山学术之精,最后以赞语评论了船山的思想和人品,并希望史馆能“立文苑儒林之极”,以推阐船山。嗣后阮元任职史馆,奉命草拟《国史儒林传稿》,其写船山的传稿虽字数不满400,且系抄录《四库提要》和余氏《传》,但船山自此有了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的学术地位,则是自阮元《儒林传稿》论定始。总而言之,清代关于船山的传记,自王敔所撰《行述》和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后,便没有也不可能再出现超出其右者。船山著作后来得以入史館,编入《四库全书》以及船山在乾隆年间列入儒林立传,均肇始于此。
正因为王敔的学行和对其父船山学的弘扬,刊于雍正十一年(1733)的《湖广通志》卷五十七《人物志·文苑》中,已为王敔作传记载:“王敔,衡阳岁贡生,孝亷王夫之子。年三十始应试,为诗文高卓,敦尚气节,督学咸器之,修府志,垂成,卒。”大概出于政治原因,该《人物志》却没有王敔之父王夫之的传记,仅在卷三十五《选举志·举人》的“崇祯十五年壬午乡试榜”下,有“王夫之,衡阳人”的记载。
【 注 释 】
①②王敔:《大行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6、74页。
③王敔:《怀音草自题》,《船山全书》第十六册《杂录之部乙》,同上版第528页。
④王敔:《湘西草堂记》,同上版第523页。
⑤《老子衍自序》,《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同上版第16页。
⑥⑦⑧《庄子解·附录》,《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同上版第482、481、481页。
⑨B13 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丛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6页。
⑩B11 夏剑钦:《张子正蒙注编校后记》,《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同上版第393、394页。
B12B14B15B16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杂录之部》,同上版第402、398、400、521页。
B17B18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楚辞通释》湘西草堂刻本。又见《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之部》,第88、89—90页。
(编校:夏剑钦 余学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