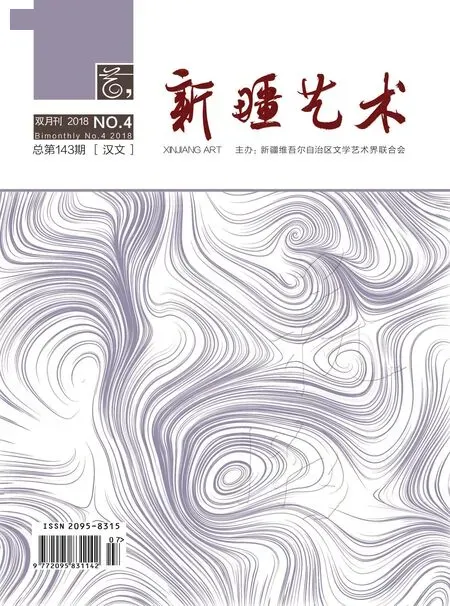二十世纪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发展的三种思潮
2018-10-27崔斌
□崔斌

音乐思潮指的是在某历史阶段中对音乐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潮流,它有三个要素:一是与音乐实践密切相关,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该时段的音乐实践活动;二是有思想的成分,即受到了某种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某种社会思想在音乐中的反映;三是具有潮流性,即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音乐思潮的表现多种多样,可以说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较为流行的音乐品种、乐曲风格等皆可作为判定音乐思潮的指标。但能够从整体上、最为直接反映整个音乐学科发展脉络的指标当属由著名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当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作品、成果集中出现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时,一定意味着受到了主流音乐思潮的影响。笔者拟通过梳理百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性音乐作品和重要音乐研究成果,并结合笔者的学术调研来揭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百年音乐发展的三次重要思潮。
本文仅针对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和与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学术密切相关的苏联学者的成果,试图从该国音乐学科的内部视角展开研究。
一、收集整理民间音乐的思潮
十月革命之后,吉尔吉斯斯坦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大批优秀的苏联音乐家开始走进吉尔吉斯斯坦从事民间音乐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最早收集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音乐的是俄国学者А·扎塔耶维奇,他的工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多部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和参考意义的作品集和研究著作:出版较早的是193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250首吉尔吉斯器乐曲和歌曲》和《173首吉尔吉斯库姆孜琴、科亚克琴、楚尔、铁木尔库姆孜曲谱》①;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出版于1971年,分别为包含428首器乐曲和歌曲的《吉尔吉斯器乐曲和民歌》(1971)与《苏联各民族民间歌曲》(1971),后者除了包含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音乐,还涵盖许多苏联境内其他民族的民间音乐资料。
А·扎塔耶维奇还利用资料的便利率先对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音乐展开了系统研究:一、确定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音乐的分类体系,按题材划分为劳动歌曲、礼仪歌曲、抒情歌曲等;按乐种类型划分为民歌、阿肯弹唱、器乐曲(奎依)等;二、明确了传统民间音乐的调式,认为混合利第亚大调是最为常见的,同时还有伊奥尼亚调式、爱奥利亚调式、多里亚调式和变化多端的交替调式;三、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音乐在整体上拥有建立在混合或单独的七声音阶基础之上的稳定调式体系。由于А·扎塔耶维奇开展民间音乐收集与研究的时代较早,记录设备较为简陋,很多辨音工作只能靠其出色的听觉来完成,因此他收集的音乐资料难免有旋律标记不清、歌词纰漏等瑕疵,但这些问题不能掩盖他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和取得的卓越成就,著名学者В·维诺格拉多夫评价说:“他记录的吉尔吉斯民歌和器乐曲具有典范意义,至今仍然是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音乐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音乐家、作曲家,都能从这些优秀作品中获得启发和灵感。”②

采访吉尔吉斯斯坦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别格里耶夫·木拉提
苏联时期另一位收集民间音乐的巨匠是В·维诺格拉多夫。他的代表性成果有:《100首吉尔吉斯歌曲和器乐曲》(1958)、《托克托古勒的音乐遗产》(1961)、《托克托古勒和吉尔吉斯阿肯》(1952)、《吉尔吉斯民间乐人》(1952)。
《100首吉尔吉斯歌曲和器乐曲》收录了民歌,《丰收歌》《牧歌》等与宗教信仰及萨满遗存有深刻联系的礼仪歌曲,史诗《玛纳斯》的精彩片段,以及1940至1952年间由作曲家或民间艺人创作的库姆孜和科雅克器乐曲等作品,即这部曲集实际涵盖了吉尔吉斯斯坦所有种类的传统民间乐曲和自十月革命至上世纪60年代间改编或新作的各类民间乐曲。《托克托古勒的音乐遗产》和《托克托古勒与吉尔吉斯阿肯》是关于著名阿肯托克托古勒的研究著作。托克托古勒(1864—1933)是吉尔吉斯斯坦最为著名的民间乐人之一,也是一位坚定的苏维埃支持者,他掌握了包括牧民音乐在内的几乎全部的传统曲目,为传统民间音乐尤其是“哭丧歌”这种仪式音乐的传承起到了关键作用,被认为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转型时期(十月革命社会主义转型时期)最杰出的民间音乐家。《托克托古勒的音乐遗产》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1-18号)收录了А·扎塔耶维奇《250首吉尔吉斯器乐曲和歌曲》中由托克托古勒在1928年表演的作品;第二部分为第19-101号,由В·维诺格拉多夫亲自记录,是托克托古勒的学生们在1940年5月至7月和1956年10月至12月间通过回忆表演的。《托克托古勒和吉尔吉斯阿肯》《吉尔吉斯民间乐人》是对包括托克托古勒和库热尼凯耶夫·穆热塔勒③在内的各类民间艺人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是考察吉尔吉斯斯坦民间艺人历史、早年艺人生存状况、民间音乐传承方式和传承体系的重要成果。
此外,В·维诺格拉多夫还记录了多支由库姆孜演奏的结尾曲,更为全面地展示了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音乐的面貌。相对А·扎塔耶维奇收集的作品,В·维诺格拉多夫收录的资料更为精确:具有准确的节拍标志和歌词,更为符合现代民族音乐学的要求和规范。
对民间音乐作品的收集和整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即对史诗《玛纳斯》的记录整理。《玛纳斯》无疑是中亚地区最重要、最典型的英雄史诗。对《玛纳斯》的系统记录和研究亦始于上世纪20年代。④最早对《玛纳斯》进行系统记录的工作开展于1922到1926年间,是对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⑤版本的记录。他演唱的《玛纳斯》第一部版本长达25000行,是迄今最为完整的一部。1947年,В·维诺格拉多夫在玛纳斯研究者依布拉音·阿布多热合玛诺夫(他曾为奥诺孜巴克夫的表演录音)的帮助下,记录下了这个版本的音乐。
苏联时期另一位著名玛纳斯奇是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⑥,他在1935—1947年间,他完整地记录了一套《玛纳斯》(400000行,包括英雄玛纳斯、玛纳斯儿子赛麦台依、玛纳斯孙子赛依台克三部分),以及一首关于叶儿·吐什托克⑦的史诗。萨雅克拜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完整地表演了《玛纳斯》故事的续篇,即以赛依台克的儿子凯耐尼木,以及凯耐尼木的两个儿子阿勒穆萨热克和库兰萨热克为主人公的篇章。萨雅克拜是在无乐器伴奏的情况下表演的,其音乐由В·维诺格拉多夫记录。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调查时观察到,比什凯克中央广场、国家歌剧院门口、各地州的广场、花园中都能看到萨雅克拜的雕像和画像,彰显着他崇高的文化地位,艺术作品中他那高昂的头颅和向上翘起的胡须更成为当代吉尔吉斯人文化自信的典范。
自十月革命至上世纪50年代,全面收集民间音乐的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产出了一大批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对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全面收集民间音乐的主力军是苏联学者,但这项工作在民间艺人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俨然成为十月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思潮:苏联学者遍访国家的各个角落,几乎收集了全部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作品;众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艺人则毫无保留地积极配合。在二者的通力合作下,吉尔吉斯斯坦的民间音乐得以较为全面地记录,促使流传于民间的口头音乐成为书面化的曲谱,为其它音乐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同时,还对吉尔吉斯斯坦民间音乐进行初步整理和研究。
二、苏联化思潮
十月革命之后,吉尔吉斯斯坦成为苏联的一部分。苏联政府迫切需要了解境内各民族文化,因此派遣大量学者、艺术人才走入吉尔吉斯斯坦(二战期间,苏联政府为了保护艺术人才,亦曾安排大量科学家、艺术家到伏龙芝避战),学者和艺术家的到来将苏联的音乐制度、音乐教育体系完整地带入吉尔吉斯斯坦;另一方面,通过加盟苏联,吉尔吉斯斯坦跨越性地完成了从奴隶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转变,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从政府到群众的各个阶层都对苏联文化产生了膜拜之情,开始在热切宣传革命、讴歌新生活的过程中积极学习苏联音乐文化。在双方的共同意愿下,苏联的音乐体系迅速完整地移植到吉尔吉斯斯坦,引领了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学科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最重要的表现有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专业的音乐院校,将苏联的音乐教育模式完全复制到吉尔吉斯斯坦,培养专业音乐人才。二是在收集民间音乐和将民间音乐运用到音乐教育、舞台表演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吉尔吉斯传统民间音乐的改造工作,以及对民族乐器的改良工作(即对乐器的材质、形制、定弦标准、音域、演奏技巧等方面加以规范和统一,并按高、中、低声部改造民族乐器,建立符合西方管弦乐编制的民乐团等)。三是通过表演苏联著名作品,或创作以民族文化元素为灵魂的作品等方式,引入交响乐、歌剧、芭蕾舞剧等音乐品种,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品种和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以上三方面工作促使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学科迅速完成了近、现代化,因此,本文将这一时期的发展思潮称之为“苏联化思潮”。

采访青年库姆孜奇扎科尔别克·都沙别

与木卡沙·阿布都拉耶夫专业音乐学校师生座谈合影
苏联化思潮的迅猛进展从一份年表中便可得知:十月革命期间,吉尔吉斯斯坦便出现了大量革命宣传队,借助苏联的文艺宣传手法发动群众,鼓舞革命。至1926年,在伏龙芝成立了第一所专业音乐学校——戏剧艺术学校。1928年比什凯克工人剧院建成。1936年,比什凯克音乐剧院建立。同年,交响乐团和交响乐爱好者协会成立。1939年,作曲家协会和音乐家协会成立。1942年,音乐剧院扩建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歌剧院,成为各类音乐表演的中心。1955年,芭蕾舞剧院建成。在此期间,各州市的音乐机构和民间团体也相继成立,至今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一)歌剧和芭蕾舞剧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后,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音乐体裁——“音乐剧”,其本质是对传统民间作品进行政治性加工,并用于政治宣传。1939年,阿布都拉斯·玛勒德巴耶夫、费拉索夫·弗拉基米罗维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尔·吉欧吉维奇·费雷共同创作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一部歌剧《美丽的月亮》,改编自一个吉尔吉斯斯坦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1940年,费拉索夫和费雷又共同创作了吉尔吉斯斯坦第一部芭蕾剧《阿纳尔》,以及歌剧《玛纳斯》。后者与《美丽的月亮》一起被视为吉尔吉斯剧作的瑰宝。
阿布都拉斯·玛勒德巴耶夫⑧,吉尔吉斯斯坦著名剧作家,他的创作生涯始于1922年,一生创作了3300多首作品,其作品《斯都切得尔玛多什》具有国歌地位,另外儿童歌曲《库鲁弄》《吉尔德日木》,合唱曲《艾穆盖克玛什》,民歌《古丽都尔穆什》《乌库杰尔居孜》等亦非常著名。玛勒德巴耶夫对吉尔吉斯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非常了解,他的作品往往触及到民族精神的精髓,并且善于融合民族和西方音乐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种类,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学者先琴科曾将玛勒德巴耶夫的创作与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音乐和苏联音乐进行了综合比较,并对玛勒德巴耶夫进行高度评价。⑨
该时期其它歌剧创作还有纳斯尔·道列索夫的《库尔曼别克》,穆卡什·阿卜德热耶夫的《暴风雨之前》《乌勒卓拜》《柯西木江》,阿合玛特·阿曼巴耶夫的《阿依达尔和阿依夏》,萨特勒汗·乌斯莫诺夫的《赛依丽》;芭蕾舞剧有米哈伊尔·劳赫维杰的《乔丽盼》等。
(二)西洋音乐方面,不得不提到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舒宾(1894-1948),他毕业于圣彼得堡高级音乐学院,是第一批来到来吉尔吉斯斯坦的苏联音乐家之一,并于1928年定居伏龙芝。他知识渊博,富有热情,还对东方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组织建立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一个专业乐队,并借助乐队向参与者传播西方音乐知识和理论,对苏联音乐文化的传入及吉尔吉斯斯坦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玛勒德巴耶夫等第一批著名的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家皆曾参与他的乐队活动,并从中受益无穷。20世纪50年代,一批从莫斯科专业院校毕业的人才进一步扩充了这一阵营,这便包括吉尔吉斯斯坦著名音乐家塔什坦·叶尔玛托夫,穆凯·阿不德热耶夫等。在苏联音乐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音乐家的共同努力下,涌现出费拉索夫创作的大量吉尔吉斯民族风格的序曲,尼古拉夫·热克夫和图列耶夫创作的交响乐作品,朱玛巴耶夫的史诗交响乐,V.居苏耶夫的中提琴协奏曲,阿曼巴耶夫、叶儿玛托夫、S·阿依提凯耶夫合作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吉勒德孜·玛勒德巴耶夫创作的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等著名作品。
(三)20世纪50到70年代,吉尔吉斯斯坦还走出了卡里·莫勒多巴散耶夫⑩。别格里耶夫·木拉提[11]等著名音乐家,这些后起之秀进一步延续了“苏联化思潮”。
卡里·莫勒多巴散耶夫是吉尔吉斯著名剧作家、作曲家,其最为著名的作品是1976年创作的戏剧《母亲大地》,该作品曾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多国演出,堪称开辟了吉尔吉斯斯坦艺术的新领域。凭借这首作品,莫勒多巴散耶夫在1976年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项,并在1979年获得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他的其它作品还有《一瞬间》《神奇的即兴表演》《在玛纳斯的阵营中》《曼库特的传说》《我们是欢乐的儿童》、芭蕾舞剧《继艾特玛托夫之后》等。
著名作曲家别格里耶夫·木拉提现任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学院院长。他在创作方面善于将各类艺术形式与本民族传统元素进行巧妙结合,其代表作有音乐剧《白色的帆船》、音乐童话剧《木板路》,交响乐《玛纳斯》《启示录》,弦乐四重奏《吉尔吉斯之歌》,钢琴曲《老人的回忆》等。1993年,他参与建立吉尔吉斯国立音乐学院,并成为该校教授、校长。2016—2017年间,笔者曾先后两次赴吉尔吉斯斯坦国立音乐学院对其展开深入访谈。在笔者眼中,作为一名深受前苏联音乐模式影响的作曲家、教育家和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别格里耶夫·木拉提具有国际化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气度,他既延续了前苏联的音乐教育体系,扎实推进学生基础素质的培养;又频繁赴欧美、亚洲考察他国的音乐教育经验,将新的元素不断融入到音乐教育中;同时注重振兴吉尔吉斯民族音乐,结合自身善于挖掘吉尔吉斯传统民族音乐特质和精髓的特点,在创作方面提倡本民族传统音乐元素的创新化。
总之我们可以将上世纪20年代直至上世纪80年代称为吉尔吉斯斯坦音乐的“苏联化”时期,学习苏联音乐和利用苏联音乐的经验改造吉尔吉斯斯坦的传统民间音乐是这一时期音乐发展的主要思潮。这一思潮是当时苏联音乐家和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家的共同心声,在双方的合作与努力下,吉尔吉斯斯坦的音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系统地奠定吉尔吉斯音乐学科的基础。
三、苏联化思潮对民间音乐发展的制约
虽然学习苏联的思潮在整体上促使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学科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也极大地改变了民间音乐的原生环境,使民间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它在自然环境下的发展方向。这种改变的根源在于民间音乐传承方式和表演环境的改变。
在苏联之前,民间音乐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其样态具有一定的活性,即在传授和表演的时候具有较强的即兴成分,而即兴成分是民间音乐在自然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出新的动力和源泉。以库姆孜曲为例,在口传心授的自然状态下,同一首库姆孜曲被不同艺人表演时,甚至同一艺人在不同场次的表演中,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便导致观众所听与学习者所学的音乐并不固定。听众可以选择切合自己内心的表演作为心中判定表演高下的标准,学习者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音乐进行适度的发展。流传至今的传统曲目正是在这种传承方式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的。
苏联时期,民间音乐离开了原生的游牧环境,走入了专业化的音乐教育和剧场等各类舞台,原有的传承方式和表演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民间音乐在自然环境中的即兴性质显然无法满足专业音乐教育的需要,因此它们被谱写成了乐谱,具有了固定的形态。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舞台表演,库姆孜奇不断创新出花样百出的新鲜手法,以翻飞的手式花样吸引观众的眼球,制造了精彩的舞台效果,比如当今最为著名的青年库姆孜奇扎科尔别克·都沙别,他曾连续5次获得国家库姆孜大奖赛的冠军,代表了当今吉尔吉斯斯坦库姆孜的最高水平。笔者曾在吉尔吉斯斯坦对其进行过三次专访,他自豪地介绍道,他的住房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奖励的。他表演的《夜莺》具有繁复而精彩的手法,翻飞的手指就像一个美丽舞者,具有超强的震撼力。他告知我们:《夜莺》一曲已有百年历史,为了增强舞台效果,他在继承传统表演手法的同时不断增加、美化原有的表演手法,使其更具观赏性。有的吉尔吉斯学者并不赞同这种一味注重视觉效果、忽略听觉效果的表演方式,认为这种表演方式实际影响了传统库姆孜曲以音声动人的美感和对曲目感情的抒发。而笔者认为,这些反对的声音正反映出了舞台化表演对传统民间音乐造成的冲击。
苏联时期还实行过某些抵制民族文化的政策,或者在宣传层面有意贬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民族音乐的发展,《玛纳斯》在苏联时期的境遇可谓典型:上世纪50年代,《玛纳斯》表演被定义为一项“业余爱好者”活动,苏联虽没有明确禁止玛纳斯的表演,却在意识形态上贬低其价值和内涵。笔者在吉尔吉斯考察期间,曾采访著名玛纳斯奇、《玛纳斯》研究博士、玛纳斯基金会秘书长巴科齐耶夫·塔朗塔里,他为我们讲述:“记得初中时,老师让我在节日晚会上演唱《玛纳斯》,我便演唱了玛纳斯的诞生部分,我觉得我唱的很好,但却受到了大家嘲笑,他们认为是过时的东西”。《玛纳斯》之所以会遭遇此命运,与其本身的“宗教”色彩及其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有关。[12]其实不唯《玛纳斯》,在苏联时期,许多中亚史诗都被压制了,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史诗作品,比如乌兹别克斯坦便产生了一种用大段诗歌赞颂列宁、斯大林和集体化的史诗作品。这些“新型”史诗仍旧使用传统的表演方法,才使中亚史诗的表演传统不至断绝。
可以说,苏联时期引入的新型音乐发展模式和乐种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扩充了吉尔吉斯人民的视野,但也制约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导致部分学者一度认为只有苏联引入的音乐才是现代的、艺术的,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则是“原始的”,这样的心态集中反映在苏联时期的音乐史著作中:巴勒拜·阿拉古什夫的《吉尔吉斯音乐历史》(1989)是一部较为普及的音乐史教科书,它将苏联时期的音乐历史细致地划分为几个阶段,但对苏联以前的传统民间音乐却仅有一段单薄的概述;萨利耶夫则在他的《吉尔吉斯艺术史》(1971)中提出:吉尔吉斯的音乐经历了一次跨越式、革命性的发展历程,而这种变化是受外来文化、尤其受苏联音乐的影响而发生的。
四、民族意识复兴背景下的民族化思潮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苏联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思想控制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民族意识的复兴。这种民族意识体现在当今吉尔吉斯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比什凯克市为例:苏联功勋雕塑和油画被玛纳斯、以及著名玛纳斯奇等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像和画像取代;许多原以苏联英雄命名的城市街道皆改用民族英雄的名字;不再使用卢布作为货币,改用索姆,且货币上的人物皆换作本民族的历史名人等等。但若认真思考不难发现,雕塑和油画是由苏联传入的;城市的街道基本上是苏联帮助建造的,并且大多还保留着它们最初的样子;即便货币,也是由苏联引入的。正因吉尔吉斯斯坦的近、现代化是在苏联时期下完成的,所以苏联文化已然植根于每一个现代吉尔吉斯人的血液中。音乐方面也是如此,当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音乐学科体系几乎全是苏联模式的,因此当复兴的民族意识试图寻找突破时,必然会遭遇诸多困难。
走在比什凯克的大街小巷,探访国立音乐学院、木卡沙·阿布都拉耶夫专业音乐学校[13]等,皆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吉尔吉斯斯坦音乐仍延续着由苏联引入的体系:《喀秋莎》《山楂树》《毕业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等苏联歌曲仍在传唱;苏联引入的手风琴、钢琴等西方乐器的表演非常盛行,库姆孜、科雅克等民族乐器的表演则延续着被苏联改造、规范后的模式。音乐教育方面,以木卡沙·阿布都拉耶夫专业音乐学校为例,该校开设有:(1)钢琴(2)弦乐(3)管乐和打击乐器(4)音乐理论(5)音乐教育(6)钢琴伴奏及室内音乐(7)吉尔吉斯民族音乐等专业。民族音乐专业所占比例非常小,且仍沿袭苏联传入的教育模式。[14]

作者与《玛纳斯》研究博士、玛纳斯奇、玛纳斯基金会秘书长巴科齐耶夫·塔朗塔里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民族意识的复兴,一大批学者开始关注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音乐的民族特征和生成民族特征的文化土壤,试图从学术角度证明吉尔吉斯的传统民间音乐既不“原始”,也不“落后”,更非西方音乐的附属品,它应与其它国家、民族的音乐一样,被视为世界音乐的一部分。
较早从事民族音乐工作的是康奇别克·都沙里耶夫院士,他在1982年出版的《吉尔吉斯民间歌曲》(1988)一书中,从调式体系、旋律结构、曲式结构,以及民族歌曲与民间诗歌的关系方面详细分析了吉尔吉斯传统民间音乐的特点;其《吉尔吉斯民歌的体裁和历史》(1993)的研究对象则是民歌、仪式歌、库姆孜弹唱、民间说唱等不同体裁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历史发展。
苏巴纳里耶夫《吉尔吉斯的民间乐器》(1986)对吉尔吉斯体鸣、膜鸣、管乐器等各类传统乐器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考证了“库姆孜”“科雅克”等传统乐器名称的词语来源;一方面从人类学角度阐释了乐器起源的社会背景,以及乐器应用、发展的社会环境。巴特玛·克别阔瓦《吉尔吉斯—哈萨克民间歌手创作比较研究》(1985)将吉尔吉斯和哈萨克音乐放置于草原文化的背景下,并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另一部著作《吉尔吉斯民间歌手的历史概况》(2009)详细考证了吉尔吉斯民间歌手在不同历史阶段,包括苏联时期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巴亚斯坦·伊萨·克夫《仪式歌的艺术特点》(2003)有机地将吉尔吉斯民族仪式与音乐联系起来,着重考察音乐和仪式的关系、音乐在仪式中的作用及意义等问题。R·Z·克德尔巴耶娃《吉尔吉斯口头文化的形成史》研究了包括说唱、弹唱在内的民间口头文化的历史。此外,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几乎每一首吉尔吉斯器乐曲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背景故事[15],阿散·卡依比勒达《吉尔吉斯民间歌曲的传说》(2000)和布达依别克·萨布尔《讲唱艺人与民间故事》(2008)便是对歌曲背景故事的收集和研究。舞蹈方面,罗别尔特·哈桑诺维奇《吉尔吉斯民间舞蹈》(1991)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吉尔吉斯族传统舞种的动作、内涵等。在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还举办了旨在保护传统音乐的学术会议,再次强调了民族音乐保护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此次会议的论文集由阿曼诺娃整理出版。[16]
音乐史方面,切列德尼琴科·达吉雅娜·瓦斯列维娜的《古代音乐文化》(1996)将音乐纳入了“民族文化”这个更大、更具底蕴的范畴中,试图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来阐释本民族音乐的“独特性”;巴拉巴依·阿拉古少夫的《吉尔吉斯百年弦乐》则研究了百年吉尔吉斯弦乐的演变,并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苏联思潮对吉尔吉斯弦乐带来的影响。
史诗《玛纳斯》的演唱也具有音乐性质,因此关于《玛纳斯》的研究也往往与音乐有关。后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大力弘扬史诗《玛纳斯》和玛纳斯精神,《玛纳斯》研究也因此迎来了一个新高潮。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艾山吐尔·阿布都德力德耶夫《史诗<玛纳斯>的历史层次》(1999),阿依聂克·加依纳阔瓦《史诗<玛纳斯>的封建因素》(1997),萨马尔·本萨耶夫《部落时期的史诗<玛纳斯>》(1999)等,这些研究皆部分涉及了音乐的内容。莫勒多哈孜耶夫《卡尼凯的骏马与托泰如一同奔驰——著名玛纳斯奇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表演艺术——附乐谱》(比什凯克,1995)和巴勒拜·阿拉古什夫《玛纳斯的音乐》(1995)是专门针对《玛纳斯》音乐的研究。而关于《玛纳斯》的两次国际会议论文集《玛纳斯史诗一千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阿斯卡尔欧夫编著,1995),《史诗<玛纳斯>的问题研究》(阿依聂克·加依纳阔瓦编著,1999)也收录有关于《玛纳斯》音乐的研究文章。
以上研究成果皆是民族意识复兴思潮的产物,其中既有专门研究音乐的著作,也有关于文学、口头传统等其它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说明民族意识复兴的思潮并非仅出现于音乐学科,而是各个学科普遍存有的一种思想状况。在该思潮的影响下,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主要特征是:往往回避苏联音乐的影响,注重强调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音乐的民族属性。
另一方面,民族意识复兴思潮主要得到了部分民族音乐家和民族音乐研究者的共鸣,并非所有音乐人都支持这一思潮;且这一思潮主要在学术研究层面发生影响,还未从根本上改变音乐表演和音乐教学实践以苏联音乐模式为基础的状况。但随着近年民族意识的升温,从学者到普通民众,从老师到学生,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人都逐渐受到了该思潮的影响,因此恢复民族传统的尝试会在学者的推动下不断上演。
注释:
①库姆孜琴是一种三弦弹拨乐器;科亚克琴是二弦拉弦乐器;楚儿(又译作“潮尔”)是草本植物制作的吹奏乐器;铁木尔·库姆孜是口弦,有木制和金属制两种。
②B·维诺格拉多夫《A.扎塔耶维其和吉尔吉斯民间歌曲和器乐曲》,莫斯科,1971年,第30页。
③ 库热尼凯耶夫(1860—1949),著名民间艺人。出生于一个民间艺人世家,其祖父别列克和他的父亲库热尼凯(1826—1927)都是著名的民间艺人。他从小就学会了库布孜、科雅克、潮尔等多种民族乐器,他的科雅克技艺尤其高超,可以模仿诸如动物哭声、雷电风等自然音声以及部分人类语言的声音,民间流传着“库热尼凯耶夫的科雅克琴声可以说话”的谚语。库热尼凯耶夫几乎传承了所有类型的传统民间音乐,尤其在传承仪式音乐方面贡献突出。
④19世纪50年代,哈萨克学者乔坎·瓦利汗诺夫和著名俄国德裔学者拉德洛夫便开始收集《玛纳斯》,两人记录了史诗片段《阔阔拖依汗的祭奠》,并对其展开学术研究。但《玛纳斯》更为集中、系统地记录始于十月革命之后。
⑤奥诺孜巴克夫(1867—1930),著名玛纳斯奇,在年少时就曾听过别勒穆拉提·库勒玛诺夫(1793-1873)等杰出玛纳斯奇的表演,这对他后期个人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帮助。与其他史诗表演者不同,奥诺孜巴克夫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在幼年便以即兴诗歌创作而知名。他演唱的版本长达25000行,是迄今最为完整的《玛纳斯》第一部的版本。
⑥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1894—1971),著名玛纳斯奇。他曾跟随同乡著名玛纳斯奇乔依凯·吾木尔欧夫(1863-1925)学习,并在1924年成为一名玛纳斯奇。
⑦叶儿·吐什托克:吉尔吉斯古代民族英雄。至今流传着以其为主人公的史诗《叶儿·吐什托克》。
⑧ 阿布都拉斯·玛勒德巴耶夫(1907—1978),吉尔吉斯最为杰出的作曲家和歌唱家之一,被认为是吉尔吉斯现代音乐的奠基人,1930年开始任伏龙芝音乐学院院长,1939—1967年间任吉尔吉斯作曲家协会主席,1953—1954年任吉尔吉斯音乐芭蕾舞学校校长,期间于1940—1947年在莫斯科音乐大学学习。他的女儿吉勒得孜(1946.6—)被认为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位女性作曲家。
⑨先琴科《玛勒德巴耶夫的歌曲创作》,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1977年。
⑩卡里·莫勒多巴散耶夫,吉尔吉斯著名作曲家,1928.9.28生于纳伦州铁列克的一个著名阿肯家庭。在童年时期,他便可以演奏多种民族乐器。成年后,他进入吉尔吉斯国立音乐与舞蹈学院学习指挥和编舞。之后他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指导老师为金兹布尔克,并于1954年毕业。1966-1973年间,他成为吉尔吉斯国家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的主要指挥和吉尔吉斯作曲家协会(1979-1997)的核心。
[11]别格里耶夫·木拉提,1955年出生于纳伦州敏库什村,他先后就读于以M·阿伯德拉耶夫命名的音乐小学、伏龙芝市国家音乐专业学校、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艺术学院等,自1977年开始,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就读本科和研究生,先后学习过单簧管、小号、钢琴、音乐理论、作曲等专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音乐创作便在整个苏联中崭露头角,并曾先后荣获以托克托古勒命名的国家音乐大奖、“玛纳斯”奖等国家级奖项,及俄罗斯、德国、瑞士等国颁发的国际奖项。
[12]史诗《玛纳斯》表演的宗教性质体现在多方面,比如玛纳斯奇往往是通过英雄托梦的形式走向表演生涯的;在表演时,他们的精神联系于另外一个世界,并会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玛纳斯》表演还会影响听众的情绪,将听众引向狂热等。《玛纳斯》和玛纳斯奇对于吉尔吉斯族还有着特殊的意义:《玛纳斯》在民族中扮演族谱的角色,其歌词中含有大量民族信息,有强烈的民族标志性;玛纳斯奇往往具有高度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甚至充当着部族的精神领袖,这些无疑都有悖苏联的政治需要。
[13]该校是目前吉尔吉斯斯坦最为著名的音乐学校,几乎当今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音乐表演和理论家均出自该校。
[14]目前吉尔吉斯斯坦从小学至研究生教育所用各等级教材均为“五线谱”教材,比如玛德维洛娃·丽玛、安德列·吉欧吉维奇·库兹涅佐夫《吉尔吉斯铁木耳库姆孜教材》(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部铁木儿·库姆孜教材,伏龙芝,1988),努拉合·阿布都热合曼《阿布都热合曼·诺夫乐曲作品集》(比什凱克,2009),未署名《吉尔吉斯斯坦儿童音乐学校教程》(比什凯克,2003)等。
[15]游牧民族器乐曲既有单纯的器乐演奏,又有弹唱曲目,前者往往有背景故事,后者往往有引言或序曲。
[16]阿曼诺娃等《传统音乐的历史、保护与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比什凯克:Kyrgyz National Conservatory,2004年。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