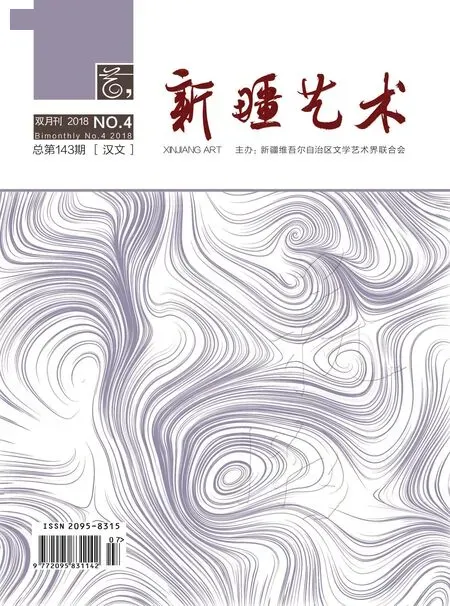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回顾与现状调查
2018-10-27赵莉
□赵莉

远眺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七公里木扎提河(渭干河)北岸、却勒塔格山对面的明屋塔格山断崖上。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339个,壁画近4000平方米,以及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石窟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8~9世纪,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它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我国四大石窟。
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流失的历史回顾
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来克孜尔石窟考察探险。伴随着考察与探险,这些探险队或多或少地都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过壁画等珍贵文物,其中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剥取的壁画最多。
(一)俄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活动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第38窟左甬道券顶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①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自一人之手。根据题记推断,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1905年,俄罗斯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为进行地理勘察,派遣M.M.别列佐夫斯基(М·М·Березовский)和其堂弟 H.M.别列佐夫斯基(Н·М·Березовский)带领考察队前往新疆库车。考察队于1906年2月6日抵达,之后考察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古龟兹地区的多处遗址。此次考察揭取了克孜尔第60窟的部分壁画。
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由俄罗斯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资助,印度学、佛教艺术史和新疆古文字专家С·Ф·奥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率领探险队两次再赴新疆进行考察。这次考察涉及古龟兹地区多处遗址,期间在克孜尔石窟逗留数日,调查了德国考察队揭取壁画后的洞窟。此次调查报告《1909至1910年俄国新疆探险考察初步简报》公布于1914年。②这次考察揭取了克孜尔第198窟、第198A窟和第199窟的部分壁画。③
俄国探险队在新疆收集的文物,先于1910年收藏在圣彼德堡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并有简要编目。后于1931~1932年,移至圣彼德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自1935年起开始部分展出。展品包括壁画、绘画、陶器、约上百件写本、照片以及遗址的考古草图等。
现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共收藏俄国探险队从新疆带走的文物2000余件,其中出自库车的文物800余件,里面有79件为壁画残片,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有10余件。

对鸟联珠纹 克孜尔第60窟(现藏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降魔变 克孜尔第198窟(现藏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佛经故事画 克孜尔第199窟(现藏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二)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3年4月7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拜城。4月10日到达克孜尔乡村庄的当天,从村民那里得知有明屋(即克孜尔石窟),立即冒沙暴前往。当晚渡边哲信和堀贤雄返回村庄,偶遇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的格伦威德尔一行,但并未向格氏透漏当天去克孜尔石窟的消息。④4月15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再次到达克孜尔,16日开始工作,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有洞窟性质、形状、壁画内容、保存状况和当时农民使用洞窟的情形,并且在部分洞窟中揭取壁画。同时,他们在洞窟中还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最为重要的要数“孔目司文书”以及唐代龟兹语寺院帐历MS00541(大谷文书五四一号)的发现。⑤23日,他们带上十几件壁画、若干出土品以及行李,在众人护送下前往库车。大谷探险队首开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先例。
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发掘了13个洞窟。⑥克孜尔第206窟甬道侧壁的部分菱格本生和因缘故事壁画以及第224窟左甬道内侧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老婆罗门独楼那像也许就是这次被揭取的。⑦
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石窟停留数日,挖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切割了若干壁画,并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⑧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11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情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等。

独楼拿 佛传故事“八王争分舍利”局部 克孜尔第224窟(现藏日本东京国立中央博物馆)
(三)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根据第一次德国探险队主要目的地——吐鲁番而命名)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前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2年和1905年对吐鲁番地区的诸遗址进行了考察探险;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龟兹地区诸遗址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
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这次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队员有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 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并丈量洞窟、绘制测图。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图、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见附表)。另外,考察队还割取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获取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本。探险队成功地将224箱的文物带回德国。⑨

龟兹供养人 克孜尔第8窟(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四次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图斯一人。他们于1913年7月1日到达克孜尔石窟,第二天就开始工作。第三次考察期间,由于一些洞窟太高,格伦威德尔难以攀登。这次由巴图斯攀登这些高危洞窟,测绘窟形图。在克孜尔第177、213和223A等窟的壁面上还存有巴图斯当年留下的漫题。这次考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割揭取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上次。此次探险队从新疆带回了156箱文物。

说法图局部 克孜尔第224窟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德国考察队前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究竟割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过程中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准确的数字。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部分已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
(四)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6~1908年,伯希和所率领的法国考察队也在新疆开展工作,期间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考察。1907年,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等,⑩并从克孜尔尕哈石窟捡了一些脱落在地的壁画带走了,[11]还重点发掘了库木吐喇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二战后,由韩百诗(L.Hambis)组织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共16卷,这项工作现在还未结束。在已出版的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 Finot)和列维(Sylvain Levi)整理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龟兹文写本由皮诺(Georges 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
从伯希和报告中可知,俄国的M.M.别列佐夫斯基曾与其通信,从信中可知俄国考察队在库车工作将持续1906年末的整个冬季。
(五)斯坦因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14年5月28日,英人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拍摄了部分壁画照片。[12]
二、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流散情况与现状调查
从1998年春季开始,新疆龟兹研究院(原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研究员霍旭初带领业务人员,开始从国外各类出版图录中翻拍、收集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资料,并将这些图片与洞窟内揭取痕迹核对,以纠正过去出版物中的一些错误。
同年秋季,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荻茨(Marianne Yaldiz)访问克孜尔石窟,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由该馆研究人员查雅(Chhaya Haeser)整理的《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和272张黑白照片。
1999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收藏在该馆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采集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取得数据28个。他们通过单幅壁画采集所得的碳14测定数据来确定某个洞窟的时代。但由于壁画的出处本身就有错误,洞窟的年代判断也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2002年9月,霍旭初研究员和笔者赴德国参加“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我们在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核对了此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13]。但由于受当时设备条件的影响,我们所拍的大部分照片在回国后没有冲洗出来。
2011年2月,笔者受邀访问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调查该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1年10月~11月,笔者受邀访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平山郁夫美术馆、京都龙谷大学博物馆,调查上述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2~2013年,笔者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时,与该馆亚洲部负责人Lilla Russell-Smith博士合作,正式启动了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对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现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和核对。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给我们提供了壁画的高清图片。
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1914年5月,这批文物在柏林开始公开展出。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批壁画的大部分已被修复。
为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常设展的装修和布展,勒库克开始考虑出售壁画。目前在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五十多块新疆壁画中绝大多数是在1923年和1928年出售的。此外,还有少量壁画被勒库克作为礼品赠送了出去。[14]
现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牛津大学阿施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以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均收藏有克孜尔石窟壁画,这些收藏品都出自勒库克收集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轰炸,位于匡尼希类特街的民族学博物馆保存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柏林时,劫走了很多文物,其中就包括克孜尔石窟壁画等。这些文物现收藏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直至2008年才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新疆文物陈列中部分面世。[15]
现在保存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有225件。
2013年1月,笔者带领业务人员赴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调查了该馆收藏的新疆石窟寺壁画和雕塑等文物。
继对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调查后,笔者又于 2013年5月、2016年 7~8月两次赴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进行调查,并与该馆研究员Kira Samosyuk女士、文物保管员Nicolai Pchelin先生共同整理了该馆收藏的龟兹地区壁画、雕塑等文物。
2015年11月,笔者带领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吐鲁番学研究院的业务人员赴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调查新疆石窟寺壁画等文物。
至此,笔者大体上理清了海外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基本情况和数量。
在远赴海外调查的同时,我们在洞窟实地反复考察并逐一核对,落实了大部分海外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所属的洞窟和原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
三、小 结
通过我们在洞窟内测量得知,克孜尔石窟被揭取壁画的面积近500平方米,出自近50个洞窟。[16]当然,这个数据包括日本人和俄国人从克孜尔石窟揭走的壁画面积和洞窟数量,但大部分还是德国探险队所为。现在,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大部分藏在德国,一部分在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散见于日本东京、京都、镰仓,韩国首尔,英国伦敦、牛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底特律、堪萨斯等地。除上述国家以外,也不排除还有其他国家收藏有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可能。[17]
此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则发现了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先生从克孜尔石窟带走的壁画等文物[18]。2017年始,北京木木美术馆陆续收购了3块日本私人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经过20年长期艰苦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最多的两大博物馆即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支持下,新疆龟兹研究院目前已收集到海外8个国家20余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的465幅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高清图片。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洞窟建筑、壁画和塑像结合而成石窟艺术,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和功能。不同派属、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由于克孜尔石窟壁画被外国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窟,给整体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因此,核对落实流失海外的石窟壁画等文物的出处与原位考证至关重要。
注释:
① 落款人名叫缪恩汉克(г.Мюнханг),但是题记写法有问题,时间是十月革命前的,但俄文写法却是十月革命后的,词尾无硬音符号,是否为人名?
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года.(Кратки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909至1910年俄国新疆探险考察初步简报》),1914.
③在С.Ф.Ольденбург,Русская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года.(Кратки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中有关于切割壁画、取走塑像头部、打包装箱的记录。
④庆昭蓉:《第一次大谷探险队在库车地区的活动——从探险队员日记与出土胡汉文书谈起》,载《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11月5-8日,大连,旅顺博物馆)论文集189-233页,正式会议论文集待刊。
⑤前者现藏旅顺博物馆,后者现藏京都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
⑥[日]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亚洲探险之旅——丝路探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⑦参见《新疆古佛寺》第271-274页,现保存在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出自第206窟的4幅壁画,在1906年格伦威德尔来克孜尔时,壁画还未被揭取,说明这几幅壁画是1909年第二次大谷探险队揭取的。参见同书第303页,现保存在日本东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出自第224窟的1幅壁画,在1906年格伦威德尔来克孜尔时,壁画还未被揭取,说明这幅壁画是1909年第二次大谷探险队揭取的。
⑧克孜尔第206窟和第224窟的壁画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内,由于资料是1910年开始整理的,因此推断这两个洞窟的壁画是在1910年之前就被揭取并带走了。
⑨包括第二次探险队所获文物。
⑩[法]伯希和著,耿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11]目前可见保存在巴黎集美博物馆的出自克孜尔尕哈石窟的4幅壁画。
[12][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1页。
[13]这次调查核对仅限于该馆库房中挂在墙壁上的大幅壁画,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对放置在两个架子里的壁画进行调查核对。
[14] Laszlo Ferenczy,Zwei Devataköpfe aus den WandmalereienderMaya-Höhlenin Kyzil,Az Iparművészeti Múzeum Évkönyvei X.1967,pp.167-174.
[15] ПЕЩЕРЫ ТЫСЯЧИ БУДД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К 190-ЛЕТИЮ АЗИАТСКОГО МУЗЕЯ,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2008;张惠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举办千佛洞——俄罗斯丝绸之路探险文物展》,《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3-115页。
[16]赵莉编译《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所出洞窟原位与内容》,《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关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原位问题考证文中记述》,《华林》第二卷,两文中均记述“出自60个洞窟”,当时调查范围涉及所有揭取壁画的洞窟(其中也包括一些自然脱落痕迹与揭取痕迹相似的洞窟),在进一步的核查中发现,有些洞窟内的壁画所属于自然脱落或被当地游人切割,此次订正为“近50个洞窟”为妥。
[17]在土耳其安卡拉博物馆展厅内就陈列有2块出自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目前尚没有条件调查该博物馆是否也收藏有克孜尔石窟壁画。
[18]丁瑞茂:《史语所藏黄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文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今论衡》第22期,2011年,第125-138页。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