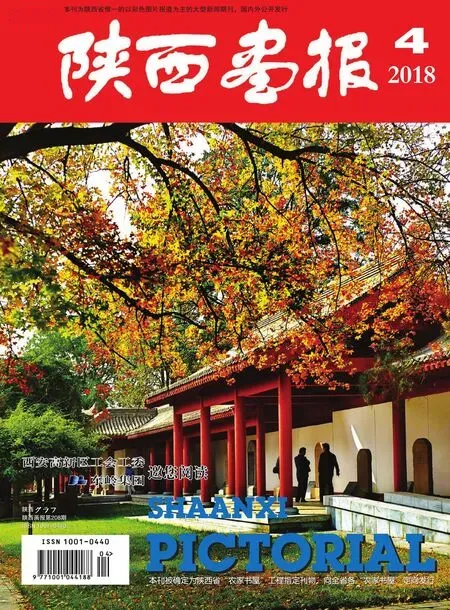从东干人的“婚礼”看秦文化的传承
2018-10-15撰文并摄影冯锐利
撰文并摄影/冯锐利
东干人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走过了150多年。大约在清代晚期,陕甘地区回族趁清政府腐朽软弱以及地方动乱的机会实施暴动,在清政府的追击下,一批回族兄弟历经长途跋涉,最终驻足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3国等地,筑建起自己的家园,从此繁衍生息。他们在当地被称为“东干族人”,自称是中国陕西的老回回。
这样特殊的一群人在当地很引人注目:黄皮肤黑头发,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地域方言。人们仍然保留着100多年前清朝时的日常用语,例如现今仍沿袭用“衙门”称呼“政府机构”, “衙役”称呼“政府人员”。他们每有聚会还会吼上几句秦腔。
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们统称为“陕西村”的东干人。电视上经常报道这些“东干人”多次返故地西安寻亲,一解乡愁。每一个“东干人”的灵魂中都生发着一颗思乡的种子。2016年10月陕西省妇女代表友好交流团,带着《我的家乡在丝绸之路的起点》摄影作品和“指尖上的丝绸作品”,来中亚省亲,我作为成员之一,用镜头记录了这种看得见的乡愁,在异地他乡听到地道的乡音。这里用一组“东干人的婚礼”道出百年前乡俗依旧之实。那婚俗比现在陕西婚俗的套路还古老,可谓为秦人古婚俗的活化石。

2016年我省妇女代表友好交流团在“陕西村”访问

新娘戴上陪嫁的首饰再一次的装扮一番
东干人的“婚礼”,依旧完整存留着100多年前婚嫁的庄重仪式。新娘出嫁时必梳一种传说的古老发型 “燕燕头”,这种发型在陕西也没有几个会梳的,可见他们对秦文化的传承的“正宗”。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位会梳 “燕燕头” 的大妈正在给新娘梳头,屋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孩子和贺喜的宾客,他们帮着给新娘扮装。先穿上手工绣制的云肩和清朝大襟长衫,待梳妆后足蹬上一双红绣花鞋,裤腿用花边扎上,宛如一幅民国年间的美人图。
接新娘的男方宾客一行,一到女方家,就给前来道喜的亲朋好友及孩子们逐一散发喜糖,然后男宾在单独接受阿訇的祝福后,才在迎亲队伍的簇拥下,由长辈将新娘抱入婚车,在祝福声中与新娘一道回家。新娘一到婆家还要再进行精心梳妆打扮一番,由家中的晚辈揭掉盖头,戴上陪嫁来的金银首饰,然后在端来的洗脸盆,象征性地洗洗手、洗洗脸,才出来见亲朋好友。这套婚俗过程,与过去秦地无两样。合影留念是必不可少的。按婚礼习俗大宴宾客的流水席是异常丰盛热闹的,婚宴呈备餐品为:美味的羊肉手抓饭、时鲜的水果、各色糖果和糕饼。我们一行几人被请入宾上客,按穆斯林的习俗婚宴席上同样是没有酒的。

拿“望远镜”看一看是不是“我”的媳妇

新娘走下婚车

拍打西安古城门寄托思念

即将出嫁的新娘依然梳着陕西传统的“燕燕头”

新郎新娘和亲朋见面合影
婚礼后的第二天,新娘要在公公婆婆和男方众亲戚面前,充分展示自己做家务和下厨料理方面的实际才干。第三天,新郎官备上丰富的礼品陪同新娘子,回门探望岳父母大人及亲属。与此同时,新娘家众多的亲戚也会一家接一家地轮流宴请新郎官和新娘子,并给新娘子回赠备好祝贺的礼物。在回门的当晚,新郎官要赶回自己的家中,将新娘留在娘家住上三五天或一星期后,再由新郎亲自前来接新娘子。新郎将新娘接回家后,东干人婚礼的仪式便告完成。
一场庄重热闹的东干人的“婚礼”仪式,它如活化石般的存在,像这古老的清末民初一样的模式,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清晰的痕迹。

参加婚礼的女宾在婚宴上
在这里,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秦文化的存在,陕西八大怪中的“凳子不坐蹲起来”“油泼辣子一道菜”等都能看到。我们用陕西话交流无障碍显得格外亲切。虽在异国他乡犹如置身西安的回坊,熟悉的乡音同样的面孔,他们也把喝稀饭叫喝米汤、把蹲叫趷蹴……陕西话说的忒色的很。他们欣赏我们的影展作品,聊着西安城的话题,询问着陕西各地他们能记住的地名,听到巴巴(baba爷爷)、妠妠(nana奶奶)和坊上一样的称呼,所有的距离瞬间没有了,忘记了此刻是在中亚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点——“陕西村”东干人的家里。
今年,“陕西村”的一些人,又来西安省亲。我陪同他们游走在古城墙、钟鼓楼大街小巷。西门是他们每次来西安必去之地,因为100多年前,他们的祖辈是从这里离开的,所以,回来省亲时总要到这里,深情地望着西门,情不自禁地双手拍打着城门高声道:我回来了!我试图用镜头解读他们乡愁,释放思乡的细节。这座城有着他们祖辈的历史根脉,以及“人”与“灵魂”的生命遗存。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东干人”得到一种精神滋养,因为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他们将借助这座城的血脉相连渊源,重新响起新世纪的驼铃声,成为“一带一路”节点上的重要成员。他们心中的“那座城”会永远成为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

红盖头是必不可少的

2018年“陕西村”的东干人来西安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