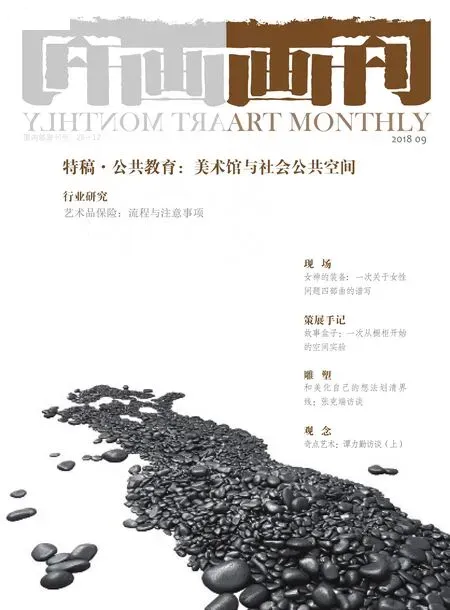用“涂抹”呈现平凡
2018-09-28孟柏伸MengBoshen
孟柏伸(Meng Boshen)

《河》 孟柏伸 2018年
在10多年的铅笔材料创作过程中,很多人简单地认为我就是个铅笔艺术家。实际上,虽然材料基本上没怎么变化,但我的作品语境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从对信仰和传统文化现状的思考再到对社会现场的不断认知,又回到对自然的关注以及对人为性的再度审视,涂抹的对象也从纸上平面到对现成物品。我并没有把自己固定在单一思维方式的创作维度之中,其间也有很多其他材料的方案,但考虑到自身的语言逻辑与作品的上下文关系,我还是比较谨慎地避免其他材料的简单介入。也许接下来我会把材料语言逐步地拓展开来,但并不会因此改变我艺术关注的方向和问题。
2007年,我刚刚从美院毕业不久,当时正处在一种寻找适合或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式的苦闷的探索阶段。就在那个阶段,一次偶然的事情,让我开始选择用铅笔去创作。我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耐的无聊夏日,我在工作室楼下的小卖部用1元钱买了根5毛钱的老冰棍。我一边吃一边将找零的5毛硬币随手放在一张纸下面,然后用铅笔在纸上去涂抹。我突然意识到这可以成为一种语言方式,并能与我之前的思考方向相结合,于是便开始了铅笔创作的尝试。之后,我找了各种不同品牌的铅笔在厚薄粗细不一的纸上去涂画,以熟悉和掌握这种材料的视觉表现特性。这个阶段,我创作了《忆风痕》系列。这个系列是想用港台流行歌曲近30年的曲风演进阐述内地在文化形态和大众信仰的变迁过程,这跟我的个人情感和记忆有关,当然也重合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忆风痕》系列 孟柏伸 木板纸上铅笔 2007年

《这是什么》 孟柏伸 玻璃上铅笔 尺寸可变 2015年
与此同时,我逐渐开始关注社会现实的复杂变化与人的道德和信仰缺失的关系,意识到一些表面的流行风潮的变迁并不足以揭示更本质的问题,开始寻找更深刻和具有文化价值的创作主题,《盲经》系列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开始的。《盲经》的准备工作非常曲折,借用盲文做作品首先要找到盲文版的经著,这个过程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几经周折只买到了盲文版的《圣经》。另外除了不完整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以花重金在网上寻到外,国内都没有任何盲文版出版物。也曾去过盲文出版社寻求帮助,但是价格让我无法在经济上承受。最后在沮丧之际,无意中联系到了退休多年的清华大学教授茅于航。茅先生得知我的初衷和目的后,决定免费为我转译盲文版经著。正是有了茅先生无私的技术支持,才得以将该计划顺利展开和推进。这个系列一做就是5年多,先做了《圣经》,之后是《毛主席语录》《金刚经》《道德经》和《中庸》。我想倒叙一下信仰在这片土地上的更替过程。
2008年,我和香港的汉雅轩画廊签约,陆续被收藏了一些作品。这样有了基本的生活和材料费,更是鲜少外出,终日都在涂抹作品中度日。当时艺术市场乃至整个中国正处于一个浮躁盛极的特殊年代,因为我本人喜欢安静又刚刚接触社会不久,也不知怎么面对那样一个喧嚣社会,为了躲避奥运的热闹就回老家创作了《盲简》。有人说我是苦行僧算是一种修行,我并不以为然,只是每个人对艺术的态度和理解的角度不同。在创作《盲经》系列整个过程中也不乏会有枯燥,期间穿插创作了《新文人取向》(2008年)和《涅槃》(2011年)等小品来调节创作状态。

《盲经》 孟柏伸 纸上铅笔 110cm×1000cm 2009年
2012年,我用几十个版本的《道德经》出版物条形码创作了《经变》,观者可通过手机扫码与之相关的ID信息互动。创作这件作品,是有感于一次在望京的书店闲逛时,发现《道德经》的出版物版本数量,这与中国的国民道德现状反差极大。2012年末,我搬到了宋庄,也对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场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也试图想让作品有新的拓展和突破。比如,在黄山用传统徽墨创作的《反映》(2013年),这组作品是想讨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手工文明或农耕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结合后某种特殊的现状。
随之,又想尝试找一些具有特殊文化属性的现成品进行涂抹。2014年创作完成了《这是什么》系列,把瓷器和古家具用铅笔涂抹覆盖掉了原有的视觉特质,其间也是体现我个人的意志和观念。原想涂的是一个祠堂或中堂,因工作量和经费的问题就搁置了。接下来涂了24个时区的时钟,然后是无影灯、化学器皿、转角镜等,之后又用铅笔芯做了一系列装置。
2016年有幸接到银川当代美术馆谢素贞馆长的邀请,与毛同强老师一同参加她的“中国制造”的项目。这个项目是每年选两位艺术家让每位艺术家各用一个大展厅根据空间进行创作。我专程去银川当代美术馆实地考察空间,当时选了馆里最大也是最高的主展厅。接下来提交了两个适合这个展厅的方案。谢馆长对我在2008年做的《悬置》方案更感兴趣,于是搁置了8年的《悬置》方案终于有机会启动和实施。
起初,我是希望银川当代美术馆能协助在周边地区寻找一棵体量适合的枯树,但在大西北实在找不到尺度合适的大树。于是我转向北京及周边的省份四处寻找,此时亦恰逢北京市政府对外公布了将迁址到宋庄旁边的潞城镇,因此便将寻找目标锁定在了潞城镇的拆迁范围内,在数十个自然村里穿梭寻找合适体量的树木。这期间我接触了上百个树主人和村民,通过和他们的沟通交谈,让我深入地了解了这些有着高度优越感的北京村民们,在面对这场城市化的运动中都有哪些反映和想法。这段经历影响和改变了我对社会现场的认知并让我对这件作品有了新的思考和态度。我在开发商和村民手里各找到一棵体量适合的树,这两棵树的尺度和形态都是为银川当代美术馆的1号馆空间量身定做的。原初的展示方案是把两棵树冠相对地悬挂在空中,最后因布展难度太大就只挂了一棵。这件作品的制作历经数月,由20余人日夜赶工才得以在开展前完成。

《触不可及》 孟柏伸 铅笔芯、木材 81cm×81cm×10cm 2015年
记得伐树的当天正赶上北京雾霾橙色预警,只伐了一部分就被迫让相关部门给制止了,数天后才得以继续伐完。我将树干运往木材切割厂整体切割,树主干部分是按每1厘米为单位逐片递增方式来切割;树的主枝是以每10厘米为单位逐步递增。用这种解剖学的方式来把这棵树截离,是我对事物系统的分析再认知的语汇方式。接下来便是剥皮和表面干燥处理。当时正是秋冬交替之时,树木干燥的速度很不理想,尝试多种方法处理后,才终于可以进行初步打磨及整体编号,接着是打磨树木表面和细抛光,最后一个环节才是用铅笔涂抹。《悬置》在3个工作室同时分步实施,在高强度的赶制过程中,我几乎就是个工头的角色,这也让我时而反思艺术的属性到底在哪里?《悬置》在银川当代美术馆成功展出后得到了圈内很多人的关注和认可,也很荣幸地获得了第二届王式廓艺术奖,得以在今日美术馆有做个展的机会,让《悬置》回到北京再次悬起。

《盲文圣经——前言》 孟柏伸 木板纸上铅笔 80cm×80cm 2009年

《悬置》 孟柏伸 木、铅笔 尺寸可变 2016-2017年
这次个展共展出《悬置》《河》两件作品。《河》是我2018年最新的作品,是用鹅卵石制作的一件大型装置。我将十几吨鹅卵石及雨花石用铅笔涂黑按照星图在展厅里摆成了一条银河。这件作品与《悬置》都是对自然物的观照用涂抹的方式来表达我近段时间来的个人思考和态度。《河》是2014年或更早一段时间的方案,也是借此个展机会得以实施。因为有了《悬置》项目的制作经验,作品《河》制作起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按预期完成。原先计划的展示方式,是有一部分石头悬吊在空中的。但为了与主厅的《悬置》方案形成一种对照的关系,后来就改为将鹅卵石全部堆放在了地面上。
这两件作品与我之前的作品在创作思路和制作模式上都有较大的区别,规模体量上也变得更大更具有视觉强度。 我通过作品向观众强势地提示了铅笔这个普通材料具有的特殊视觉性,同时也再次拓展了铅笔介入对象的可能性。这也包含了我个人的观念——呈现平凡的力量。铅笔、石头或树木以及纸张都是我们日常非常熟悉的东西,多数时候是人们忽略甚至漠不关心的对象。经过简单的处理结合重新再回人们的视线的时候,一切就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原本普通物质的价值被重新认知和肯定,这也是我想要达到的一种效果,也是我要表达的一种艺术的价值。

《悬置》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