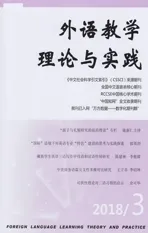藏族学生英语三语写作中母语和汉语作用研究*
2018-09-13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建林李筱媛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建林 李筱媛
提 要: 藏族学生英语三语(L3)习得受到母语藏语(L1)和第二语言汉语(L2)的双重影响。以多语交互影响研究者提出的类型近似模型、第二语言主导模型和累积增强模型为理论基础,收集L2水平不同的藏族L3学习者的作文语料,从流利度、词汇丰富度和词语错误率等三个维度对比分析。结果表明L1和L2在L3写作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L1在作文构思阶段发挥作用;L2水平越高,词汇错误率越低,但L2水平在词汇丰富度上并不具有区分力;教学媒介语对L3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结果对于藏区英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 引言
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藏族自治地区有专门为藏族学生开设的藏族中学,其教学模式通常有两类。第一类模式称为“以汉为主”,学生汉语水平较高,所有课程的教材用汉语编写,课堂教学媒介语也是汉语,藏语只作为其中的一门课程教授;第二类模式称为“以藏为主”,学生汉语水平较弱,除英语课程外,其它课程的教材均以藏语编写,授课媒介语是藏语,汉语只作为其中一门课程教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没有专门用藏语编写的英语教材面世,两类模式下的英语教材仍然使用汉语编写,并且由于既懂藏语又懂英语的教师比较少,英语课堂的教学媒介语主要是汉语。对于藏族学生而言,藏语是其母语(L1),汉语是第二语言(L2),英语是第三语言(L3),英语学习必然存在多语交互影响现象。由于两类模式下学生在L1使用状况和L2水平两个方面存在差别,那么这两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学生L3的习得?如果是,它们又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本研究将以甘肃省某藏族中学为例,通过对两类模式下学生英语L3作文文本的对比分析,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二、 相关文献
有关L1、L2对L3习得的影响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多语迁移领域(Multilingual Transfer)。多语迁移可发生在语音、词汇、句法等层面(Cenoz等,2001;De Angelis,2007; Rothman,2015;Slabakova,2016)。L1、L2与L3之间的语言距离、L1和L2语言使用近况、L2地位和学习者语言水平、学习年龄、学习者认知水平等均对L3习得产生影响(Amaro, Flynn & Rothman,2012;Qin & Jongman,2015; Silva-Corvaln,2016)。对于L1、L2在L3习得中的作用,研究者们提出了以下三种模型。
Bardel & Falk (2007, 2012)和Falk & Bardel(2011)等在多项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第二语言主导模型(The L2 Status Factor Model,L2SFM)认为,L2对L3习得产生主导影响作用。Falk & Bardel(2011)对比了两组学习德语L3的成人学习者在习得宾语代词位置时的表现。一组L1为法语,L2为英语;另一组L1为英语,L2为法语。研究者让受试对不符合语法的L3句子进行判断,结果发现,英语L2学习者在对和英语结构一致的错误的L3句子进行判断时,正确率只有39%,而法语L2学习者的正确率是83%;与此相反,法语L2学习者在对和法语结构一致的错误的L3句子进行判断时,正确率只有29%,而英语L2学习者的正确率是93%。此研究表明L3学习者受到了L2的负迁移作用。Falk等人从L1、L2与L3之间的认知相似度方面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按照生成语法理论,L1的习得过程是语言输入与大脑中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prerequisite)之间的互动,而L2和L3的习得还多了两个影响因素,即百科知识和业已习得的语言知识。因此,相较L1,L2习得和L3习得之间在认知过程和学习情境方面具有更多的相似性,L2和L3学习者具有更多的元语言知识,更能意识到自己在学习一门外语。Williams & Hammarberg(2009)也认为L2在L3学习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学习者总是有意识地使L3更像一门外语。Falk等人还根据神经语言学有关理论对L2SFM进行了解释。他们引用Paradis(2009)关于程序性(procedural)记忆和陈述性(declarative)记忆的理论指出,L1知识属于程序性知识,存储在程序性记忆中,而L2(Ln)知识属于陈述性知识,存储在陈述性记忆中,这两种记忆依赖于大脑的不同部位。因此,相对于L1而言,任何后来习得的语言(L2,L3,Ln)之间更容易产生相互影响。
Flynn, Foley & Vinnitskaya(2004)以及Berkes & Flynn(2012)提出的累积增强模型(Cumulative Enhancement Model,CEM)认为三语习得是一种累积效应,学习者习得的语言越多,越有助于下一种语言的习得。他们的研究对掌握不同数量外语的英语学习者习得英语标句词短语(Complementizer phrase, CP)进行了对比: 第一类学习者是学习英语L1的儿童,第二类是学习英语L2的成人(母语分别为西班牙语或日语),第三类是学习英语L3的成人和儿童(L1为哈萨克语,L2为俄语)。结果表明,相比前两类学习者,第三类学习者更容易习得CP结构。Flynn等人依据普遍语法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学习者不会在大脑中重复表征近似的句法结构,而是将正在习得语言的CP结构和已经习得语言中有关CP的普遍语法结构融合在一起,从而促进新语言CP结构的习得。也就是说,习得的语言越多,大脑中关于CP的普遍语法表征就越牢固,因此越有利于习得某种具体语言中的CP结构。Flynn等人据此认为,“业已习得的语言对新语言语法结构的习得会产生积极作用……累积增强模型能为解释这种新语言知识的(高效)习得提供理论模型”(Berkes & Flynn,2012: 163)。
第三种模型是语言类型近似模型(The Typological Proximity Model,TPM)(Rothman 2010, 2013, 2015)。该模型认为L1和L2中哪一个更能影响L3习得取决于它们与L3之间类型学上的相似性,或者说取决于学习者所感知到的相似性(perceived Typological Proximity),相似性越高的语言对目的语的影响越大。TPM和CEM一样都主张L3习得中的累积迁移效应。不同的是,CEM认为L2的累积迁移效应是非负面的,而TPM认为这种累积迁移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其原因是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还不能完全正确地感知三种语言之间类型学上的相似性,因此会错误地将L1或L2中的某种语言结构迁移到L3结构中去。
本研究中,藏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尽管藏语是拼音文字,而且存在语序倒装等现象,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表明藏语和汉语哪个与英语之间更具有类型学上的相似性。因此,TPM模型似乎还不能对藏族中学生L3习得中L1和L2的作用做出解释。L2SFM和CEM实际上都主张L2在L3习得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在L2水平越高时越能发挥正面促进作用。另外,按照Paradis(2009: 113)所提出的最佳年龄阶段(optimal period)假设,2至5岁是儿童习得隐性语言知识(implicit knowledge)的阶段,超过这个阶段的语言学习则称之为有意识的显性知识学习。多语者语言认知研究表明,在显性知识学习阶段,多语学习能促进学习者语言意识的发展,学习者具有更好的语言学习、管理和维持技能(Kemp,2007)。以上理论似乎均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成人L2水平越成熟,元语言知识越丰富,语言管理能力越强,产生正迁移的趋势越明显,越有利于L3习得。那么,对于藏族中学生而言,“以汉为主”学生汉语L2水平已经完全成熟,并且明显高于“以藏为主”学生水平,这是否意味着其在L3习得中的表现更好呢?本研究将收集两类模式下藏族中学生英语书面语语料进行对比分析,以求探讨L1和L2在L3写作中发挥的作用。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甘肃省某藏族中学高三年级四个班的学生,其中两个班教学模式为“以汉为主”,英语由同一位老师讲授。另两个班为“以藏为主”,英语由另一位老师讲授。如前所述,由于懂藏语的英语师资有限,四个班的授课语言均为汉语。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基本情况及其英语学习策略等。学生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四个班的学生全部为藏族,男女比例基本平衡。“以藏为主”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是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汉语处于会说也会写的水平,但不熟练,有四分之一多的学生汉语交流有困难。“以汉为主”学生中有43%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学习英语,但汉语水平都比较高,90%以上会说也会写,42%的学生和汉族学生没什么两样。四个班学生每天学习英语的时间都是1.5小时左右。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3.2 研究语料的收集及教师访谈
研究语料为英语作文文本。写作任务是一道高考模拟作文题,由任课老师组织在同一天上课期间完成,要求学生针对“高三学生要不要在课间休息时讨论上节课所学内容”为话题给校长写信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供了简单的提纲,要求字数100字,时间为30分钟,纸笔作答。作文完成后,为便于对比研究,每个班随机选取30份作文作为研究语料,录入电脑。同时对任课教师进行了访谈,主要针对本次作文的难易度、教学方法、对学生英语学习的评价等。两位任课教师均认为此次作文难易度适中,基本能够反映学生英语写作水平。
3.3 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从流利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三个维度展开,具体指标为: 作文平均词数、平均句长和平均词长(流利度);词汇丰富度(复杂度);词汇错误率(准确度)。研究表明,这几个参数对于以上三个维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何华清,2009;张新玲,201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藏语、汉语和英语在各个词类的词汇语法方面差异较大,本研究只选取词汇错误进行归类和分析,暂不涉及句法错误。用wordsmith软件统计平均词数、平均句长和平均词长;用Range32软件对文本的词型(tokens)、词类(types)和词族(families)等进行统计,并计算类型符比(TTR)。词汇错误率的统计步骤为: 制定错误标注体系,利用Nvivo软件进行标注,统计频数。词汇错误标注体系的制定以桂诗春、杨惠中(2003)词汇错误分类方法为依据。他们将词汇错误分为词形错误和词汇错误,其中词形错误包括拼写、构词及大小写错误,词汇错误包括词序、词类、替代、省略、冗余、重复以及语义含糊错误。本研究中省去了“大小写”、“省略”、“重复”、“语义含糊”等四个参数,主要原因是: 第一,文本录入电脑的过程中改变大小写的情况比较多见,因而对其进行统计的误差会很大;第二,这几类错误对于本研究对象来说并不典型。错误标注体系如表2所示。为了提高错误标注的信度,研究者与一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共同讨论并制定每个错误类型的定义,各自标注5份相同的作文,然后对差异之处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再各自标注5份相同的作文,一致性为0.84,经过再次讨论后由研究者独自完成所有语料的的标注。

表2. 错误标注体系

续 表
四、 研究结果
4.1 作文流利度
表3为作文流利度统计数据,显示“以藏为主”两个班的作文平均长度分别为97和87.9,“以汉为主”两个班的作文平均长度分别为69和76.4,并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以藏为主”两个班与题目所要求的100字长度更加接近,但是“以汉为主”两个班还有一定差距。然而,从平均句长上来看,四个班学生的平均句长分别为13、12、11、14,无显著差异。从平均词长上来看,也基本相当。也就是说,单从作文长度上来看,“以藏为主”的学生要比“以汉为主”的学生表现好。

表3. 作文流利度
4.2 文本复杂度
再来看词汇丰富度,表4显示四个班在词汇使用方面的差异。类型符比(标准类型符比)是词汇多样性的统计指标,这一数值越高,说明学生在作文中使用不同词汇的能力越强(陈建林,2011)。由于类型符比受作文长度的影响,作文长度越长,比值越低,在统计中使用标准类型符比来消除这一影响。标准类型符比是在控制文本长度情况下的类型符比。从本研究来看,四个班级作文的类型符比分别为14.3、14.9、14.8、12.7,不存在显著差异;将统计文本长度设定为50后对标准类型符比进行统计,发现四个班级均在78左右,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是否意味着两类模式下的学生作文词汇丰富度没有差别呢?其实并不完全是。由于本研究中文本长度较为有限,单从类型符比值来看,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词汇丰富度。但如前所述,由于类型符比会受到文本长度的影响,在类型符比相同的情况下,作文总词数长的学生使用词汇更加多样。本研究中,从使用的词类数量来看,“以藏为主”两个班分别为371和351,而“以汉为主”两个班仅为270和263,存在明显差异;从使用词族数量来看,“以藏为主”两个班分别为295和279,而“以汉为主”两个班分别为213和209,也存在显著差异。综上,不难得出初步结论,与“以汉为主”学生相比,“以藏为主”学生在英语作文中使用了更多的词汇。

表4. 词汇丰富度
注: 考虑到拼写错误对统计的影响,只统计出现在Range32中第一、二、三级词汇中的单词,从而排除拼写错误对统计数据的影响。
4.3 文本准确度
本研究中文本准确度的分析采用错误分析法。表5是四个班级错误统计数据。

表5. 错误统计表(平均每千字错误数)

续 表
注: 无法执行卡方检验的标注为“#”。
首先来看错误总频数。每千字错误数分别为: 藏1班303.9,藏2班341,汉1班258.8,汉2班237.2,有显著差异(P=0.000)。“以藏为主”合计644.9,“以汉为主”合计496,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0)。两类模式下的词汇错误率在23%至30%之间。两者对比,“以藏为主”学生作文错误率要高于“以汉为主”学生。从五个大的错误类别来看,“以藏为主”学生的词类错误每千字为34次,几乎是“以汉为主”学生的两倍(每千字17.5次),具有显著差异(P=0.014)。词序方面的错误比较少,分别为每千字4.4次和5次,两者相当。构词方面每千字的错误数分别为77.3和57.5,尽管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以藏为主”学生的构词错误相比“以汉为主”学生超出了三分之一。拼写错误几乎一样,均为每千字83次左右。冗余错误数分别为68.6和48.5(P=0.066),尽管两者差异还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以藏为主”学生错误数比“以汉为主”学生超过了40%。替代方面的错误数分别为98.7和80.1(P=0.156),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除了“词序”和“拼写”这两类错误之外,在“词类”、“构词”、“冗余”和“替代”四个方面,“以藏为主”学生都比“以汉为主”学生所犯错误数要多。
从下一级错误类别来看,在“代词”、“介词”和“词型”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两类学生在“代词”上的错误数分别为17.4和7.2(P=0.041),在“介词”上的错误数分别为29.7和10.7(P=0.003),在词型方面的错误分别为35.7和20(P=0.033)。仔细观察,尽管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以藏为主”学生分别在“词类”下的动词错误、名词错误,“构词”下的动词错误、造词错误等几个方面均较“以汉为主”学生超出50%以上。如果进一步对两类模式下学生在三大词类“动词”、“名词”、“形容词”方面的错误数进行统计的话,“以藏为主”和“以汉为主”错误数分别是44.7和33.3;46.9和43.6;10.2和8.4。其中在动词方面前者要超出后者将近40%。总体而言,“以藏为主”学生只有在几个类别(“词类”下的“副词”和“词序”、“构词”下的“名词”、“拼写”、“冗余”下的“名词”和“形容词”)上的错误数持平或稍稍低于“以汉为主”学生之外,其余均超出。也就是说,“以藏为主”学生在文本准确度上表现没有“以汉为主”学生好。
五、 讨论
回到前文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即“以汉为主”教学模式下L2水平更高的学生是否在L3作文上的表现更好呢?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很难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从作文流利度和词汇丰富度来看,L2水平更高的“以汉为主”学生反而表现不如L2水平较低的“以藏为主”学生。而在准确度上,前者表现要好于后者。也就是说,两类模式下的学生在作文质量的三个指标上表现并不一致。Ellis & Yuan(2004)认为,作文流利度和词汇丰富度属于构思能力(formulating competence),而准确度属于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也就是说,“以藏为主”学生在作文构思能力上要优越于“以汉为主”学生。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的“以藏为主”学生认为在写作时很大程度上依靠母语藏语进行构思,而“以汉为主”学生则只有40%左右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藏语进行构思。心理词汇表征研究(Jiang,1999)发现心理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强弱程度受到语言熟练程度的影响。崔占玲等(2009)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藏-汉-英三语者的心理词汇和概念联系存在强弱差别,即藏语词汇与概念的联系最强,汉语次之,英语最弱。也就是说,以藏语构思,能更加熟练地建立词汇与概念的联系,表现在作文内容上,就会有更多的话可说,也会使用到更多的词汇。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以藏为主”学生作文长度显著高于“以汉为主”学生,并且使用了更多英语词汇的原因。那么,作文长度能否代表作文水平高低呢?秦晓晴等(2012)发现单纯的频数统计对于作文水平高低并没有区分力。从本研究来看,尽管“以藏为主”学生在内容长度上的表现要好于“以汉为主”学生,但是在平均句长和平均词长两项指标上,并没有表现出优势,并且,在代表词汇知识丰富度的标准类型符比这项指标上,两类学生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尽管“以藏为主”学生使用了更多的英语词汇,但是从词汇知识的掌握程度上来看,两类学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思考的是,两类学生的英语心理词汇到底如何表征,“以藏为主”是否存在藏-英语义共享较强,汉-英语义共享较弱,而“以汉为主”学生是否存在汉-英语义共享较强,藏-英语义共享较弱的现象呢?语义共享模式差异是否会导致词汇知识存储的差异?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再来看两类模式下学生在文本准确度方面的差异。总体来看,“以藏为主”学生的词汇错误率要高于“以汉为主”学生。有关研究(何华清,2009)表明学生词汇错误与作文水平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项指标来衡量的话,“以汉为主”学生的英语水平要高于“以藏为主”学生。这是不是意味着学生汉语L2水平较高的确会对英语L3学习产生正面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学生所犯错误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以藏为主”学生英语词汇错误较多,而“以汉为主”英语词汇错误较少。如前所述,本研究错误分析只针对其词汇错误而言,词汇错误总的分为词类、词序、构词、拼写、冗余和替代等六大类错误。按照桂诗春(2004)的分类,拼写和构词属于词汇感知层面的错误;而词类、词序、构词、冗余和替代则属于词汇-语法错误。
首先来看拼写错误,这类错误与感知表征、特别是记忆有关,是词汇感知层面最典型的错误,与学生写作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太大关系(桂诗春,2004)。但是拼写错误可能与学生对单词的错误发音有关。何安平(2001)发现,中学生拼写错误中有一半以上可能与其错误发音有关,她进一步指出,这种发音错误可能与母语负迁移有关。而本研究中两类模式学生的拼写错误率几乎一致,如果拼写错误受到发音错误的影响,而发音错误受到L1(或L2)负迁移影响的话,那么,两类模式学生的发音错误到底是受到了L1还是L2的影响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不论如何,本研究中四个班的拼写错误率几乎一致也说明拼写错误与学生作文水平高低并不存在相关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两类学生在L3词汇感知层面没有差异。
本研究中词汇-语法错误还可进一步区分为语法错误和语义错误。其中替代错误就属于语义错误。在这类错误中,两类模式的学生在词型错误方面有显著差异,即“以藏为主”学生更容易用语义不同的词来替代某一概念。这说明学生L3词汇与概念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还不够强,是学生语言水平较弱的表现。从词类、构词、冗余等几大类别的错误来看,“以藏为主”学生所犯错误更多,说明“以藏为主”学生的词汇语法知识水平较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呢?原因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第一个原因来自于L1影响。以“代词”和“介词”错误为例,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以藏为主”学生代词错误主要出现在不会使用物主代词上。比如,“*we class are arguing ...”, “*we active time ...”等。这可能与其母语藏语中没有物主代词有关。藏语中的代词只有人称代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和不定代词,所属关系是通过人称代词来实现的(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从以上两个例子也能看出学生在表示所属关系时使用了人称代词。再来看介词使用错误。这类错误主要是学生添加多余的介词造成的,比如“*... discuss on after class”, “*... study with everyday”等。藏语中没有介词这一词类,介词的语法功能主要是通过名词格的变化来实现。比如,要表示英语介词of的“所属”功能,藏语通过名词的“属格”来实现;要表示英语介词by,with等的“工具”功能,藏语通过名词的“具格”来实现;表示英语介词to, on, in等“方位”功能,藏语通过名词的“业格”、“为格”、“从格”等来实现。藏语的这些格的功能都是通过在名词后面添加“助词”来实现的,助词的形式变化多样,依据名词后面的音节而定(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而汉语中有介词,其语法功能的实现和英语比较相似。因此,不难看出,“以藏为主”学生在介词上所犯错误较多是受到了L1负迁移的影响,而“以汉为主”学生在介词使用上的低错误率可能是受到了L2正迁移的影响。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Rothman(2015)提出的类型近似模型,即在某一语言规则上与L3更近似的L1或L2更能成为迁移发生的源语言。
第二个原因可能与教学有关。在对授课教师进行访谈时,他们均认为对于“以藏为主”学生而言,英语语法是一个难点。主要原因与教材编写语言和课堂媒介语有关。“以藏为主”的学生汉语水平普遍较弱,加之学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汉语语法体系,对于使用汉语进行的语法讲解理解起来难度自然就会很大。而“以汉为主”学生由于汉语水平普遍较高,汉语语法体系也已基本完备,对于用汉语编写和讲解的英语语法规则理解起来自然要相对容易。由此可以看出,汉语L2水平的确对英语L3学习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一结果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Flynn等人(2004)提出的累积增强模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作用既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直接作用在于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可以利用比较成熟的L2语法体系来帮助建立L3语法体系,而间接作用则是通过教学媒介语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恰好教学媒介语就是L2,那么L2水平越高,L3学习效果可能越好。
六、 结论
对于藏族中学生而言,汉语L2水平越高的学生在英语L3文本准确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而在作文长度和复杂度上并未表现出优势。因此,很难说藏族学生的L2水平在L3习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汉语L2水平越高,英语词汇语法的习得效果可能会更好。但是这一作用又与L3教材编写语言以及课堂授课语言等教学媒介语联系在一起,即教学媒介语恰好是学生的L2时,其水平越高,越有助于L3词汇语法的习得。尽管汉语L2对英语L3作文水平高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似乎并非如第二语言主导模型所提出的那样对于L3英语学习具有绝对主导作用。相反,藏语L1在英语L3学习中既发挥了正迁移作用,也发挥了负迁移作用。总之,由于藏族中学英语教材用汉语编写,教师中既懂藏语又懂汉语的人员很少,目前的状况可能会给汉语水平较低的藏族学生英语学习造成一定的困难。可以设想,如果英语教材使用藏语编写,授课教师也用藏语讲解,那么“以藏为主”学生英语学习效果可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