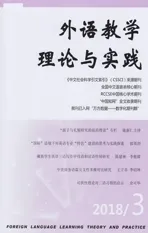人际语用学研究的社会认知路径*
2018-09-13南京大学沈星辰
南京大学 沈星辰
提 要: 从传统范式到现阶段范式,不同礼貌研究路径在两大争论焦点上持有不同立场: 其一,礼貌研究的视角;其二,礼貌现象的解释层面。作为前沿研究成果之一,Long(2016)面向关系工作提出的社会认知路径尝试解决上述争论。该路径侧重交际中人际关系的探讨,对于礼貌研究两大争议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但受自身研究背景的局限,未能对人际交往与社会认知过程提出完整的解释。因此,更为完善的人际交往社会认知路径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1. 引言
语言礼貌研究自Lakoff(1973)、Brown & Levinson(1978/1987)及Leech(1983)以来,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相关研究或许是语用学领域中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争议最广泛、最长久的话题之一。笔者认为,从传统范式下的礼貌研究到现阶段范式下的礼貌研究,两大争论焦点渐趋明显,不同礼貌研究路径对其持有不同立场: 其一,礼貌研究应采用分析者视角抑或参与者视角;其二,对礼貌现象的解释应注重认知层面抑或互动层面。针对上述争议,本文讨论近年出现的一种社会认知路径(Long, 2016),探讨其对于解决上述争议的贡献与不足,从而为未来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礼貌研究指出方向。
2. 礼貌研究的两大争议
2.1 分析者视角VS参与者视角
基于研究视角,可以将礼貌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Grainger, 2011; Culpeper & Haugh, 2014): (1) 第一阶段,传统礼貌路径(如Lakoff, 1973; Brown & Levinson, 1978/1987; Leech, 1983);(2) 第二阶段,后现代路径(如 Watts, 2003; Locher, 2004; Locher & Watts, 2005);(3) 第三阶段,交互路径(如Terkourafi, 2001, 2005; Arundale, 2006; O’Driscoll, 2007; Grainger, 2011; Haugh, 2007; Culpeper & Haugh, 2014)。
传统礼貌路径采取分析者视角(analyst’s perspective)或客位路径(etic approach),表现为采用自行界定的礼貌理论概念进行研究。事实上,传统礼貌理论框架均致力于对礼貌现象进行抽象理论建构,根据相关学者(Sifianou, 2010;Culpeper & Haugh, 2014)的总结,其共同点包括: 其一,认为礼貌是一种理性活动,其根植于人类获得和谐人际关系与避免冲突的需要,因而具有普遍性,相关理论框架尽管留有一些文化变异的余地,但总体上具有普适性;其二,礼貌是一种理性活动,由一定的原则或规则统领,礼貌框架的目的就在于从礼貌现象中抽象出相应原则或规则;其三,没有区分作为学术建构的礼貌概念与常人礼貌概念;其四,均产生于Austin与Grice语言哲学思想兴盛时期,“言语行为”、“意图”、“含意”(特别是特殊会话含意)、“合作原则”等概念在相应框架中均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有研究者(Terfourafi, 2005)指出,传统礼貌研究对礼貌的定性均为特殊会话含意。
后现代礼貌路径(postmodern approach)或话语路径(“discursive approach”)采取参与者视角(participant’s perspective)或主位路径(emic approach),该路径发端于Eelen的CritiqueofPolitenessTheories(2001)一书对于传统礼貌路径的批判。Eelen (2001)指出,传统路径中对于礼貌概念的建构并没有认识到礼貌是交际中交际者对于交际行为的评价,而作为交际评价的礼貌只能在实际交际过程中由交际参与者作出(Watts, 2010),因此,传统礼貌路径的分析者视角及与之相关的脱离语境的礼貌判断均是不可靠的。后现代礼貌路径研究者采取建构主义视角(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认为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在交际中进行协商的。相应地,礼貌研究重心应在于对真实交际场景中的交际者礼貌判断的潜在争议进行研究(Grainger, 2011)。因此,后现代礼貌路径认为传统路径中的分析者视角或者抽象礼貌概念建构对礼貌研究没有任何作用。后现代礼貌路径的优点在于对自然语料的重视以及指出礼貌判断的争议性特征。但是,这一路径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比如,虽然其中较激进的学者(Locher & Watts, 2005)提出要抛弃一切的理论建构,但即使是他们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化也是不可避免的(Terfourafi, 2005; Grainger, 2011),比如其中尝试从意图(intention)、感知(perception)、评价(evaluation)等层面对礼貌现象进行解释,同时参与者本身对于礼貌的解释和评价也是一定程度上理论化了的。Terkourafi(2005)甚至指出,后现代路径偏离了解释语言选择这一任务,而似乎倾向于将礼貌理论简单化为一种对交际者用什么词语来指称其行为的描述。
交互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路径和后现代路径有重叠,但其综合采用了分析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建构。具体而言,交互路径的研究者在坚持后现代路径所倡导的对具体语境下的自然话语语料和交际者对于意义的建构的研究之外,[注]由于但不限于这些因素,交互路径的研究者们(如Terkourafi, 2001, 2005; Grainger, 2011; Arundale, 2006; Haugh, 2007;O’Driscoll, 2007)也大多认为自身的研究是礼貌的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Grainger, 2011)。重新引入了Goffman原先倡导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指对于交际的分析不仅需包括哲学/语言学层面的描述,还应包括交际者所受到的社会道德规约(Goffman [1983]1997: 171),这一思路呼应了Grice的“言语是社会行为”(Austin, 1962; Grainger, 2011)的观点。在具体分析中,交互路径研究主要借用了会话分析方法,特别是其中的话轮转换、话题控制等概念(Sacks et al. 1978; Schegloff et al. 2002)。总体而言,交互路径吸取了后现代路径的长处,但保留了对于礼貌概念的抽象理论建构和总结,以此解释交际中的语言活动。该路径中不同研究者对于礼貌的抽象理论建构有所不同,如Terkourafi (e.g., 2001, 2005)采用基于框架(frame-based)的路径研究礼貌现象,[注]同样借用(认知)框架概念来解释礼貌现象的还有Watts (2003), Locher (2004), Locher and Watts (2005)等,但Terkourafi (2001, 2005)是目前而言最为详尽的基于框架的礼貌路径(Culpeper & Haugh, 2014)。而Grainger (2011)采用礼貌研究三阶段整合路径分别对礼貌现象的不同层级进行研究。
概括而言,从礼貌研究的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礼貌研究者对于抽象理论建构的态度经历了否定与再否定的过程,但可以看出,传统路径的理论建构与交互路径的理论建构存在较大的不同: 举例而言,传统路径的理论建构由于来自于研究者本身文化的相关概念的抽象,不可避免带有相关文化的烙印,对其他文化中交际现象的解释力不够,因此饱受“西方中心主义”等批评;而交互路径,如Terkourafi(2001, 2005)基于框架的路径与Arundale(1999, 2006, 2010)互动面子理论,采用了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概念(如前者的认知框架以及后者的分离/联结面子),超越了传统的分析者VS参与者视角的争论,提供了将抽象理论建构与参与者解读成功整合的可行路径。然而,就目前而言,这些路径仍然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此处不再详述。
2.2 认知论 VS互动论
礼貌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长久争议是认知论(“cognitivism”)与互动论(“interactionism”)在礼貌理论中的地位之争。这一争议在礼貌研究中首先为Brown & Levinson(1987: 194)提出,他们指出,与认知论一样,自己的理论框架不能解释交际中的浮现特征(emergent properties),这些特征在交际过程中产生,不是交际者已有的特征。Brown & Levinson进一步指出,优化的礼貌理论将最可能从对于交际系统性的研究(即互动论范式)中产生。
基于上述论点,Arundale(2006)进一步归纳了传统礼貌路径存在的描写/解释不充分性:
其一,孤立的社会自我概念。对于面子概念的评价需要回归其基础,即Goffman (e.g., 1967)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概念。Goffman将社会自我定义为社会化的自我,其社会化为其进行各种仪式化(ritual)交际提供了规则与脚本。在这一定义中,社会化指自我将各种预先存在的社会文化规约进行内化(internalize)的过程。持批评意见的研究者认为,Goffman的社会自我概念以及继承其概念的Brown & Levinison框架,将社会自我错误简化为被动遵照社会文化规约进行活动的“能判断的木偶”(“judgemental dope”)(Arundale, 2006: 198),并认为,真正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于个体在具体交际中对于有意义行为无数次的构建与解读,因而个体对于社会文化规约具有构建作用,而非被动接受。
其二,心理化的面子概念。Brown & Levinson(1978/1987)的礼貌研究的传统路径继承了Goffman将面子定义为公开的自我形象的社会心理面子观,并加以发展,从内在需求角度定义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注]Brown & Levinson(1978/1987)对于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解读被学界广泛定义为一种需求观,但Brown本人却声明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解读为个体需求是将其误解为一种具体化、心理化的概念(见Arundale, 2006)。即积极面子是使个体需求得到他人肯定的需要;消极面子是个体各种行为的实施不受阻碍的需要,因此将面子发展为一种个体化的社会心理观念。
其三,单纯心理层面的交际解释。Schegloff(1988,见Arundale, 2006: 199)指出,Goffman虽然指出对于交际的研究与其侧重于个体及其心理,不如侧重于不同交际者的行为在交际中的交互作用,但是Goffman(1967)在具体研究中通过“仪式化要求”来解释交际秩序(interactional order),可见其对于交际的解释仍然是从社会心理层面作出的,而非从会话的序列性组织(sequential organization)进行解释。
回顾礼貌研究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后现代路径下的礼貌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互路径礼貌研究均采用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作为哲学指导,并大多采取民族志方法论与会话分析作为分析路径,因而能够更好地描述交互性特征。这类路径的共识或可大致归纳如下: 社会自我不是孤立的内化社会常规的个体,而是在与其他社会自我的交际关系中产生和维持;意义(包括信息、行为、关系)不是单纯的由说话人发出后为受话人接受,而是在交际中由交际双方共同建构,因而会产生浮现特征。因此,其分析单位是“互动”而非交际者,是两个或以上话轮组成的话语序列而非单个语句(Arundale,2006)。
基于本节所回顾的两大争议,我们将在第3节呈现有助于消解相关争议的一种社会认知模式,即Long(2016)关系工作的社会认知路径。然后,笔者将在第4节对上述理论路径加以简要的评价。
3. 关系工作的社会认知路径
Long (2016) 是对礼貌研究者对于抽象理论建构的存在是否合理有效的长久讨论的一个回应。Long 不同意Mills (2011: 34)认为礼貌研究的“宏大理论时代”已经终结的观点,而认为以文化普遍性为特征的理论建构可以是有效的,前提是该理论是对于交际中潜在的认知处理机制的描述。同时,Long指出,礼貌研究的交互路径虽然就文化普适性理论建构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因对认知机制的解释不够清晰等问题,仍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描写与解释不充分性(Long, 2016)。在此基础上,Long(2016)提出其关系工作的社会认知路径,重点强调了凸显(“salience”)(Long, 2016: 1)这一认知机制,包括认知凸显(cognitive salience)与情感凸显(affective salience),构成关系工作(relational work)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
相关研究(如Eagly & Chaiken, 1993; Oscamp & Schultz, 2005,见Long, 2016)认为,认知凸显和情感凸显共同构成社会认知的标记性(“markedness”)。认知凸显又可进一步分为“相关”(“correlative”)凸显与“对比”(“contrastive”)凸显,指的是对于客体的相关属性与特征的感知,而情感凸显指与某一特定客体相联系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反应(Long,2016)。需要指出的是,主流认知科学研究一般仅将本文的对比凸显视作认知凸显,即对于现象的处理结果与期待(expectation)形成对比,因此成为有意注意(conscious attention)的目标。但Long(2016)将认知凸显的概念拓宽,认为只要一个现象的典型特征或特点在社会现象感知中被选择与识别,不管与期待是否相符,该认知处理过程就是“凸显”的。[注]Long指出,这样的“凸显”定义方式与Kecskes(2011)跨文化语用学社会认知模式中对“集体”(“collective”)凸显与“浮现”(“emergent”)凸显的区分相似。
基于认知凸显和情感凸显的认知处理机制,Long构建了“关系工作的社会认知路径”(“social cognitive account of relational work”),这一路径如图1所示:[注]尽管“图1”是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的,但其本质上是一个类似流程图形式的工作过程图示,因此本文沿用Long(2016)的做法,称其为“图”而非“表”。

认知凸显指示符合预期的角色—关系的行为(“相关凸显”)该预期得以确认指示超出预期的角色—关系的行为(“对比凸显”)该预期受到挑战新指示的角色—关系被接受新指示的角色—关系被违背情感凸显积极情感回应 (可能)积极情感回应 (可能)消极情感回应 (可能)
图1.关系工作的社会认知路径
如图1所示,首先,Long指出,交际行为“指示”(“index”)了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是否合乎预期,即,交际者基于交际双方的历史关系,将交际中的特定行为感知为符合或超出其预期,前者为相关凸显,而后者为对比凸显。其次,不同类别的认知凸显可能产生不同的情感凸显,具体而言,符合交际者角色—关系预期的行为在认知处理层面属于相关凸显,即其不太可能成为有意注意的对象,因此也不太可能产生情感反应或评价;另一方面,超出交际者角色—关系预期的行为在认知处理层面属于对比凸显,因此认知和情感层面均更可包括高意识参与度的处理过程。第三,就对比凸显行为而言,如果其指示的角色—关系为交际者所接受,那么产生的即为积极情感凸显,如果未被接受,那么产生的即为消极情感凸显。
Long在该研究中同时给出了一个更能体现该路径交互性特征的图示,如图2所示:

图2 关系工作的交互模式
图1与图2是同一路径的两个不同呈现方式,其区别在于图2展示了交际双方不同预期的交互。图中1到4四部分分别指示不同的角色—关系。第1部分表示符合交际双方(A与B)角色—关系预期的行为,第2部分指符合A预期但不符合B预期的行为,第3部分反之,第4部分指既不符合A预期也不符合B预期的行为。在具体案例研究中,Long展示了交际双方预期的历时变化及其交互、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认知处理结果(包括认知凸显与情感凸显两层面)。
4. 理论评价: 优势与不足
(不)礼貌研究中对于认知概念的采用并非始于Long(2016),此前已有Watts(2003)从关联论出发研究礼貌,Terkourafi(2001, 2005)将认知框架看作礼貌判定的基础,Culpeper(2011)提出社会认知整合模式以解释不礼貌现象。但是,在笔者看来,Long的路径应该是目前而言认知机制的界定较为清晰、对礼貌现象的解释较为系统的路径。这一路径存在以下优势:
第一,在人际语用领域引入了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认知机制,独立于具体的文化概念但又能与之兼容。Long指出,在对话语经历了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认知处理之后,交际者可以根据自身所处文化语境对相关行为进行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具体评价,如“智慧”、“亲和”、“礼貌”等。
第二,从认知凸显角度兼容了礼貌的语用观与社会文化观。Culpeper & Haugh (2014)认为现有的礼貌研究对于“礼貌”持有两种观念: 其一,礼貌的语用观(pragmatic view)(如 Leech, 1983; Brown & Levinson, 1978/1987),将礼貌视作一种解决交际问题的策略,如对于交际冲突的避免和消解;其二,礼貌的社会文化观(socio-cultural view)(如Lakoff, 1973; Goffman, 1967; Watts, 2003; Locher & Watts, 2005),将礼貌视作一种对于特定文化中社会规范的遵守,即,若某一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则在礼貌评价时得到积极结果,而若不符合社会规范,则在礼貌评价时得到消极结果。礼貌的语用观与社会文化观的争端在礼貌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成为对传统礼貌路径进行批判的对象之一,如Ide(1989)对于东西方礼貌概念差异的讨论,Kdr (2013) 对人际交往中仪式性成分与策略性成分的讨论(另见陈新仁,2016),Watts(2005)对于礼仪性与礼貌性行为的讨论,Terkourafi对于礼貌作为一般会话含意或特殊会话含意的讨论。但近来学者们逐渐发现礼貌的上述二分法并不一定准确,如Pizziconi(2011)指出,所有的语言选择都是基于语言使用者本人对于语境和人际适切性的理解,同时也都被语言使用者策略性地操控;Watts (2003)同样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并不是极端的策略性或仪式性礼貌,而是无数可能的中间状态。Long从认知凸显角度为上述观点为解决极端性观点提供了一个可行解释框架,不同性质的礼貌的区分主要是认知凸显程度的区分,这种程度的区别是连续统的,而非截然对立的。
第三,将人际关系全部纳入统一的框架进行解释。经典礼貌框架(特别是Brown & Levinson框架)面临的另一重大批评是其仅包含了人际关系的很少一部分,即对于人际冲突的避免,而未包括如不礼貌等的讨论(如 Culpeper, 1996)。Long的社会认知路径从认知处理层面指出,消极的人际关系建构主要表现为消极情绪反应的产生,后者是由于特定行为所指示的角色—关系不符合交际者预期,从而引起对比凸显,而在认知处理之后这一角色—关系未被交际者接受。
第四,正如第三点所提及,Long的路径基于认知凸显和情感凸显的核心概念,使认知处理和情绪反应得以系统联系,从而进一步使礼貌的解读和评价得以系统联系,具体而言,相关凸显的行为在情感凸显层面很少可能成为有意识处理的对象,而如果果真进入情感层面有意识处理,其结果很可能是积极的;对比凸显行为在情感凸显层面很可能成为有意识处理的对象,其结果基于预期的调整与否,可能是积极或消极的。Long指出,这一点解决了先前礼貌路径中礼貌解读与评价的不连贯,特别如Locher(2004)中,认知层面无标记的概念在评价/情感层面却成为有标记的概念。Long的路径对于情感层面的重视在先前礼貌或更广层面的人际语用学研究中也是大部分缺失的,而近来不少学者逐渐意识到情感层面在人际语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如Locher & Langlotz,2013; Culpeper,2011)。
第五,“角色—关系”这一概念很好表现了个体与关系的互动性特征,即,个体的角色是在交际关系中建构的。Goffman的社会心理面子观、Brown & Levinson的面子需求观以及大部分礼貌框架均将面子作为自我的属性,而未考虑面子的动态建构性。从这一方面来说,Long的社会认知路径很好体现了互动论的立场。
当然,Long的社会认知路径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该框架对于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与区别未进行细致论证。比如该框架中符合预期的行为如进入认知处理,更可能产生积极情感凸显;不符合预期的行为如被接受将产生积极的情感凸显,而不被接受则将产生消极的情感凸显,这样的对应关系似乎并不一定能成立。比如,一个对手的言辞激烈的挑衅是符合预期的,但似乎较不可能使人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其次,该框架中作为一个完整的关系工作尚缺少不少重要元素,如语言、语境、评价等。以语境为例,在Long的框架中,由于语境元素的缺失,似乎不能描述不同场景下角色—关系可能产生的变异;同时,关系评价虽然与情绪有关,但两者似乎不能等同(Locher & Langlotz,2013)。第三,该框架仅描述了社会认知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并未描述人际关系对于认知的反作用,即,由于人际关系的不同,交际者对于同一行为(如戏谑)的理解可能会不同。
5. 结语
本文对当前礼貌研究(或广义人际语用研究)现状从两方面进行了综述: 其一、研究视角之争(观察者/研究者视角VS参与者视角)及与之相关的理论终局窘境;其二、研究范式之争(认知论VS交互论)。本文所评述的Long(2016)关于关系工作的社会认知路径尝试将人际语用学与社会认知相结合,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两大争端的回应。该路径尝试以“凸显”认知机制这一文化普适性概念解决研究视角与理论上的争议。
Long(2016)关于关系工作的社会认知路径对礼貌研究两大争议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但目前而言,该路径仍存在一定的有待完善之处。该路径从人际互动出发,侧重对于交际中人际关系的探讨,对于意义理解过程并未进行细节性的讨论,同时也未能涵盖人际关系对于行为理解的反作用等。因此,更为完备的人际交往的社会认知路径还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