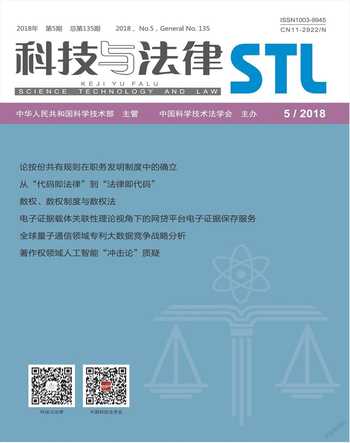网络环境下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法立法保护
2018-09-10张志伟
张志伟
摘要:在体育赛事节目只能被认定为录制品的情况下,仅将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扩展到网络领域并不能周延地保护体育赛事节目。 因为现阶段我国还不宜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这意味着网络广播组织播放的体育赛事节目被网络盗播时,无法通过广播组织权给予其保护。所以,为周延地保护体育赛事节目,在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延伸至互联网领域的同时,还应完善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关键词:体育賽事节目;著作权法;修改思路
中图分类号:D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945(2018) 05-0089-06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一些网站未经许可对别的媒体直播的体育赛事节目进行实时转播,严重损害了赛事组织者、传播者等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通过法律保护体育赛事节目是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问题在于保护体育赛事节目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并不是为广播组织规定专有权利,适用一般原则条款毕竟有其不确定性。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固有局限,学界普遍认为《著作权法》是保护体育赛事节目的最佳路径。但运用《著作权法》保护体育赛事节目,需要明确其法律性质。我国《著作权法》将要进行的第三次修改,仍然坚持了著作法与邻接权二元分立的立法模式。这说明我国《著作权法》所坚持的独创性标准仍然是著作权体系意义上的独创性标准,要求智力创作具有较高程度的创造性。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体育赛事节目的创造性程度较低,其不具备作品独创性的要求,无法成为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品[1]。在我国的著作权法司法实践中,从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观点来看,一般也不认为体育赛事节目属于作品,因为体育赛事节目在独创性上尚未达到作品所要求的程度[2],而只能被认定为录制品[3]。
如果体育赛事节目不能被认定为作品而只能被认定为制品的话,基于现行《著作权法》第45条的规定,广播组织转播权尚不能规制通过网络实施的盗播行为。因为2001年《著作权法》为了配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广播组织权仅满足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最低要求,并且当时传播技术并不涵盖互联网,仅包括传统的无线方式和有线电视进行的转播[4]。我国奉行“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司法实践中,法官也不能够超出立法原意将《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转播权”扩张解释为可以涵盖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转播。
不少学者主张应将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扩展至互联网领域,为规制网络盗播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对体育赛事节目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5]。为保护广播组织的正当利益,并在立法上实现技术中立,应当对广播组织的转播权进行扩张,使之能够控制通过任何技术手段和媒介实施的同步传播行为[6]。但在我看来,仅将《著作权法》第45条第1款规定的广播组织的转播权扩展至互联网领域,仍难以全面规制网络盗播行为。因为这种立法建议只是扩大了广播组织权的内容,并未涉及广播组织权主体的扩大。因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5条的规定,广播组织权的主体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不包括网络广播组织,但网络广播组织如今已经成为直播体育赛事的重要媒体。例如,2015年腾讯公司与美国职业篮球协会即NBA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腾讯公司以5亿美元的对价购买了NBA联盟5个赛季的网络独家直播权,腾讯公司通过其网络平台直播NBA赛事节目。如果网络广播组织直播的体育赛事节目被盗播,由于其不是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则仍然无法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性质若定性为制品,则如何通过著作权法的修改以周延地保护体育赛事节目仍需继续探讨。
一、体育赛事节目“网播”保护的国际争议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新的传播媒体大量涌现,传统广播电视有了更多的竞争者和替代者,分流了大量观众。首先,网络电视台、IPTV等大量出现,而在网络上传播音频、视频内容的网站更是不计其数;其次,传统的广播组织纷纷通过自己的网站播放广播电视节目,利用网络进行广播正成为其提高视听率和扩大覆盖面的有效方式,如中央电视台通过无线方式直播奥运会节目的同时,央视网也会同步直播。不少网播组织虽然还没有“台”的称谓,但其传播视听节目的业务,事实上已经成为其重要业务,所实现的功能与传统的广播组织基本相同,其盈利模式也差不多,收取广告费、注册费、点播费等。这种网络广播组织的播放节目的新形式简称为“网播”。“网播”具有不受时空限制、互动性强的优点,与传统广播在播放节目的效果上差别不大,因此,网络从功能上来讲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广播。但这些广播节目内容的新的提供者能否成为各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组织权的主体,目前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大的争议。
打击网络盗播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体育赛事节目是网络盗播的重灾区。首次规定广播组织权现行的国际公约为《罗马公约》,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其目的是制止广播节目的盗播。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的广播组织制度在互联网环境下受到了很大冲击,主要表现为网络盗播活动十分猖獗,严重侵害了广播组织权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沿用传统的广播组织制度已难以适应网络环境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自1998年至2006年连续召开了15届会议,讨论并提出了有关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最新法律文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SCCR/15/2),就是想通过更新和扩大广播组织的权利,为打击网络盗播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在讨论过程中,各国对将传统广播组织的转播权扩展至互联网领域都表示比较一致的支持,这有利于打击不经许可通过互联网转播广播节目的行为,维护广播组织权利人的正当利益。但对于网络广播组织是否应纳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范围却存在很大的争议[7]。发展中国国家普遍认为,草案设计的广播组织权利保护水平过高,会妨碍本国民众对信息的获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阶段保护网络广播组织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一些版权法上的利益主体如作者认为如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保护范围会损害其利益,一旦“网播”受到保护,则公众使用网络广播中的作品会受到网络广播商的限制,作品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势必会缩小,而作品的价值或者说市场影响力与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这必然会损害作者的利益,这是版权人不愿意看到的。日、美等发达国家普遍主张应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保护范围之内。日本国内的法律目前正在考虑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之中。美国政府也主张,由于普通广播和网络广播在功能上完全类似,应当一视同仁地给予法律保护。发达国家之所以强烈支持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条约保护,主要是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是互联网信息输出的主要国家,大量互联网信息被别的国家的社会公众可以不经许可免费获取,这对其是不利的。如果对“网播”给予法律保护,那么发展中国家民众要想获取其互联网上的信息,则必须经过许可且要付费使用,这无疑可以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取信息的流量,并且获取大量的许可使用费,无疑将有利于本国网络产业的发展。最终,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个草案的内容难以达成一致,这个草案早已停止讨论。
二、播放体育赛事节目的网播组织能否成为我国广播组织权的主体
有学者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类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等网络广播组织,与传统的电台、电视台一样都是合法的传播者。邻接权是传播者因传播作品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网络广播组织和传统的广播组织一样,在传播作品时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资金和技能,对其劳动成果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不能基于传播者身份的不同,而剥夺其应该享有的权利[8]。王迁教授也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应坚持技术中立的原则,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的范围提供保护。如果从网络广播与传统广播在传播效果上没有差别的角度讲,网络广播组织应与传统广播组织一样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应该注意到,广播组织权利制度不仅仅关系到广播组织的私益,它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密切,与一个国家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权联系甚大。如果扩大广播组织权主体的范围,则会对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利益造成很大影响。在立法中只强调对广播组织的利益保护,而忽视了广播组织的公益性,最终将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技术中立是不少国家著作权法立法的一个原则,但利益平衡原则相比技术中立是我国著作权立法应优先考虑的原则。利益平衡原则是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基石,是知识产权法追求的主要目标,它贯彻于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理解利益平衡原则的要义可以先考察著作权法的起源和立法目的。
在人类没有著作权法之前,任何人的智力成果都处于共有领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是否发表自己作品的自然权利。但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知识的增长、文明的进步十分缓慢。近代国家肩负着繁荣文化科学事业、实现公民文化社会权利的宪法责任。著作权法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或者刺激机制应运而生。它赋予了创作者对于智力成果的专有权,但却大大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了知识的创新和增加,推动了文化科学事业的进步。著作权体现了私法上的平衡并实现了公法上多赢的目标,它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多赢机制[9]。从著作权法的起源和立法目的来看,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手段,最终目的在于繁荣文化科学事业,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就著作权法而言,其有两个主要的价值目标,一是保护著作权法上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利益;二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公共文化福利和知识的增长,繁荣科学文化事业。两种利益如果存在冲突,在利益衡平时,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于权利人的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对个人利益的限制[10]。因此,著作权法上的这种平衡并不是追求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绝对平衡,它是在公共利益优先保障的前提下,尽量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客体即知识产品是一种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知识产权分享的规模化和广泛性是知识产权法的最终依归。知识产权法以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以确保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11]。失去了公共利益这个前提,一切个人利益便失去了依托。在利益冲突难以协调的情况下,低位阶的法律利益让位于高位阶的法律利益是利益平衡原则的应有之意。一般来说,充分保护权利的专有利益会激励更多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和传播,会促进社会发展和繁荣文化科学事业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但这往往限于国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而言。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一旦跨越国家,利益平衡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充分保护他国公民或者组织的个人利益会激励更多的知识和信息的创作,却不一定会促进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网络广播组织是否应纳入广播组织权主体的国际争议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我国现阶段不宜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第一,现阶段如果给予网络广播以法律保护,难以在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实现平衡。保护网络广播虽有利于规制体育赛事节目的网络盗播这一局部利益,但从整体上看则会触动我国社会公众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利益。未经网络广播组织许可,社会公众不能收听、收看网络广播,意味着社会公众往往要通过付费才能获取网络广播中的信息,就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大部分民众的购买能力都比较有限,因此,不愿意付费获取网络广播中的信息,客观上会妨碍社会公众获取网络中的信息,从而影响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没有必要超出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其保护。发达国家保护网络广播组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民众的购买力普遍较强,付费获取网络广播信息不会成为获取信息的障碍。相反,由于发达国家的网络产业化已经十分成熟,客观上反而促进了互联网上信息流量的增加。将网络广播纳入法律保护不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拒绝给予网络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本国的社会民众能够方便地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来促进本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虽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宜赋予其广播组织权。不赋予网络广播组织相应的广播组织权,网络广播组织仍可以依靠其经营项目生存发展,而我国公众可以自由地从网上接收各种广播节目包括体育赛事节目,了解各类信息和知识,这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待将来保护网络广播组织对社会利益影响不大这一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保护范围,以平衡社会公众和网络广播组织的利益。
三、体育赛事节目的周延保护还需要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英美国家,由于对作品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要求极低,体育赛事节目都是作为作品而受到版权法的保护。英国《版权法》通过将“录音”、“影片”、“广播”列为法定作品的客体。体育赛事节目作为“影片”受到版权保护[12]。美国《版权法》将体育赛事节目作为视听作品受到保护。美国国会在1976年的《版权法》报告中指出:连续画面只要向公众进行实时传播同时进行了录制就可以作为电影作品受到保护[13]。而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二元结构体系,将智力成果按照独创性的高低区分为作品和制品。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性质在大陆法系国家虽存在争议,但在实务界关于体育赛事节目法律性质的争议却几乎不存在。这是因为规制网络盗版、保护体育赛事节目完全有法可依。根据《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的规定,作为体育赛事节目权利人的播放组织享有控制一切媒体行为的权利。体育赛事节目的权利人包括网络广播组织,控制一切媒体行为包括互联网转播。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第94条的规定,体育赛事节目的权利人享有发行、复制以及为广播、公开放映或网络传播目的而使用体育赛事节目的录像载体的排他性权利。体育赛事节目的权利人也包括网络广播组织。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著作权法已經解决了通过著作权法保护体育赛事节目的问题,但这对于我国立法完善并没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为网络广播组织在现阶段不宜成为我国广播组织权的主体。 但是,考虑到广播组织包括和体育赛事组织者无论谁是节目的制作者,它们在保护体育赛事节目、打击网络盗播的问题上是利益共同体,可以通过完善录制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解决规制网络盗播的法律依据问题。目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限于“交互式”播放,而不包括“非交互式”播放。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源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第8条: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14]。但WCT第8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是为了将数字网络中的作品传播权纳入到著作权中,该项规定的权利范围比较广泛,并没有局限于何种传播形式。“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只是用于说明数字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具有交互性特征,而不是说明数字网络传播方式仅为“交互式”传播。我国已经加入了该公约,对来源于别的缔约国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保护,扩大到了“非交互式”的传播。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目的与WCT第8条相同,但却将数字网络传播方式限定在“交互式”传播,立法表达与立法目的明显不符。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一失误,是对WCT第8条的一种生吞活剥[15]。同时,对于本国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要小于其它缔约国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为本国公民提供的权利保护水平低于别国公民的权利保护水平,不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著作权益,也不利于我国公民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国外的作品未经许可通过互联网非交互式传播,我国有义务提供法律救济,而本国的作品未经许可通过互联网非交互式传播,我国却没有义务提供法律救济,这对我国著作权权利人明显不公。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应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扩大到非交互式播放行为,这有利于规制网络盗播行为,充分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同时,对于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并没有负面影响。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为作者、表演者和录像制作者,并不包括广播组织。即使广播组织不是体育赛事节目的制作者,仅是传播者,但体育赛事组织者和包括网络广播组织在内的传播者存在利益连带关系,出于理性考虑,二者自然会约定将赛事组织者享有的体育赛事节目信息网络传播权由对方享有,网络广播组织直播的体育赛事节目从而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间接保护。在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延伸至互联网领域的同时,完善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周延地规制体育赛事节目的网络盗播。
四、具体立法建议
基于体育赛事节目只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录制品,我国在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同时,还应积极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以使我国著作权法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从而为体育赛事节目提供周延的法律保护,保障我国体育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建议有二:第一,将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修改为“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下列权利:(一)许可他人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转播其广播电视节目”;第二,将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七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删除,将该项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第十条第六项规定的广播权合并,将第十条第六项修改为“播放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公开播放作品或者转播该作品的播放,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权利”。
参考文献:
[1]王迁.论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J]法律科学,2016(2):182-191.
[2]朱文彬.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保护——央视公司诉世纪龙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评析[J].科技与法律,2013(2):67-72.
[3]祝建军.体育赛事节目的性质及其保护方法[J].知识产权,2015( 11):27-34.
[4]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围著作权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78.
[5]宋海燕.论中国如何应对体育赛事转播的网络盗播问题[J].网络法律评論,2011(2):217-236.
[6]王迁.论广播组织转播权的扩张——兼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42条[J]法商研究,2016(1):177-182.
[7]胡开忠.信息技术发展与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的重塑[J].法学研究,2007(5):90-103.
[8]张革新.现代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37.
[9]徐瑄.知识产权的止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平[J].中国社会科学,2003(4):144-154.
[10]冯晓青.著作权法目的与利益平衡论[J]科技与法律,2004(2):84-87.
[11]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313.
[12] Hugh Laddie. The Modern Law of Copyright and Designs(4Lh,Edition), LexisNexis, London(2011), 451.
[13]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 (2t.h, EdiLion), Aspen Law&Business(2002)-4.
[14]靳学军、石必胜.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J].法学研究,2009(6):106-116.
[15]乔生.信息网络传播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