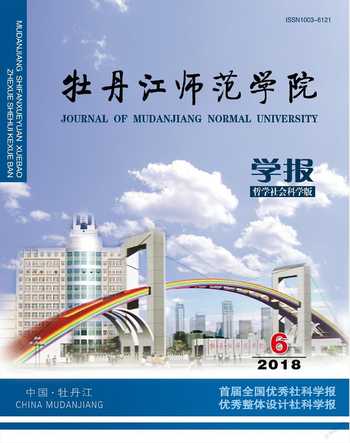论当代小说《茧》的叙事动力与审美品格
2018-09-10高虹石峰
高虹 石峰
[摘要]以叙事学为理论背景,细读当代作家张悦然的小说《茧》,从故事层面、话语层面、阅读层面三个角度对作品的叙事动力进行分析,揭示这部小说作品的审美品格。
[关键词]当代小说;叙事学;叙事动力;审美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
文本的内部运动取决于不稳定因素和紧张因素的引入、纠结及其化解。不稳定因素主要指文本中的故事性元素,緊张因素主要指文本中的话语性元素。正是由于不稳定因素和紧张因素被作者不断引入文本,叙事活动才能在文本内部从头至尾地发展,读者才能在阅读活动中对这一发展过程不断产生动态反应。[1]308本文将从文本的故事层面、话语层面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三个角度,浅析小说《茧》的叙事动力,揭示其中蕴含的审美品格。
一、故事层面的叙事动力
(一)叙事动力的宏观设计:激起欲望、延迟满足、最终满足
批评家布鲁克斯在《情节阅读》中,开创了一种心理分析方法,强调情节的时间性与生命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根据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将情节视作激起欲望、延迟满足、最终满足的过程。在《茧》这个作品中,李佳栖一直都渴望得到父亲的爱,而程恭一直渴望着李佳栖的爱。这两个人渴望爱、寻找爱、得到爱的历史是他们成长的历史,是贯穿文本始终的两条情节伏线,也体现出推动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作家张悦然如何处理故事中的两条伏线,使之鼓动波澜,发展成叙事之流呢?
1.程恭对李佳栖的爱
检视文本中“程恭对李佳栖的爱”这条动力线索,我们发现,作家张悦然安排这条线索“冲波逆折”多次,甚至一度变成了“潜流暗涌”。程恭对李佳栖的爱是从关注开始的。程恭清楚地记得李佳栖刚刚转入医大附小的情景:“上午第二节课后,老师把你领进教室。你细细高高的站在门边,细密阳光啄着你左边的脸,整个人像是锁在一帧过曝的相片里……”。[2]118
这份爱遭遇的第一次阻力来自李佳栖的家庭。李佳栖加入了程恭、大斌、子峰、陈莎莎组成的伙伴小团体,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李佳栖和程恭发明的各种游戏。那时,李佳栖发现跟程恭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这让她不再对生活疏离,想要在奶奶家生活下去。可是,李佳栖的奶奶徐绘云和李佳栖的堂姐李沛萱认为,李佳栖不应该跟“差生”混在一起。在暑假里,她们把李佳栖关在家里,李佳栖和程恭就靠给彼此写信来保持联络。
第二次阻力来自李佳栖的聪慧和早熟。李佳栖的聪慧和早熟让程恭产生了小小的自卑心理,他一心想要做些事来让李佳栖崇拜自己。在“死人塔”玩耍时,李佳栖看到人脑标本,就想到要把记忆留存下来,程恭想,“在你说出来之前,我竟然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又跑在了我前面,想到这个就觉得很失落。”[2]127看到程恭的植物人爷爷,李佳栖想弄清楚植物人的灵魂困在身体里在干什么,程恭觉得,“你用了一种大人跟小孩说话的口吻,沧桑、世故、闪烁其词,这令我很厌恶,甚至有一点受伤。”[2]146于是,程恭开始疯狂读书,想尽办法研究“灵魂对讲机”,想要把植物人爷爷唤醒,找出害他的凶手,并且改变自己的命运,承担家族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想要让李佳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大吃一惊”。
第三次阻力来自于程恭知道了一个秘密。在他研究“灵魂对讲机”的过程中,程恭无意间听到教堂牧师和妻子的对话,了解到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很可能就是把自己的爷爷害成植物人的“凶手”。李佳栖就变成了程恭“仇人”的孙女,这个秘密让程恭陷入了内心的纠葛当中。 “如同被冰封在一个巨大的冰块里,一种彻底的隔绝,可是我没有挣扎,也没有试图逃离,我必须呆在这孤独里,哪儿也不能去,因为如果想要摆脱它,就必须和你分开,我应该开始恨你了吗?这一场庞大的家族仇恨,如同一张巨大而致密的网,把我们两家人全部罩在底下,谁也别想逃脱。”[2]209
第四次阻力来自于李佳栖的丧父和转学。从那以后,两个孩子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漫长分离。这是小说文本中唯一的一次,李佳栖从程恭身边逃离,而这次逃离,实际上是程恭把李佳栖“弹开”的。心里装着“秘密”的程恭,忍受不了李佳栖在他面前炫耀父亲来看她的幸福,“你一脸沉醉地回忆着你和爸爸度过的夜晚,用一种不加掩饰的炫耀口吻,像是在告诉我,那从未得到过的宠爱究竟是什么滋味。你在提醒我,你可不像我,是没有人疼的野小孩。”[2]213在这样的心态下,程恭说出了伤害李佳栖的真相——“你在撒谎”“他不要你了”“你还是别骗自己了”。所以,这一次,文本告诉我们:是秘密,先于这两个孩子存在的秘密,离间了程恭和李佳栖之间的感情。
随着李佳栖转学离开,“程恭对李佳栖的爱”这一叙事动力线索转入了“潜流暗涌”的状态——爱变成了思念。关于思念,小说中的正面描写有两处。第一次是千禧年跨越千年的夜晚,在“泉城广场”,“末日,那时候我想到了这个,然后想到了你,我时常会想起你,但都是裹在一些事里,家族的恩怨、背叛和隐瞒,而这一次,是纯粹地想到你。那个好像什么都知道,总是跑到我前面去的小女孩”。第二次是SARS蔓延,程恭被隔离在317病房的隔壁,他想念着李佳栖,“我抱着箱子站在走廊里,廊道阴暗,空气里洇着雨的气味。……雨水淋湿了门前的地板,就是同一块地板,从前总是盈满阳光,下午的橘色阳光,你说它们像跳跳糖。”关于程恭思念李佳栖的侧面描写,在小说文本中出现过很多次,都是通过大斌、子峰和陈莎莎这几个童年伙伴来表现的。特别是陈莎莎,她爱了程恭很多年,但是她知道,“李佳栖早晚会回来的”,“你喜欢李佳栖”。在小说文本中,这条叙事动力的暗线一直持续,直到十八年以后,李佳栖与程恭重逢。
2.李佳栖对父亲的爱
关于李佳栖追寻父爱的这一条叙事动力线索,作家张悦然在小说文本中设定了三个结果。
其一,在父亲从前的学生“许亚琛”那里,李佳栖感受到本该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物质富足;在父亲从前的生意伙伴“谢天成”那里,李佳栖得到了从父亲那里没能得到的“生活上的照顾”;在父亲从前的同学和同事,大学教授“殷正”那里,李佳栖得到本该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精神上的引领”。
其二,与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联系,李佳栖用自己收集到的父亲的成长过程的碎片,拼凑出“父亲”一生的完整经历:他经历狂暴的青春和无法守护的爱情;他草率决定了婚姻;他消沉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和诗意精神;他苦心经营的跨国生意,在动荡中萧条下去;他的生命和激情,被家庭琐屑慢慢磨蚀。
其三,李佳栖在追寻父爱的过程中失去“唐晖”。唐晖是李佳栖在大学时代的学长,是一个愿意包容她并且教会她什么是爱,却始终无法理解她对父亲的深情的男人。李佳栖一次次与父亲的“故交”彻夜饮酒不归,唐晖在这个过程中渐渐丧失了耐心,最终弃她而去。这个结果使李佳栖在北京失去了名义上的家,于是她回到济南,回到“南院”,与程恭重逢。自此,文本的两条叙事动力的线索,在小说的结尾合而为一。
研究了文本的两条伏线之后,我们发现:程恭成长的线索是以他不断体会对李佳栖的感情作为动力的,它带领读者去体会人性和情感的深度。而李佳栖成长的线索,是以她不断寻找父爱的脚步为动力的,它带领读者不断地走入时代和社会的背景中,去领略生活的宽广。《茧》这个小说的文本就是在这样深且宽的情感河道中奔涌而成的。与此同时,小说中写到了唐晖对李佳栖的爱、陈莎莎对程恭的爱、大斌对李沛萱的爱、李佳栖妈妈对李佳栖爸爸的爱、汪露寒对李叔原的爱、汪露寒父母之间的爱、徐绘云对李冀生的爱、李冀生对陈淑贞的爱。这些情感都可以作为小说两条动力主线的余波和微澜,荡漾在小说文本这条情感的河道中,为这个小说作品增加层次和色彩。
(二)叙事动力的微观设计:感知、行动、存在
叙事学研究者戴维·赫尔曼将叙事作品中人物的行动细分为三种不同的过程类型:行动(doing)过程、感知(sensing)过程和存在(being)过程。他认为,在史诗里,行动过程要比存在过程更重要;在心理小说中,感知过程要比行动过程更为重要。[1]305我认为,在小说《茧》这个文本中,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分析人物的活动,从而描述文本中所呈现的叙事动态。下面简要梳理“程恭”这个人物在小说第三章开始部分的行动序列。
存在状态1:程恭知道爷爷的灵魂还关在身体里。
感知过程1:“要是他没有变成这样,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爷爷吧。……生出一股从来没有过的使命感:我必须把它解救出来。”[2]165
行动过程1:程恭去图书馆借书,想找到解救爷爷的办法。
存在状态2:“在那些深奥的句子里,得到一种肃穆的满足感。”[2]166
感知过程2:“你(李佳栖)耸了耸肩膀,脸上又露出大人般不屑的神情……‘你确定你奶奶你姑姑真的希望他活过来吗?……从前只是觉得你有点刻薄,现在才发现你是异常冷酷。”[2]167
行动过程2:程恭回家问奶奶和姑姑,发现没人希望爷爷醒过来。
感知过程3:“你(李佳栖)又想到了我没有想到的东西,跑在了我前面,真是可惡。……我忽然意识到,是躺在床上的一动不动的爷爷在供养我们。”[2]170
存在状态3:“我蓦地想起我们在死人塔里看到过的那颗苍白的脑,那会不会就是爷爷的?我打了个寒噤。爷爷究竟是怎么变成植物人的?”[2]170
行动过程3:“临睡前我缠着姑姑,追问她爷爷是怎么变成植物人的。……另外那个凶手呢?……他还住在南院,对吗?”[2]170-179
感知过程4:“她(姑姑)睡着了,留下我一个人,躺在黑暗和一大堆问题里。……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境遇,我正是生活在一口狭小的井里。我一无所有。即便拥有你们几个好朋友,拥有一些快乐时光,那也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你们会离我而去……那枚钉子,那个凶手。是他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生命轨迹。我坐在那个冷寂的角落,仇恨像越烧越旺的篝火。……”[2]180
存在状态4:“这个落魄的、破败的家族正等着我去拯救,我一定要把另一个凶手找出来。……我要发明一台可以和爷爷的灵魂通话的机器。灵魂对讲机。”[2]183
行动过程4:“每天中午回家匆匆吃过饭,就跑到图书馆去借书。人体解剖学、机械原理、佛教、古代炼金术……我把那些深奥的书翻了一遍……我开始在本子上画草图……我把攒了很多年的小猪存钱罐砸碎了……两个星期后的一天,等到天黑下来,我拎着一只硕大的塑料编织袋走出家门,快步朝医院跑去……一切就绪,我把手伸进饼干桶里,郑重地按下开关……。”[2]1183-1187
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在《茧》这个文本中,人物总是先感知,再行动,在行动的结果中存在,存在的同时又在感知,感知又引起新的行动。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一个人物连贯的行动序列。与此同时,不同人物的行动序列会交织在一起:一个人物的行动可能被另一个人物感知,引起另一个人物新的行动。如此,不同人物的行动序列编织在一起,故事的情节如永动机一般向前发展。在作者这样精心的设计中,小说具体篇章的叙事过程可以呈现出疏密有致、动静相宜的美感。
二、话语层面的叙事动力
(一)读者与叙述者:认知的差异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可能会发现,小说文本中没有哪一个人物是不重要的,如果没有意义,这个人物根本就不会被作家设计出来,并且出现在文本中。但是,那些文本中的“故事讲述者”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读者与“故事讲述者”在认知上的落差,造成小说文本在话语层面的“势能”。随着小说文本话语的展开,“势能”渐渐转化为“动能”——那些貌似“不重要的人物”,在“主要人物”的身边悄悄编织着一张动态的网,跟“主要人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背景的他们,不动声色地改变着周围的一切,直到“主要人物”恍然大悟,才发现他们的命运虽然可以选择,却只能循着多年前就已经被“不重要的人”埋下的伏线,在不经意间走下去。
程恭是《茧》这个作品中绝对的“一号男主角”,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之一。在程恭自己的意识中,改变了他命运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他的爷爷害成植物人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甚至当了院士的大人物——“李冀生”。他认为,如果爷爷没有被害,自己就是“副院长”的孙子,会拥有“显赫的身世、幸福的家庭、宽裕而自由的生活”;自己的奶奶不会因为守活寡而变得暴戾乖张;自己的爸爸不会因为无人管教而堕入牢狱;自己的妈妈也不会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抛弃儿子与“蜜饯叔叔”私奔。但是,在程恭与李佳栖的对话中,读者却发现了与程恭这个叙述者的观点截然相反的事实。那就是,改变程恭这个孩子命运的人,其实并不是他那个曾经坐在副院长的位子上还不懂医术,阻止好医生上手术台的爷爷—— “抗日英雄”程守义;也不是把程守义害成植物人的大人物——“院士”李冀生;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徐绘云、姑姑、大斌、陈莎莎、汪露寒,等等。
徐绘云对程恭的意义在于“希望”。作为著名教授李冀生的妻子,徐绘云每天的工作只是默默无闻地做饭、照顾孩子们,但她最有可能得知“植物人案件的详细内情”。表面上,她对程恭不理不睬,还警告孙女李佳栖不要跟程恭来往,实际上,作为一个教徒,她对丈夫的做法深感良心不安,她把这件事“忏悔”给牧师听,并且通过牧师,在每年程恭过生日的时候,满足他一个愿望,作为补偿。徐绘云的善举对刚刚遭受失母之痛的程恭意义重大。第一次得到礼物的程恭有这样的感受,“我骑着自行车从教堂出来,凉爽的风吹着脸颊,双脚越蹬越快,脚踏板好像就要从脚下飞出去了,那种快活的感觉我一直都记得。陌生人的善意使我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2]74
“姑姑”对程恭的重要意义在于“守护”。姑姑瘦小不美,工作是在药房里抓药,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她始终陪伴着程恭,为他洗衣做饭,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一辈子没有出嫁。她的付出,使得程恭避免逃学、避免变成街上的“混混”,也使他没有因为仇恨就对李冀生做出暴力行为,走上如他父亲一般锒铛入狱的路。
程恭的妈妈虽然抛弃了他,却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给了他“信心”。她给孩子听世界名曲、讲故事,希望把孩子培养成杰出的人物。她说“小恭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这句话让程恭的内心总是保存着向上的动力。还有汪露寒,她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仍然选择了“善”的信仰,去医院照顾植物人,替自己的父亲赎罪,即便被植物人的家属打骂也不曾放弃。她让程恭懂得了“救赎”,甚至对她心生感激。这些默默无闻的“次要人物”在小说文本中时隐时现,似乎从不被“重要人物”重视。但是,读者却能够从他们的言行中,感觉到温暖的力量一点点融化程恭这个“重要人物”内心的坚冰,使他从爷爷被害所造成的郁愤不平的心境中渐渐解脱。
“大斌”对于程恭的意义在于“知遇”。作为从小长到大的朋友,他在自己的家族企业中,给了程恭事业起步的机会。他让程恭有机会成为企业的管理者,赚到足以养家糊口的钱,让程恭有机会在实践中摸索出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真正树立了自信。“陈莎莎”对于程恭的意义在于“宽容”,即便有些“心智不明”,陈莎莎也知道程恭并不爱自己,甚至经历哮喘发病,程恭“见死不救”之后,陈莎莎也原谅了程恭,依然给他关怀,对他不离不弃。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程恭终于能够坦诚感激之情:“是她使我没有彻底崩坏,完全毁灭。”[2]408读到这里,读者就会明白,作者写下这个祝福,既是给陈莎莎的,也是给所有默默无闻奉献过善意和爱心的“次要人物”。在小说文本中,叙述者与读者这种认识上的差異,恰好构成了叙事向前演进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使得叙述者的“讲述”行为和读者的“阅读”行为得以持续地发生。
(二)读者与人物:价值观的差异
好的叙事可能会涉及伦理问题,它会引领读者去探讨伦理问题。在《茧》这个小说中,伦理问题的探讨用了两种形式,一种是虚写,一种是实写,二者前后相继,互相映衬。这就是读者与人物价值观的差异,这也是小说话语层面的叙事动力之一。
小说《茧》的作者张悦然,“虚写”程守义和李冀生的价值观差异。此处的“虚写”,指的是作者并不直接描摹这两个人物的处境、心理、行动和语言,而是通过小说文本中其他人物的言行回顾这两个人物。程守义,出身行伍,是抗日时期的“战斗英雄”,但是在和平年代,他不懂医术,为了自己的面子滥用“副院长”的权力,阻止好医生上手术台,造成病人的死亡。李冀生趁程守义昏迷之机,把钢钉插到程守义的脑中,把程守义变成植物人,扫除障碍以后,他救死扶伤,钻研医术,培养后辈,成为德高望重的“院士”。小说中多次写到李冀生身上的“凛然正气”,显然,李冀生认为自己做得对。
但是读者却通过整个小说的叙事,看到了李冀生本人不曾完全了解的这个事件的另外一面。程守义成为植物人,一石激起千层浪:程守义的妻子空守几十年活寡,程守义的儿子锒铛入狱,程守义的女儿终生未嫁,程守义的孙子程恭险些误入歧途。李冀生的同谋者汪大夫畏罪自杀;李冀生的大儿子与受害者的女儿虐恋,最后因车祸丧生;李冀生的孙女李佳栖因为丧父流离失所;李冀生的另一个孙女李沛萱被受害者的孙子毁容……读者不会像李冀生那样笃定、冷静。读者会发问:李冀生做的对吗?一个生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另一个生命的价值吗?一个生命有权利用自己的律法去判处另一个生命死刑吗?李冀生那样做是一念之差吗?他会后悔吗?
小说叙事的任务不是给出伦理问题的答案,而是在文本的虚构中把人的处境描摹得细腻逼真。它告诉读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面对这样的抉择。细腻逼真的艺术效果是“虚写”达不到的。所以《茧》的作者张悦然在文本后半部分,“实写”了程恭对陈莎莎“见死不救”的一幕:
“陈莎莎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正张大嘴巴拼命呼吸。脸已经变成酱紫色,双手扣住脖子,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我蹲下,又站起来,四周看了看,然后想起客厅木头箱子上有药瓶,可能是治哮喘的。但是我没有动,还呆在门口。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举起手臂,想要够到我。渐渐地,她在视线里模糊起来。我心里变得很静,像是被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俯瞰着人间,她只是那么小小的一团,在地上蠕动。她的生命如此渺小,如此没有意义,就像一只虫,手指一碾就被抹掉了,不会留下痕迹。既然他带来麻烦,就应该被抹掉。我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力,让她消失的权力。你爷爷的脸浮现出来。……一些生命高于另外一些生命,一些人掌握另外一些人的命运,这难道不就是世界的逻辑吗?”[2]400
这一段描写把程恭与陈莎莎,李冀生与程守义联系起来,在文本中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读者可以通过这样的叙事虚构,感受到人物在生死抉择瞬间的种种“闪念”,从而对人性和伦理产生更深切的体悟。如果叙事是一条河流,那么读者与叙述者价值观的差异、读者与人物认识上的差异,都可以看作河水里的漩涡,它们的存在使叙事充满了危险又迷人的气息。
三、阅读层面的叙事动力
(一)悬念
悬念是读者对尚待讲述的内容的关注。悬念是作者设下的,是读者阅读过程中体验到的。《茧》这个文本中,有些悬念长长的,穿越整个小说的始终,有些悬念短短的,只潜伏在某些章节、某段叙述中;有些悬念单纯如一,有些悬念不停变奏。下面节选小说第一章第一节,来自“李佳栖”声音的几段叙述,并列举读者体验到的部分悬念。
第一段:“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了,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哦,还去过一次药店,因为总是失眠,我一直待在这幢大房子里,守着这个将死的人。直到今天早上,他陷入了昏迷,怎么也叫不醒。”[2]1
悬念一:将死的人是谁?看护的人是谁?两个人什么关系?为什么昏迷了还不送医院?
第二段:“有个男人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隔着阴鸷的光线、湿漉漉的水汽和十几年的时光,我认得出那是你。程恭,我轻轻叫了一声。你慢慢睁开眼睛,好像一直在等我,等的乏了,就睡了过去。……我站在那里,不敢迈出楼洞。生怕一旦汇入外面的天光,我们就会再度失散。”[2]6
悬念二:程恭与李佳栖之间为什么有这样深的感情呢?两个人为什么会失散十几年?
第三段:“下午见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横亘在我们之间,那个秘密,也许你早就知道了吧。它可能已经在漫长的时光里消融,渗入生命的肌理。”[2]8
悬念三:秘密是什么?怎么会渗入生命的肌理?为什么无法视而不见?程恭和李佳栖会谈这个秘密吗?
我们看到,在《茧》这个小说文本的开端部分,作家张悦然设下了三组悬念。其中,“悬念三”属于贯穿整个小说始终的一类悬念,小说的全部叙事文本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悬念二”覆盖了小说叙事内容的前三章;“悬念一”则在小说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回答完毕。需要注意的是,悬念并不只在小说的开头出现。小说叙事每向前发展一步,作者都会引入新的悬念。比如,为了回答“悬念二”关于“程恭和李佳栖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感情?他们为什么会失散十几年?” 小说的前三章内容,讲述了李佳栖和程恭在南院相遇之前,各自不幸的幼年经历,还回顾了他们在南院相遇之后,一起度过的快乐光阴。这样的设计无疑满足了读者对“悬念二”的追索,同时,这也为“悬念三”的展开设下厚重的铺垫。紧随其后,作者把悬念三里的“秘密”摊开,抛出了它的变奏——“李冀生到底是不是害程守义的凶手?李冀生为什么要把程守义变成植物人?”这两个悬念成为推动小说最后两章的叙事动力。
(二)好奇
好奇是读者对已经讲述的内容中的空白部分的关注。比如,小说《茧》的第二章,以程恭的声音叙述的部分有这样一段:
“教堂是个聚宝盆吗,怎么什么都有,转眼就能变出一双我这么大小孩穿的凉鞋,也许牧师会变魔术,不是一直在讲那个叫上帝的神吗,可能神传授给他一点法力。回到家,我跟姑姑讲了这件事。姑姑说一定是上次我去的时候,牧师就看到我的凉鞋破了。可是我记得那次牧师根本没有看到我。”[2]73
这一段叙事讲述了年幼的程恭从教堂的牧师那里得到新凉鞋之后的疑惑心理,还有他姑姑对牧师送鞋动机的猜测。牧师到底为什么给程恭礼物?为什么要程恭每个星期都去教堂?小说作者只交代了姑姑的猜测,这个真实的情况并没有在这一章说明,读者显然不会对此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一定会感到好奇。
小说《茧》第三章的结尾部分,李佳栖向谢天成询问关于家族世仇的“秘密”。“汪露寒有没有说我爷爷和他爸爸为什么要害程守义。他说:程守义是领导,平时总压着他们,他们都挺恨他。但是按照汪露寒的说法,她爸爸很宽厚,应该不会这样去报复一个人,所以应该主要是李冀生的意思。”在这里,谢天成的转述部分地回答了程守义被害的原因。但是,汪露寒的父亲悬梁以后,人证彻底消失,没人知道这个案件的主谋到底是不是李冀生了,人们只能根据“脑中插入钢钉却不致死”的手术难度,猜测主谋是医术高明的李冀生,李冀生会害程守义吗?李冀生为什么要害程守义?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李佳栖通过父亲与汪露寒得知一点内情;程恭通过牧师得知一些内情;程恭的姑姑因为观察到李叔原与汪露寒隐秘的恋情而猜测到一点内情;《走近院士李冀生》的电视纪录片,通过追索李冀生的人生历程,展现李冀生的性格特征,也提供了一点内情。但是,所有痕迹,都只是真实的历史残存的碎片,似乎永远无法拼凑出故事完整的原貌。作者留出的这个空白,就是要读者怀着好奇,向小说文本的更深处漫溯,向人性和历史的更深处追问。
(三)惊讶
惊讶是读者以意外的方式对空白加以填充时的体验。在小说《茧》这个文本中,读者的“惊讶”既可以制造出“轻喜剧”的效果,也可以制造“荒诞剧”的效果,还可以制造“恐怖片”的效果。
1.轻喜剧效果
小说中“大斌”这个人物,常常令读者感到“惊讶”,自帶轻喜剧效果。他暗恋李沛萱多年,去美国追求未果,回国后念念不忘。可是,他竟然很快就和电视台的美女主播结婚,只因为对方“长得有一点像李沛萱”。婚后女主播出轨于电视台台长,大斌伤心欲绝,发誓要离婚,可是,他行动上却竭力挽救这桩婚姻,不惜放下尊严对女主播重新展开追求。大斌言行滑稽,却透露出他内心的憨厚,总能令读者不禁莞尔。
2.荒诞剧效果
汪露寒自愿当义工照顾植物人,被程恭的姑姑和奶奶阻止。之后,医院里发生一件怪事——植物人程守义竟然从病房凭空消失,不知去向。醒了?没醒?死了?没死?文本中都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病房的护士、守门的门卫,竟然都表示对此一概不知,口径极其统一。警察出动全城搜寻,也一样没有着落。“植物人失踪”,这事多么荒诞!这足以让读者在惊讶之余,深深体味在俗世中行救赎之术的艰难,透露出小说主题中深刻的反讽意蕴。
3.恐怖片效果
在《茧》这个小说文本中,程恭这个人物一直努力与自己心中的“戾气”作斗争。他心中的“戾气”,是因为遗传了爷爷和爸爸的暴力基因,也是因为妈妈的遗弃,奶奶的乖僻,姑姑的懦弱和李佳栖的离去而造成了心灵的损伤。这股“戾气”在文本中横行了两次,每次都营造出人性黑暗的恐怖效果。
其中一次是在程恭成年以后。程恭深知自己內心深处并不爱陈莎莎,却深深受制于肉体欲望,因此困顿空虚。所以,当陈莎莎哮喘病发作,程恭选择袖手旁观,任凭陈莎莎濒死挣扎,却见死不救。另外一次是在程恭儿时。李佳栖将要转学离开的傍晚,程恭本想去赴约与佳栖告别,却深感自己既无法接受佳栖离开,也无力将她留在身边,因此在半路“虐杀”一只受伤的流浪狗泄愤。
“我把双手插进排水沟旁边的积雪里,然后把他们推进沟里。雪哗啦哗啦地砸在狗背上,狗慌乱地摇晃着身体。我跨到排水沟的另一边,把边沿的雪全都推下去,雪没到了狗的脖子,只剩下竭力仰着的脸。它在看着我,它让我知道它在看着我,喉咙深处断断续续地发出几丝叫声,已经被寒冷勒得很细的声音。我盯着那张漆黑的面具,想象着在它后面的充满恐惧的眼睛,多么微不足道的生命啊。……”[2]282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会“惊讶”于程恭对“狗”和对“陈莎莎”的残忍,甚至对残忍的画面感到恐惧。与此同时,读者也会发现:此处程恭的残忍与他对李佳栖的深情,似乎矛盾又统一。这种惊讶的体验,能够令读者为小说文本的叙事过程所吸引,并且深深沉浸在故事营造的种种氛围之中。如果叙事是一条河流,那么读者有关于悬念、好奇和惊讶的阅读体验,就是笼罩在河上的烟霭,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呈现出变幻无定的风姿。
四、结语
叙事学理论认为,“叙事对事实及经验加以把握的方式是其他解释和分析模式,如统计、描述、概括,以及通过抽象概念进行的推理所无法做到的”。[1]285小说《茧》对社会现实的把握,也因其叙事艺术的“审美”品格,而具有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学科无法替代的价值。本文谨从小说的故事层面、话语层面和读者阅读层面分析这个作品文本的叙事动力,希望抽丝剥茧地呈现其审美品格,帮助读者领略当代小说叙事艺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M].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张悦然.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张爽.《老残游记》与五四小说“心态化”叙事模式的比较略述[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81-86.
[4]冀艳.真纯而细腻的体验 忧伤而不绝望的抒写——迟子建小说研究梳[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78-84.
[5]付冬生.乡土认同与身份追寻的双重困顿——沈从文小说《八骏图》中“大海”意象分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87-92.
The Narrative Power and Aesthetic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Novel Cocoon
GAO Honga,SHI Fengb
(a.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b. Beij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close reading of the novel Cocoon by ZHANG Yue-ran, a contemporary writer,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narrative power of the novel from three aspects: story level, discourse level and reading level to reveal the aesthetic character of the novel,taking Narrat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Keywords:contemporary novels; narratology; narrative power; aesthetic charac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