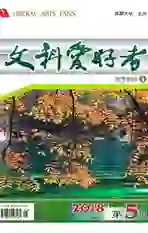从沈从文湘西小说的“酒神”精神看中西文化之共性
2018-09-04吕学彬
吕学彬
【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尼采生命力充盈的“酒神精神”和沈从文小说对湘西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对待苦难现实的浪漫精神,探究中西方文化的共性问题,带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天然互通性。
【关键词】中西文化 ;酒神精神;沈从文;共性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8)05-0020-02
中西方文化思想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沿着各自生存空间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心灵写照,它们是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生活形态的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但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上看,中西文化的共性问题带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天然互通性。
一、南京师范大学的张永教授曾撰文《“酒神”:沈从文的民俗审美情绪》(《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证了湘西民间“酒神精神”的形成
湘西地域空间的偏隅造成文化独立,汉民族对湘西苗民的征服激励了苗人的野蛮天性,以及神学观念尚未解体,巫风炽盛,使得湘西酒神精神异常突出,表现出一种对待情爱狂热与浪漫,凸显酒神原始野性的尚武的“游侠者精神”。他认为酒神精神代表了沈从文在精神领域所建立的审美理念,包含了自然健康的生命力象征和探索,以及构建理想生命形态的支点和介质。
张永教授所说的酒神精神,是尼采在1871年发表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作为阐释悲剧艺术而提出来的。在尼采看来,祭典仪式上的狂欢烂醉与放纵情欲,都是为了解除个体束缚、复归自然,与世界本体融合,从而解脱痛苦。尼采认为,“醉”是一切审美行为的前提,是最基础的审美情绪,“醉”的本质是“力的过剩”,“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是“高度的力感”。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通过它,人可以超越个体化原则,达到世界的生命状态,理性隐退,感性、欲望和本能获得彻底解放自由的发挥,从原始的生命力充盈之中获得无限的幸福和快乐。
同时尼采又认为现实是痛苦的,它的外表是迷人的,人对现实应该采取艺术审美的态度,逃离痛苦的现实。这就要借助于类似祭典仪式上狂欢的“酒神冲动”,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象征着生命的痛苦与欢乐。但它的本质充盈着生命的力感,通过放浪形骸的手足舞蹈,演变成为对生活的一种放纵情态,一种对世界的距离,一种对人生的放达精神。在艺术上,对由外象而求解脱的热烈渴望需要由酒神——情欲的放纵状态来实现,就要求艺术家通过创作“给予”世人解脱的“酒神冲动”,即酒神精神。
笔者认为,沈从文以湘西地域为题材的小说在这方面的特色更为突出。通过一种内在生命体验形式:“沉醉”的酒神精神,呼唤国民“野性”与“人性”的回归,用野性的气息冲破这“死水”一般的生命意识。苏雪林女士在三十年代对沈从文小说指出:“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吹鼓,所以有许多读者不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个别民族争生存权利。”沈从文自己也说,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他在寻找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以野蛮和优雅并存的方式呼唤生命真谛,在黑暗腐败与文明堕落的现实,生命应该充满强而有力的生命力,“这探究爱与死的人固执地爱着世界,顶礼膜拜那宗教式的理想人生,同时又企图用爱与死的各种形式装饰苦难。面对旧中国的苦难,他固执地借手中的笔,将生命的原始强力、原始情欲以及原始诗意涂抹糜烂疲软的国民,极具古希腊神话里的酒神精神”。沈从文通过他构建的“神话小庙”给历经生灵涂炭的国人以生的美好,生的美丽,唤起对生活的期望,以野蛮武性的力量奋力抗争苦难的现实,“把这种苦难视为一个生命的过程,以此来给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注入新的野性思维之血液,与‘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的生命意识相抗衡,恐怕正是沈从文乡土小说最大的潜在功利性表现吧”。
二、纵观沈从文以湘西地域为题材的小说,无论是其早期的尚武题材的作品,还是成熟期的湘西系列,我们都不难发现,在看似平静的笔触下,饱含着作家对底层人民纯真朴实的爱,对不幸和苦难生活的揭露,他通过充满悲剧的“呐喊”,关注苦难的现实
沈从文对民族劣性的疲弱也是耳闻目睹的,他从北京逃到青岛,战乱不仅给国人带来灾难,也给他带来了心灵的创伤,甚至他在有的作品里面描写了民族抗争的情结,赶明儿有人会说:“老同志不瘪,争一口气,不让自己离开窄窄的沟儿向宽处跑。他死了,他硬朗,他值价”。这是沈从文内心发出的呐喊,是借一个老兵的口警醒蒙昧的沉睡者,莫再垂怜大风雨下疲弱的生命,去同敌人拼出自己的血吧!那样才能守住自己的“土”,守住僯弱的生命个体。沈从文说:“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青年人的感觉。”我相信,没有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会无动于衷,特别是一个经历了从军生涯而又执着的从中走出的沈从文,他的笔记录的不会仅仅是那一幅幅野性屠杀的图景,而我们要从中解构出他对那些只顾苟延残喘的国人赤裸裸的剖析。在《如蕤》集《黄昏》,黄昏的云彩为日光烘托出炫目美丽的色彩,镶了金边、白边、玛瑙边、淡紫边,谁能知道在这朦胧的余光里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以监狱为生活依托的穷人,做着冷漠的看客,被“打猎一样”捕来的无知的庄稼人胡乱地问供,迷迷糊糊被砍了脑袋,令人心冷的是,那些围观的“顽童与无事可忙的人物”,同样继续着鲁迅先生无知与麻木的“看”与“被看”的景观。如果说沈从文的心对无知愚昧的国民是冷漠的,那么鲁迅先生的心也是麻痹无情的么?
汪增祺说沈从文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他并没有想把时间拉回去,回到封建宗法社会,归真返朴,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希望能在一种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品德,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發展”。沈从文自己也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与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长庚》)。我们只有从沈从文在乡野与从军的坎坷经历下,于极端困苦的境遇中,这些带有作者“迷醉状态”下写作的理想中的美好世界,体悟作者“酒神精神”悲剧后面隐伏着的,对现实生命意识的愤慨,才能真正读懂沈从文对另一种生命意识弘扬所存在的真正意义。
在当今社会里,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中西方文化思想也进入了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全新时代。尽管东西方之间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国情的不同,确实会在各自的文化上引起差异,但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国情的不同,并不是人性和人心的不同。所以从根本上说,这些差异是属于形式上的、非本质的差异;是对共同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