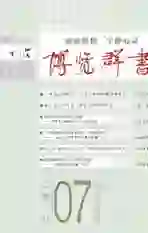工人的癌症与小说《慈悲》
2018-08-29成朱轶周春英
成朱轶 周春英
《慈悲》是路内的新作,于201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得第二届书店文学奖年度书籍,也被评为“2016年度影响力图书”文学类第二名。路内是最好的70后小说家之一,著有“追随三部曲”以及《花街往事》等作品。
《慈悲》以长江中下游的苯酚厂作为小说背景,通过反映生产有毒物质的苯酚厂工人的恶劣生存状况,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工人下岗这样的巨大变革,探讨中国工人的出路和命运。这部小说涉及一个世界性的主题:自然环保。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将一幅上世纪下半叶蓝领工人的生活现状图徐徐展开,从小说开篇,苯酚、肝癌、坐牢、死亡等字眼就不断地出现,属于那个时代的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人如何挣脱苦难的现实,如何唤醒人对自然的“慈悲”之心,《慈悲》给出了答案。
时代变革,命运沉浮
如果说“十七年”的工业小说渲染的是工人阶级的崇高和伟大,那么,《慈悲》挣脱了固化意识形态的捆绑,贴近最现实的小人物,还原最残酷的现实生活,展现最真实的工人故事。上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处于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慈悲》叙述了这半个世纪的苯酚厂变迁以及工人们的命运沉浮。这与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荡、改革开放、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经济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但其中不变的是“苯酚”,“苯酚”贯穿整部小说,串联了各类人物,引導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工厂待遇低下的起步阶段,苯酚的毒带来了工厂的补助。苯酚车间是有毒车间,工人可以喝解毒的牛奶,但在工人们的一致建议下又改为了营养费。这便吸引了其他车间的段兴旺、广口瓶、长颈鹿甚至是一些事业单位人员自愿到苯酚车间工作。工厂发放补助原先是一件造福工人的政策,但这样的补助已经变成了死亡的陷阱。补助制度的背后是工人更加残酷的选择——要钱还是要命?工厂是在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还是让人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呢?苯酚的毒意味着钱,钱就是命,有了钱就可以活着。这样的逻辑已经深深扎根在工人的头脑中,他们早已陷入了苯酚的恶性循环,不可自拔。
在工人们为了生活而奔忙时,苯酚的毒正在悄无声息地腐蚀工人的生命,小说开篇的这段话直击工人的生命现状:
苯酚车间的老工人,退休两三年就会生肝癌,很快就死了。老工人为什么在厂里的时候不生癌,偏偏要等到退休生癌?师傅就对水生说,苯有毒,但是如果天天和苯在一起,身体适应了就没事,等到退休了,没有苯了,就会生癌了。
这读来可笑,却又饱含心酸。工人们劳作在充满苯酚气味的车间中,苯酚竟成为了生命的养分和能量,一但离开就如鱼离开了水,走向了死亡。师傅是否知道苯酚的危害,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师傅的早逝已经印证了他的论断是错误的。水生也曾提到:“一个苯酚车间里,三分之一的人退休了立刻生癌,这个比例几十年都没有降下来过。他们都过得很痛苦。”生命的消逝应该得到其他人的反思,但死亡却使苯酚厂的工人们麻木。因为在苯酚厂里,死亡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到了一定程度就再也无法触及人心的柔软。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苯酚的毒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之后,水生和邓思贤决定单干,他们先在须塘镇建造了六个小苯酚厂,又到浙江建造化工厂,他们赚到了生平从未想到过的巨额现金。但是像林福先这样的年轻工人又将重蹈覆辙,做一个痛苦的苯酚车间工人。苯酚一直在被继承下去,让更多年轻的生命为它的异香殉葬。水生也囿于苯酚的旋涡,失去了师傅和妻子,还戕害了一批年轻人的生命。
当人心归于平静,当水生再回首他的一生,工人的信念已经被苯酚扼杀。水生在年轻时曾认为工厂就是自己的家,但工厂却带走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被迫逃离,在买房时他想,“最重要的是,这里离化工厂很远,再也闻不到各种让人发昏的气味了。”但这只是逃避,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直到水生做完了最后一单生意,他对年轻人林福先说,“我也不会再去做设计了。”他已经丧失了对自身工作的热情,是现实的残酷扑灭了他心中的烈焰。
在小说结尾,弟弟云生认为世间本来就没有真庙假庙,只要人幸福就是真庙。玉生曾说她闻到父亲和水生身上的苯酚香味就心安,工人们一直坚信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苯酚才罹患了癌症。他们又何尝不是活在想象的幸福中呢?他们就这样在谎言中离开这个世界。水生作为幸存者,到底也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是什么导致了悲惨的生活,他能做的只有逃避。只要苯酚工厂还存在,死亡就还在继续,我们需要打破苯酚的谎言,以及头脑中虚妄的幸福。在物质丰富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去改变现状,而不是像水生一样一味地逃避现实。
缅怀自然,慈悲为怀
中国文学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但是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怀一直存在。在不同的时代,文学对生态反映的模式是不同的。上溯到神话传说对自然的敬畏,再到老庄的“天人合一”,到了现代,一些作家虽身处繁华的城市,却依旧着力回归自然,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废名的乡土田园。直至现代,外界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也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态环境正在被边缘化,现代文明正快速地吞噬着乡村自然,例如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对自然的执着,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亲手将世外桃源消解。《慈悲》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部生态小说,但路内将最为现实的环境展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自然的一丝残存,只有苯酚、工人和癌症。
那么,路内为何要从苯酚厂这样的背景入手写作呢?苯酚厂对于这篇小说,对于路内又有何深意呢?
小说以苯酚厂为背景,以工人为主体,再以时代变迁为线索,构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不断冲击。路内常被人形容为“工人作家”,事实上,路内并没有真正在工厂工作过。但是《慈悲》也不是路内凭空虚构的一部小说。路内曾深受父亲的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故事来自他父亲的真实经历。《慈悲》相当于老一辈工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录的是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时代中工人们的凄惨生活。
路内在写作《慈悲》时有意识地改变了以往的创作风格。从2007年的《少年巴比伦》到2016年的《慈悲》,近十年间,路内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慈悲》与之前的五部相比,无论构思风格还是写法都显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路内在谈到《慈悲》的时候说,“我想提供一个更坚实一点的文本出来,这个文本放弃了我以前常用的荒诞、变形的手法,我想使用一次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路内所呈现的现实背景是复杂的,但其中必定包括生态环境的现实。从宏观角度来看,弥漫着苯酚香气的城市,被化工厂污染的石杨镇是工业战胜生态的结果。从微观角度看,罹患癌症去世的师傅和段兴旺,肝硬化的玉生等人是被工业摧残的典型。如果地球无法使人类生存,生活使得人类痛苦,人类的未来将变得模糊。路内不是将美好的东西破坏给人看,而是将最肮脏的一面暴露在读者眼前。
《慈悲》创作风格的改变也来源于路内本人的成熟。《慈悲》出版,路内已过了不惑之年,他开始了以更透彻、更严肃、更理性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人生阅历的丰富使得他脱离了曾经的青春气息与幽默笔法,而是以沉重而残酷的视角来揭示生态的破坏和工人的困窘。
作者选择苯酚厂作为小说大背景,也与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近年,国家对环保问题非常重视,作家的创作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路内创作《慈悲》的初衷也许并非是对生态与自然的关怀,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苯酚厂是一个聚焦点,其中流露出的肮脏、悲惨和死亡是无法与环境破坏相分离的。虽然小说并未直白地指出“环保”主题,但整篇小说都以生态环境为牵引。工人以苯酚为生,又因苯酚而死,沉浸于苯酚气味中,又试着逃离苯酚,由此衍生出水生一家的跌宕起伏,根生的悲惨一生等等。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的力量在于能将历史和现实永远地用文字封存,并且经过一些虚构来伪装,像事实却又不是事实。《慈悲》中的故事是真实,也是虚构,现实主义的笔法将读者带入了一种“幻真的体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远去,但历史遗留的问题还亟待解决,如何去达到环保意识的强势阶段,需要整个国家的富强,更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我们无法目睹真实的历史,却可以通过阅读加工过的真实,《慈悲》旨在唤醒我们对生态的关怀。
苯酚时代,何去何从
从整部小说的发展来看,作者从“前进化工厂”写到了浙江的国际化工厂,苯酚厂发生了空间、时间和规模上的改变,苯酚是一个特殊的工业品,一个时代的标志,有其特殊的象征意味。我们可以将其层层剖析开来。
小说中最为直观的就是苯酚带来的死亡,苯酚象征着生命的流逝与腐蚀。作为一种化工产品,苯酚可以创造财富,同时也会释放有毒的香气。苯酚的作用是尸体防腐剂,有多少苯酚厂的工人们在苯酚中工作,在苯酚中生病,在苯酚中死亡。即使不在苯酚厂工作,生活在这样一个苯酚气味弥漫的城市,疾病与死亡也终将来临。就像玉生,年轻时就饱受肝炎折磨,50岁就去世了,在殡仪馆里,“房间里有一股苯酚的气味,芳香异常,水生和复生都哭了。”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结局,仿佛苯酚到人生命的尽头还是纠缠不休。还有那死因不明的汪兴妹,从污水池中打捞上来时她身上竟是异样的蓝色。这不是一种美好的色彩,而是毁灭的、变异的颜色。
小说不仅重复强调苯酚对人的摧残,还刻画了绿色的消逝和磨灭。石杨镇的变化就是最令人痛心的例子。水生第一次来到石杨,石杨的山清水秀已然消逝,“早年在镇口的那座瞭望塔不见了,变成了烟囱,只见黑烟滚滚,河水浑浊乌黑,泛着不正常的油光,空气中有一股臭鸡蛋的气味”。这都是一家小化工厂造成的,其中的农民工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直接上岗。人类对于财富的渴望足以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自然界的积淀在短短几年间就被化工厂的肮脏替代。
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导致了生命和自然的流逝?小说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人类自己,人类那颗永不满足的心。水生和邓思贤在须塘镇完成六个小厂的建造之后,水生认为“再要造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产能过剩,而且城里城外都是苯酚的气味”。陈水生和邓思贤帮老板成功试车之后被扫地出门。邓思贤闭目,想了想说:“后道工序上,还有排污处理没有设计,环保上通得过吗?”水生懂得适可而止,邓思贤懂得环保排污,这就是人的良知和理性,但他们却被扫地出门,他们的环保意识也被扫地出门了。对自然的关怀无法得到行动上的实践,两个技工的慈悲之心被区区几万块钱的现金打发了。被拜金主义冲昏头脑的老板更是为所欲为。当世界没有了反对的聲音,这个错误的声音更会在幻象中扩大,充斥整个空间。
《慈悲》并没有猛烈抨击人类破坏自然的野蛮行径,而是以客观的角度,呈现出上世纪下半叶苯酚厂工人的凄惨生活以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慈悲》关注的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未来和美好的明天,而且还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良知和尊严。如何让更多人前卫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直面现代性生态危机而发出自己的批判之声,从而达到人们一直在追求的诗意栖居,只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成朱轶,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