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序列音乐研究和教学的过程
2018-08-21郑英烈
郑英烈
一
勋伯格创作于1921~1923年间的第一部完整的十二音作品《钢琴组曲》(Op.25)的问世,标志着由勋氏创立的十二音体系和相应的十二音技法已经成熟。这是世界作曲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至今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有人称其为“古典十二音技法”。这个体系及其技法诞生之后,在欧洲历经磨难。勋伯格认为“每个音和每个人一样,都应该是平等的”。于是,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认为这是文化领域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个阵营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没落的音乐。事实上十二音音乐在两个阵营都遭到禁止。所以,十二音音乐自其诞生后的20年里,用该技法进行创作的作曲家并不多,只限于勋伯格的圈子 (后被称为“新维也纳乐派”)及少数追随者。1938年,被称为“记录电影之父”的荷兰摄影家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反映、宣传中国人民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由勋伯格的学生之一艾斯勒(前东德国歌《蓝旗歌》的作曲者)全部用十二音方法创作配乐,效果特好(如今网上仍能下载)。1945年二战结束后,西德的达姆斯塔特“新音乐国际夏季讲座”(类似音乐节)曾经成为传播交流十二音音乐的重要场所。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作曲家聚集在一起,演奏、介绍由于第二次大战而未能公演的作品,探讨这些作品的新的构思方法。这种音乐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后来却成为西方音乐的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活动,许多当时的先锋派作曲家如布列兹(法)、斯托克豪森(德)、路易吉·诺诺(意)等都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或领导者。先锋派作曲家除了音高序列之外,还尝试把节奏、音色、音量、发音法等要素用序列方法纳入其作品,叫“整体序列主义”(Integral serialism)或“多维序列写作”。“序列音乐”的称谓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毕竟序列音乐的基础是音高序列即十二音序列,后来十二音音乐便和多元素的序列音乐一起,统称为“序列音乐”。本文标题中的“序列音乐”就是指包括十二音音乐并以其为主体的广义的“序列音乐”。
二战结束前,国人中虽有少数“海归”作曲家,但他们从未引进过序列音乐。直至二战结束后,上海国立音专请来两位犹太裔德籍作曲家弗兰克尔和许洛士任教理论作曲组,当时还是学生的桑桐才开始接触无调性音乐和序列音乐的基本原理(老师并无在课堂讲授,主要靠自学)。1947年,还是学生的桑桐竟创作出《夜景》(小提琴与钢琴)、《在那遥远的地方》(钢琴)两首十分成熟的作品。前者是纯粹无调性的,后者是有调性的民歌主题与无调性伴奏的巧妙结合。这两首作品的横空出世,在中国是超前的,以致日本音乐界人士惊呼:“中国的作曲家搞现代音乐比我们早了三年”。此后的30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类作品了。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初,序列音乐在中国是被彻底划入禁区的。无人敢问津,也无条件接触,更别提研究和引入教学了。1958年,茅于润翻译出版了勋伯格的《和声的结构功能》一书,因第十二章(该书最后一章)出现“十二音”和“不协和音的解放”的词句,便被省去;及至2007年重新修订出版时才补上。电影导演叶向真请罗忠镕为她于1981年拍摄完成的影片《原野》写配乐,当叶得知罗写的音乐是用十二音技法时,竟不敢采用。直至80年代,陈铭志用罗忠镕《涉江采芙蓉》的序列写了八首钢琴小品,手稿放在钢琴上;一日来了一位朋友,无意中拿了手稿来视奏,大加赞赏。当陈告诉他是用十二音创作时,他竟一脸正经地说:“你还是不要采用这种方法”。由此可见,这个禁区虽然从改革开放开始,便悄悄地被打破了,但当人们谈及这个话题时,依然心有余悸。
二
“大跃进”结束后的1961年,湖北艺术学院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但只持续了两年时间。1963年春天,中央提出文学艺术的“三化”政策。“三化”者,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之简称也。随着政策之实施,在文艺界刮起了一场极“左”的风暴。就音乐而言,在反对“大、洋、古”的幌子下,钢琴、小提琴等外来的形式和工具,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惨遭砍杀。钢琴专业的学生改学琵琶、二胡,钢琴副科一律被取消,和声共同课(包括附中和声课)也被取消了。全校只保留作曲系的和声课。我是教和声共同课的,一夜之间便“下岗”了。被借调到武汉音乐家协会(湖北省音乐家协会的前身)搞《湖北民歌集成》编辑工作。1964年正式被调到图书馆资料室。十二年后的1976年,我被湖北艺术学院师范班(今武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的前身)借调担任教学工作。1977年末恢复招生,师范班招进了一班正规三年制的学生,我又继续担任该班的理论课教学两年。
1979年,“第一次全国音乐院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在我院召开。这是全国音乐院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学术交流的盛会。该次学术会议的发起人和总策划是时任副院长的谢功成教授。我院是东道主,必须为大会提供足够份量的论文。这是领导一再向我们提出的号召和期望。经过半年的努力,我撰写了论文《五声性变化结构和弦规律初探》和翻译了《现代对位及其和声》一书。时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长期的禁锢已初步被打破,全国理论作曲界(尤其是恢复招生制度后进校的一批优秀学子)正如饥似渴地寻求了解外界新鲜事物的途径,在这关键时刻,《现代对位及其和声》的推出,自然立刻受到同行广泛的关注。会议结束时,上海音乐出版社的代表王秦雁先生向我约稿,将该书列入下一年度的选题计划。
通过这次和声会议,谢功成老师已看出我的潜力,有意结束我被师范班“长期借用”的状态。但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把我调回作曲系,只好通过“曲线救国”(谢功成语)的方法,先将我调到“音乐研究所”(音乐学系的前身)。在研究所的几年里 (1980~1984),没有硬性的教学任务,可将全部或大部份时间投入课题研究。
首先要解决的是选题。根据我本人的志趣、条件和当时国内专业作曲界的迫切需要,我选择了“序列音乐”,兼顾与此课题有关的现代西方作曲技术理论。
从事此课题的研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1.“文革”前该领域属于禁区,如今要冲破这个禁区,除了自身的胆识之外,还必需取得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支持;2.那时学校尚无进口外国图书资料的专款,与该领域有关的文献资料,图书馆里是一片空白,我必须自找门路;3.何谓“序列音乐”?我尚一无所知,真正的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课题是我自选的,若搞不出成果来,岂不贻笑千秋?关于第一个问题,经征求有关领导和专家意见,得到了肯定和支持;第二个问题,我的一位在美国的挚友林肯兄表示会竭尽全力给我以帮助;第三个问题,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序列音乐的研究就这样开始了。
三
我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是马不停蹄地阅读、翻译有关资料,若是完整的文章,便及时寄《音乐译文》发表,让同行先睹为快。当时该杂志的主编黎章珉先生对我的翻译能力已有充分的信任,甚至到了事先约稿,限定时间,收稿后一字不改地发表的地步。这给我工作的进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另方面,只要是中国作曲家用十二音技法写的作品,有一定创造性的,我必及时加以总结,写出文章发表,起到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
1981年5、6月间,我将研究的初步成果给作曲系本科毕业班和第一届研究生开了几次讲座,简要地介绍序列音乐的基本原理和写作要领。结果同学们很感兴趣,纷纷要求把讲稿印发出来。下半年,我将几次讲稿的内容进行整理补充,写成了1982年的油印本《序列音乐讲座》。至此,总算有了一本初步的教材。1983年,我用这本教材给在校的另一届研究生开了第二轮讲座,授课次数略有增加。经过第二轮讲座,我已不满足这个版本了,于是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补充,于1985年9月推出修订稿《序列音乐基础》,由原先的9讲扩充到16章,并正式开设“序列音乐写作”课。
1983年我获晋升为副教授,不久被调回作曲系。回顾在研究所的三年多,对我是很有利的。没有教学任务,相当于“自学研究生”。一旦做出成果,调回作曲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研究序列音乐的脚跟尚未站稳,便发生了一件事。中央音乐学院的苏夏教授在《人民音乐》1982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创新和探索》的文章(以下简称“苏文”),大肆贬损序列音乐,说当初(西方)探索序列音乐的人是“标新立异”“仿效时髦”“拾人牙慧”……。甚至未加考证地引用《纽约时报》专栏音乐评论家哈罗德·匈伯格的一段文字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事实是,约莫搞了二十五年的系列主义音乐及其变种,竟没有一曲能在国际乐坛上流传下来。时至今日,作曲家几乎都同这一运动决裂了,他们捶胸顿足,自悔不迭,重又回到传统,弄起那种舒坦一些、更富个人情趣的音乐来了。”当时我一看便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误会。匈伯格是一位相当权威的音乐评论家,怎么可能轻易去否定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呢!他所说的“系列主义音乐”必定是指前文提到的“整体序列主义”音乐,而不是指十二音音乐。我立刻写了一篇《“序列音乐”的概念及其他——兼与苏夏同志商榷》的文章进行反驳和澄清(载《人民音乐》1983年第6期)。苏夏教授没有服气,又在《人民音乐》1983年第9期上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再谈创新和探索——兼与郑英烈同志商榷》。我又回敬了第二篇文章《再谈序列音乐的概念及其他——兼答苏夏同志》(见《人民音乐》1984年第4期)。双方文章的内容这里就不赘述了。这场笔战虽然只是两个回合四篇文章,却持续几乎长达一年半时间。大概年长的同行还有印象,年轻朋友却是不知道的。当时音乐界关心我国新音乐发展的人士(尤其是音乐学院学作曲的学生)无不感到困惑。澄清概念、扫清道路对于继续研究、传播序列音乐是很有必要的。
1986年,我终于正式开设第一期的“序列音乐写作”课,学员包括作曲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校内外进修的青年教师共十余人(见图1)。在中国大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序列音乐写作”纳入正式课程。因为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点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味,我将其戏称为“序列音乐讲习所”。开这门课和开其他新课不同。因为是冲破禁区的大胆尝试,开课前由时任副院长的童忠良提交学校党委讨论批准才付诸实施的。

图1 第一期学员包括广西艺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1986年)
经过两三轮课之后,终于出了一批十二音作品,有的还相当不错,如周晋民的钢琴弦乐五重奏《山鼓》(获湖北省室内乐创作一等奖),彭志敏的钢琴曲《风景系列》和杨衡展的钢琴曲《但曲》(均在《音乐创作》上发表)等。此后,又陆续开过几轮“序列音乐写作”课。在教学中,我常用勋伯格告诫学生的精神去要求每一位学员:不要单纯模仿,要走自己的路。每轮结业时,学生都必需交一首作品,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性,其中不乏较为成功的作品。最后,我把历年来学生的作品精选出一部份,录制成两盘磁带,作为作曲系与兄弟院校乃至外国同行交流之用。
1986年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教材,我又趁机作了一次补充修订,书名改为《序列音乐写作基础》,书中收入有十多位中国作曲家的数十个谱例,都是前一版本所没有的。我有意加重中国作品的份量,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更多“洋为中用”的直接经验,以及进一步突出该书的中国特色。
自从罗忠镕在《音乐创作》1980年第3期发表他的第一首十二音作品《涉江采芙蓉》之后,我们在频繁交流中成了好友。1986年春夏之交,经罗先生的推荐,我被邀到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讲学。讲学的题目是《基本集合对十二音和声的控制》。因为讲课内容新鲜有趣、学术性强,甚受欢迎。尤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求知若渴,整个大教室都爆满了。讲完后,系主任陈铭志兄告诉我:他们学校经常有外国专家来讲学,可每次他都要到处拉人来听,不然就会冷冷清清;这次请我来,他有点担心,结果听众如此踊跃,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我问他这是何故?经他解释,原因很简单:外国专家不了解中国,低估了中国学生的水平,给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讲课,就像讲故事。学生不能满足,自然不来了。
1987年和1988年,我又相继开了两轮课,每一轮都加进了新的内容,如“音级集合理论”“组合性序列的写作规律”“从调性到无调性的演化过程考证”等等。可惜书稿已发,来不及补充这些材料。这两轮课的授课时间已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都进行结业考试和作品观摩,以此两项作为学生的总成绩。
1989年,在全院“优秀教学成果”评奖中,我的“序列音乐写作课”获一等奖。那次评奖是相当严格和隆重的,参评者要面向评委和听众,在限定时间内介绍自己参评课程的情况,然后由评委投票,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因为总共只有六个得奖名额,不具备竞争实力的教师是不敢报名的。
文章发表前后,曾经历了一番折腾:那时我家没有电话,更谈不上传真了。与编辑部多次对话都是通过书信,编辑部把修改编辑过的原稿复印件寄给我,我认同后再寄过去,都是用的“特快专递”;最后还要签“合同”等等。文章发表后,得了96美元稿费,编辑部还赠送样书6本。当我将其中的一本送给年轻的系主任彭志敏时,他说:“郑老师,能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即便其他的都没有,也够了。”
1989年我在《黄钟》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叫《发展我国现代音乐必须有相应的教学措施——开设“序列音乐写作”课十年回顾》,对自1979年开始,开过的两轮讲座和六轮课进行一次总结。6月初我和当时的系主任彭志敏,音乐学系的汪申申,西安音乐学院来武汉音乐学院读研的陈士森一行四人,带着几十本该期的《黄钟》到上海音乐学院参加现代音乐年会,准备在会上交流有关开设现代音乐课的心得。可惜当开幕式结束后正开始发言时,会议便被一群学生“冲”了,主持人桑桐只好宣布休会。那天是6月4日。
1990年,我被邀到中央音乐学院和广西艺术学院讲学。在中央音乐学院讲了8个专题,在广西艺术学院讲了4个专题。除与序列音乐有关的内容外,还有现代和声的内容。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情况很是感人。场场爆满不说,作曲家石夫和段平泰教授每天早早便骑自行车来占座位,石夫坐在第一排正中,自始至终录音。可见那时候的作曲界人士对包括序列音乐在内的现代音乐信息是多么感兴趣。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李吉提教授事后对我说:“你这次来讲学盛况空前,是很风光的。”
之后我又继续开了两轮课。一共是两轮讲座和八轮课。(因为我还有别的教学任务,该课不是每年都开的,一般是每两年开一轮)前五轮课是一个学期,后三轮课因内容更充实了,改为一个学年。1996年退休后,便再没有开这门课了。
四
那本1990年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初版的《序列音乐写作基础》到了第4次印刷之后,责任编辑王秦雁先生建议我修改后再出“修订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2005年前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修订稿。除原来各章作必要的修改外,又补充增加了六章,更名为《序列音乐写作教程》。“好事多磨”,经过近两年的周折,终于赶在“北京现代音乐节勋伯格研讨会”(2007年5月)前夕出书。
2007年5月26日至6月3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北京现代音乐节”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该音乐节规模宏大,包括国内外音乐家演出的多场音乐会、勋伯格研讨会(包括勋伯格研究论文比赛)、管弦乐配器法学术研讨会(包括配器比赛)等。
大约半年前,组委会便来函聘我作为“勋伯格研讨会”的五位顾问之一(其他四位是:吴祖强、罗忠镕、杨儒怀、李吉提)。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也特地开了一个动员大会,院长彭志敏教授号召研究生们踊跃参加这次机会难得的论文比赛,结果我院提交参赛的论文有11篇。论文作者的心目中,认为我是研究勋伯格的专家,纷纷把各自的文章拿来请我提意见和修改,那阵子我真的是应接不暇,终于给每篇论文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经“勋伯格研讨会”论文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11篇参赛论文有6篇获奖(其中1篇为一等奖),几乎占全部获奖者的一半。
为了起带头作用,我自己也写了三篇文章,它们是《阿诺德·勋伯格年谱》《勋伯格是怎样走向“十二音”的》《〈摩西与亚伦〉的创作背景》。作曲系将提交给大会的14篇论文印成一本十分精美的《2007北京现代音乐节勋伯格研讨会论文集》,我的三篇文章照例被排在最前面。这三篇文章后来都在《黄钟》发表了。
“勋伯格研讨会”组委会嘱我准备一场一小时的讲座,我准备的题目是《勋伯格和他的歌剧〈摩西与亚伦〉》(见图2)。勋伯格采用十二音方法创作的这部歌剧是未完成的,三幕只完成两幕(33年去美国后没时间继续写完)。这部歌剧采用了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题材,隐喻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需要一位民族英雄来拯救他们。勋伯格自认为这部歌剧是他最满意的十二音作品,但在我国尚少有人知道。参加研讨会的,有一位研究勋伯格的美国女专家叫Severine Neff(见图3),她听完我的讲座大感意外(大概她没想到中国也有她的同行),散会时热情邀我共进午餐。

图2 在研讨会上作《勋伯格和他的〈摩西与亚伦〉》的学术讲座

图3 与Severine Neff合影
参加研讨会回汉后,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最高奖项)发出通知,此届增设“理论评论奖”(金奖二名,银奖八名,铜奖十六名)。学校科研处通知我:学校已评选出四本书,其中有我刚出版的《序列音乐写作教程》(见图4),要我提供6本样书让科研处送中国音乐家协会评审。评审结果,该书获二等奖(银奖)(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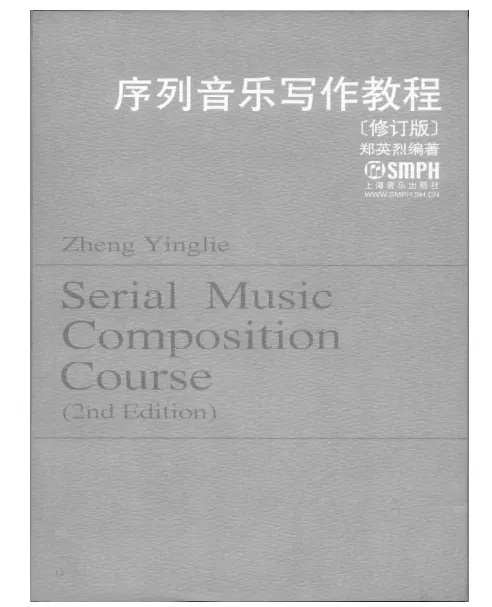
图4 《序列音乐写作教程》封面

图5 “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二等奖证书
2016年3月10日,作曲系副主任刘涓涓来电话,说有位美国杨伯翰大学的Stephen教授明天要来访问我,他对我研究的序列音乐课题很感兴趣,并索要我的《序列音乐写作教程》这本书。第二天我准时于上午九时到达系办公室,Stephen教授因堵车,来晚了一点。原来这位教授是美国杨伯翰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对中国音乐文化有浓厚兴趣,已先后来过中国12次,目前正在从事有关中国当代作曲家课题的研究(见图6、7)。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有关武汉音乐学院和我的信息的。座谈中他向我了解一些中国新音乐及这方面的研究现状。我问他能读懂中文吗?他说他有个台湾的学生可帮助他。

图6 作者与Stephen教授合影

图7 左起:刘涓涓、郑英烈、Stephen、赵曦
以上所述,就是我从事序列音乐研究和教学的全过程。迄今为止,《序列音乐写作教程》这本书已六次印刷,印数12000册,对专业性的理论书来说,这个印数算是不小了。能有1万2千人读这本书,已远超当初的预料。如今我已处于耄耋之年,精力早已耗尽,再不可能有新的建树了,特撰此文,为序列音乐的研究划上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