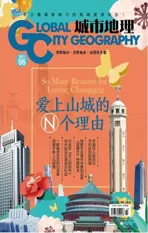海东“小故宫”瞿昙寺
2018-08-11李万华马英健
文+李万华 图+马英健

瞿昙寺始面朝瞿昙河,背靠罗汉山,建成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是典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初雪过后,瞿昙寺的殿堂和庭院显得格外静穆。

瞿昙寺始面朝瞿昙河,背靠罗汉山,建成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是典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初雪过后,瞿昙寺的殿堂和庭院显得格外静穆。

瞿昙寺始面朝瞿昙河,背靠罗汉山,建成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是典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初雪过后,瞿昙寺的殿堂和庭院显得格外静穆。
依山而立,面水而居,瞿昙寺像大多数佛教寺院那样,坐落在罗汉山前、瞿昙河畔,呈将军坐帐之吉形。罗汉山虽然植被稀疏,但四季风从浑圆端正的山顶拂过时,依旧会发出声响,瞿昙河水流淙淙,从未停止,沿岸旱柳青杨,即便是无雨,也潇潇不已。这些天籁与寺院梵音交织,如同山泉,时时荡涤这一方形胜之地,使之清凉安稳,人常康健。
瞿昙寺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原本只是一处小小的修行之地,据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秋瞿昙寺竣工之时,此处不过是3间不施斗拱的小殿。但在时间嬗递之中,瞿昙寺建筑规模和形制渐渐扩大,从简陋佛堂到洪武皇帝敕赐寺名,及至后来建廊筑城,最终成为一座具有碉楼堡垒的宏伟建筑群。瞿昙寺兴盛之时,整座寺院在土筑的堡城之中,寺院东南是居民区。这些居民区与寺院一起,成为一座城廓结合的城镇,寺前建有方形瓮城,朝廷曾调拨军兵进行防卫。现在,瓮城与堡垒都已不见,一些残存的颓败墙体,以及依稀可辨的基址,于草色之中,迎来朝阳,送走晚风。
汉式形制的藏传佛教寺院
虽然瞿昙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却有着典型的汉式建筑形制,融明代官式风格和甘青地方汉族建筑风格为一体。中轴线上的高大建筑,将瞿昙寺分成3个相连而又独立的院落,它们在肃穆、凝重的整体风格之中,又各有异。
瞿昙寺的前院和中院,更多显示出汉地佛寺“伽蓝七堂”的形制:强调中轴线,主要门、殿序列居中,钟鼓楼、配殿及其他建筑对称均衡分布,以烘云托月之势,突出主体建筑,围合成空间院落,以备佛事仪轨和寺院生活之需。瞿昙寺后院,则仿照北京紫禁城而建,它们对应奉天殿东文楼西武楼的典型配置。其中国殿以抄手斜廊与两侧廊庑相连这种组合方式,曾是唐宋以来宫殿、祠观和庙宇的定制,但这样的遗存现已很少,瞿昙寺是珍贵实例之一。
穿过山门殿,便可见得瞿昙寺的第一个院落。此处只有两座碑亭东西相对,静无声息,这使院落简明疏朗,草坪开阔匀整,青檀树枝叶繁茂,云杉四季常青,低矮灌木在春夏开出明丽花朵。碑亭中藏有皇帝御制钦赐的寺碑,显示着曾经的皇恩浩荡,但同时,也透露出明皇朝曾经的权力和威仪,寺碑成为一种特殊关系的象征。

瞿昙寺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一座汉式形制的藏传佛教寺院,各殿的形成,将整座寺庙分为3个相连而又独立的院落,让人一路行来,颇有“曲径通幽”之感。其后院因仿照北京紫禁城修建,故有“小故宫”之称。
金刚殿因为原来殿内塑有四大金刚而得名,现塑四大尊天王。四大天王体现了明清佛教雕塑的鲜明特点,在宣扬佛教教义的同时,又融入世俗人物特点,端坐之像,威猛英武。汉传佛教寺院中,入山门之后的第一重殿便是天王殿,殿两侧供奉四大天王。瞿昙寺的金刚殿实际以天王殿为蓝本,它依然体现着汉传佛寺的一些特点。金刚殿与同一中轴线上的瞿昙殿,以及后面的宝光殿共同组成瞿昙寺的第二院落。
“瞿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本姓,源自梵文“乔达摩”。公元1392年,洪武皇帝御赐寺额“瞿昙寺”,六百多年前的金字大匾,现依旧悬挂于瞿昙寺殿前廊内。瞿昙寺殿内供奉横三世佛,即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佛经中说,佛有三世,过去是燃灯佛的时代,那时没有战争杀伐,没有贫富悬殊,没有贵贱高低,那是一个祥云缭绕的时代,幸福如同花朵,四季常开;将来是弥勒佛的时代,那时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人们相处,亲如兄妹,那同样是无限美好的时代。唯有现在,这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须要历经若干千年,在这诸多千年之间,要不断遭受战争、瘟疫、洪水、地震等灾难,在这个时代,人们唯有行善利众、心怀悲悯才能减缓痛苦。瞿昙寺殿左右分立朵殿和4座佛塔,这是藏传佛寺的特点,它们共同组成立体曼陀罗,是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宇宙模型,是僧侣和藏民族最为虔诚的供养方式。
宝光殿的建成,晚于瞿昙寺殿二十余年,是明永乐扩建时最为重要的建筑,其建筑形式及构造特色都与瞿昙殿相仿,左右亦有朵殿。大殿内檐保存有大量明代原始彩画,这些彩画技法简练,图案设色以石青为主,墨线勾勒,色彩沉稳。特别是那些描绘在木板上的伎乐天,他们曼舞空中,手持乐器,彩带飞动,身姿翩跹。站于殿内,仰望之时,似乎能听见他们赞扬佛陀的美妙音乐,并且能感觉到他们那月亮和珍宝一样的心。

瞿昙寺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一座汉式形制的藏传佛教寺院,各殿的形成,将整座寺庙分为3个相连而又独立的院落,让人一路行来,颇有“曲径通幽”之感。其后院因仿照北京紫禁城修建,故有“小故宫”之称。
中院院落两侧,周围廊庑连接小鼓楼和小钟楼,三世殿和护法殿亦成为回廊一部分,宝光殿前又有影壁设置。这些建筑按照寺院形制密集一处,院落空间狭小,紧凑严密,殿内酥油灯闪烁摇曳,门户开处,金刚尊像显现庄严之相,肃穆凝重的寺院气氛由此越加浓郁。
隆国殿在高大的石刻须弥座上,是瞿昙寺规模最为宏大的建筑。须弥座雄厚素雅,刀法朴实。雄踞其上的隆国殿,重檐厚墙,门窗雕刻玲珑精巧,殿内铺满天花,遍绘彩画。因为内柱略显纤细,造像比例缩小,加之正脊上不再有金刚尊像,这使隆国殿更像一座宫殿,而非佛殿。殿内有遗留的玉石像座,石刻须弥山和象背云鼓,这些都是瞿昙寺的珍宝,工艺精美。殿内至今供奉一块刻有“皇帝万万岁”的檀香木牌匾,牌匾上有献匾之人的姓名和竖立日期。如若站在殿前巨石平台上眺望,青檀树掩映之中,瞿昙寺殿宇楼台层层呈现,让人顿生“多少楼台烟雨中”之感。
隆国殿殿前两侧,大钟楼和大鼓楼互相对峙,与大殿共同组成一殿二楼的布局,两楼下层与回廊连檐通脊,隆国殿又以抄手斜廊与两侧廊庑相属。回廊连贯绵延,殿宇巍峨壮丽,建筑史上,这种高大与适形之美,曾历经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兴盛之极。古文字中,所谓“复道行空”,“青台紫阁,浮道相通”,都是描述这种一气呵成互相呼应的建筑模式。
后院是瞿昙寺历代营建之中最为辉煌的部分,整座建筑完全采用当时北京故宫建筑的造型,所谓“小故宫”便由此而来。

瞿昙寺不仅建筑形制大气,其装饰配件也非常优雅,杂糅了官方和地方两种风格,无论是吻兽、瓦当、斗拱、樨头,还是砖雕、石雕、木雕,都尽显精致。

瞿昙寺不仅建筑形制大气,其装饰配件也非常优雅,杂糅了官方和地方两种风格,无论是吻兽、瓦当、斗拱、樨头,还是砖雕、石雕、木雕,都尽显精致。
官式和地方风格杂糅的饰件
一个建筑群,如果只有高大宏伟的建筑物,而没有精雕细镂的局部装饰,这个建筑群便显得生硬,毫无光彩可言。细节的装饰,如同画龙点睛,它给予建筑的,并非外在的鲜明华美,而是内在的灵动,是盎然生机。瞿昙寺的建筑装饰,同瞿昙寺的主体建筑一样,同样体现官式与地方两种风格。官式趋向严整雍容,地方显露灵活巧妙,这两种风格相互杂糅,却又相互比较,最终相得益彰,风采各异。这些建筑装饰通常包括吻兽、瓦当、斗拱、樨头、梁架绘画、砖雕、石雕、木雕、瓜柱柁墩、栏杆、窗以及寓意纹样等。
瞿昙寺的吻兽多为青瓦。这些蹲踞在殿宇屋顶的小小瑞兽,官式风格与地方风格迥然不同。官式吻兽规制统一,造型优美,制作精益求精,鳞片由小棍划出,身体、腿部和尾部鳞片逐渐缩小,符合物理常规。这些吻兽是寺院初建时,由调遣而来的宫廷工匠所制。地方风格的吻兽造型变化多端,手法自由灵活,常常随心所欲,夸张怪异,却又神采飞扬,鳞片常用半圆形工具压制而成,稍显生硬。瞿昙殿顶的狮形截兽,雄狮蹲身欲纵,作吼状,《传灯路》记载,狮子作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故而群兽慑伏。

瞿昙寺不仅建筑形制大气,其装饰配件也非常优雅,杂糅了官方和地方两种风格,无论是吻兽、瓦当、斗拱、樨头,还是砖雕、石雕、木雕,都尽显精致。
在古代中国建筑中,瓦当一直有装饰美化和遮护建筑物檐头筒瓦的作用。有文曾如此记载:“因其正当众瓦之底,栉比于檐端,瓦瓦相值,故有当名。”瓦当滴水之上常刻有图案文字,图案行云流水,取材广泛,文字常取吉祥之意,或是纪念文字,如“长乐未央”“与天无极”。瞿昙寺瓦当滴水共有二十多种,图案纷呈。早期瓦当滴水尺寸较大,图案多以佛像、佛八宝和梵文为主,后期瓦当滴水尺寸有所减小,图案亦不太讲究,出现兽面瓦当和花卉滴水。说寺院初建之时,某殿曾用龙瓦当,出自宫廷工匠之手,后来因故换去。这些檐头瓦当滴水,长期沐风栉雨,承袭时间流转,早已见惯世间沧桑,于岁月之中,悄然无声。
斗拱,是装饰性极强的建筑构件,由方形的斗、升、拱、翘、昂组成,这些组合部分彼此叠加,相互穿梭,硬性材料体现的是柔软丝线的编织之美。在瞿昙寺悬起的檐角下,在顶与柱之间,诸多斗拱精巧中透出雍容,玲珑之中全是典雅,它们重叠回环,如同卿云烂漫,如同日月光华。它们体现的是建筑的节奏与旋律,是变化与统一。
中国西部壁画的延续
曾有人说,中国西部壁画,可用八字概括:前有敦煌,后有瞿昙。敦煌和瞿昙寺,分列祁连山两端,敦煌在山之西北,瞿昙寺踞于山之东南。这两个地方,也是祁连山西北—东南方向延伸的结束点,源自祁连山的大泉河与湟水河,分别滋养哺育着这两个地方的洞窟和佛寺。敦煌壁画,从前秦开始,延续时间自北魏到元代,其间十余个朝代风雨更替,壁画风格时时发生变化。瞿昙寺壁画,大部分出自明代早期,清代壁画,所占比例不多,然而明代早期壁画中的人物服饰衣冠,又具有宋元气象。这样,敦煌和瞿昙寺两处壁画,使中国西部壁画有了一个发展延续与结束的完整过程。
譬如清代壁画《达摩东渡》,刻画的是达摩祖师渡海东来的一个场景。画面中,大海波涛翻滚,暗礁耸立,一场风暴刚刚过去,或者即将来到,小船在波浪之间平稳行驶,达摩于蒲团之上,凝眸而坐,镇定自若,冥心虚寂,却又显得神慧疏朗,志存大乘,一袭暗红色袈裟,袒胸露乳,舟子坐于舱顶,望着汹涌起伏的海面。这幅壁画,线条格外突出,波浪的走向,舱顶席子和蒲团的编织,船身的刻画,达摩袈裟上的涡纹,水花,细细观赏,除去达摩的异域面容,席子和蒲团不同的编织手法,袈裟上的纹路,树木勾叶点花的技法,都出自平民之手。
瞿昙寺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鼎盛到中落,再从中落到分化的沧桑历程。明代近200年历史,明王朝13个皇帝,曾给瞿昙寺赐寺额、封都纲,下达敕谕、诰命,颁金印、图章,赠佛像匾额,赐田园林地,分封瞿昙寺上层。清代300多年历史,瞿昙寺虽然渐次走向分化,但清朝皇帝依然以赐匾等方式显示朝廷的优渥。皇朝的赏赐,以及民众的虔诚供奉,使瞿昙寺曾有许多珍贵文物。其中一尊石刻“米拉日巴修行”像,高17厘米,讲述的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祖师米拉日巴在山洞中苦修的情景。作品中,米拉日巴尊者一袭单衣,静坐岩穴,双目微阖,洞内洞外,干干净净。据说,米拉日巴在洞穴修行时,半夜来一小偷,寻找东西,米拉日巴尊者放声大笑,小偷问,你笑什么,米拉日巴尊者说,我白天都找不到任何东西,你黑天半夜,能摸到什么。米拉日巴传记中说,米拉日巴在山洞的苦行,他妹妹见了以后,不禁大哭,尊者却开怀朗笑。米拉日巴曾言:有人扔来烂泥巴,正好种朵金莲花。这尊石雕作品以壁塑山水为衬景,高浮雕鎏金石刻为整体背景,这种独特手法,不同于将佛像有序排列的惯常做法,将尊者与环境融合,表现出尊者“门外无人迹,室内无血迹,能死此山中,瑜伽心已足”的出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