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与认识自我
2018-08-02陆建德
☉陆建德
改革开放后不久,锺叔河先生发掘整理了很多珍贵的晚清史料,辑成一册册的“走向世界”丛书。学界在这些著述中不仅看到了晚清中国士人首次走出国门后的见闻,还对本土经验或者说中国社会的世俗人心有了新的认识。外部世界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使中国士人“睁眼看世界”,这是一般教科书上都提到的。另一位湖湘人士的贡献可能在魏源之上,他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那时的中国士大夫非常不愿意去“夷狄之国”,他们担心,与洋人打交道出力不讨好,有辱名节。郭嵩焘也有类似的顾虑。他在光绪二年(1876)的日记中记载,慈禧几次召见他,要他“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郭嵩焘到了英国后,当地的统治程度之高让他发出由衷的赞叹。他以新奇的眼光观察国外的风土人情,对社会的组织和种种科技的发明尤多属意。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就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
上海世博会召开前,不少关于世博会历史的材料都提到陆士谔如何在未来小说《新中国》(1910)描述上海博览会场景。其实郭嵩焘早在光绪三年(1877)的日记里就多次说到他与几位英国人商议在上海设“博物馆”,并从日本驻外使节处了解日本参与世博会的经验。郭嵩焘把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称为“妙西因”或“画馆”,所以他提到的“博物馆”不是存放古物或文物的,而是一个举办国内外“赛会”即博览会的场地。

《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很多章节现在读起来还非常有新鲜感和震撼力。比如郭嵩焘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伦敦一位马车夫在车内发现一把雨伞,记得是一位到中国驻英使馆的客人留下的,于是把伞交到警察局,警察再把伞送到使馆。显然,郭嵩焘意识到“小事”不小:在广大民众配合下,政府在这种事情(即“失物招领”)上可以大有作为。他还注意到警察局对拾金不昧的行为有一些详细的规定,一一抄录。实际上他在自问:为什么晚清中国没有这种有益于整个社会的设施?是政府之过还是支配大众行为的价值观不能为这种制度提供保证?我们知道,“失物招领”和无偿献血等制度后来也成为我国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是否成功又当别论。
从上述例子可见,本土经验不是永远不变的。光绪年间,像郭嵩焘那样的先觉者真正站在了我国文化界的前列,他们看了海外的世界以后,能够用新的角度看待本土经验,意识到某些重要的欠缺和盲点。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逐渐认识到什么是公民社会和公共精神。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又不断变化,有着发展、变形的潜质。假如本土经验是原材料的话,那么它的动态的“定型”需要大家(批评家乃至整个社会)用雕塑的工具使它略具鲜活的形状。我们永远是通过想象力和价值观来建构、形塑我们丰富、复杂而且多元的本土经验。
我们对本土经验有浓厚兴趣,同时又希望超越它。本土经验需要我们带着比较的眼光去发掘、认识。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的社会既热爱又保持距离的态度有助于本土经验获致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自我。本土与世界其实早就搅和在一起了,难分难解。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们又在不断地纠偏,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塑造一个更加灵活开放、更加成熟厚重的自我。
向世界介绍中国当然极其必要,然而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选择性地介绍的文化是否具有亲和力,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比较的眼光和自知之明,而后两者都来自对别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现在的社会崇拜“八”(“发”),这是畸形时代畸形欲望的生动体现,把对“发”的崇拜推向世界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形象?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发”是“因得到大量财物而兴旺”,与“发财”的意思是一样的。公正,仁慈,诚实,信义,这些才是体现价值的伦理观念,而“发”则不是,强盗小偷,赌棍毒枭,谁不想“发”呢?,把“发”定为追求目标,是把我们的民族去道德化,去伦理化,这还不是最可忧虑的吗?政府追求善政,办好遍布全国的失物招领处,人人都急人所急,这才是一百多年前郭嵩焘的梦想。认识自我,在细处用心用力,这是我们在提出诸如“走向世界”之类宏大口号的同时切切不可忘怀的,也正是重读“走向世界”丛书的意义所在。
中国思想评论(2017)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丛书之一,全书挑选了杨光斌、张广生、高翔、张康之等名家的十余篇关于合法性概念、中西方文化与中国发展道路、政绩与地方干部晋升、国际社会“去中心化”时代的合作秩序建构、对外政策与中国特性、中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在全球秩序重构中的作用等的文章,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在这些问题上学术界的前沿观点,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乃至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及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和学术借鉴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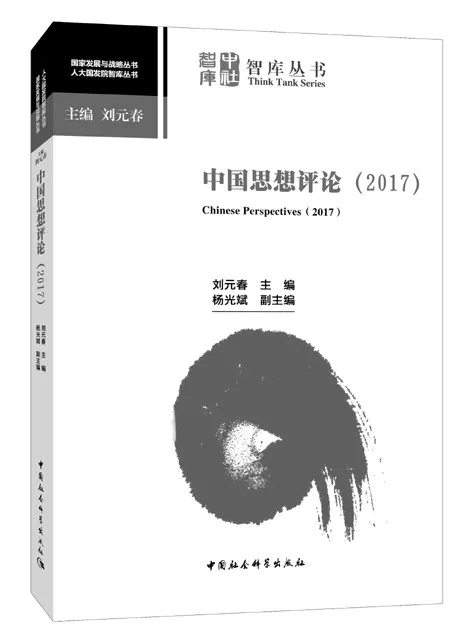
作者:刘元春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