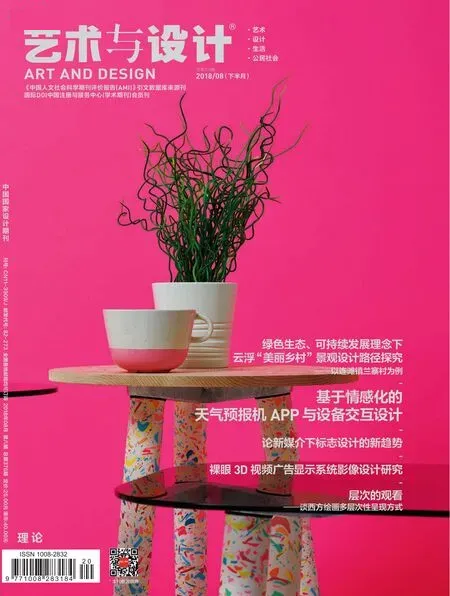隋唐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丝绸纹样探析
2018-07-31陈黄婉红蔡建梅
陈黄婉红,蔡建梅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杭州 310018)
一、引言
研究隋唐时期的丝绸纹样,敦煌壁画可谓是选材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敦煌壁画兴盛于隋前、中、后和初唐。当时出现了大量的纹样图案,如几何纹样、植物纹样、花鸟纹样和瑞兽纹样等。而佛教思想在汉代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唐代时期形成了中国式佛教。据传,推动佛教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和外来的侨民游僧。当时的佛教以鲜明的个性适应当时社会的特殊需要,使中国的佛教哲学达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水平。虽在晚唐时期存在灭佛迹象,但对后世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加上唐朝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为佛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丝绸产业迅速发展,各式各样的丝绸纹样也随之出现,在民间纷纷流传。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把最早的宗教称为“宗教艺术”,佛教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射,纹样展现的是一千年内涵博大的文化。佛教与艺术相伴而生,不可分离。
二、隋唐丝绸纹样的提炼
敦煌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其壁画中的图案为丝绸的纹样带来了更多与佛教相关的题材。据史料记载,壁画多以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和动物图案居多,并从中提取了三种纹锦样式进行分析,分别为方格纹>锦、对狮纹锦和莲花纹锦。

图1 几何纹佛座

图2 斜方格纹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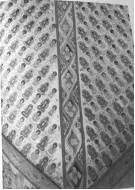
图3 菱格纹边饰

图4 方格纹锦

图5 狮子卷瓣莲花纹藻井

图6 团窠联珠对狮纹
(一)方格纹锦
中国佛教艺术在敦煌壁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丰富多彩的壁画图案中发现了不同样式的方格纹锦。田自秉先生曾在《中国纹样史》书中写道:“几何纹在世界各国原始装饰中具有普遍的性质,成为共同的工艺文化现象。几何纹之所以在装饰纹样中最早的也是最多的出现,与人类的原始思维有关。”隋唐莫高窟380窟(图1)为几何纹佛座上的纹样,其几何纹仿自犍陀螺雕刻,以“回”字形的图案构架排列,并在回字形的方格内画对角线,颜色以黑色、墨绿色、蓝紫色和大红色为主,颜色分布规律,方位随意。到了盛唐时期,方格纹显得较为复杂,莫高窟217窟(图2),此斜方格纹边饰绘于佛龛上的边饰,上中下各有四叶小花连续纹。而斜方格连续纹处在中间,主要色调为蓝色、绿色和红色渐变间隔,中间还伴有浅色,提亮了整个边饰。方形格纹与弧形线条相结合,增加了纹样的美感,更加引人注目。至晚唐,莫高窟12窟(图3),与盛唐纹样相比,此菱格纹增添了佛像图案。小佛像大致以斜线的规律整齐排列,中间绘有四叶小花,小花由两个相对的卷云纹组合而成。色彩渐变效果减弱,与盛唐时期的纹样大有不同。图4方格纹锦,该件为经锦,征集自青海民间,织物略有褪色,采用红绿相交的格子为主要题材,格子内填以动物纹。方格纹样以不同的经纬线肌理和图案拼接组成的图形运用在丝绸上,为丝绸图案带来了鲜明的格律之美以外还伴有一定的时代蕴意。方格中某些纹样有特别的喻义,如唐太宗时《服制》规定“七品服龟甲、双距、十花绫、色用绿。”地方向朝廷贡品中有龟甲绫、双距绫、十花绫等图案来表示官职的高低。
(二) 对狮纹锦
狮子是除了龙凤以外影响力最大的神兽,具有守护、辟邪、勇猛与佛教法力的象征。据佛经故事记载:佛主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唯我独尊,作狮子吼,群兽慑服”。认为佛主释为人中的狮子,其形象代表力量的同时也包含了宗法血统和皇权至上的思想。在中唐时期,莫高窟231窟(图5)为狮子卷瓣莲花纹藻井,因受当时金银器物上的图案影响,将狮子纹样与莲花纹相结合。从纹样中不难发现卷瓣莲花中心绘一卧狮,四周边饰以石榴卷草、回纹为主纹饰,四边卷草纹中各有一伽陵频迦鸟演奏音乐,颜色较为鲜艳,大致为亮黄色,为晚唐和宋代所承袭。狮子纹样在丝绸上体现的和敦煌壁画上略有不同。图6为唐代团窠联珠对狮纹锦残片,基本以黄、褐色调为主,古朴清新。残片整体采用对称原则织就,联珠团窠纹左右一边,中央同样是对称的的雄狮,头蹄相对。团窠纹四周织有跳跃的雄狮。在民间,世人认为狮子的形象也能够代表吉祥如意的意思,因此会有流传口诀“龙愁凤喜狮子笑”;“眼如铜铃方宽口,张嘴露齿伸舌头,铜头铁额大蒜鼻,慈眉善目笑逐颜”。
(三)莲花纹锦
佛国素有“莲花净土”之称,佛教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莲花境界”。据《观无量寿经》中一记载,在众生去世时,如来佛、大势至、观音等菩萨坐于莲花宝座上,手持莲台,接引他们。在民俗意义上,莲花代表女性,意蕴为多子之物。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出,莲花纹锦在隋、唐初、唐中、晚唐时期呈现的样式各有不同。隋代莫高窟311窟小莲花纹边饰(图7),莲花有八瓣,分别为白、绿、褐、蓝四色,反复连续排列。边饰上下为蓝色背景,饰有白色圆珠,格调清新自然。初唐时期的莲花纹锦显得较为华丽,如莫高窟321窟的莲花纹藻井(图8)。方格内的莲花由卷云纹和叶纹组成。八个椭圆卷云叶纹为莲瓣,花中八个小石榴叶纹和花外八个大叶纹、小叶纹均向外作放射状,构成莲花层层绽放的形态。方井周围的边饰也由叶纹组成,纹样足够统一和谐。盛唐时期,大多纹样由莲花和牡丹纹结合组成宝相花。莫高窟46窟(图9)其边饰纹形有人称之为宝相花。中心为四叶莲花,两端各一卷云桃形莲瓣,成长方形单元,反复排列连续。受敦煌壁画的影响,丝织纹锦的图案也显得格外精致。图10此绫由独窠宝花纹为主体和十样宾花组成,其宝花实为正视的莲花,可看见莲子和莲瓣,花间还有蝴蝶穿插。从技术上看,独窠绫所需的花本大小为两窠绫的两倍,四窠绫的四倍,技术难度十分高,唐大历年间颁发的《禁大花绫锦等敕》中也将独窠绫列于禁断之列,由此可见此件织物的珍贵。
三、佛教文化对丝绸纹样产生变化的原因
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先从上层皇族中开始传播,唐代皇帝武则天推崇佛教,佛教发展极盛,曾多次举行无遮会,然后逐渐流传到民间。古代的高僧和士大夫是反映社会变化和权力再分配的主要力量。他们把佛教和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在一起,使他们形成独特的思想体系。佛教吸收道教的“神仙道”与“黄老道”两家思想居多,神仙家讲“存神养性,意在凌云”,佛教则讲“飞行变化”“能隐能彰”;黄老道讲恬淡寡欲、清静无为,佛教也讲寡欲、无为,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如同佛教与道教始终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而又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一样,佛教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的儒学,也一直处于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摄的关系之中。粱漱溟先生在其《儒佛异同论》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期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远高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来说话,更不复归到人身上——归结到佛。前者属世间法,后者则出世间法,其不同彰彰也。”大致意思是,儒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佛教则是关于佛的学说。唐代宰相狄仁杰、李峤、姚崇等人都把佛教主张的慈悲和儒家提倡的“仁”及“仁政”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他们治国的指导思想。思想的稳固也减少了社会动荡。有了外来文化与固有传统文化思想的相结合,为丝绸纹样的发展增添了不少灵感创作。

图7 小莲花纹边饰

图8 莲花纹藻井

图9 莲花纹边饰

图10 -右 莲花纹锦
佛教从根本上也决定着人类道德实践的范围、层次和方式。在长期的宗教信仰活动中,出于宗教活动的现实需要和对神明的敬畏,宗教逐渐成为丝绸纹样重要的设计题材,并促进了丝绸纹样设计主题的多元化发展。如《楞严经》云:“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莲上……”。即莲花便成了丝绸艺术的重要题材。佛教文化的渗入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心理。唐代丝绸积淀着唐代信徒的佛教信仰意识、对佛陀的仰慕情感和宗教艺术精神,这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古代“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审美原则。佛教讲的“圆觉”“圆寂”都有圆满通彻之义。佛教宗派华严宗以“圆融无碍”的理论为法宝。所谓“圆融无碍”,也叫“无尽缘起”,即体用全收,圆通一承,相入相即。丝绸纹样的排列及样式也遵循了该理念的原则,例如唐
代宝相花,其花型饱满圆润体现了佛教美学中的“圆满之美”的蕴意。
四、结语
佛教是历史上首次向我国国内固有传统作强烈冲击的外来文化,它的传入引起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至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佛教在唐代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一套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个性鲜明的发展历程使得轻工业得以快速发展,丝绸作为一种佛教信奉的载体,除体现了它的精致美感以外,也有安抚民心的作用。唐代丝绸纹样有鉴于前代发展基础,也逐渐趋向成熟。因此,深入了解唐朝丝绸文化,对后世丝绸纹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