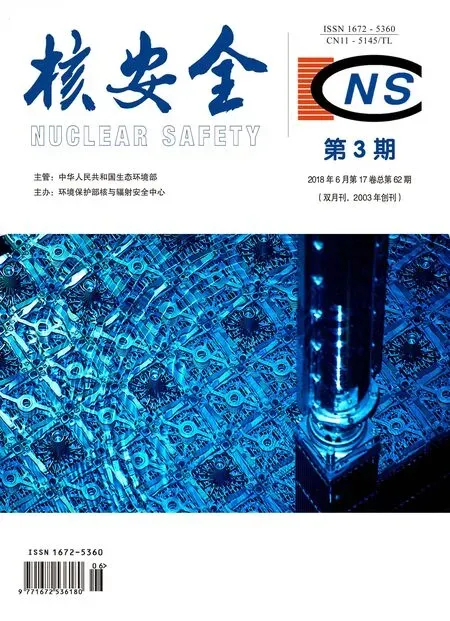实际消除早期放射性释放或大量放射性释放的安全目标定位研究
2018-07-27李华升刘泽军李吉根
刘 宇,李华升,刘泽军,李吉根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 100082)
国务院已于2012年10月批准发布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1](以下简称“核安全‘十二五’规划”)提出, “十三五”期间及以后我国新建核电机组尽可能从设计上做到实际消除放射性释放,对我国后续新建核电厂需满足的安全要求及达到的安全目标作了明确的规定。
国家核安全局于2016年10月发布了修订版的《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2](HAF 102—2016),其中多处提出“实际消除可能导致早期放射性释放或者大量放射性释放”(以下简称“实际消除”)的安全要求。但“实际消除”的安全要求并不是一条具体的、明确的安全设计要求,而是统筹核电厂安全设计的总的安全要求,因此也可以说是核电厂安全设计所达到的安全目标。另外,HAF 102—2016中对“实际消除”安全目标的提法,跟核安全“十二五”规划中的描述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可以说是一致的。
在我国核安全监管框架体系内对 “实际消除”的安全目标进行准确、合理地定位,是正确理解HAF 102—2016相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也是制定相关监管政策前首先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只有对该安全目标的定位是准确的、适当的,才能丰富与完善我国当前的核安全目标体系,制定出的技术政策才能跟我国现行的核安全法规相匹配,对我国现行的核安全法规进行有机地补充与完善。
在研究“实际消除”的安全目标在我国核安全目标体系中的定位问题之前,笔者对核安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实际消除”这一安全目标的背景,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HAF 102的修编过程、以及我国核电发展的形势等进行了广泛调研与思考,并深入研究了国内外各监管机构/组织的核安全目标的层次结构、内容范围和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实际消除”的安全目标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最后提出该安全目标在我国核安全目标体系中合适定位的建议。
1 核安全目标
国际核能界并没有对“核安全目标”有普遍的论述或定义。但对于建立和实施安全目标的意图和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IAEA)进行过相关说明,它的形式可以是抽象的,或者具体的;涉及选址、设计、建造、调试、运行和管理等各个方面。美国核管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简称NRC)于1986年发布的安全目标最终声明中,把安全目标定义为监管机构建立用于明确监管的理念和方法可接受风险的考虑,尤其是可接受风险的概念。
安全目标涉及到核电厂安全的多个方面,因此其表述可以是定性的或者定量的;也可以是确定论的或者是概率论的。层次越高的安全目标,一般而言,则越可能是定性的。而且安全目标的建立和实施应该是成体系的,也就是说需建立一个安全目标管理体系或框架。
随着核安全技术的发展和核安全认识的提高,安全目标体系也会随之不断发展的;尤其在发生较大的核事故之后,核安全要求将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安全目标体系框架将可能做出适当的调整。
2 国内外监管机构或组织的核安全目标
国外主要核安全相关的监管机构或组织,包括: IAEA、NRC和西欧核监管协会(Western European Nuclear Regulators Association,简称WENRA)等,在制定核安全规范标准与实施核安全监管活动过程中,不断地加深对核安全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并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核安全目标管理体系。
2.1 我国核安全目标
2.1.1 核安全目标的提出
2003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法》,规定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防治放射性污染,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核能、核技术的开发与和平利用”[3]。有一系列行政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和《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等,均有保障人员和公众健康、保护环境等规定。2017年,我国批准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在第一章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了“为了保障核安全,预防与应对核事故,安全利用核能,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4]。
我国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核安全规定HAF 102—2016对核安全目标有明确的规定,包括与上述一致的基本安全目标[2],该基本安全目标的描述与法律中的规定是一致的。实际上,我国提出的基本安全目标主要基于IAEA发布的《基本安全法则》(SF-1)中有关安全目标的描述,因而属于顶层的安全目标。
除了核安全法规HAF 102—2016中提出的顶层安全目标外,我国一些导则如《核动力厂安全评价与验证》(HAD 102/17—2006),政策性文件或监管技术文件如《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以下简称“核安全‘十三五’规划”),也提出了一些较高层次的安全目标,这些安全目标的情况见表1。这些安全目标可能分别属于定性安全目标或者定量安全目标,其中后者便于在工作中使用。

表1 近期我国提出的核安全目标
2.1.2 核安全目标的管理框架
我国的核安全目标层级特征比较典型,自上而下逐层建立安全目标,以实现对人员、社会和环境的有效防护,而且每层级安全目标都通过法律、法规、导则和规范标准进行支撑,形成了较完善的安全目标管理体系框架。
无论是核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是核安全法规HAF 102—2016中规定的基本核安全目标,均为定性安全目标,反映了对核安全提出的概括性要求和期望,因此基本安全目标在我国核安全目标体系中属于顶层的核安全目标。
基本安全目标是通过辐射防护设计和安全设计两个方面进行实现。无论是辐射防护设计,还是安全设计,都是采用纵深防御的手段来防止发生事故和减轻事故后果,防止事故对人员和环境造成危害。核动力厂的纵深防御通常分为五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对应安全目标,各纵深防御层次的安全目标参见表2。由此,HAF 102—2016分别从辐射防护设计和安全设计角度说明了这些期望和要求属于高层次的安全目标。

表2 我国核动力厂纵深防御体系及安全目标
中间层次的安全目标是在我国核安全法规所做的设计和运行方面的要求及规定,包括确定论和概率论的安全规定。
低层次的安全目标是在国家核安全局基于验证技术和成熟方法所发布的对具体设计的指导性建议,即:监管导则、技术文件等,其中包括定性的要求和定量的指标等。
2.2 IAEA核安全目标
2.2.1 IAEA安全目标
2006年,IAEA发布了《安全基本法则》(SF-1)[6],其中对IAEA的核安全目标系统中基本安全目标进行了明确,即:保护人类和环境免于电离辐射造成的有害影响。这个基本安全目标在核安全目标体系中属于顶层安全目标,为满足这个顶层安全目标的要求,文件做了详细的解释性说明,包括:
(1)控制对人类的辐照以及向环境的放射性物质释放;
(2)限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类事件可能导致堆芯、链式反应和其他辐射源失控;
(3)发生这类事件时减轻其放射性后果。
为了实现这一基本安全目标,在文件SF-1中制订了10项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确定了满足基本安全目标所应考虑的各个方面,包括为IAEA的安全标准及其安全相关计划奠定基础的安全目标、安全原则和安全概念。比如基本原则1——安全责任,规定“引起辐射危险的设施和活动负有责任的人员或组织,必须对安全负主要责任”。
2012年,IAEA发布了No.SSR-2/1“Safety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Design”;后续考虑到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并于2016年10月修订并发布了No.SSR-2/1(Rev.1)。这两份文件对SF-1中提出的基本安全目标进行响应,对核动力厂安全设计中建立的基本安全要求和采取的安全规则进行规定,从辐射防护设计和安全设计两个方面保证核动力厂无论在设计阶段,还是在正常运行状态,都能实现基本安全目标。IAEA No.SSR-2/1和No.SSR-2/1(Rev.1)建立的安全要求、原则和目标,紧次于顶层安全目标,是较高层次安全目标。
2.2.2 IAEA安全目标管理框架
IAEA安全目标体系的层级结构是比较清晰的,具有“金字塔”式的层级框架,而且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准则、标准、规范和导则,包括一些安全要求以支持安全目标的实现。而且IAEA在一次咨询会议上专门讨论并提出了核安全目标体系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根据IAEA安全标准文件体系,《基本安全原则》文件发布后将继续发布配套的《安全要求》文件和一系列《安全导则》文件作为支撑。“安全要求”确定为实现基本安全目标和基本原则所必须满足的各项要求,这些安全要求属于次级别的安全目标。正如IAEA于2016年发布的《核电厂安全:设计》(SSR-2/1,Rev.1)确定了核电厂设计的各项要求[7],以及提出的各项安全目标,内容包括“必须实际消除可能导致高辐射剂量或大量放射性释放的核动力厂事故序列”,这些安全目标或安全要求是次级别的目标。

图1 IAEA核安全目标体系框架图Fig.1 The frame of IAEA safety goal system
“安全导则”就如何遵守安全要求提出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属于低级别的安全目标,为满足“安全要求”,一般应提出技术措施或特定的安全指标,如:《核动力厂安全评价与验证》(NS-G-1.2)提出了如何满足核动力厂安全评价方面安全要求的建议和指导,提出了包括已有的和新设计的核动力厂堆芯损坏概率和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概率在内的特定安全指标等[8]。
2.3 美国核电厂安全目标
2.3.1 美国NRC安全目标及提出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三哩岛核电站事故的发生,使美国核工业界和监管机构都需要知道核电站“How safe is safety enough”(如何才能足够安全)。美国反应堆安全咨询委员会(ACRS)建议,核动力核电厂应建立明确的定量化安全目标,相应地美国核管会(NRC)特别事故调查组也提出完善安全目标和安全原则的建议。1980年10月,NRC启动完善安全目标的计划,是为了更清楚地定义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目标水平,并确保普遍认为这样的目标水平是足够的。
1981年,美国NRC提出了核电站安全目标政策声明的草案,声明中提出了两个定性安全目标。为了便于实现上述的定性安全目标,NRC提出了两个定量安全目标。1983年,美国NRC发布了正式的核安全政策声明(48 FR 10772),维持以前的安全目标框架(包括定性安全目标和定量安全目标),只是作了适当的修改。
1986年,美国NRC发布了安全目标的最终政策声明(51 FR 30028),声明中保留了之前的两个定性安全目标[9]。 但对于定量安全目标,声明中只保留了核电厂带来的个人急性死亡风险和癌症死亡的社会风险两个目标,就是经常提到的两个 “千分之一”目标。
不管是定性安全目标,还是两个“千分之一”的定量安全目标,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难以评估个人和社会风险,评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很大,因而都不易于使用。对此,NRC在1997年6月提出两个辅助目标,即概率安全目标,包括定量化的CDF和大量放射性早期释放概率(LERF)目标,以便在核电厂安全监管活动使用[10]。美国NRC提出的各类安全目标详见表3。

表3 美国NRC安全目标
2.3.2 NRC安全目标的管理框架
研究美国核安全法规和监管导则,以及安全目标的制定,就会发现美国NRC安全目标系统框架还是比较清晰的,美国NRC的监管框架参见图2。美国NRC在建立安全目标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其最基本的核安全目标,但无论制定两个定性安全目标和定量安全目标过程中的争论,还是最后以政策声明的形式明确与发布,都是围绕着“保护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核电厂正常运行及发生事故都不会显著增加公众的健康和安全风险”这个中心议题展开,因此其顶层安全目标可以理解为“保护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不会受到明显的附加风险”。
1983年NRC发布了正式的核安全政策声明,以及后续的修改完善,最终提出的两个定性安全目标和定量安全目标,都是围绕着公众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行约束和限制,即不会产生“明显的附加风险”。定量安全目标中明确:个人风险为“核电厂附近个人的急性死亡风险”,社会风险是指“核电厂周围居民的癌症死亡风险”;“明显的附加风险”分别相对于其他事故和其他原因,不应超过其0.1%[11]。定性安全目标和定量安全目标明确了NRC对核电厂安全的期望,属于高层次的安全目标。辅助安全目标,是NRC有利于监管决策和监管活动而发展出的安全目标,是对定量安全目标的解释,因此也属于高层次的安全目标。
美国核电厂安全监管采用了基于性能和风险指引型的监管体系,并考虑了代价和利益的平衡。在NRC提出的安全目标基础上,制定了完善的法规、导则或技术文件,并根据安全要求和系统特点,对构筑物、系统和部件(SSC)提出必要的性能指标和可靠性/可用性指标[12]。这些指标作为较低层次的安全目标,支持核电厂安全设计满足较高层次安全目标的要求。

图2 美国NRC监管框架Fig.2 The frame of regulation by U.S.NRC
2.4 欧洲组织和监管机构的核安全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和德国的核安全委员会在研究下一代压水堆安全时,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中首先提出了“实际消除大规模放射性物质释放”的相关概念[13]。自2000年起, WENRA基于“反应堆安全协调化”工作,多次发布细化的安全目标,尤其关于在堆芯是否熔毁情况下的放射性释放。
2010年WENRA发布了新建核电厂安全目标的声明[14],其中包括:安全目标O1-O7,这七个安全目标是在系统性研究IAEA SF-1中确定的基本安全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安全目标详见表4。2013年WENRA发布了“Safety of new NPP designs”(《新的NPP设计安全问题》),说明了一些关键安全问题的共同立场以及福岛核事故的反馈,这些较详细的共同立场对上述安全目标进行很好地支撑[15]。

表4 WENRA安全目标
欧洲安全目标的制定与发布,对IAEA安全目标的制定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其中间层级和较高层级的安全目标,部分被IAEA安全目标体系框架所吸收。
3 福岛核事故对核安全目标的影响
福岛核事故对全球核能发展和核安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促使核能界重新审视之前所建立的安全目标体系的合理性,也重新思考美国NRC早期提出“How safe is safety enough”的经典命题[16]。根据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以及世界核安全组织和各国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研究成果,归纳对目前的核安全目标体系产生的主要影响参见表5。
随着对福岛核事故研究的深入,可能将会有更多的方面直接影响安全目标管理体系。进一步讲,福岛核事故对安全目标体系产生系统性的间接影响,可能涉及到安全目标管理体系的各个层次。

表5 福岛核事故对安全目标的影响
4 “实际消除”安全目标
4.1 “实际消除”安全目标的提出
“实际消除”(practically eliminated)最早是由法国和德国在研究下一代核电厂安全方面的原则时提出的[17]。后续作为安全设计目标,应用于欧洲压水堆(EPR)的设计,并逐步被IAEA接受和采纳,体现在安全标准和要求系列文件中。实际消除的事故序列应进行专门的分析。同时注意不能用一个总的概念截断值来进行论证[16]。
2012年10月,国务院批复了核安全“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安全目标包括:具有较完善的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以及CDF<10-5(堆·年)和LRF<10-6(堆·年);对于“十三五”及后续建设机组,提出了“实际消除”的安全目标[1]。提出该安全目标,是为了确保即使在严重的堆芯严重损坏工况下,有效包容放射性以便不会对环境和公众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 2016年,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修订版的《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HAF 102—2016),其中明确提出实际消除的安全设计目标。2017年,国务院批复的核安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新建核电机组的类似要求[5]。
“实际消除”核安全目标的提出,既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从技术和工程角度提出了更高的安全目标,即:在设计基准事故或设计扩展工况范围内,核电厂事故不会导致放射性物质显著外泄。另外,提出“实际消除”安全目标,并不是要取消厂外应急计划,因为福岛核事故已经证明了厂外应急响应的重要性。“实际消除”安全目标中的“大量放射性释放”,其具体定义在HAF 102—2016中详细规定,与二级概率安全分析(PSA)中 “大量放射性释放(LRF)” 的含义存在一定的差异。
4.2 “实际消除”安全目标的影响范围
实际消除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既考虑堆芯放射性物质的释放,也考虑厂址内其他放射性物质贮存设施特别是乏燃料池放射性物质的释放;既考虑内部事件导致的严重事故,也考虑极端外部事件导致的严重事故;既包括事故早期释放,也包含事故晚期释放;既考虑通过大气途径的排放,也考虑放射性废液排放。这些具体事故现象的相应管理措施,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才能真正起到作用[18]。
对于威胁安全壳完整性的严重事故现象,在采取附加安全措施降低其发生概率的基础上,可通过确定论、概率论或工程判断等方法和手段,分析论证安全壳完整性在发生这种严重事故现象时也不会造成明显影响。这种分析论证可使用最佳估算的方法,采用现实的分析模型。
“实际消除”的安全目标还同时考虑到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公众对核电厂安全信心的恢复,在这方面需对社会舆论导向、公众安全认识和宣传方面做出规定和要求,以保护社会和公众的心理免受伤害。
4.3 “实际消除”安全目标的定位
通过对比分析国际上确立的主要核安全目标和相关监管框架和安全目标管理体系,在研究我国现行有效的核安全法规、监管框架和安全目标管理体系基础上,我国确立“实际消除”的安全目标,对我国核动力厂的安全设计及现有安全目标管理体系的可能存在以下方面的影响:
(1)“实际消除”安全目标的提出考虑了福岛核事故对环境和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并且考虑了社会对核电的可接受性,是对我国顶层安全目标的进一步的合理解释;
(2)“实际消除”安全目标是在国际机构和主要核电国家现有核安全要求的基础上,对安全要求的进一步扩充和发展,体现了核电厂安全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3)“实际消除”安全目标对核动力厂安全设计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纵深防御第四层次;
(4)“实际消除”安全目标直接影响核动力厂安全设计中考虑的状态,即设计扩展工况(DEC),包括:没有造成堆芯明显损伤(DEC-A)和堆芯熔化(严重事故,DEC-B)的核动力厂状态;同时影响核动力厂在应对超设计基准内/外部危险方面的安全设计,以避免“陡边效应”的发生;
(5)“实际消除”安全目标需要详细的安全规定和安全要求等较低层次的安全目标所支撑,以明确实现该安全目标所需的具体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与研究,“实际消除”的安全目标在我国核安全目标管理体系中应该属于高级别的目标要求。
5 结论
“实际消除”安全目标作为我国核安全目标管理体系中较高层次的安全目标,在新形势下对核安全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加有力地支持顶层安全目标要求,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现有的核安全目标管理体系。
对“实际消除”安全目标的准确定位,是正确理解该安全目标的前提,同时也为制订相关的技术政策指明了方向,为从确定论安全目标和概率安全目标上提出具体的安全要求和安全规定明确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