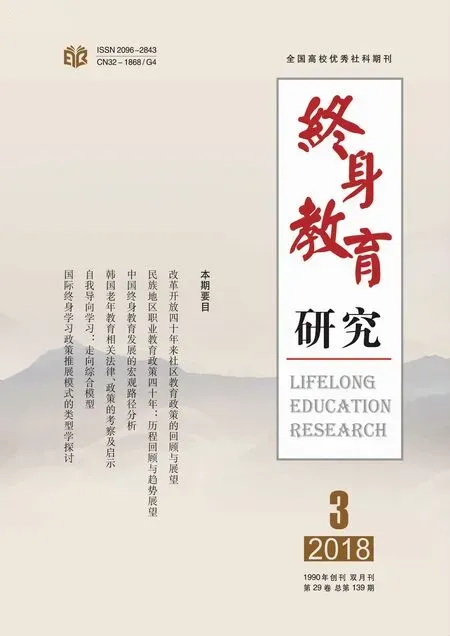国际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类型学探讨
2018-06-12□朱敏
□ 朱 敏
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
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合成词,包括终身学习政策和推展模式两个概念。
终身学习政策意味着终身学习已经从远古的一种理念、信仰,近现代的一种思想、理论进入到当代社会公共政策,尤其是教育、劳动领域的政策议程当中,这表明它不仅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更是被确定为政府的公共政策事务,成为国家、政府需要关注和管理的一项基本工作,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着普遍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终身学习进入政策范围意味着不仅要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恰当的界定,进而有利于聚焦政策推展工作,也提醒我们必须关注其实施方案的选择和过程的优化,最大程度、最有效率地将计划加以推行,确保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
依据国内外学界对政策的一般性认识,我们可以将终身学习政策界定为: 国家机关、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在某一时期为促进其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意识、观念、行为而制定的具有权威性的各种形式的计划、规定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总和。[1]37就国内外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的现实来看,终身学习政策主体有国家、政府、政党和代表性国际组织等。政策目的各国情形有异,如“提高终身的就业能力”“实现国家的经济复兴”“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培养积极的公民”等都是常见表述。政策活动多样,包括一系列相关的措施、计划、项目或行动方案等,如欧盟的“苏格拉底计划、达·芬奇计划和欧洲青年计划”、英国的“产业大学”和“学习账户”、瑞典的“学习圈”、日本的“公民馆”等。政策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其规范性和指导性的定位方面。
推展,简要地说就是推进和开展,是政策的实施过程,即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向其民众及各社会组织等推进并开展各种相关政策的实践活动。推展模式指国家机关、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在推进和开展某一政策事务的过程中,依据对该事务的一定认识、理解及其价值取向而采取的具有较为明显特征或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方法的组合。因此,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是指国家机关、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在推进和开展终身学习政策过程中,对终身学习思想或观念所持有的较为稳定的基本理解与价值取向,以及为体现这一理解和价值取向在实践中采取的相对明显和稳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各种途径、方式、方法、措施或行动策略的组合。[1]39
终身学习政策推展中的权利与义务: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与新自由主义福利改革[1]83-89
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有进步主义社会民主(progressive social democracy)和新自由主义福利改革(neo-liberal welfare reform)之分,这一研究洞见来自英国萨里大学教授科林·格里芬(Colin Griffin)。1999年,格里芬基于对英国世纪之交终身学习政策发展所面临的技术快速变化和国家作用论争的两大现实背景,根据对“教育(提供)——学习(功能)”“国家——市场”这两对基本关系的认识与区分,着眼英国本土终身学习发展实践而提出。
进步主义社会民主模式的观点是: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福利。现行的终身学习政策基本上是传统教育政策的延伸,不同的是教育的范围扩大了。因此,终身学习政策当仁不让地承担教育在促进社会民主中的伟大任务,即教育或者学习更多属于国家提供的福利事业,且承担完成一系列社会民主功能的职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终身学习政策是典型代表,其终身学习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每个人平等、公平地接受基本教育提供必要的权利保障。这一教育权利的实现不仅是为个人能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更是为能够在不断变化和冲突加剧的人类社会中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促进世界和平,并最终学会生存——每个人全面发展,并拥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和尽可能掌握自己命运所需要的思想、判断、行动、情感和想象等方面的自由。第二,国家对终身学习承担主要责任。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在它看来,政策本身就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职能,“目前教育之所以经常凭偶然性确定方向,受到盲目的指导,在无政府状态下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坚持从政策到策略,再从策略到计划的逻辑过程,以保证从上一阶段到下一阶段所做出的决定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2]。终身学习既然被当作许多国家教育政策制定和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国家在其中承担基本责任,不仅要认真研究和制定终身教育政策,而且要在机构设置、管理方式、经费支持、人员配备、标准评估和科学研究等诸多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持,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不论教育系统的组织情况如何,非集中化程度或多样化情况如何,国家应对公民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教育是一种集体财产,不能只由市场来调节。特别是在国家层面,要在教育问题上达成共识,确保总体的协调一致,并提出长远的看法。”[3]在上述认识框架下,进步主义社会民主模式通常从两方面来推进终身学习政策:第一是尽可能地扩大受教育的机会,确保教育和学习的公平。这种机会不因学习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教育背景、民族、性别等差异而不同,尤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终身学习机会的弥补和获得。第二是尽力消除参与终身学习的种种障碍。如建立先前学习认定机制来贯通各类学习成果;提高基础教育的参与率和质量,为个体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联合相关利益者筹措终身学习账户,为学习者参与继续教育提供经费支持等。
新自由主义福利改革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它关注的是“学习”而不是“教育”。该模式认为学习不等同于教育,不管是什么学习,它都有一个社会维度,终身学习中的学习是个体与社会生活的一种功能,目的是寻求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第二,终身学习更多的是涉及个人和社会事务。终身学习被认为与个人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度、消费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它不再(事实上也不太可能)成为国家的一项社会政策或教育政策。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和政府的职责被弱化,学习服务及相关产品主要交给市场(更确切地说是教育市场)。这个教育市场是一个被管理的市场,由政府组织,并由法律条文来界定参与者的相对权利与合约责任,这种模式使国家角色更具有策略性(strategical)特征。这种模式巧妙地隐藏了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的以下事实:教育作为一项国家的基本福利在逐步缩减,学习成为一种商品的意识在逐步提高,学习产品的开发与提供也同时交给市场,国家的责任减少而个人责任在增加。该模式之下的两种基本的推进途径是:第一,以倡导、鼓励终身学习为主。比如,积极宣扬终身学习的态度和精神,创造鼓励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表彰或树立终身学习的先进个人及组织典范等。第二,国家的责任转变为主要为人们的终身学习创造条件。如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在职进修制度;组织有关机构对学习信息进行收集与发布并提供学习指导;采取有助于刺激终身学习的财税政策等。
终身学习政策的组织模式:市场主导、国家主导与社会合作[1]91-101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是这一研究成果的提出者。2000年,基于对终身学习政策核心要素的抽离和西方国家制度的类型,他提出终身学习政策的市场主导模式(market-led model)、国家主导模式(state-led model)和社会合作模式(social partnership model)。为了分析的可控性,格林将终身学习政策范围限定在义务教育之后,主要是高中后教育和初始职业教育(initial vocation education,即首次接受的正规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与培训领域,较少涉及高等教育和失业培训领域。
市场主导模式认为终身学习政策推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行动;学习是需求导向性的;个体对自己的学习负有主要责任;国家更多的是倡导和指导;各种私人机构和组织在开发终身学习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依据一般的商品经济来对学习产品进行投资并获取相应利润。格林认为,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促成这种发展的原因除了网络及各种新技术提供的契机和支持外,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改革思潮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所坚信的理念前提是,个体都是有理性的存在,会在充分自由的市场中做出符合个人利益的选择,市场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会自动淘汰赝品,保留精华。
国家主导模式认为国家在终身学习政策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公共部门对终身学习活动进行规划、决定、组织,并承担大部分资金。它反对市场化,因为那样会带来投资不足与不平等。但格林以为这种模式变革速度缓慢,难以适应越来越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对越来越灵活、多样和复杂的个性化学习要求也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学习者的积极性。若是政府部门的判断、决策失误,可能会带来较大范围的损伤,影响整个事业的进程。
社会合作模式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力求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平衡,通俗地讲就是“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的结合。这种模式一方面认识到个体责任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倡机构多样、利益相关者多样,并且鼓励最大限度地运用新的学习技术。与市场模式不同,该模式强调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国家就是要在市场不能完成时发挥应有的作用,强调国家管理与监管,实现市场主导与国家主导两种模式的有利结合。在德国及临近德语区国家,如瑞典、奥地利、丹麦,这些模式都有比较集中的体现,这些国家一般都有社会融合度高、具有良好的手工艺传统及专业组织、劳动力市场管理较好等基本特点。
终身学习政策的现实描摹:补偿、继续职业教育、社会创新与闲暇[1]101-104
澳大利亚教育学者阿斯平·大卫(Aspin David)和查普曼·约翰(Chapman John)是近年来活跃在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研究领域的专家。2001年两人在合著的《国际终身学习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ifelong Learning)中提出,可以将当前国际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状况划分为四种不同的政策类型。
补偿教育模式(compensatory education model)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初始学校教育的不公平或缺失问题,以提高学习者的基本识字和技能水平。这一模式在许多原本教育水平就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这种推展模式中,终身学习主要面向的是在基础教育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提供终身学习在本质上是一种学习机会的弥补。
继续职业教育模式(continuing vocational training model)将终身学习限定为在工作领域中的继续学习,目的主要是应对因技术、信息、知识等变革所带来的工作场所的变化,以便学习者能够及时更新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在多数相关的终身学习政策中,这种模式通常与解决社会的失业问题联系密切。为发展终身就业能力的终身学习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社会创新模式(social innovational model or civil society model)也被称为“公民社会模式”,该模式将终身学习从个人视角转向社会层面,认为终身学习是解决社会困境、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继续教育和学习,提高学习者作为现代社会公民所需要的素质,从而更明智、有效地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解决社会导致的疏离与排斥,促进社会经济的转型和进一步民主化奠定良好的基础。相比个人化的终身学习,社会创新模式下的终身学习政策具有社会变革的特征。
闲暇导向模式(leisure oriented model)使终身学习摆脱了工具性的束缚,认为终身学习主要是为了丰富个人的闲暇生活以及促进自我实现,带有明显的哈钦斯学习型社会的理想色彩。在这种模式中,终身学习更多的是个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并且指向更为理想的人本化图景。
以上模式是在总览全球终身学习政策发展基础上的概括,很容易在现实中找到相符的案例。如闲暇模式,最明显和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代表性国家就是日本。补偿教育模式在许多倡导终身学习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找到。继续职业教育模式明显集中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创新模式则在北欧等几个主要国家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终身学习政策与社会转型:补缺、变革与多样化[1]104-108
2004—2006年期间,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艾伦·罗杰斯(Alan Rogers)提出,当今社会的终身学习发展忽略了两个问题:培训者培训和终身学习在促进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对于后者,罗杰斯的主要考虑在于“终身学习”一词已经失去了教育的激进维度,更多的只是适应性,且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忽视甚至有可能失去了学习的社会维度。在终身学习已成为主流利益集体工具的时候,那些立志进行社会变革的人又该如何来进行终身学习呢?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思考的背景下,罗杰斯根据目前有关社会转型的三种主要教育形式,即社会转型教育的匮乏模式、社会转型教育的处境不利模式和社会转型教育的多样化模式,就终身学习如何有所作为,研究归纳出三种社会转型下的终身学习应用模式,分别为:终身学习的矫正匮乏模式(remedy deficit model)、终身学习的克服处境不利模式(overcome disadvantage model)、终身学习的提高多样化模式(enhance diversity model)。
矫正匮乏模式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通过向教育资源缺乏者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可以使他们重新有机会参与教育活动,进而使他们有能力融入现代社会。罗杰斯认为,这就是英国比较教育学家罗纳德·珀斯顿(Rolland G.Paulston)所说的传统的教育观点:教育具有普遍性,在任何社会中没有实质差异,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未成熟的年轻人以最快的方式变得自律,进而融入社会。
克服处境不利模式与上述观点相对,认为部分人贫穷和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的原因并不是缺乏教育,而是受到了社会精英所控制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排斥甚至压迫。因此,比提供学习机会更重要的是变革现存的教育体系,通过教育甚至社会转型来克服学校教育中顽固存在甚至被不断强化的不平等,真正的教育应是人民的。这种模式同巴西成人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 Friere)的教育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认识到社会权力关系的作用,强调变革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认识到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是社会成员本身缺乏教育。但该模式进一步指出,同时应该意识到现存社会结构本身的不足,作为个体生活其中的社会本身也需要作出某些变革和调整,如教育制度的变革、允许多元价值存在、尊重学习者的个人教育选择。这种模式与弗莱雷的教育思想的差异在于,前者讨论的更多的是被边缘化及排斥等问题,而弗莱雷指出的是压迫与压制,更为激进。
增强多样性模式认为在现代教育中,多样性正日益受到重视和研究,终身学习政策必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终身学习本身的特点就是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学习者的多样性、学习地点的多样性、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学习时间的灵活性、学习结果的开放性,它打破传统正规教育的单一框架,倡导开放与灵活,为批判性反思与创造性行动提供了广泛机会,这种视角的终身学习更多地关注不同情境中的个人学习。传统教育观点依据所谓的标准界定出来的个人缺陷,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需要的并不是共同标准,而是对不同个体生命表现的尊重,以及在不同情境中对有需要的人做出个性化回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教育“四大支柱”之“学会共同生活”,就是倡导终身学习多样化的一个明证。 罗杰斯进一步指出,研究终身学习政策的多样化,实际上关注的是个体和地域的“身份”,这种身份不是孤立的,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身份都是通过其与周围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且这种身份具有重叠性、流动性。既然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只归属于一种关系,这种观点下的终身学习政策实施必定倡导学习情境化、个体化、地方性和自我责任,并且强调批判反思精神,因此应该研究如何鼓励群体的共同反思,使社区通过群体反思在新的环境下重建身份。终身学习政策的实施不应简单地接受别国经验,而应在与他人分享与交流,或在他人帮助与启发下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本土方案。
不同社会制度中的终身学习政策:社会公正、文化、开放社会与人力资本[1]108-112
汉斯·舒尔兹(Hans G.Schuetze)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与产业等。 2006年,舒尔兹与凯西(Catherine Casey)在《比较》(Compare)杂志上发表《终身学习的意义与模式:通往学习型社会的进程与障碍》(Models and Meaning of Lifelong Learning: Progress and Barriers on the Road to a Learning Society )一文,集中阐述了他对终身学习模式的思考:国家和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差异对于理解学习型社会意义重大,这些差异会影响对终身学习政策有效实现路径的选择。评价不同国家的终身学习政策模式,更合适的方式是研究不同的、更广泛的社会模式(social models)类型,这些社会模式在如何看待政治文化、福利国家与市场的作用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
解放或社会公正模式(emancipatory or social justice model) 倡导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通过教育来促进机会均等。舒尔兹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规范的甚至有点乌托邦式的观念。这种模式推动的是全民终身学习。相比之下,其他三种模式在涉及范围上都更为狭隘,尤其是最后一种,只定位在与工作有关的培训上。
文化模式(culture model) 认为终身学习是每个人的生活本身的过程,目的是获得生命圆满与自我实现(life fulfillment and self-realization)。这种观点下的终身学习并不像第一种模式那样,倡导把终身学习制定成为一项促进社会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政策,也不包含任何功利或实用性因素,它是“为了学习本身的学习”,指向文化目的或是闲暇时光。舒尔兹认为文化模式更强调个人在自己学习信息的知晓和获得机会上承担主要责任,而解放模式更多定位在需要帮助或存在某些学习障碍的具体人群,进而提供相应的学习机会。
开放社会模式(open society model)对于发达、多元文化与民主国家来说,终身学习是一个完备的学习体系。开放社会模式是对现代开放社会典型学习现状的描述,即对任何想要学习的人来说,都不应该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学习障碍,从这点来说,它又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它包括消除制度性学习障碍的所有努力,尤其包括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远程教育与学习、在线学习等。
人力资本模式(human capital model)的终身学习政策主要关注与工作相关的继续培训与技能发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雇主对更高质量、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劳动力队伍的要求,本质上是为了就业而制定的政策。现在这种模式正被多数国家和政府所倡导,因为将终身学习看作一个继续的培训体系,十分符合目前知识经济背景下各国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竞争。与传统的观点相反,终身学习的人力资本模式认为个体劳动者为了提升就业能力与生涯机会,应对自己获取技能与素养承担主要责任 。
终身学习政策的两大基础模式:人力资本与人文主义
201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者卡皮儿·德夫·雷格米(Kapil Dev Regmi)基于对过去十多年间西方有关终身学习政策模式的主要研究(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安迪·格林提出的三种组织模式),提炼并描绘了目前国际终身学习政策的两大基础模式:人力资本模式(human capital model)和人文主义模式(humanistic model)。[4]
终身学习政策的人力资本模式和20世纪的人力资本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贝克(Gary Becker)都曾鲜明地表示,人力资本即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的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积极的联系,相比农业、工业等传统的非人力资本要素,对教育的投资就是最好的经济策略。在人力资本模式看来,教育既是消费也是资本,可用来开发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该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条件。终身学习是其中的工具之一,具体策略包括:鼓励个人和国家参与全球性竞争,如要求参与国际成人能力测评、国际成人素养调查等各类教育和学习测评。鼓励开发信息通信技术来提升学习过程,应用远程学习、电子学习等来排除终身学习的参与障碍。确保个人学习和寻求工作的自主性,避免国家层面的规范对个人创造性潜能甚至是个人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限制。支持这一原则的国家通常致力于提倡教育系统的灵活性,甚至是跨国之间的教育和学习的流动。知识与技能被看作是个人财富,因此终身学习主要是个人的责任。第二个假设是对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系统的管理、资助和治理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为此常用的策略有:将知识视作私人产品,与市场机制密切联系。鼓励私有化,为教育贸易提供基础,如配合择校行动的“学校教育券”制度以及贸易服务总协定中的相关教育条款。鼓励私有部门参与管理和治理教育,这些机构也是教育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第三个假设是强调通过教育投资来发展人力资源,认为人力资本是全球知识经济的基本设施,对国家和个人都有裨益。如世界银行早在1968年就宣布了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对教育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其中和终身学习发展有关的两份最主要的报告是2003年的《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终身学习:发展中国家的挑战》(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和2011年的《全民终身学习:投资知识与技能以促进发展》(Learning for all: Investing in people’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mote development),第二份报告中提出的方案甚至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终身学习战略的参照路径。
终身学习的人文主义模式的倡导与发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密切。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该“指向人性的充分发展”“促进国家、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理解、宽容、友谊”。其根本目的在于减少社会不平等,缓解社会不公,保障全民基本权利。其他采取这种模式的组织,如南非发展共同体(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认为,终身学习的目的是民主的公民身份,个人、群体与社会结构的联结,地区和全球环境下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国际成人教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Adult Education)也提出,成人和终身学习与社会、经济公正,平等、尊重人权、文化多样性、和平建设、自我决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模式同样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民众教育(mass education)的目的是培养积极的公民身份,这种公民身份不仅仅限于找工作和人力资本开发,更倾向于培养公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如集体决策),尤其是反思能力。公民身份的培育有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为此,需要学习型社会的支撑。第二,终身学习的目的是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重视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为此,建设社会资本是优先事项,这不仅有利于终身学习发展(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经常性互动,如集体学习),而且将教育视为公共产品,有利于社会成员获益。当人们的共同目的指向社会发展时,社会资本理论对终身学习的人文主义模式更具有借鉴意义。第三,重视能力提升。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观,能力兼具工具和内在价值,教育是影响其他能力发挥的基本能力,必须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人力资本理论。联合国发展署从1990年以来将成人识字率和学校注册率作为指标纳入人类发展指数的行动,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分类框架[5]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终身学习研究所为当年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集体撰写了一份背景报告,题目为《终身学习的概念与现实》(Con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Lifelong Learning)。报告指出,终身学习原则在教育政策领域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标准或者是一种全新的主导性话语。鉴于各国教育制度的千差万别,全球终身学习政策的分类学(typology)会有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也没有适合一种情况的单一模式。但这种分类尝试可以减少同组个案之间的差异,同时放大不同组个案之间的差别,作为描述全球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的一种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报告明确提出了以下五个基本分类维度。
终身学习政策的范围(scope),指的是终身学习政策在教育领域的整合程度,具体包括整合的教育阶段的多少、学习对象的年龄范围、不同层级学习之间的联结情况(以确保教育路径的开放和灵活)。在此维度之下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模式(integrated approach)和局部模式(disintegrated or sectoral approach)。2007年《捷克共和国的终身学习战略》(Czech Republic’s strategy of Lifelong Learning)就采取了整合方式推展终身学习,该政策认为终身学习如何看待教育方法和教育组织原则有概念上的根本不同,传统教育系统内外的所有学习形式都应该相互联系,这有助于教育和劳动之间的过渡。局部模式通常关注某一阶段、某一类型的教育或具体教育问题,例如专门涉及正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外的学习活动。2011年《马来西亚终身学习文化适应蓝图》(Malaysian Blueprint on the Encultur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明确提出,终身学习是基础和高中教育之后的所有形式的学习,目标群体是15—64岁的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群,主要聚焦在终身学习的经济贡献方面。泰国和伯利兹也是类似模式。
终身学习的定向(orientation),包括人文和经济两种基本模式。有关这一维度的分类在前面已有详细论述。该报告指出,现实情况中很难找到完全单一的人文或经济模式,绝大多数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涵盖了某一模式的一些特征或要素。2006年的《挪威终身学习战略》(Norwegian Strategy for Lifelong Learning )具有明显的人文模式倾向。2010年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高等教育、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终身学习政策》(Policy on Tertiary Education,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and Lifelong in Trinidad and Tobago )则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人力资本发展上,以及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
终身学习的形态(modalities),指的是学习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经典分类。大多数国家的终身学习政策都会纳入所有形态,但也有国家明确把终身学习限定在正规教育之外的学习过程。津巴布韦2005年的《国家行动计划:全民终身教育2015》(National Action Plan: Education for All towards 2015)把终身和继续教育用来作为正规教育系统的补充,目的是提高处境不利群体的教育参与和机会,其中的成人扫盲也主要和非正规学习环境相关。
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成果的同等认定(recognition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formal,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as equal components of education),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是否能够和正规教育并列,其学习成果可否被认定是考察当前终身学习政策类型划分的一个重要维度。2007年丹麦的《终身学习战略:全民教育与终身技能升级》(Strategy for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Skills Upgrading for All)在成人教育与继续培训领域推动了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定,具体措施包括立法支持、构建能力评价质量保障体系、开发简易便捷的成果记录工具、面向双语和移民群体对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进行全国性的信息宣传。2009年印度《全国技能开发行动》(N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Initiative)中的技能认定体系和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就吸纳了这方面的策略。对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成果认定已成为当前国际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的新趋势。
终身学习利益相关者的参与(partnership),这是全球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将其作为维度之一合理可行。尽管从国家层面来说,政府承担着终身学习运作的基本责任,但与来自不同层面的公私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研究与教育机构等的透明合作是成功推动政策的关键,参与治理和多方合作可以把各关键方组织起来,共同推进终身学习政策发展。2007年克罗地亚的《成人教育战略》(Strategy for Adult Education)提出伙伴合作是教育系统内外各方合作的不二选择,必须吸收雇主、各类机构、社会组织、投资者、学习的各类协调机构和促进者等共同参与。2012年肯尼亚的《教育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 for Education)采用了公私合作方式,主要目的是建立创新性的资助倡议,如教育债券、低息贷款等。
根据以上五个基本维度的划分和阐释,该报告推演出一个多维度矩阵(见表1)。这个矩阵被理解成一个初步方案更为适合,可以作为继续探讨、测试和提炼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策类型的使用和具体政策文本相关联,并不必然就反映各个国家全部的终身学习政策样态,因为有些国家终身学习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必然会存在多样化的政策。

表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提出的终身学习政策划分的基本维度
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类型学探讨是全球终身学习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认识与研究产物,有利于我们对终身学习政策发展与实践做出阶段性的总体回溯,并为其未来发展路径提供指针。上述各类研究成果既有特色之处,也存在不少交叉、相似的思考。比如有关终身学习政策的人力资本和人文主义的基本定向;比如从国家教育制度和社会模式视角对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可能性推测与演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五个基本维度作为一种最新的研究动向,既有对前期研究成果的承继(如定向和学习目的维度、利益相关者维度、范围维度、学习形态),也有对终身学习实践新发展的吸收(如学习成果认定维度)。其间的联系、区别和发展需要更多的研究力量加入,以助推全球终身学习政策的可持续发展。